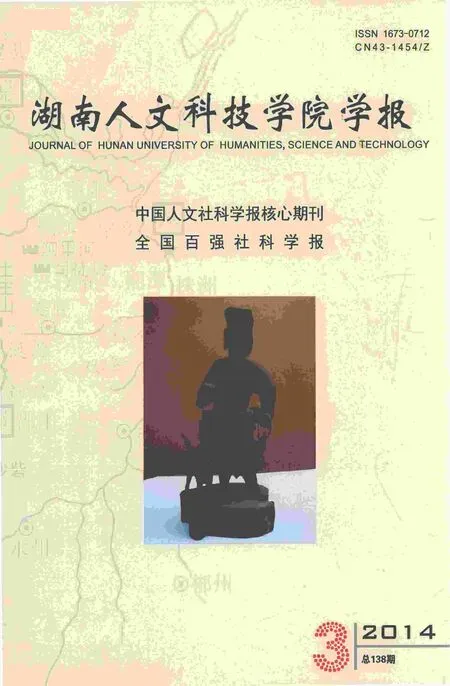文化与身体之歌——重读《白鹿原》
胡 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娄底417000)
林福南曾指出,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群的‘社会继承’,包括整个物质的人工制品,还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生活条件下以及代代相传的不断发展的各种活动中所创造的特殊行为方式”[1]。将身体置于文化的视域中,能使身体获得全面的审视,在更深入的层面认识身体之于文学的意义;同时文化也只有关注个体的身体存在,才能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身体是文化的场所,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为在身体的文化表达之外或之前,我们不可能认识到肉身的认同。相反,任何身体都恰恰只有借助这些所谓作为文化的结果的表达才是可辨认的”[2]。任何对身体的言说和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它所寄存甚至对抗的文化代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身体置于文化的视域成为众多作家的选择。
《白鹿原》在这些文化与身体合奏之歌中是最杰出的代表。“《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历史、文化最为完整最为坚实的重构。它在社会、文化构成上找到了中国历史社会稳定运行三千年的原因。”[3]凭借对历史的创造性追问和深沉而厚重的反思力量,陈忠实以构建“民族秘史”的意图向人们讲叙了一段基于个体身体体验的民族岁月。作者抛弃了庸俗的政治预设论,站在鸟瞰历史风云全部景观的高度,以个体的身体存在为本,通过个体的身体遭遇、生存境遇、命运沉浮审视了清末明初到20世纪中叶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摒弃了先验的道德判断,烛照出民族历史及国民精神的混沌之域和隐秘角落,展现了历史流程的浩瀚与宏大。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扛鼎之作”的《白鹿原》如同一枚回味深长的橄榄,它深广而丰厚的文化意蕴耐人咀嚼、引人深思和遐想,是永远说不尽、道不明的。此文选取散发着独特文化信号的白孝文、田小娥、白嘉轩的生命轨迹对其文化意蕴稍作探询,以期管中窥豹。
一 白孝文:传统伦理道德压抑下的逆反身体
白孝文是作品中命运浮沉颇大的一个人物。他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耐人寻味,预示着传统文化内在的致命症结。他是白家的长子,传统规定中白姓家族的继承人。他出身于道德氛围极其浓烈的家庭,自小受到礼仪家庭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严厉管教,饱读圣贤典籍,思想上接受了传统道德的全面洗礼。因此,他一直严守封建道德,仁义谦恭,正人君子。当他从白鹿书院回到原上后,“神态端庄,对一切人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明显地有别于一般农村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4]148,并很快“在族人中的威望如刚刚上山的太阳”[4]267。文中并未特别提及白家对于这位长子非同寻常的教育,但我们可以从孝文新婚期间的遭遇见出些端倪。起初,孝文对于男女之事无甚了解,经由媳妇的点拨引导下受到性的启蒙,初尝美好的他一发不可收拾,变得极为贪婪。奶奶怕他色重伤身,父亲担心他重色忘德,于是一场围绕他性生活的规劝与训诫便展开了。可见,白家力图规划长子的日常行为,将他培养成白鹿村继白嘉轩后又一个仁义道德的化身。尽管白孝文始终表现得中规中矩,实则被控制的身体已埋藏了叛逆的种子。
田小娥的出现,使另一个始终被压抑的更为真实的白孝文浮出水面。与其说是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使他做出败坏道德的事情,不如说是白孝文借助田小娥的出现,渴望解放自己作为白家长子而被重重规划的身体。田小娥淫荡的身体,对于白孝文来说,是如此自由,如此放任,不受限制,这个身体不受到传宗接代的制约,而完全只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工具。这对一直受到严格限制包括身体的白孝文而言是一个多么新奇的世界。因此,尽管他一开始严词怒斥了田小娥,最终还是无力抵抗田小娥藐视道德的身体。在田小娥鲜活的身体贴近他饥渴的肉身时,白孝文的宗法理念之坝彻底崩溃了。即便如此,由于道德伦理的强大制约,在偷情败露之前,他还是无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在田小娥面前总是表现为性无能。直到他的奸情败露,受到族法惩治后,被解除了作为族长继承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不再需要作为传统理想主义道德的负载者后,他才彻底获得身体的解放,充分显示了自己雄性的强健。如他自己所言:“过去要脸是那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象个男人样了”[4]315。这是他对礼教规范与人性冲突一次不自觉的顿悟。身体是一个鲜活的存在,过度的压抑必然会导致反抗。在此基础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后来的彻底堕落。
白孝文的人生轨迹,“所学”与“所为”的尖锐矛盾,令人不得不思索中国漫长历史上何以培养出如此“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细细思索却是有据可循的:中国传统伦理的绝对二元化对立,包括灵与肉、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的不可调和,否认个体的肉身存在,高蹈形而上的道德伦理,造就了中国人的两面性和人格的分裂,它成为身体在世不可回避的生存之痛。在这个意义上,白孝文实际上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成为自觉站在传统文化对面的“孤独者”。苦难的人生经历使白孝文得以冷眼审视深植于白鹿原的传统文明,然而,逃离传统又何以寄身呢?活着的希望是什么,时代没有给叛逆者提供更好的选择,白孝文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夹缝中的苟且偷生者。“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4]507成为他人生的唯一目的。他纵欲,吸毒,抛妻弃子,杀人如麻,冷酷无情,阴险狠毒,寡廉鲜耻,服从于这一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如果说鹿子霖是儒家文化负面价值的显性表现者,那么白孝文几经周折的人生道路,则展示了儒家负面价值的形成曲线和必然性。较之鹿子霖的显性体现,根正红苗的白孝文的蜕变更能深入传统文化病灶的内核,揭示传统文化中无可救药的弊病。
二 田小娥:传统文化缝隙中的挣扎肉身
田小娥无疑是《白鹿原》上最重要的女性形象,也是白鹿原上最富于生命力、最鲜活的生命个体。她是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美丽罂粟,以其清晰饱满的形象表述着生命的纯粹,实现着向大自然与原始生命野性的回归。对她来说,身体与存在是同构的。她热切地拥抱与身体相关的一切感觉,这身体知暖知热,会笑会哭,为所欲而欲。她因此成为白鹿原中最真实的生命存在。她的一切举动都先于语言和符号的拨弄,伦理对她来说,并不比求生的欲望更重要。她对伦理的消解是以对欲望存在的确认开始,又以对它的语言幻觉本质的揭示结束。她以肉身的敞开表达对遵命于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渴望打开和释放生命深处冲动的向往,从而在常识、常规之外亲历了一种不加伪饰,撕去包装后的本真意义上的生活。
最初,美丽、妩媚的田小娥是郭举人的妾。对于郭举人来说,她不仅是一具可供泄欲的鲜嫩的肉体,同时也是借以延年益寿的极好的“泡枣”工具。作为妾的存在,田小娥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牺牲品,她没有尊严,只是一个被任意宰割的性奴隶。但是身体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当它受到压抑、迫害时,总是力图挣脱牢笼,实现自己的解放。德勒兹将身体视为一部巨大的欲望机器。它内部充满了能量和力,始终如一、精神饱满地生产着、创造着。它不知疲倦,不知厌烦,变换无穷,它是一股活跃的升腾的积极性的生产力量。将身体完全等同于欲望,自然未必全然正确,但德勒兹的理论无疑肯定了身体的积极主动性的一面。长工黑娃的出现,激活了田小娥潜存的身体能量。她对情窦未开的黑娃先是悄悄地试探,继而是暗送秋波,频频发出情爱的信息,终于,两情相悦,放射出性爱的火花。从世俗的观点看,他们的偷情好似伤风败俗的。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性爱,首先是为了满足性的饥渴,是“闷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份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合乎人性和人道。同时,田小娥这种合乎人性的生命需求又是和反抗封建压抑一并产生的,她以性的方式获得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的同时,又以性作为反抗社会的武器。
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将身体分为社会身体、世界身体、政治身体等五种形态。田小娥之所以成为白鹿原上最重要的女人,不仅是因为她以女人的本能和本性争取了享受个体身体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她作为社会身体的存在。身体不可能单独存在,它总是受到当时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它总是处于与其他身体的相遇、交叉、碰撞的途中。田小娥几乎参与了白鹿原上每一次大的争斗,并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她为核心,结成了一张性关系网,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鹿精魂”作抗争,并在不知不觉中微妙地改变着固若金汤的封建家庭伦理和结构形态。一方面,田小娥洋溢着生命原欲的身体,点燃了黑娃的生命之火,使他踏上了叛逆的道路;激发了白孝文被传统伦理压抑的生命本能,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诱发了鹿子霖鲜廉寡耻的淫欲,使他背上“乱伦”的罪名并决定性地使他走进猪狗不如的行列。正因为这身体如此鲜活,如此具有颠覆力,极力维持儒家传统文化既定秩序的白嘉轩才如此痛恨这身体,一向仁义宽厚的族长在对待田小娥的事情上变得格外严厉和无情,他孤立她、鞭笞她,甚至力排众议,造塔镇压她的鬼魂。白嘉轩与田小娥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是传统伦理与个体生命始终存在的尖锐冲突。于此,田小娥以肉身的生动超越了一己之存在,以类的存在,成为楔入传统文明的眼中钉、肉中刺。她最终被摧残、被毁灭的生命也喻示身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传统文明的根基,却终究无法对抗其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田小娥处于白鹿原权力交锋的风口浪尖上。在此,身体作为异己的存在,成为权力支配下的玩具、武器和工具。鹿子霖以权力相迫,诱骗了田小娥的身体,其后又将其作为报复白嘉轩的工具,扒下了白孝文的裤子,给白嘉轩以致命的打击。她最终的灭亡亦是与权力对抗的必然结果,宗法家族制的集体统治不允许个体生命自由肆意的生长,她成为严酷族规下的牺牲品。在这双重意义上,田小娥以其内涵的深刻与丰富的自足成为白鹿原上又一个负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生命个体。
三 白嘉轩:儒家文化驯服下的压抑之躯
与田小娥相映衬和呼应的是作品的中心人物白嘉轩。田小娥指涉的是白嘉轩身上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凸现出他在历史转型中悲剧性的矛盾。然而,白嘉轩的生命却并非如此简单。“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含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全部价值,既有正面,也有反面”[5]。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使白嘉轩毕生考虑的是“我应该……”,而不是“我想要……”,一丝不苟的奉行使他的身体成为异己的所在,无法享受到生命的欢娱。即使作品是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5]3这种具有刺激性的开场来推出人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潜在制约,使白嘉轩的身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繁殖的个体而存在,无法获得生命爱欲的狂喜。作为文化的被动铭刻者,身体的僵化使白嘉轩的生命缺乏创造性,他执着、几近顽固地维护着传统文化中扼杀人性、限制个体自由发展的负面的封建纲常礼教。正如鹿兆鹏所言,白鹿村是一个“封建堡垒”,而白嘉轩则可以说是这个“堡垒”的“堡长”,他的传统文化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难以改变的,不可能如朱先生所说的“顺时利世”。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他作为封建文化载体的悲剧感日益浓重。“存天理,灭人欲”的坚守,使他不得不经历儿子教育的失败,女儿的叛离。家庭的分崩离析暗示着传统文化已成昨日黄花,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对于白嘉轩,我们很难进行简单的道德和历史判断,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复合多重的形象。在他身上,寄予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复杂而深刻的思索。
当身体置于以社会、制度、律法、权力等为核心的文化中时,它既可能改写社会,也可能被社会塑造,既可能利用社会,也可能被社会利用,既可能控制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控制。在福柯的视线里,身体更多的是被动性的,它不改变世界,而是消极但又敏感地记录、铭写、反射世界。身体是来源的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这些事件的烙印,它们的连接、倾轧、分离、争斗、冲突都刻写在身体上,而不是刻写于语言和观念中。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是一种身体性的管理,它将身体束缚起来,让身体中的狂野能量驯服。白嘉轩正是这样一个被传统文化驯服的个体。“他把朱熹以来维护封建人际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思想、哲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甚至操作法式,都自然圆活地融贯于日常生活中去了”[6]。作为儒家文化人格神的象征,白嘉轩凝聚了传统正统文化中诸如人格、礼仪、仁义、自律、勤劳、节俭、和穆、耕读传家、中庸之道、经世致用、修身养性等优良传统。他自觉接受传统文明的浸染,身体对他而言,不过是对儒家文化身体力行的工具而已,缺乏创造性和独立性。这使得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精髓的坚决守护者,另一方面又是儒家负面文化的顽固维护者。
白嘉轩一生秉着“学为好人”的宗旨,将自己塑造成刚直男子汉的形象。他将仁义内化为自己的骨髓,全力支撑着“仁义白鹿村”的大厦。他修复祠堂,重修族谱;善待长工,为人公正;兴办学堂,振兴教育;整顿法纪,严厉惩处赌博、抽大麻等歪风邪气;身先士卒,不惜自残身体伐神取水;铁面无私,残酷处置违反族规、家规的儿子和女儿;密谋“交农”事件,维护族人的利益;以德报怨,极力营救曾经陷害自己的鹿子霖、黑娃。总之,白嘉轩的血液里流淌着封建农人意识,信奉耕读传家,在孩子面前既言传又身教,固守农人的品格——把劳作看成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同时坚守着封建伦理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强烈的族长意识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正是他这种无可挑剔的传统道德修养和人格意志,才使他成为宗法制家族的道德神,并得以维持着封建宗族制度和宗嗣组织的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白嘉轩的人格、修养、品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集中体现,寄予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与缅怀,对儒家人文理想的憧憬与向往。
身体作为人类欲望的载体,固然有其本能性,但身体总是处于特定的文化中,它无法摆脱文化而独立存在。某种意义上,身体与文化是同在的,身体总是负载着文化的深厚内涵。“承认身体,连同它在历史、文化和世界的现象学中的位置是不可摆脱的”[2]133。正如《白鹿原》中白孝文、田小娥、白嘉轩等人的存在,我们无法割裂身体与文化的联系。在这种统一中,身体获得了全方位的呈现,并由此反映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中国文化表象的深层底蕴,在这一意义上,《白鹿原》堪称中华民族的秘史,即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与精神史。
[1]BULLOCK A,STYLLYBRASS O.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rderm thought[M].London:Fontana,1982:150.
[2]伊丽莎白·布隆芬.身体及其敌视者[M]//汪民安,陈永国,何怀宏.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出版社,2003.
[3]郑万鹏.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1):69-74.
[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5]李星.《白鹿原》民族灵魂的神秘史[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3(9):26-30.
[6]费秉勋.谈白嘉轩[J].小说评论,1993(4):20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