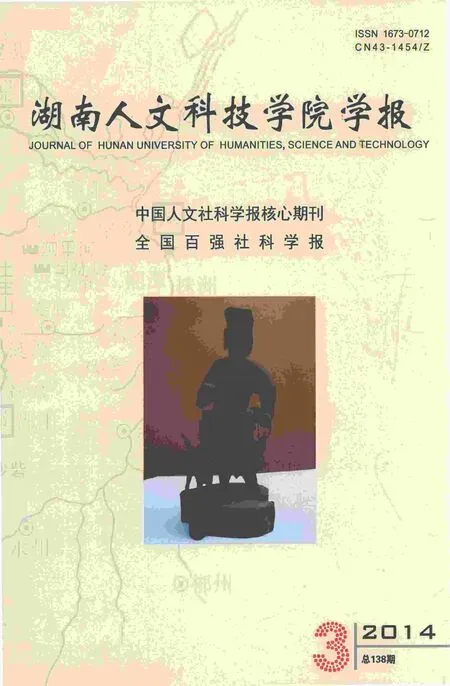刍议我国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
刘谢慈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 湘潭411100)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相关立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务操作层面的尴尬,但仍然存在不足,如相关概念的定位不准,主体范围不明,赔偿数额不确定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常认为,相较于自然人而言,法人不存在精神痛苦,故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缺乏依据。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人的精神利益不断受损并引发了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因此对确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的探讨就显示出其独特价值。
一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最初的一味被否定至现在获得学界和立法认可,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发展是我国法律制度进步的突出表现之一。因传统法律在损害赔偿问题方面重“物质”轻“精神”,对比日本,德国,匈牙利等国,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较晚,直至民国才正式立法。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否曾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至今理论界对其仍是莫衷一是。1986年《民法通则》120条①之规定是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此法条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名词性说法,至今亦为人所诟病。理论界普遍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的空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至此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展至新的高度,但该解释完全否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②之规定,法人在我国法律所拟制人格之存在,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由我国立法可知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对象仅限于自然人,立法的初衷也是为了保证自然人的非财产性损害获得赔偿,2001年的解释第5条更是明文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明确地否定了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有学者指出,我国对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立法上的体现十分模糊,《民法通则》第120条并未对之全盘否定,而之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及侵权法对其的否定态度相较于国外最新研究是一种倒退[1]。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从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法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因而存在很大的商讨空间。
二 法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争议
基于民法原则角度考虑,法人作为与自然人同样的民事主体,在共同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甚至更多的承担义务的前提下,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合理且公平的。
(一)否定说及其缺陷
否定观点中提出的法人无精神痛苦说,认为法人仅是一种“具有财产能力的权利主体”,但其作为“纯粹的拟制物,本身既没有意思能力,又没有行为能力。”更多地强调了精神损害的伦理性,偏重于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如俄罗斯最高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就界定为“citizen”③。事实上,对精神损害的内涵理解学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说认为法人没有精神痛苦,故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损失,法人虽无精神痛苦,但有精神利益[2]。笔者认同广义观点,将精神损害视为简单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情感,若深入到法律本质层面,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是拟制人格,精神损害除精神痛苦外还应包括精神利益。从广义上来理解,法人虽没有肉体感官上的痛苦,但其人格权是受到法律承认的,其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商业秘密权若受到侵害,亦可视为对其“精神利益”之损害,从此点出发,法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有理论依据的。而所谓的人格保护说狭隘地将人格局限在自然人的权利范围内,指出防止法律人格权的泛化,单纯强调对自然人的侵权赔偿,这无疑是对法人人格权的否认。单从法人人格预设的形成发展过程也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一些国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营业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法人的人格权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从个别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的转变,而这也是世界各国近年来相关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我国《民法通则》更是设专节规定了人身权制度,它对法人人格权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集中、全面的规定,明确法人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信誉权等人格权。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独创[3]。而无形财产说将法人的权利单纯当做财产权利,将法人人格权的伤害视为对其财产权的伤害,混淆了人格与物质的定义,更不可取。
(二)由肯定说引申出的“折中说”观点
法人有机体说将法人代表的痛苦上升为法人的感觉[4]。法人成员痛苦说将法人组成人员的痛苦集中体现于法人组织体本身,在实践领域的操作方面具有极大便利。因法人内部成员多为自然人之集合,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会造成其名誉、荣誉的丧失,最终将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其组织成员。而面对众多成员之诉求,提起多方诉讼无疑会造成资源浪费,最终结果也不一定令人满意。将成员的精神损害赔偿理解为法人集合体的精神损害赔偿从而使法人享有相关诉求也未尝不可,这也可从一定程度上保障法人人格利益及其成员的个体利益,亦不悖与立法初衷。而法人实在说为日本学者几代通说,其认为即使是法人也存在着主观上的名誉性,因此,应该肯定法人具有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5]这三种主张虽各有优点,但并不完全切合我国实际。结合相关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可将三者综合,采“折中说”以取长补短,以法人实在说为理论支撑,结合有机体说和成员痛苦说,将三者集中体现于立法上,同时明确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请求主体、适用范围及理论依据。
三 法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分析
(一)法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1.法学界“新思潮”的涌现
一个国家法律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同步,法律移植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近年来,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或是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态度都发生了一定转变,否定论不再占上风。法人的非财产性损害赔偿(我国称之精神损害赔偿)权益由最初被全盘否定到现在获得了部分肯定。如果理论界能进一步阐明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的工具性,削弱法律人格的人伦性,改变传统理论的逻辑谬误,则法人获得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的资格或许将被最终认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律融合将加快这一进程,实践中不断增加的各类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也促进了相关立法的成熟。
2.国内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随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各方面的研究讨论相继展开。但因我国相关制度起步较晚,又多沿袭德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逐渐出现了理论与现实操作脱轨的局面。定义的模糊性、适用范围的狭隘性和主体的不明确性造成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纷争。我国传统观点对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态度,立法也明确规定精神损害主体限于自然人,法人并无相关权利。但随着纠纷的即时变更和日益呈现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法人在诉讼中提出了与纠纷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在相关侵权案件中,轻者导致法人名誉受损,重者迫使法人停产倒闭。前者,如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诉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名誉侵权案就是明证;后者,如《文汇报》1993年7月26日报道《没给八千元,损失八万元》披露的“华旗果茶”事件,很能说明问题[6]。鉴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确定法人的精神损害请求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传统观点逐渐受到驳斥和挑战。法律之威严在于其用词的严谨准确,面对越来越多的矛盾,残酷的现实对法律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漏洞日趋明显,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资格显得尤为必要。
(二)法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
1.法人一般人格权的实质
就法人是否有权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笔者持肯定态度。我国法学界存在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一方面逐步扩大法人人格权,另一方面否认法人实质享有相关权益的资格。否定论者认为即使法人存在精神损失和人格权,也因其不能同自然人一般体会痛苦而无法从“精神”上获得赔偿。笔者认为既然法律已明确规定法人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信誉权、商业秘密权等权利,就应该使此类权利在受损时得到相应保护。自然人人格权的确立过程是一个技术化的价值考量,与自然人的伦理性基础并无密切的关联性。自然人人格权也是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所以,赋予法人人格权并不与人格权的本质相抵触。而一味强调法人与自然人的不同,再从此角度讨论法人不享有自然人的权益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即:自然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自然人能感知痛苦;法人无法感知痛苦;法人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上便是我国理论界的类型化思考,这实质是对法人与自然人人格权益的一种狭隘解释。此类观点也为各国理论界主流认可,如英国学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肯尼斯的观点所示:“法人,作为原告,能够对其遭受的各种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是显然对于某些类型的侵权行为如侮辱或凌辱,由于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法人不可能受这种侵权行为的损害,不过,法人对此给其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损失,仍有权提起诉讼。”[7]这实质是还未理清法人人格权的深层内涵。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法人的人格权和自然人的人格权从法律角度而言都是一种技术化,工具化的过程,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权利。法人确实与伦理性没有丝毫联系,法人人格的确立使得人格原本就技术化、非伦理化的过程更加鲜明。此种认识虽有失偏颇,但也恰好将法人人格同自然人人格分离,体现了法人功能的多样性,降低了法律人格的人伦性,从而能更客观地分析法人人格权的内涵,为法人权益获得更全面的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2.一般人格权为法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奠基
肯定法人的一般人格权,承认法人存在“精神利益”是法人获得非财产损害赔偿的理论前提,这也为其获得赔偿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法人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的侵害即是对其精神利益的侵害。与传统的精神痛苦不同,法人精神利益不要求法人具有事实上的感官与痛苦,它在客观上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直接经济损失,如雇佣律师支出的诉讼代理费用,刊登广告消除影响的费用;间接经济损失,如企业名誉受损,造成市场占有率降低,消费者信誉度下降,同时造成内部成员心理恐慌,导致生产水平低,库存积压,造成的损失无法直接估量。基于这两种损失法人都有权主张非财产性损害赔偿。
实践中确实多有法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法院在几起侵犯法人名誉权的案件中作出了部分肯定的判决。虽然此种例子在我国较为鲜有,且现今我国主流观点仍是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主体资格,但不可忽视的是类似诉求确实存在,且随着时代变迁,此类请求会日趋增多,其存在类型化的可能性。最高法院的判例可以视为对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初次尝试,同时世界各国法律的发展趋势也日趋明朗化,以德国、日本为典型代表。不论从立法或是司法实践,我们都不难发现对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由否定到逐渐持肯定甚至支持的国家不在少数。如今法人的一般人格在我国获得承认,笔者认为法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资格只是时间问题。不论从国外的发展势头出发,还是从国内的现实诉求考虑,法人的精神利益受损有权获得赔偿都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外现实环境相互作用使得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成为可能。
至此,笔者就我国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简要探讨,对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资格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进行了粗浅分析,旨在充实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涵。现阶段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仍持否定论,但就司法操作层面而言问题已经产生。随着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在我国得到立法认可以及对“精神损害”这一概念在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传统的否定论受到了严重冲击。瑞士等国的相关立法和德国民法界的拨乱反正也为我国民法典相关制度的编撰提供了宝贵经验。将法人的人格权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既符合历史潮流,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司法制度必将在立足于国内实际的基础上逐步与世界接轨。
注释:
①民法通则12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侵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②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③A Writ(A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S Plenum)20 December 1994 No.10,此为俄国1994年最高院颁布的法令。
[1]周利民.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2]王冠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再探索:基于比较法上的观察[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5):6-7.
[3]沈洁.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D].上海:华东政法学院,2006.
[4]柯原峻一郎.关于集团的名誉毁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9-50.
[5]几代通.不法行为中损害的种类[J].民事研修,1989:37.
[6]陈有西.企业反侵权法律指南[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300.
[7]KANIS K.The rights of legal person:Kenrcth Smith[J].English Law,200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