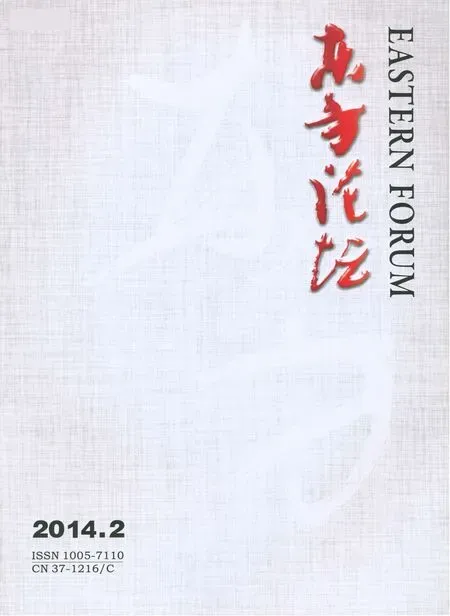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席 志 武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席 志 武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再到完全放弃的过程。它的流变与梁启超对于时局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从它的最终旨趣来看,破坏主义所指向的仍是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义内容。因之也可说,破坏主义实际上是梁启超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
梁启超;破坏主义;新民策略
“破坏主义”是梁启超于1899年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明确提出的政治口号,这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最具有社会冲击力的启蒙主张。其时梁启超刚刚经历过戊戌政变的失败,流亡至日本。来到日本之后,梁氏不仅对之前的失败教训作了深刻反省,而且借途于日文开始接触到大量西方资产阶级著作,这些“畴昔所未见之籍”使得梁氏“思想为之一变”。因此之故,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一改维新变法时期的温和渐进的改良主张,而表现出与之前全然不同的激进策略和破坏主张,“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氏“破坏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基于对清廷诸多弊政的一剂猛药,然而需指出的是,破坏终非目的,它只是对于时局所做出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又直接指向“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张,诚如梁氏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所言,“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思想不自由,民智便无进步之望矣。”[1](P277-278)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氏的破坏主义,即是他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的“新民主义”的一种策略。
一、梁氏“破坏主义”之流变
梁启超的一生颠沛流离、跌宕起伏,其思想表现出如其师康有为所责难的“流质易变”的特征。对此梁启超本人也有着清醒认识,他对自己的评价即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2](P86)“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3](P46)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从萌芽到明确提出,再到自美洲游历归来后的完全放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流变过程。
1895年,遭遇甲午惨败之后的中国社会受到极大震荡,舆论大哗,士人纷纷要求图新求变,这一思潮直接催生出“公车上书”的发生。时年梁启超23岁,思想与行为均追随其师康有为,未超出康氏藩篱。次年七月《时务报》开,梁氏即“专任撰述之役”,开始报馆生涯。他在这年所发表的《变法通议》,充分表达了他拯时救弊的政治主张,即可视作为梁氏“破坏主义”的萌芽时期。
《变法通议》是一部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它首先针对的就是当时守古不化的社会空气。某种意义上说,“变”对于当时僵死的社会而言就是一种“破坏”。关于此,梁启超有一个很好的“老屋子”比方,“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4](P2)身处这样危局当中,酣嬉鼾卧者有之,束手待毙者有之,苟安时日者有之。在梁启超看来,这三者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归于死亡。而真正“善居室者”,是应该“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只有拆除废坏的地方,重新去修葺,招集工匠,准备材料,进行新的构造,才可能实现真正的“高枕无忧”。治理国家同样也是如此,面临危局,只有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消除诸种弊端,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当时的清帝国即是这么一幢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老屋子”,若想继续维持统治,不从根本上进行维新变法显然是要坍塌。为了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梁启超不仅罗列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以作说明,还举了清朝的诸多变革来作印证:变服色、变文字、变历法、变赋法、变役法,变刑法等,并且认为“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既然变法是必需且必要的,而且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唯一方法,那么如何“变”?梁氏所开的剂方是要“知本原”,“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4](P10)这也因此成为《变法通议》的最终宗旨,对此梁氏在时隔20多年后回顾说,“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2](P84)由此可知,梁氏的改良主张都是建立在对于清朝现有制度的弊病之上。这与后来“破坏主义”主张所要求的“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无疑有着血缘近似之处。
1897年,梁启超受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此时他的言论日趋激进,“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2](P85)据狄葆贤所记,梁氏在将去湖南之前,即与同志商定好了教育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1](P87-88)在上述四种宗旨当中,梁氏又极力主张第二和第四项。梁氏这种急进、革命的主张,不仅给当时的学生带来一种“头脑风暴”,更是让顽固守旧的湖南士绅狂躁不安。他们深恐梁氏言论扰乱传统纲常秩序,数度上书要求禁绝言论,并且还组织了一个“翼教”联盟,对康、梁大加鞑伐,认为梁氏言论“伤风败俗”“误尽天下苍生”,[5](P148)针对梁氏倡导的民权、平等之说,他们也有着针锋相对的驳斥,“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5](P144)应该说,守旧士绅的反抗愈是激烈,也恰恰印证出梁氏鼓吹革命与破坏主义的态度愈是坚决彻底。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同年十月创办《清议报》于横滨,继续鼓吹民权自由,宣扬革命排满主张。梁氏的革命激情在此时表现得尤为剧烈,“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7](P2)他在《瓜分危言》(1899)中猛烈抨击清廷“自取瓜分之道”的诸多罪责,如甲午之战所以惨败,是因为筹练海军的款项被挪用至修建颐和园工程,致使最后“割千余里之辽台,偿二百兆之金币,元气尽斫,国丑全露,以启戎心而速危亡。”[7](P41)不仅如此,梁氏还表达了他对于清廷腐败无能的愤激之情,“今政府者,以顽固为体,以虚诈为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也。”[7](P70)基于对清廷的清醒认识,再加上身处日本时受到各种西方革命思想的冲击,梁氏此时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破坏主义主张,“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破坏主义何以可贵!曰: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阏进步之一大根原也。”[8](P25)然而需指出的是,不管梁氏的破坏主张有多坚决,他对清廷有着怎样的愤慨和不满,在梁心中,皇帝作为一个“圣主”形象,显然已成为一个英明仁勇、充满遗憾的宪政理想,“我皇上深观中外之故,注意立宪之政,以开民智、伸民权为唯一之主义。而十年以来,上制于西后,下阻于政权,辅佐无人,有志未逮,去年始一著手,未得行其志,遽遭幽闭,新政蹉败。”[7](P69)梁氏的这种“反朝廷不反皇帝”的革命倾向,最后衍变为一场声势盛大的“勤王运动”。
武力勤王以失败告终,失意中的梁启超非但没有因此放弃破坏主义的革命主张,反而因之变得更加成熟和愈发热烈。在1900~1903年这几年中,梁启超深受时局刺激,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破坏”与“革命”言论,无不充斥着对于晚清政局的责难和对于破坏主义的期许,“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10](P50)梁启超认为,中国积痼太深,已不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所可以维持,必须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进行一场彻底的大变革才可以救国救种、保国保种。于此而言,破坏主义就是当时挽救时局的独一无二之法门。在梁启超的不断阐述和建构中,“破坏主义”因此和“革命”(Revolution)的含义相交织,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内涵,《释革》一文中,革命与破坏主义几乎同义,“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这,而别造一新世界。”[10](P40)在梁氏这里,“革命”也不仅仅限于政治范畴,他认为,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革命,宗教、道德、学术、文学、风俗、产业等等,皆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梁氏此一阶段所大力提倡的“文学革命”(文界、诗界、小说界)也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历史蕴涵。然而在触及到悲哀的现实政治时,梁氏又不得不大发悲叹,“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呜呼!”[10](P44)
梁启超彻底决绝的革命姿态在《新民说》的前半期(以第十八节《论私德》为界)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贯彻,与此同时,他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国民道德建设上,以期获得一种迥异于前的自下而上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路径。“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P2)诚然,这种“新民”主张即是包含有一种对于传统旧思想的批判,和对于西方文明思想进行汲收的策略。梁氏在《释新民之义》中说得也很明确,“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7](P5)尽管如此,梁氏在《新民说》前期表现最明显的,仍是好为急切之言,要求冲破旧的思想格局,以新学说变易旧思想为旨归。如《论公德》是因为公德乃“我国民所最缺”;《论国家思想》是因为“吾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论进取冒险》是因为“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论权利思想》也是因为我国民“无权利思想而已”……诸如此类。这之中实际上也就蕴涵了一种对于传统旧道德、旧思想的破坏主义倾向。也即是说,“破坏主义”在《新民说》中,已经不单单停留在政治一端,它已经指向了文化道德层面。这实际上可以说是破坏主义内涵的一种深化。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开始了漫长的美洲之行。饶有兴味的是,他在三月十八日写给徐君勉的信当中,仍表示了对于革命坚定执着的信念,“长者(指康有为一笔者注)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1](P320)然而不久后,他在另一封《与雪庵书》的信中就道出了自己对康有为的妥协,表示接受其指责,承认往日的行为实属“悖谬”,并要“诚心悔改”,至此梁启超可谓是初步放弃了之前的革命主张。[1](P325-326)这种状况在后来梁氏的言论中逐步得到印证,如他于六月二十七日写给蒋观云的信就说,“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P328)而后,梁氏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私德》一文,即宣示了他对于破坏主义的全新看法,认为破坏与建设不可分割,“古今建设之伟业,固莫不含有破坏之性质,古今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11](P130)由于感受到当时“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士”都倾心于破坏主义,且“今之言破坏者,动曰一切破坏”,如此一来,“破坏”对于“几无一部分而无病态的”社会就不成为一种有效的疗救手段,反而会“流弊千百”,最后招致国家趋于灭亡。关于此,梁启超回国后在一次演说中也谈到过此次思想转变的缘由,他说,“……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6](P3)至此可以说,梁氏对于破坏主义的提倡在1903年的上半年即宣告结束了。
二、“破坏主义”的内涵
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自己在1915年即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12](P51)梁氏最初登上历史舞台即是与其师康有为一起进行“公车上书”,倡导维新变法。纵观梁氏一生,几乎他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救时”而展开,他的最终目标也即是期望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近代化国家。然而现实的失败教训告诉他,要想彻底革新这个有着几千年顽疾的中国社会,广大国民的参与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何让“愚陋怯弱”的国民来适应目前这个新的时代大变局,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就成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政治革新和民众启蒙,在任何时候来说无一不是艰苦卓绝的伟大事业,梁氏所要面临的来自旧势力的阻力可想而知,而这些阻力,也就成为梁氏“破坏主义”的主要对象。
首先来说政治革新。政治革新所针锋相对的就是一个“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之所以积弱患贫,受尽外族欺压凌辱,其根源即在于延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政制度,因此需要“破碎而齑粉之”,[11](P64)建立一个“政体之最良”的“君主立宪制”。[9](P1)早在1896年,他对此就作了深刻揭露,“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愚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4](P96)正是由于一种起于自私的“防弊之心”,以国家为一姓之私产,所以罪大恶极的如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等“民贼”们呕心沥血,遍布罗网,精心搭建起一整套精而且密的防弊之法,“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9](P28)这种钳制国民的愚民、柔民、涣民政策使得民众斫丧元气,变得愚陋怯懦并自居为奴隶,甘心受治于专制之下。故人人自主之权归诸一人,天下之利归诸一姓。梁氏因此说,“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制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13](P76)梁氏于此可谓对中国的积弱根源做了一个系统清理,那即是中国积弱全在于专制独裁的君权政体。“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10](P90),“天下坏伦常毁天性灭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于专制政体”。[10](P98)独夫专制使得中国失去了文明进化之资格,使得广大国民不知有其权利,使得西太后党之政府守旧自大,使得中国任人宰割利权尽丧,使得外国之逼迫日益加重。既如此,梁氏明确标示出他的破坏主张,“今欲举秦汉以来积敝,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8](P13)民权之议是梁氏对抗君权专制的一把利刃,同时也是革除清廷诸多旧弊的法宝。
其次就是民众启蒙。民众启蒙所要指向的是“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梁启超曾指出,人才乏绝,百举俱废,是中国所以讲求新法三十年而一无所成的根本原因。那么有着四万万之众的中国何以人才如此匮乏?这就必然要触及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改造问题。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认为要想国家自强,必须废科举、立学堂、译西书、开报馆等,并且认为这些都是开民智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然而即便是这些应于时势的开明主张,在当时的“蒙翳固陋窒闭之中国”,仍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奋力抵抗,他们以维护孔学圣教为旗号,指责梁氏推崇异学、乖悖伦常、背戾圣教等,是“乘外患入侵之日,倡言乱政,以启戎心”之举。[5](P124)由此这使得梁启超对孔教的看法略有改观,他在《新民说》中说,“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11](P59-60)正因为孔教屡屡被人作为抗拒维新变法和束缚国民思想的凭藉,所以梁氏干脆一改维护孔教之义,认为孔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因为保教会妨碍思想自由,[10](P55)而思想不自由,开民智就成了空谈。之后梁氏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还这样为自己申辩道,“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1](P278)梁氏最后表示说,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以自任。但是,透过梁启超前后的言论看,他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破坏”,并没有如他对待君主专制那般的干脆利断,相反,还一直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这也进而决定了梁氏所谓的“新思想”,并非完全的舍弃旧学,而是建立在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革新、对于西方文化进行采补和汲取的基础之上所完成的中西文化会通的理想。正如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所说的,中华文明“迎娶”欧美文明,“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4](P4)此“宁馨儿”既是梁氏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破坏”后以期达到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对民众进行启蒙所欲实现的目标。
1899~1903年间,梁启超在他的相关著论中不止一次地盛赞过“破坏主义”,他不仅认为这是医治“积数千年之沉疴”的中国的最佳策略,同时也认为这是疗救四百兆身患痼疾的民众的灵丹妙药。惟有破坏,才能使得国家真正走上进步之途。他说:“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荡魑魅魍魉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之下手第一著也。”[9](P50)明确这一点后,那么另一个问题就紧接而至:如何破坏?破坏的方式有哪些?对此,梁氏也作了具体分析。
其一、关于“用人力以破坏”和“听自然而破坏”。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有着这样的评述,“用人力以破坏者,为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故将来之乐利,而已偿目前之苦痛而有余。听自然而破坏者,为无意识之破坏,则有破坏无建设,一度破坏之不已而至于再,再度不已而至于三,如是可以历数百年千年,而国与民交受其病,至于鱼烂而自亡。”[11](P60)两相比照当中,不难看出梁氏对于前者有着十分明显的倾向性,也即倡导有意识之破坏而拒斥无意识之破坏。如他在罗列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欧洲革命、日本维新等历史时,无不对其充满了艳羡之意。因为这些国家都是经历过有意识的“人力破坏”,并且最终将扰乱的种子彻底铲除,所以它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蝉联往复之破坏”出现的可能性。令人倍感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无意识之破坏”层见叠出、山崩地坼,如洪杨之乱、捻党之乱、回部苗疆之乱、义和团、广西之乱、四川之乱等起义暴动接二连三,这些此起彼伏的破坏又是“现时漂摇脆弱之政府”所不能够妥善应对的。既然政府不能定难,那么“此后所以定之者,惟有二途:一曰国民,二曰外国”。实际的情形又比想象得更加糟糕,“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国民尚且无力担当,开门揖盗显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外国的干预只会丧权辱国,使国家民族趋于沦丧。到此,这也可以说是梁启超的破坏主义走向终结的时候,他竟然说,“吾今不要求公等以鼓吹破坏,不要求公等以赞成破坏,即惟要求公等以扑灭破坏。”[15](P26)那么,我们也似乎可以这样去归结梁启超的意思:破坏,要么就有意识地去破坏;无意识的破坏,宁可维持现状。
其二、关于“无血之破坏”和“有血之破坏”。两种破坏方法实际都属于“用人力以破坏”的范畴,前者的范式如日本明治维新,后者则如法国大革命。梁启超一直都倾心于无血之破坏,他说:“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能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11](P65)在他看来,破坏终究不可避免,能够实行无血之破坏当然很好,倘若不能,也只好实行有血之破坏。梁氏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不爱惜民命,恰恰相反,梁氏对于国家民族充满了无限的悲悯同情。他说,“一破坏之不忍,而终古以破坏乎!”[11](P66)早破坏即早受一日之福,而且所破坏可以较少,所保全者自多。如果一破坏不忍,则天然无意识之破坏将绵延不绝。况且,在今天这样腐朽的国体、政治、官吏的统治下,每年间接杀人者,或远比法国大革命来得惨烈。梁氏因此感叹道:“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污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夭戮之,疠戮之,刑狱戮之,盗贼戮之,干戈戮之。”[11](P67)再加上如今国家破败,还有十数国饿狼猛虎般的西方列强强势侵入,由此不难想象,我国民在数年、数十年后所需承受的苦痛或将更加悲惨。既如此,当下之破坏也就十分的紧迫和必要。可令人遗憾的是,梁氏发现那些倾心参与破坏的人,专任破坏,且主张一切破坏,大多无有建设之精神。这恰恰是令梁氏内心感到极大不安的。与此同时,这里也蕴含着梁氏对于民众启蒙(“新民”)的一个更加深刻的考虑,一如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黄君道之口所说的:“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若到那民德民智民力可以讲革命,可以做革命的时候,这又何必要革命呢。”[16](P38)于是后来梁启超很快就转而批评破坏主义和反对革命,开始大力提倡所谓的“开明专制论”。
其三、破坏与建设。应该说,梁启超在论及“破坏主义”时自始至终就十分注重“建设”之义,如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中说,“破坏之与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与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坏也;与成立两相济者,人为之破坏也。吾辈所以汲汲然倡人为之破坏者,惧夫委心任运听其自腐自败,而将终无成立之望者,故不得不用破坏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9](P50)在梁氏看来,只有人为之破坏与成立(“建设”)相关。同样的观念在《论进步》(1902)中也有具体体现,如他引用玛志尼的话,“破坏也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并且认为“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11](P67-68)也就是说,破坏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为实现建设的手段,建设才是目的。显然,梁启超“破坏主义”的这一层内涵是被当时的国人所忽略了的,当他发现留学生界和内地学校都受此思潮影响时,并未感到欢欣鼓舞,他说:“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6](P3)因此梁氏后来在《论私德》(1903)中对破坏主义作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建设与破坏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苟有所缺,则靡特建设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另外,建设也应伴随着破坏之始终,“不惟于破坏后当有建设,即破坏前亦当有建设。”[11](P130)在强调这一点后,梁启超对那些高喊“一切破坏”的人做了批评,认为“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并且还对新学青年提出了警示:“中国已亡于彼等(“老朽”)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之而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11](P136)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要针对的是传统君权制度和思想文化,即要求打破君主专制和孔学圣教对于国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禁锢,提倡民权和自由也就成为梁氏思想的题中之义。至于破坏的方法,梁氏始终考虑的都是“随破坏随建设”,而不是完全的破坏、彻底的破坏。包括他在后来表明自己放弃“破坏主义”时也一样,他更关注的还是如何建设一个近代化国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氏“破坏主义”终旨一直都没有变,他的思想只是被时人误解或者部分忽略了。
三、“破坏主义”是一种新民策略
梁启超的“破坏”言论,无不是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不论是前期的大力提倡,还是之后的全然放弃,都反映出他对于时局的清醒认识,其出发点都在爱国,“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8](P27)那么要爱国救国,仅凭一二英雄豪杰显然无法匡救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而应该从国民全体下功夫。况且,国乃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1](P1)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寻求自立自强之道,就必需以“新民”作为第一急务,此可谓是救亡图存之根本。关于“新民”之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专设一节做了详尽阐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1](P5)在这句话当中,实际上已经潜藏有一种固已存在的“旧民”现象,一个从“旧民”到“新民”的破“旧”立新的转变过程,以及一个“新民”所应具备的品格素养问题。
首先来说一种固已存在的“旧民”现象。梁启超应该是他那个年代最了解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对民族深沉的爱,不仅表现于他的浓烈的爱国情怀,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批判。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一文中,梁氏从六方面揭露了“旧民”身上所存在的诸种缺陷:一曰奴性。他认为国民秉奴隶性者最多,从居上流的高官权势者到乡曲小民,“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吾民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甘居奴隶,且以此为荣。二曰愚昧。梁氏认为,国民之智慧关乎国脑,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然堂堂中国,“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且全国之官吏与民庶皆愚昧之人,“未有通常之智慧”。三曰为我。爱己利己是人之本然,但毫无利群之心则一己之利也将不保。中国群力薄弱是因为“为我”之心太深,以致国家难以自存于竞争世界。四曰好伪。梁氏指出,今日之中国人,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皆以伪之一字行之。民无信不立,举国之人持一伪字以相往来,定难立于天地间。五曰怯懦。中国民俗向来柔弱,然处今日生存竞争最剧最烈百虎眈视万鬼环瞰之世界,“无勇”之害不仅损及民权,国权也将消亡。梁氏因此说,为国民者不可以无勇,并提倡“尚武之精神”和“中国魂”,此乃“民力”之体现。六曰无动。针对国人如木偶、如枯骨的“无动”现状,梁氏提出要打破这一死气沉沉的局面,“动者万有之根原”,人应该富于冒险进取精神,而不是安于现状,以不动为至善。[9](P18-28)
其次,是一个从“旧民”到“新民”的破“旧”立新的转变过程。毫无疑问,上述梁启超所分析的六种国民缺陷都是要破除的,这不仅是“新民主义”的重要内容,更是“破坏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戊戌变法时期,新起的维新派就注意到国民愚弱的社会现实,于是大力提倡要从国民入手,实现救亡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是严复的《原强》(1895)一文。具体到“新民”内容,严复就有“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梁氏的“新民主义”,几乎都是围绕着严氏此义所做的发挥和推进。具体而言:“鼓民力”方面,梁氏不仅强调要从生理上对中国人种进行改造,如强健体魄、讲究卫生、禁食鸦片、禁戒缠足、禁止早婚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倡以一种尚武精神来塑造“中国魂”,这种“中国魂”即以爱国心和自爱心和合而成的“兵魂”。为进一步激发民力,梁氏还创作了《中国之武士道》(1904)一书,认为吾族乃“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并以此激励同胞发扬吾国人之武士道,以涤荡文弱之风。“开民智”方面,梁氏将开民智视作国家自强的第一要务,是兴民权和立国权的前提。并且认为开智的根本在于教育,而随后的废科举、立学堂、兴学会、立师范、立女学、立幼学、译西书、开报馆等系列主张即由此开出。另外,梁氏还提出开民智要与开绅智、开官智并启,尤其应以开官智为起点,因为“官贪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13](P45)“新民德”方面,梁氏极力提倡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来对传统封建伦理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大力输入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群治思想、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进取冒险精神等等,以重塑国民道德。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也即要将原来的乡民、臣民、部民改造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
最后是一个“新民”所应具备的品格素养问题。如果说从“旧民”到“新民”过程所体现的是“破坏主义”的“破”的内涵,那么这里则关乎到“破坏主义”的“立”的意义。很显然,梁启超在《新民说》针对国民道德所存在的缺憾树立了诸多新的道德观念,它们实际上是可以归结为“公德”与“私德”两个大方面。梁氏其实说得很清楚,道德无外乎公私二者:“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1](P12)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氏在《新民说》中立专节论述的,包括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义务、自由自治、竞争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等思想在内,无不属于公德范畴。而且事实上,已有论者将上述内容归结到“公德”条目下做了具体分析。①详见[美]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六章内容的专章论述。不难发现,梁氏在前期所论列的这些公德条目,无不以利群固群善群为旨归,服务于他的“群治”理想,而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所最缺的,“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1](P12)因此才有必要“采补其所本无”来进行革新。梁氏认为,只有发明了“诸德之源”的公德,新道德才会出现,“新民”也才会到来。然而需指出的是,梁氏提倡公德从来就没想过要把它与私德对立起来,为防止此种现象,梁氏在1905年只好又专门论述私德的意义。他开篇即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11](P118)并且申明,“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11](P119)梁氏认为,私德是传统文化中最为偏重的道德,那么如何“淬厉”这种本有之道德,他提出了三个进德修身的要领,即正本、慎独、谨小。梁氏这种处理传统“旧”道德的方式,恰恰又印证了他最初所提出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由此,梁氏“新民”所具备的“新道德”,即可说是西方道德与传统道德的相互补充,也即公德和私德的融合。这个客观事实也充分说明,梁氏的“新民”思想自始至终都完整地落实了他的“破坏主义”策略:随破坏随建设。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作为他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一直都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它从来不意味着要彻底粉碎和毁坏一切,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蕴涵。通过上述考察不难发现,梁氏的“破坏主义”就如同“幽灵”一般,不断闪现于他的新民思想发生的整个环节,成为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最富于鼓动性和穿透力又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政治话语。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苏舆编.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侯德彤
Destructionism: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Strategy in His Early Years
XI Zhi-wu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China )
Liang Qichao's destructionist claims went from germination to maturity, and to complete abandon. This transition was related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also embodied his refl ec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culture and thoughts. Destructionism eventually pointed to the new citizen doctrine advocating civil intelligence and civil rights. Therefore, destructionism is actually Liang's new citizen strategy in his early time.
Liang Qichao; destructionism; new citizen strategy
K256.5
A
1005-7110(2014)02-0020-07
2014-01-21
席志武(1985- ),男,江西高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