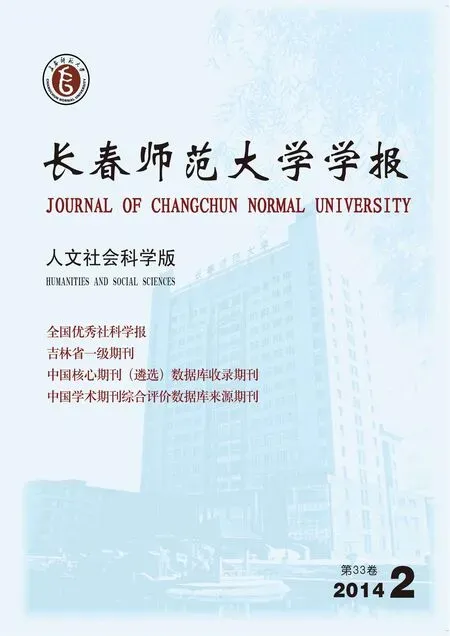“种”的博弈:基于虚拟社区田野之上的文化内涵分析
田廷广,武 玮
(1.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2.西藏民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种”的博弈:基于虚拟社区田野之上的文化内涵分析
田廷广1,武 玮2
(1.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2.西藏民族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售、捐献精子,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售精、捐精的“主力军”。本文尝试以“互联网”为“虚拟社区”开展田野工作,从人类学和遗传学的视角揭示高级知识分子精子深受市场青睐的文化内涵。
精子;博弈;互联网;文化内涵
以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为基础进行的对“虚拟社区”①的田野调查,使人类学摆脱了传统田野调查的局限,不必亲身去遥远的“异域”,就可以轻松做到“在此地,研究彼地”[1]。笔者以网络为调查点,通过整理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出售精子的相关信息,探讨人们为发展下一代而进行的种的选择,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种”而优则仕与家族的“延续性”
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离不开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2],则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最根本的保证。“种”是生物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类的两性关系的结合、种的繁衍是一种生物的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义。[3]14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型社会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种结好果”、“什么花结什么果”等农业谚语不仅揭示了农作物生产发展的自然规律,亦是对人类自身繁衍、进化的一种“经验性”的认识与总结,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经历了群婚、血缘婚之后,发现在这样一种婚姻形态下所孕育的后代存在着智力等方面的先天性缺陷,而不同地区、部落、种族的人进行通婚之后所生育的子女较为健康、智力健全。作为家族祖先在世间神圣权力的代表——族长(家长)为了更好地延续家族的血脉,保证家族的强大,必须在“种”的选择上做到“优化”,而这种“优化”的“种”的筛择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所构建的一种“⊥”字型的“未来”亲属结构。所谓“⊥”字型的“未来”亲属结构是指两性双方在寻找配偶之时,会各自以对方为基数纵向向上数三代及横向看与其构成血缘亲属关系的同辈人中是否存在“遗传病史”或者“智力低下”等现象,若无此现象,则隐含着两性双方有机会构建一种“未来”的亲属关系。反之,男女双方的家长会代表家族作出符合家族利益的选择。比如:男方择偶时,会对对方个子的高低有所要求,尤其是较矮的男性及其家族,在择偶之时会更多考虑女性的身高问题,希望改变下一代,达到“改良品种”的目的。
社会中部分主体选择高级知识分子精子作为“种”的对象,亦为一种“种”的“优化”过程,淘汰其“劣质”的“种”,实现“种”而优则仕。面对各种新思潮、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长久以来存在的“家族的延续”、“香火继承”等儒家伦理观念并没有减弱。面对不育等生理性状况,现代人会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种”的选择,改变了过去领养、过继等形式,使其“种”在“继”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孕育”。
二、得与失:传统家之情感的回归
情感是指个体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欢喜、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回归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抽象意义上的家园,既有现世人对家族祖先的情感,也有对在世人及未来人的情感。现世生活的人无法进行传宗接代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家族内部及外部的情感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他们对家族产生“负罪感”、“自卑感”。他们会千方百计去烧香拜佛、求医问药,祈求早得贵子,若不能生育,则自惭形秽,感觉低人一等。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一种“时尚性”的情感回归方式,即通过他人出售或者捐献的精子而获得“种”的延续,逐渐地被社会大众所选择。部分社会群体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种”的青睐,表明当事人在无法凭借“亲生血缘”的延续回到家族情感生活时,选择“社会父亲”的角色来满足此种意愿。
社会大众通过各种办法扭转家族血缘“继”和家族情感的“失去”局面,是为了“得到”一种“继”的延续和情感的“回归”。只不过这样一种因“失去”而对“得到”的渴望,似乎如同普通人对于一件奢侈品的奢望,是一种“求不得”所带来的苦。从人类学的视角解释“求不得”的苦,可以理解为“得到”(get something)和“失去”(lose something) 的对立关系。两性双方出现不育等生理病状时,面临的将是一种失去“种”的痛苦,是一种“失去”而得不到的苦,是一种寄希望于“种”上的“得到”。如果从内观的角度思考“得与失”,或许可以称之为思想感情的内在推力。那么,这样情感的得失,以何而生呢?这就是缘于社会两性双方执着于“家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的家族情结。如果从存在论的角度解释“得与失”,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量的积累与缩减。高级知识分子的“种”作为一种社会选择的对象,实质是社会部分个体错误地以为可以使“种”的主人多年来所积累的文化知识依托“种”得以遗传,文化素质水平较低的人将“文化资源”依托“种”而遗传到所孕育的生命个体之中。将高级知识分子的“种”作为优先选择对象,是现世人回馈家族情感的最好礼物,是中国人对传统家之情感的一种外化表现。中国传统意义上以乡土社会为基础而形成的“父系传承体系”中,人生的终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和家族的兴旺。在“家”的情感回归面前,“个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必须以“集体”利益为主,这也是中国人形成“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国家情怀”的情感基础。
三、“祖坟冒青烟”民间观念的现代化“转移”
民间有句俗语“祖坟冒青烟”。其内涵是指,生活于现世的人将家庭的兴衰荣辱归因于祖先的庇佑。为了更好地使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最大化地得到祖先的庇佑,首先要达到对祖先的“孝”。如何实现对生活于“阴界”祖先的“孝”?最好的选择是对祖先的“供奉”。通过借用某种供品(如纸钱、水果、香、蜡烛等)达到与祖先的沟通。在出现生育问题的家庭中,他们希望通过对祖先的“谄媚”获得生育问题的解决,即未得到“种”的家庭希望祖先保佑得到“种”,以延续家族的谱系。同时,在拥有血缘延续的家庭中,他们依然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光耀门楣”等希望寄托于祖先身上,即得到“种”的家庭希望祖先保佑使“种”得到“优化”。而祖先的庇护常常通过一种外界“话语权”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外界“话语权”的具体化表征就是当后世对祖先供奉的“虔诚度”等于或高于生活于“阴间”祖先的“满意度”时,其家族的祖坟就会有“青烟”的出现。
过去,村民习惯于将“青烟”作为生活于“阴间”祖先对现世后代的一种“回馈”。即使是对科学有了一定的认知之后,仍然有人不时说出类似于这样的“民间俗语”,以表达自己对“他人或家族”的一种夸奖。生活于共同村落或者社区的人,享有相同的外界资源,却出现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他们必然会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可进一步引申为“羡慕”、“嫉妒”的心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殖技术的发展,面对“不育”等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采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取代过去祈求神灵庇佑等办法以期望得到延续家族香火的“种”。选择高级知识分子的“种”则更多地是社会部分群体希望在家族香火延续的基础上,能够达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光耀门楣”等社会目的。实际上,这反映的是“祖坟冒青烟”等民间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转移”。
四、辟谣与科学:“知识文化遗传”的否定
部分群体青睐于高级知识分子出售或捐献的“种”,一方面,认可了“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观点,并以社会个体文化水平的高低将不同群体的人的“种”进行了分类,无形之中产生了“隐性”社会阶级;另一方面,盲目地认为或者相信文化知识能够通过社会个体的精子这个“种”得到遗传,以利于下一代的“优化”。在葫芦岛晚报的“售精广告”中②,“种”的主人尤为强调其学历、外貌等特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遗传是生物个体亲子之间通过肉眼或借助各种技术措施所能识别的一切表形特征的相似性,是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或现象是亲代将遗传物质传递给子代并表现其功能的反映。也就是说,亲代的身高、脸型、单双眼皮等表形特征能够遗传给子代已经得到了科学的验证。
社会群体中高学历者的高学历的形成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物理的过程,也就是将我们所学习的知识作为一种信号,激发大脑中某些细胞的活性,外化地表现为一个人考虑或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显得更加智慧,但这一过程并没有改变遗传的载体DNA,这样我们便可以知道知识的架构和积累无法影响其个体的DNA,而DNA 也不会对其个体的学习产生限制。总之,科学实验和社会实例表明,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识并不能通过“种”遗传给子代。但我们承认亲代所拥有的高智商可以作为一种可遗传因子遗传给子代,因为高智商作为一种大脑的构成是由DNA控制的。而智商并不等于文化知识水平,所以社会中的部分个体应站在科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五、反思
人类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持续性是主要的方面,历时性的继续或继承是重要的方面。“继”不仅是新陈代谢的关键,也是维持文化和社会存在的主要环节。[3]59社会大众对高级知识分子“种”的青睐,无外乎是希望在完成家族谱系的纵向延续基础上,通过对“种”的选择而实现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在情感上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此种行为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孕育生命个体的“种”与其所具备的知识、文化、身世等因素无关。所以,不应该依据“种”的主人的文化程度来对“种”进行等级划分,产生“隐性”社会阶级。这就要求相关当事人在对待、处理此种社会问题时,不要带着一种“有色”眼镜去寻找所谓“优质”的“种”。应坚信科学、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为社会中部分不法出售“精子”的组织或个人买单,更不可助长有违中国传统基本伦理道德的不良社会风气。同时,应该加大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当事人应在选择“试管婴儿”、“代孕母亲”、“代孕夫”的过程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呼吁社会建立生命伦理价值体系。此外,“在社会人类学这一学科看来,所有的系谱和亲子关系的建构都是文化的。”[3]24由于新的生殖技术的发展,依靠“种”的选择而形成的“社会父亲”关系将不同于“亲生父亲”关系,在新时代、新环境下如何进一步区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亦是非常必要的。
[注 释]
① Howard Rheingold 或许是第一个写虚拟社区的人,他将虚拟社区定义为“出现在网络上的社会集合体,当一定数量的人长时间地讨论共同的话题,具有丰富的人类情感,在赛伯空间形成人际关系的网络时,这种集合体便出现了。”转引自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450页。
②《葫芦岛晚报》2011年12月5日报道,记者据建昌一家网站出售精子的广告找到了“种”的“生产者”,该“种”主人是安徽人,市高考状元,研究生毕业于国内最好大学之一。29岁,身高173cm,体重65公斤,五官端正,方脸,双眼皮,身体健康。因经济状态突变,忍痛出售精子。出售价格在3000元以上。
[1]周大鸣.二十一世纪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453.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1.
[3]麻国庆.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013-12-04
田廷广(1987- ),男,黑龙江富锦人,黄河科技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藏族和羌族民族历史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
G0
A
2095-7602(2014)02-0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