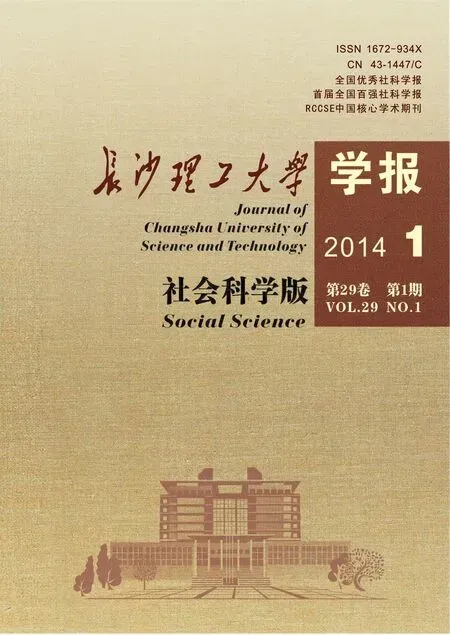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
——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孟 泽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
——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孟 泽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周作人;新诗;国语;自由;传统
汉语诗歌“进化”到“新诗”,①意味着它必须超越发育饱满的传统“教养”和“体制”,遗蜕破茧,解构重构,确立新的“自我”,方可以造就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典范。同时,汉文化以及汉语本身的“宿命”,或者说,汉文化和汉语所指示的规定性、必然性,又一定会在“新诗”所能创造的新的精神版图、品相和形制中,获得必要的回响和反应,汉语诗歌的感发机制与诗意生成,诗歌与政治、道德、伦理、宗教的互动,汉语诗歌与汉语“声音”的发育变迁,以及它与音乐已经和可能建构的关联,无不暗示着某种它无法逃离的必然取径。对于诗歌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宿命,在某种意义上,汉语的限度,就是“新诗”的限度,新诗的属性,对应着汉语的属性。对此,周作人曾经给出过非常具有启示性的诠释。
一、“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新诗的定义
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有“很好的声调”。胡适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1]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他们另走了一条欧化的路”。
在作于1929年的《过去的生命》序中,周作人对自己“所写的诗的一切”做了如下解释:“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的散文没有什么不同。”[2](P620)摆脱了“旧镣铐”,却并不以新诗人自居,是出于对自己气质、性情的认定;不承认自己所做的诗算“真正的诗”,则是因为有对“新诗”的更高理想。
1921年6月9日刊于《晨报》的《新诗》中,周作人说:“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的表示出来,因此根基并不十分稳固”,“现今的诗坛,岂不便是一个小中国么?本来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为甜美,所以革新的人非有十分坚持的力,不能到底取胜。”[2](P695)在《〈农家的草紫〉序》中说:“现代新诗之不能满人意,大抵都是承认的,其实也是当然的事,不值得什么悲观与叹息。我们屈指计算新诗之产生,前后不过八年,这七八年在我们看去虽是一大段时间,但在文化发达的路程上原算不得什么;我们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期望每年出十个诗人,每月出百篇佳作,不但太性急,也不免望太奢了。”“我觉得新诗的第一步是走了,也并没有走错,现在似乎应走第二步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自由,正当需要新的节制。不过这第二步怎样走法,我也还说不来,总之觉得不是那些复古的倾向,如古风骚体或多用几个古字之类;反正第二步是跟着第一步走的,真正在那里走的人,各人都会去自己实验出来。”[2](P735-736)
对“新的自由”的信任,意味着周作人对于“语体诗”的高度认同,所谓“新的节制”,作为“跟着第一步走”的“第二步”,在周作人看来,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韵律、语言及形式上的自我约束,而意味着坚持“新的自由”的同时,“新诗”必须拥有更多的诗的本体要素才足以自我成立和自我支撑。
“新诗”是诗的,在题为《宗教与文学》的演讲中,周作人对“诗”与“文”,作了大致的甄别:“文学,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一是诗。这是精神上的区别。形式上,文又可分为韵文与散文两种,诗又可分为有韵诗与无韵诗。虽然古时常用诗或文来讲科学或哲学的很多,但就精神上讲,文学总是创造的,情感的,与那分析的,理智的科学实在不能互相调和,因为性质很不相同。宗教也是情感的产物,与文学相类。而文学就精神上区别,又可说,诗是创造的,情感的,与宗教有关的;文是分析的,理智的,与宗教冲突的。”[3]“诗”、“文”之别,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区别,而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诗歌是创造的情感的,离分析的理智的科学最远,“文”可以是“韵文”而终归是“文”,“诗”可以“无韵”而终归是“诗”。
这种观点与周作人对诗歌批评的要求是一致的,他说“研究文学的人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能够分析文学的成分,探讨时代的背景,个人生活与心理的动因,成为极精密的研究,唯在文艺本体的赏鉴,不得不求诸一己的心,便是受过科学洗礼而仍无束缚的情感,不是科学知识自己”[4](P180),也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
在对于“小诗”的辩护中,周作人为“新诗”给出了更加明确的释义:“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或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凡诗都非真实简练不可,但在小诗尤为紧要。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切迫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我们表现的欲求原是本能的,但是因了欲求的切迫与否,所表现的便成为诗歌或是谈话。譬如一颗火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在这程度之下不过是普通的说话,犹如香盘的火虽然维持着火的生命,却不能有大光焰了。”“‘做诗,原是为我自己要做诗而做的,’做诗的人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兴,觉得不能不说出来,而且有恰好的句调,可以尽量的表现这种心情,此外没有第二样的说法,那么这在作者就是真正的诗。”[5]
周作人对于诗的阐释,更强调诗的全体的要素,而不是单纯的“新”、“旧”对立,他认为,在“文学的进化上,虽有连接的反动(即运动)造成种种的派别,但如根本的人性没有改变,各派里的共通的文艺之力,一样的能感动人,区区的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只足加上一层异样的纹彩,不能遮住他的波动。”[4](P179)
既然“新诗”不能移易如上作为“诗”的规定性,“新诗”在走出“第一步”后,又不免“四顾茫然”,那么,成就“真正的中国新诗”,将有待于融化“新潮流”“旧方法”,重建诗的轨辙。周作人在1926年6月刊《语丝》82期的《〈扬鞭集〉序》中谈到《新青年》时期“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尹默早就不做新诗了,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他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分略有差异的缘故。半农则十年来只做新诗,进境很是明了,这因为半农驾御得住口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的手法,……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2](P739-741)
除了“新诗”必须是“诗”——“以抒情为主”的,“浪漫主义”的,“象征”的,“美化”的,“新诗”还应该是个性化的。在《个性的文学》中,周作人充分肯定了“个性”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必要性,他引英国戈斯为印度那图夫人诗集说的话说,“她要做诗,应该去做自己的诗才是。但她是印度人,所以她的生命所寄的诗里自然有一种印度的情调,为非印度人所不能感到,然而又是大家所能理解者:这正是她的诗歌的真价值之所在,因为就是她的个性之所在。”“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无论他是旧是新,都是一样的无价值,这便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个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1)创作不宜完全没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的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6]
这样的“个性”,无疑还包含了民族性和文化历史性的义项。
虽然意识到文学与宗教的关联,文学曾经指向“把我们与最高的神合一”,现在的文学需要“结合全人类的感情”,但是,周作人认为,“近代个人的文学也并不是绝对可以排斥的”[7],而且,“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这个人的文艺也即真正人类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文艺。”[8]基于相同的理念,周作人诠释了艺术的普遍性:“文学家虽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因为据我的意见,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9]
无论情感,或者趣味,包括基于特定情感与趣味的艺术创造,周作人始终强调其中个性对于所谓普遍性、人类性的前提与决定性[10]。他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惟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现在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我们不必一定在材料上有明显的乡土的色彩,只要不钻入哪一派的篱笆里去,任其自然长发,便会到恰当的地步,成为有个性的著作。……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如我们因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orano)一般。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11]
二、“诗的效用”——“善之华”与“恶之华”
对于诗的个人性与集体性的审慎分别,联系着周作人在诗的“效用”观上的理智。
在《诗的效用》中,周作人对于俞平伯的“好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诗的效用,我以为是难以计算的。文艺的问题固然是可以用了社会学的眼光去研究,但不能以此作为唯一的定论。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诗的创造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几乎是生理上的需要,仿佛是性欲一般;这在当时虽然是戏语,实在也颇有道理。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此外功利的批评,说他耗费无数的金钱精力时间,得不偿失,都是不相干的话。”“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合,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功利的批评也有一面的理由,但是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的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的性质,他虽声言叫文学家做指导社会的先驱者,实际上容易驱使他们去做侍奉民众的乐人,这是较量文学在人生的效用的人所应注意的地方了。”这种关于文艺在功能与效用上的“得失”“正反”的辨析,是针对性的,又几乎是预言性的,对于文艺来说,“效用”不能作为前提来设定,一旦作为前提,再神圣的“效用”也可能会适得其反、走火入魔。何况,过于现实的“效用”观从来都可以是神圣的,义正词严的。
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周作人对所谓文学的“人生派”“艺术派”的分殊,作了“各自有他的环境与气质的原因”的澄清,强调“人生派”“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因此必须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12]。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再次强调“‘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13]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艺术派”“人生派”的分殊,正是“效用观”的分殊。类似的问题还有关于文学与“善”的关系问题。
俞平伯提出“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周作人认为,如果将“善”解作现代通行的道德观念里的所谓善,“这只是不合理的社会上的一时的习惯,决不能当做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倘若指那不分利己利人,于个体种族都是幸福的,如可鲁泡特金所说的道德,当然是很对的了,但是‘全而善美’的生活范围很广,除了真正的不道德文学以外,一切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在这范围里边……这样看来,向善的即是人的,不向善的即是非人的文学: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字面上似乎还可修改,因为善字的意义不定,容易误会,以为文学必须劝人为善,像《明圣经》《阴骘文》一般才行,——岂知这些讲名分功过的‘善书’里,多含着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里去呢?”[9]“我近来不满意于托尔斯泰之说,因为容易入于‘劝善书’的一路。”“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14]
在《情诗》一文中,周作人说“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我承认一切的情诗。”“‘性是自然界里的爱之譬喻’,这是一句似乎玄妙而很是确实的说明。生殖崇拜(Phallicism)这句话用到现在已经变成全坏的名词,专属于猥俗的仪式,但是我们未始不可把他回复到庄严的地位,用作现代性爱的思想的名称,而一切的情歌也就不妨仍加以古昔的Asmata Phallika(原意生殖颂歌)的徽号”“性爱是生的无差别与绝对的结合的欲求之表现,这就是宇宙间的爱的目的”“恋爱因此可以说是宇宙的意义”“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正是当然的”“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新诗的精神”[15]。
不止是对于“情诗”予以人类学的阐释,事实上周作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定义了诗歌,这是诗歌走出以神圣的政治或伦理名义编织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迷宫的重要法门。周作人屡屡申述“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16],虽然说的是人伦物理,但也正是他对于文学情感的态度与主张。在著名的《人的文学》中,周作人把“新文学”定义为“人的文学”,而所谓“人”,他的定义是“(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因此,他认为,“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这句话几乎解构了人们下意识的对于人的生命本能的道德打量与道德清算,“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文学不能回避对此的表现,因此“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17]。
这种人类学的视野,正是周作人区别于“五·四”时代众多诗家的根本所在,理论辨析的宽容与从容也由此而来,他作有《艺术与道德》[18]的专文,介绍蔼里斯从人类心理的角度对于文艺的审视,他曾说“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19]。因此他不拒绝研究《猥亵的歌谣》,认为“仿佛很神秘的至情,说得实一点便似是粗鄙的私欲,实在根柢上还是一样。”“猥亵的歌谣起原与一切情诗相同”,把它们视为“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20]。不再把审美与道德、思想与行动等量齐观,周作人从根本上否定以道德要求和“效用”指标考量艺术的惯习。即使如此,他仍然坦诚而警觉地意识到,自己骨子里其实有“道学家”人格,近乎“法利赛人”。
三、汉语的限度,新诗的可能与“运命”
与胡适设计“新诗”的未来时对于“纯粹的国语”的想象不同,周作人对于“语言”的认识更深入也更真确。他的语言工具意识,并未传导出工具论式的语言观,而是充分体认到语言对于文明嬗替的根本性与自身的遗传性,即语言同时体现出一种不能忽视的反工具论的精神属性与本质上的连续性。
在周氏看来,“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这当然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用字更丰富,组织更严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两者的发达是平行并进,文章语虽含有不少的从古文或外来语转来的文句,但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故能长保其生命与活力。”[21]在强调“口语”之于“国语”的根本性的同时,周作人出离了对于文言的简单否定,他说:“国语古文得拿平等的眼光看他,不能断定所有古文都是死的,所有的白话都是活的。”[22]
意识到“我们生在这个好而又坏的时代,得以自由的创作,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致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所以我们向来的诗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因反抗古文遂并少用文言的字句……”[23],周作人反思当年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认为“光绪末年的主张是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民国六年的主张是洪宪及复辟事件的反动。”“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出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其“系属与趋势总是暗地里接续着”,“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21]。“古文者文体之一耳,用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体而在隶属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白话文亦文体之一,本无一定属性,以作偶成的新文学可,以写赋得的旧文学亦无不可。”[24]“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25]
因此,周作人勇于宣称:“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26]“新诗”还缺少这种“融化”。他认为,在“新文学”里,“小说与随笔之发达较快,并不在于内容上有传统可守,不,在这上边其实倒很有些变更了,它们的便宜乃是由于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应用……”[27]
为了能够较自然而充分地叙事(“叙复杂的事实”)、抒情(“抒微妙的情思”)、说理,“须是合古今中西的分子融合而成”“一种中国语”[21],既大胆欧化,“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28],改变汉语“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之不足;同时,基于叙事抒情的文学共性,也基于汉文字语言共通的表现力,又必须坦然面对并且倚重自身的传统财富,包括方言中的“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29],以便为“新诗”“开出最宽阔的门庭”。
周作人对于“新诗”可能性的思考,出于对传统资源的理性审视,他说,“虽然现在诗文著作都用语体文,异于所谓古文了,但终是同一来源,其表现力之优劣在根本上总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学里去查考前人的经验,在创作的体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帮助。譬如讨论无韵诗的这个问题,我们倘若参照历来韵文的成绩,自《国风》以至小调……可以知道中国言文的有韵诗的成绩及其所能变化的种种形式;以后新作的东西,纵使思想有点不同,只要一用韵,格调便都逃不出这个范围。试看这几年来的新诗,有的是‘白话唐诗’,有的是词曲,有的是——小调,而且那旧诗里最不幸的‘挂脚韵’与‘趁韵’也常常出现了。那些不叶韵的,虽然也有种种缺点,倒不失为一种新体——有新生活的诗,因为他只重在‘自然的音节’,所以能够写得较为真切。这无尾韵而有内面的谐律的诗的好例,在时调俗歌里常能得到。我们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话诗的两条路:一是不必押韵的新体诗,一是押韵的‘白话唐诗’以至小调。这是一般的说法,至于有大才力能做有韵的新诗的人,当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话唐诗’以至小调为条件。有才力能做旧诗的人,我以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苏黄或任何人为条件。”[30]
周作人并不认为,朝讲求音韵声调的方向努力,是“新诗”难以规避的前途(与鲁迅有所区别)。但是,他认识到,汉字汉语连同其音韵声调,已经塑造出汉语诗歌本身及其创造者和接受者的某种难以解除的习性和品格,“不必押韵的新体诗”并不比“押韵的”更容易获得接纳。他说:“中国人的爱好谐调真是奇异的事实,大多数的喜听旧戏而厌看新剧,便是一个好例,在诗文界也全然相同”,“中国小调的流行,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换一句话说即是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9]而“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哪里去找新的根苗……”[31]“念古文还有声调可以悦耳,看白话则意义与声调一无所得,所以兴味索然。”[9]
基于汉语及汉语诗歌的此种赋性,周作人在指出“不必押韵的新体诗”是“新诗”的出路的同时,他对汉语诗歌与汉语及其声韵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检讨,他说:“中国没有史诗而散文的史发达独早,与别国的情形不同”,“没有神话,或者也是理由之一,此外则我想或者汉文不很合适,亦未可知。《诗经》里虽然有赋比兴三体,而赋却只是直说,实在还是抒情,便是汉以后的赋也多说理叙景咏物,绝少记事的。”周作人从佛经翻译的偈体,看出普通汉语韵文的难以记事,直到弹词宝卷“乃是一种韵文的故事”,他举弹词《天雨花》为例,认为其“句调却也不无可取”,尽管其中难免“语固甜俗”,但“如欲以韵语叙此”,而“风骚诗词各式既无可用,又不拟作偈,自只有此一法可以对付,亦即谓之最好的写法可也。史诗或叙事诗的写法至此而始成功,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汉文协韵作叙事长篇,此由经验而得,确实不虚,但或古人不及知,或雅人不愿闻,则亦无可奈何,又如或新人欲改作,此事不无可能,只是根本恐不能出此范围,不然亦将走入新韵语之一路去耳。不佞非是喜言运命论者,但是因史诗一问题,觉得在语言文字上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度,其次是国民兴趣的厚薄问题,这里不大好勉强,过度便难得成功。中国的叙事诗五言有《孔雀东南飞》,那是不能有二之作,七言则《长恨歌》《连昌宫词》之类,只是拔辣特程度,这是读古诗的公认之事实,要写更长的长篇就只有弹词宝卷而已。写新史诗的不知有无其人,是否将努力去找出新文体来,但过去的这些事情即使不说教训也总是很好的参考也。”[32]
无论语言文字的能力,或者文化兴趣的厚薄,都难以勉强,“过度便难成功”,创新是有限度的,这是基于“文学史的教训”,基于比较立场的文学与文化的观照,照见的自然包括“新诗”所具有的可能性与无可逃逸的必然性:叙事便难免成为“一种韵文的故事”,“唯用此形式乃可以汉文协韵作叙事长篇”,“中国的诗仿佛总不能不重韵律”,此所谓“运命论”也。这样的“运命”,正是可以与曾国藩所谓“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之类的总结相贯通的,同时与考古学家李济所说的“中国人的历史表明,象形文字的主要长处是它作为某种最终的、简单明了的真理的化身,经受得住各种冲击和压力……拼音的思维是一种行为类型,而不是一种神秘才能”(《安阳》),也就是说,汉字汉语有着一种内在的诗性,因此,汉语诗意的诗意构成,必须呈现这种诗性,而无法回避它。
对于“民歌”、“童谣”的不间断的留意,同样联系着周作人对于“新诗”的“运命”的审察。
1919年周作人为刘半农搜集的《江阴船歌》作序,认为刘氏的实验“给想用口语做诗的人一个很好的参考”[33]。在《歌谣》一文中,他认为民歌“从文艺的方面我们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吉特生说,‘民歌作者并不因职业上的理由而创作,他唱歌,因为他是不能不唱,而且有时候他还是不甚适于这个工作。但是他的作品,因为是真挚地做成的,所以有那一种感人的力,不但适合于同阶级,并且能感及较高文化的社会。’这个力便是最足供新诗的吸取的。意大利人威大利(Vitale)在所编的《北京儿歌》序上指点出读者的三项益处,第三项是‘在中国民歌中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后边又说,‘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与欧洲诸国类似,与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合。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这一节话我觉得极有见解。”[34]周作人甚至认为,“歌谣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一民族之非意识的而是全心的表现,但是非到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发达的时代不能得着完全的理解与尊重。”[35]
在谈到中国民间歌谣似乎显得“特别猥亵”的原因时,周作人还揭示了汉语诗歌的一种历史“运命”。《〈江阴船歌〉序》谓:“民间的原始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曲折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便当,以至变成那种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36]
文人与“民众诗人”在创作上的隔膜,实际上正是口语与文言的隔膜,这种隔膜一方面使口语无法获得提升,一方面导致文言以及形式(“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又无法有效覆盖人民广阔的情感与心灵,结果是民众的创作无法“雅驯”,无法拥有细腻曲折的表达力,很难上升到可以被普遍认同的高度,而文人写作也同样不能获得心灵、价值乃至表达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因为缺少口语与文言的交流互动,也使汉语丧失了对于广大的“情欲”世界(即生命世界)的正常体验力和表达力。语言的睽隔其实就是认识、价值的睽隔,就是“事实界”(实然)与“道德界”(应然)的睽隔,这同时意味着社会文化的僵固、封闭与二元对立。
周作人所代表的“五·四”以来知识界对于“新诗”的热情,伴随这种热情而升起的对于民歌的关注,事实上正隐含了为新文学、新文化弥缝消除这种二元对立的潜在动机,尽管可能并不自觉,结局也未必美好,特别是当“民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物,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图腾而“一元独大”的时候。
四、“不统一的自然”——关于“打油诗”“杂诗”
对于既是“自谦,但同时也是一种自尊,有自立门户的意思”的打油诗、杂诗,周作人的解说仍然透露了他对于汉语诗歌及其可能性与限定性的辨正:“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同样地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只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名称虽然是打油诗,内容却并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甚正经,这正如寒山子诗,他是一种通俗的偈,其用意本与许多造作伽陀的尊者别无不同,只在形式上所用乃是别一手法耳。”[37]《小河》“当时觉得有点别致,颇引起好些注意。或者在形式上可以说,摆脱了诗词歌赋的规律,完全用语体散文来写,这是一种新表现。”“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其次是形式也就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传》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所以说到底连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38]
《老虎桥杂诗》题记曰:“我称之曰杂诗,意思是与从前解说杂文时一样,这种诗的特色是杂,文字杂,思想杂。第一它不是旧诗,而略有字数韵脚的拘束,第二也并非白话诗,而仍有随意说话的自由。”“说到自由,自然无过于白话诗了,但是没有了韵脚的限制,这便与散文很容易相混,至少也总相近,结果是形式说是诗而效力仍等于散文。”“白话诗的难做的地方,我无法补救,回过来说旧诗,把它难做的地方给毁掉了,虽然有点近于削足适履,但是这还可以使用得,即是以前所谓打油诗,现今所谓杂诗的这物事。因为文字杂,用韵亦只照语音,上去亦不区分,用语也很随便,只要在篇中相称,什么俚语都不妨事,反正这不是传统的正宗旧诗,不能再用旧标准来加以批评。因为思想杂,并不一定照古来的几种轨范,如忠爱、隐逸、风怀、牢骚那样去做,要说什么便什么都可以说,但是忧生悯乱,中国诗人最古的那一路思想,却还是其主流之一,在这里极新的又与极旧的碰在一起了。正如杂文比较的容易写一样,我觉得这种杂诗比旧诗固然不必说,就是比白话诗也更为好写,有时候感到一种意思,想把它写下去,可是用散文不相宜,因为事情太简单或者情意太显露,写在文章里便一览无余,直截少味,白话诗呢又写不好,如上文所说,末了大抵拿杂诗来应用。”[39]
周作人的“打油诗”、“杂诗”实践,不仅表明特定的知识结构、书写习惯对于写作的决定性影响,同时联系着汉语在书写与表达上的可能和“便宜”,这未尝不是聂绀弩们的“打油诗”别开生面,居然可以观照一个时代的“美学”依据。周作人对此的自我阐释,其实与周作人对于“新诗”、“新文学”的整个态度是融洽的,并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周作人认为,“一切均可以平等而个人的趣味决不会平等,一切均可以自由而个人的性情决不能自由;有这个不幸(或者是幸)的事实在那里,艺术的统一终于不可期。”“我们没有宗教家那样的坚信,以为自己的正信可以说服全世界的异端,我们实在只是很怯弱地承认感化别人几乎是近乎不可能的奇迹,最好还是各走各的,任其不统一的自然,这是唯一可行的路。”[40]
在《做旧诗》中,周作人说:“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人的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但是我却不能命令别人不准做,不但是在我没有这个权威,也因为这样的禁止是无效的。”[41]“最好任各人自由去做他们自己的诗,做的好了,由个人的诗人而成为国民的诗人,由一时的诗而成为永久的诗,固然是最所希望的,即使不然,让各人发抒情思,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情。”“做诗的人要做哪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5]
表面看来,周作人写作“打油诗”、“杂诗”似乎有违他自己当年的承诺,实际上却意味着他对于“新诗”情感与形式一律性、统一性的否定。“不统一的自然”、“完全的自由”,包括向旧体制寻找灵感的自由,正是他所认同的“新诗”在起点上的权力和使命。不仅“新诗”迈向自由的最初步伐,多少可以见到“打油诗”、“游戏诗”的形迹,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打油”意味着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诗意诗性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无论形式,或者心灵,所谓彻底的解放终不免是一种奢望,汉语与汉语诗歌,不必也无法逃离属于自己的规定性。
很难说周作人是“新诗”的专业从事者,但他对于诗的含茹和思考从未停止。显然,他是最早从“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与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的,也是最早从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解放出来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
[注释]
①“新诗”作为一个词,在古汉语文献中不止一见,与近代以来所说的“新诗”“新体诗”所指完全不同。相对于“古诗”,唐人多称“近体诗”为“新诗”,郁达夫《诗的外形》中录引褚厚之《投节度邢公》,其中有句“一卷新诗满怀泪,频来门馆诉饥寒”,杜荀鹤《辞九江李郎中入关》有句“卷许新诗出,家怜旧业贫”。其实,类似的用法,六朝文献中就不止一见。
[1]胡适.谈新诗[J].星期评论(双十节纪念号),1919-10.
[2]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周作人.少年中国[J].1921,2(11)//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4.
[4]周作人.神话与传说[N].晨报副镌,1922-6-26.//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5]周作人.论小诗[N].晨报副镌,1922-6-21.//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713-720.
[6]周作人.新青年[J].1921,8(5).//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 [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2-53.
[7]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宗教与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7.
[8]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文艺的讨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5-66.
[9]周作人.诗的效用[N].晨报副镌,1922-2-26.//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700-703.
[10]周作人.文艺的统一[N].晨报副镌,1922-7-11.//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77-78.
[11]周作人.旧梦·序[N].晨报副镌,1923-4-12.//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732-734.
[12]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N].晨报,1920-1-8.//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45-46.
[1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N].晨报副镌,1922-1-22.//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3.
[14]周作人.致俞平伯[J].诗,1922,1(4)//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706.
[15]周作人.情诗[N].晨报副镌,1922-10-12.//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723-726.
[16]周作人.题魏慰农先生家书后[N].//夜读的境界[M].1933: 694.
[17]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J].1918,(5)6.//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31 -35.
[18]周作人.艺术与道德[N].晨报副镌,1923-6-1.
[19]周作人.《秉烛后谈》序[N].//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 [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353.
[20]周作人.征求猥亵的歌谣启[N].//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58-562.
[21]周作人.国语文学谈[N].京报副刊,1926-1-24.
[22]周作人.死文学与活文学[N].大公报,1927-4-15.
[23]周作人.旧梦序[N].晨报副镌,1923-4-12.//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732-734.
[24]周作人.《现代散文》序[N].//苦茶随笔[M].
[25]周作人.苦口甘心[J].艺文杂志,1943-11,1(5).//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157.
[26]周作人.扬鞭集序[J].语丝,1926-6(82).//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739-741.
[27]周作人.骆驼祥子(日译本序)[M].//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31.
[28]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M].
[29]周作人.绍兴儿歌述略[M].
[30]周作人.古文学[N].晨报副镌,1922-3-5.//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367-369.
[31]周作人.一岁货声[N].1934.//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 [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19.
[32]周作人.文学史的教训[N].//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 [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473-479.
[33]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N].//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 [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747.
[34]周作人.歌谣[N].晨报副镌,1922-4-13.//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25.
[35]周作人.《潮州畲歌集》序[J].语丝,1927-4(126).//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68.
[36]周作人.《江阴船歌》序[N].//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 [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59.
[37]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前言与后记[N].1944-9-10.//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30.
[38]周作人.小河[N].//周作人文类编:夜读的境界[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29-631.
[39]周作人.《老虎桥杂诗》题记[N].//周作人文类编:夜读的境界[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34-635.
[40]周作人.中国戏剧的三条路[J].东方杂志,1924-1,21(2).//周作人文类编:花煞(卷六)[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531-532.
[41]周作人.做旧诗[N].晨报副镌,1922-3-26.//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三)[M].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704.
[责任编辑 陈浩凯]
The Properties of Poetry and the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Zhou Zuore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MENG Z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Among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Zhou Zuoren was the first one to have come out of the conflicting binary arguments that cancelling each other,such as Ancient and Vernacular Chinese,Old Literature and New Literature,Old Poetry and New Poetry,Loc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He was also the earliest advocator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or of"new poetry",to transcended the purely enlightenment standpoint.His interpretations and sorting ou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New Freedom"and" New Restraint"in Chinese poetry,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goodness"and the nature of"beauty",especially the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Chinese poetry,are still of great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Zhou Zuoren;new poetry;national language;freedom;tradition
I207.25
A
1672-934X(2014)01-0067-09
2013-10-29
孟 泽(1963-),男,湖南双峰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闽南师范大学文化诗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
——探析文类与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