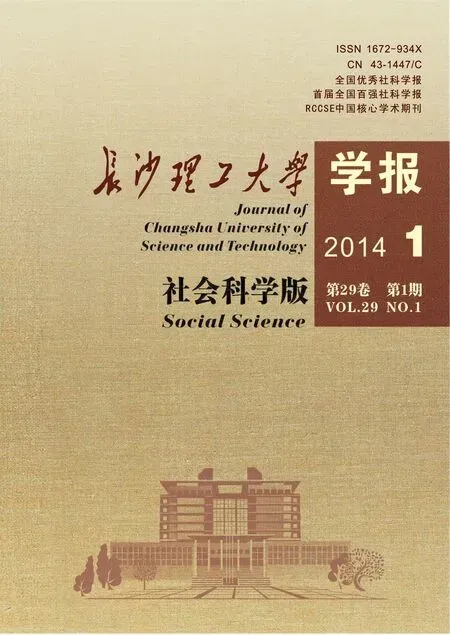存在基于自然种类词的后验必然真理吗?
文贵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存在基于自然种类词的后验必然真理吗?
文贵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克里普克与普特南根据严格指示词的理论,认为有关自然种类词与科学上的摹状词是严格指示词,它们之间的同一陈述乃是形而上学的必然真理。文章通过具体分析表明,自然种类词与科学上的摹状词都不能被认为是克里普克-普特南意义上的严格指示词,因此,不存在基于自然种类词的后验必然真理。
自然种类词;严格指示词;真理;同一性
1970年代以来,克里普克(S.Kripke)与普特南(H.Putnam)各自独立地发展了一种被称为“科学本质主义”(scientific essentism)的哲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种类词(natural kind term)像专名一样(不同于有关人造物的语词),是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它们的用法则是严格指示性用法。具体到实例,水就是H2O,黄金就是原子序数是79的那种元素形成的单质;而对于生物例如老虎或者柠檬,则它们同一于刻画了它们基因结构(DNA)的理论术语。对于严格指示词之间成真的同一陈述,则其在形而上学上必然是真的。这样的观点合理吗?
一、克里普克与普特南的基本观点
上述理论在克里普克那里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命名与必然性》以及论文《同一性与必然性》中;在普特南那里主要体现在《“意义”的意义》以及《语义学是可能的吗?》。克里普克在模态逻辑方面的研究成果世所瞩目。他关于专名方面的理论来源于他对模态逻辑的研究[1](绪言P3)。而模态逻辑中的这样一条定理在他的关于后验必然真理的理论中具有中心地位:(x)(y)[(x=y)→□(x=y)],它可以解释成:“对于每个x和y,如果x同一于y,那么x同一于y是必然的。”[2](P362)基于此,他一反分析哲学传统内的主流观点,认为专名不等于一个或一簇摹状词,提出了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全新观点。按照他的说法,“我的固定指称记号意谓着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记号在一切可能世界内指称同一对象。”[2](P372)在《命名与必然性》里,他也解释了,“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克里普克讨论了下面三种不同的命题:(1)同一的对象必然是同一的;(2)严格指示词之间成真的同一性陈述是必然真的;(3)在实际语言中所谓“名称”之间成真的同一性陈述是必然真的。[1](绪言P4)我赞同克里普克的看法,命题(1)与(2)都是自明的论题。当然命题(2)相对于命题(1)稍弱,因为如果考虑到在某些可能世界中对象可能不存在的话,它的严格性值得推敲。不过,与克里普克一样,我们对这一点姑且不论。我所不能同意的是命题(3)。因为它的前提条件-克里普克认为通常所谓的专名就是严格指示词的观点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注意,他理解的专名就是日常意义上的专名,例如,他说,“我们规定,‘名称’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名称,而不是罗素的‘逻辑专名’。”[1](P6)克里普克声称“日常语言的名称是严格指示词这种自然的直觉其实是站得住脚的”[1](绪言P5)。克里普克用了黄金做为例子来说明这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普特南称之为逻辑的必然性[3](P57)):黄金是一种原子序数为79的元素,这一点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我们还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进一步研究颜色和金属特性是怎样从我们所发现的黄金这种物质中得出的。就这种性质是从黄金的原子结构中得出的而言,它们是黄金的必然性质,即使它们毫无疑问地不是“黄金”这个词的意义的组成部分,而且不是以先验的确定性来被人认识的)[1](P103)。
普特南也独立的从语义学研究得出以上结论。不过普特南不太关心专名的问题,也没有去论述因果历史的命名理论。普特南主要关心的是自然种类词的意义,“不过,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的兴趣不在必然真理理论,而在意义理论。”[4](P473)早在《语义学是可能的吗?》中,普特南就对传统语义学提出了质疑,对意义理论缺乏进展不满。他批判了传统观点,认为“说某物属于一个自然种类仅仅是将性质的一个合取归属于它”[5](P591)这种说法恰恰是假的。以柠檬为例,普特南指出:
“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柠檬’的意义可以通过详细说明一个性质的合取来给出。对于这些性质中的任何一个而言,‘柠檬具有性质P’都是分析真理;而如果P1,P2,……,Pn是该合取中的所有性质,那么‘任何具有性质P1,……,Pn的东西都是一个柠檬’,也同样是一个分析真理。”[5](P591)
当然,普特南这里质疑的性质指的是表观性质,如柠檬的色黄、味酸、果实形状等等。他认为这种思想的错误在于这样的性质合取根本不是分析真理。普特南指出,这种考虑遇到的最明显的困难就是自然种类可以有非正常成员。按照他的理解,一只三条腿的虎仍是虎,在这点上蒯因对分析性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对自然种类词的意义问题,他严厉地批判了基于表面性质的操作定义,认为非另辟蹊径不可。在著名的“孪生地球”论证中,普特南认为,具有无色、透明、解渴、充满江河湖海等与水一样的表面特征的液体XYZ其实并不是水,因为其微观结构不是H2O:
“你所描述的那个可能世界,不是一个在其中‘水是XYZ’的世界,而是一个在其中湖泊充满XYZ,人们喝着XYZ(而不是水)的世界。实际上,一旦我们发现了水的本质,就不可能有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水不具有这种本质。一旦我们发现水(在实际世界中)是H2O,就不可能有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水不是H2O。特别是,如果一个‘逻辑上可能的’陈述就是一个在某一个‘逻辑可能世界’中能够成立的陈述的话,‘水不是H2O’就不是逻辑上可能的。”[4](P472)
普特南的意思是,既然现实世界中水是H2O,那么,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世界,水不是H2O就不是可能的。按照模态对当关系,“水不是H2O不是可能的”等价于“水是H2O就是必然的”。普特南与克里普克两人分别经过独立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过,普特南似乎不太强调必然真理,较少正面论述它。从他对水与黄金的论述看,他比较强调样本在原初固定自然种类词的指称时所起的作用。另外,他强调语言的劳动分工,指出,对每一个语言共同体,都至少存在一些词汇,与之相关的标准只有少数专家才掌握[4](P466),这和克里普克不太一样。
二、自然种类词是否是严格指示词
像水、黄金这样的自然种类词真是严格指示词吗?克里普克与普特南当然会回答是。但是,如何判断我们要对之作出陈述的两个样本是否是同一自然种类呢?同一性到底有没有判定依据?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对他来说,或许这个问题显得多余。他的思考其实是以公理(x)□(x=x)为出发点,同一个对象必然同一于自身。无论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里,同一个对象不可能不同一于自身,否则,那就会是不同对象了。无疑,这种说法在形而上学上是成立的。对克里普克的这种观点,普特南作出了一个解说:
这恰恰相同的东西(the very same)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克里普克说-‘=’在逻辑里所精确意味的事物。它意味着同一性(identity)。克里普克声称,同一性是一个初始的逻辑概念(notion),认为它能够或者应该被解释则是一个根本的哲学错误。[3](P66)
但实际上,克里普克还是用到了一定的标准。以水为例,他指出: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物质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例如据称在苏联所发现的高聚水(Polywater),它具有与我们现在称之为水的东西非常不同的识别标志-那么,它也是水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是同一种物质,即使它不具备我们最初用来识别水的那些外貌特征。[1](P107)
克里普克的意思还是求助于物质组成,“因为它是同一种物质”。既然化学成分(在这里作为H2O)一样,不管该物质表现出的其他特征相差多大,总还能称为水。普特南则说得更翔实一些,把“具有相同的物理化学组成且服从相同的规律”作为物质(substance,实体)同一性的标准[3](P60)。他本人在《“意义”的意义》中主要求助于物质结构,使用的术语是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而在《水必然是H2O吗?》中,他用了显微结构(subvisible structure)这个术语。但这样就能够充分地保证物质同一性了吗?
我们所熟悉的水,其实里面就含有好多种不同的化学成分。氢有三种同位素,氧稳定的同位素也有三种,细分下来H2O其实有十八种之多。在今天可以视为由同一种成分构成的水,也许将来会被视为由不同成分构成的。例如,水中所含的氘能够作为核聚变原料,如果人类能够解决核聚变可控利用问题,大量分离水来提取氘作为核聚变的原料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人们并不是没有这样做过)。这种情况下,水就很难被视为是一种物理化学性质均匀的纯净物了。毕竟,如果水的物理性质完全均匀,那么电解或者蒸馏提取重水就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在其他领域,如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医疗诊断等领域,同位素示踪法应用颇为广泛,这说明,物质成分能否被认为是同一的,很大程度上约束于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普特南曾举出铁的例子论及同位素并强调这没有影响,他说他的讨论把科学限制在高级中学程度。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与古代人把鲸视为一种鱼的做法并没有根本区别,因为那毕竟也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阶段。科学本身的发展很难停留在某个阶段,利用科学的某一发展阶段来固定认识是不可取的。
而且,存在一些物质名词,其本身似乎不需要什么隐藏结构,需要的只是表面特征。比如鹅卵石(pebble)与砾石(gravel),汉语与英语中都不要求其有什么隐藏结构。形成鹅卵石或砾石的母体岩石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基本上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形状与大小。对于鹅卵石来说,只需要它们具有一定的形状(棱角磨平、边缘滑溜)与大小(太小的可能被称为砾石,大到一定程度的pebble在英语中被称为cobble,而汉语中没有对应的专门术语)要求。这种情况下,自然种类词就很难说是具有严格指示性了。其实,普特南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坦承存在表面特征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名词,例如他自己举出的玉的例子[4](P482-483)。但这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丧失彻底性了。
应该承认,按照科学发展的趋势而论,普特南要求根据科学来进行精确区分的观点确实不无道理(但不要停留在某一阶段,应该保持开放性)。总的来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的区分越来越细致,这是一个事实。譬如,人类目前已经制备出来的有机物早已超过一千万种,科学当然要求能够详细地区分它们。这也反映在日常语言中,人们要求愈来愈细致地区分事物。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存在一些相反的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反而把本来精确区分的事物认作是同一的了。下面我们来看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他的《语言和人》之《语言的社会学考察》中对中国古代对马、牛、羊的汉字的一些讲解。他指出,用“牛”作偏旁的字数目粗略估计有:《汉语大字典》329个、《康熙字典》228个、《辞海》59个、《词源》54个,而《现代汉语词典》与《新华字典》均只收46个,而《常用字表》仅收8个。陈原总结到,“首先,古代社会对不同年龄的牛,都给创造一个汉字(碍于计算机字库仅收常用字的限制,在这里我们无法列出这些字-引者注);换句话说,不同年龄的牛各自形成一个概念,对每个概念都给一个代码”;“其次,各种不同色泽的牛,也都有一个代码……可见古代汉人祖先对牛辨得很细,每一个不同的概念都给出一个特殊的符号来”[6](P93-94)。“至于公牛,母牛,小牛,阉牛,水牛,各有其不同的代码,这就更不言自明了”。但是,现代汉语里,这些字绝大多数都已经死亡了(其实,“五六百年前或者甚至七八百年前的学者早已不认得这些字了”[6](P91))。
根据陈原的考查,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断,当古代(比如2000年前)汉语的使用者们面对着三岁的牛A与四岁的牛B时,大概不必认为其是同一种类的牛,否则也没有必要以不同的概念来称呼它们了。而我们现代人面对着这些牛时,固然会在个体意义上承认他们是不同的牛(就像张三与李四是不同的人一样),但我们恐怕很难认为那是两个种类有别的牛。我们可以认为,日常语言中关于马、牛、羊等动物的分类原则并不能照搬生物分类学上的“门”、“纲”、“目”、“科”、“属”、“种”、“亚种”的分类谱系。相同与不同的界限的划定应该是由语言共同体确定的,可以说是内在于语言共同体的,而不能以无限精确界定的“上帝的眼光”来划定;而科学固然对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有着强大的影响(主要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但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科学所划定的界限当作唯一标准,而且,科学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对于这一点陈嘉映先生评论到:“我和普特南的区别在于,他认为科学指称是一种更优的指称,而我则认为那是一种不同的指称。”[7]
三、科学上的摹状词是否是严格指示词
像H2O、Au(黄金)这样的科学术语实质上是缩略摹状词。H2O指分子式是H2O的纯净物,Au则指原子序数是79的那种元素形成的单质。这样的摹状词是严格指示词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艾耶尔(A.J.Ayer)在他的《二十世纪哲学》结尾处构思了一个思想试验来反驳普特南的看法:
让我们设想,在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里,我们遇到了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具有H2O的化学成分,但却没有下雨、止渴、灭火等等性质,那么我当然不能把它称之为“水”,而且如果大多数讲英语的人也这样看,我就感到惊奇。[8]
如果同样由H2O组成的物质居然表观性质差别很大,那它还是水吗?普特南在《水必然是H2O吗?》中作出了回应,“这是可想象但不是可能的”。他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发现由同一成分组成的物质能够服从不同的规律,那么我们的整个世界图景-不仅是我们的哲学-将要被修正。”[3](P325-326)他的意思是,既然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物质组成决定着物质行为,那么我们去假设一个在其中物质组成不决定物质行为(就像艾耶尔的思想实验中的例子)的可能世界,这样做是没有依据也是不必要的。如果实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克里普克会同意那种物质是水。但他自己认为这种情况乃是一种在其中答案会成为绝对任意的那种问题情境[3](P325-326)。简单的说,普特南认为那样的一个世界不是可能世界,他事实上预设了世界的齐一性前提。
即使我们同意普特南的这种预设,也仍然可能存在问题。科学上指称物质的摹状词保持着开放性,可能会指称多种物质。拿黄金(符号Au)作为例子,虽然地球上黄金只存在一种天然核素,即197Au,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很稳定,但是黄金存在数十种不稳定的人工核素。其中的195Au相对稳定一些,半衰期长达186天,另外还有几种半衰期长达数天的人工核素。也许在宇宙中某个不知名的星球因为种种原因会不断的产生天然的195Au,这应该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我们会把这种物质当作黄金吗?我想不会,即使不考虑它的衰变产生的放射性对人体的危害,仅仅在金融意义上就不成立了。试想一下,假如某个人花大价钱买了一些这样的“黄金”,在家保存才半年,这些“黄金”就已经衰变得几乎只剩下一半了,没有人会愿意承受这样的经济损失。那么,195Au恐怕并不会被视为“真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除了说“真金不怕火炼”以外,恐怕还会说“真金不怕久放”。而这样一个世界在自然规律方面并没有任何不同于我们现实世界的地方。
再来看一个例子。SiO2(二氧化硅)作为自然界极广泛存在的物质,能够形成多种不同物质,人们是逐渐认识它们的。例如不纯的二氧化硅就是沙子,比较纯净的形成石英(quartz),纯净透明的石英就是水晶(可以含有微量杂质带上颜色)。它们虽然在化学性质上几乎没有差异,却可能因为晶体构造差异导致其物理性质差异较大。可是按照克里普克的说法(见前面所引的他评论高聚水的例子),会把它与普通石英视为同一种物质。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各种同分异构现象。同分异构体中因结构不一样会造成物理化学性质相差很大的构造异构(structural isomerism)现象(例如乙醇与甲醚)。即使同样的分子结构,也可能因存在空间构型的差异而形成立体异构(stereoisomerism)现象,比如常见的手性异构(chiral isomerism)现象。手性分子虽然差异很小(在空间结构上具有镜像性而不能完全重叠,就像左右手的差别一样),但这对地球上的生物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绝不能简单地视为相同。构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除了无手性的甘氨酸外,都是左旋的。地球上仅仅原核生物体内存在一定的右旋氨基酸。而立体异构中的构象异构(conformational isomerism)形成的分子差异则极小,对物理化学性质可以认为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是依赖于我们目前的科学认识来看的。也许将来,我们会认为具有不同构象异构的分子有着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这绝非不可能的。毕竟,人类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手性异构的。
所以我们认为,科学上的摹状词所指称的对象是内在于一定阶段的特定科学理论的,未必不能接受修改或修正,它们并不是绝对的严格指示词。当然,我们可以考虑承认,它们受修正的可能程度还是有差异的。
四、结论:扩张解释的失败-不存在基于自然种类词的后验必然真理
本文的结论是不存在关于自然种类的严格指示词,也根本没有有关自然种类词的形而上学(或逻辑)意义上的后验必然真理。
考虑克里普克与普特南两人的失误之处,笔者觉得主要在于他们作出了扩张的解释。科学上的摹状词如H2O仅仅反应了一定阶段的科学对世界的认识。但是,科学是持续发展的,今天的科学理论难保不在以后被推翻(虽然完全推翻的可能性小,但却很可能被修正)。施太格缪勒也指出:“根据我的观点,事情甚至还要复杂些,因为科学的进步是会分支的;因而也不能排除‘指称分支’的可能性。”[9]说“水是H2O”或“黄金是原子序数是79的那种元素的单质”不过是反应了化学的某种认识。即使同意一切可能世界都遵循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自然规律,这种认识的必然性强度还是最多与物理学里面的陈述“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的相当,依我看,还不一定。但很明显,物理学(或化学)里的必然性并不能代替形而上学的(或逻辑的)必然性。如果说存在严格指示词,那也是像“25的非负平方根”与“3加2”之类非经验表达。的确,25的非负平方根同一于3加2是必然的,但这并非后验真理。但如果说,克里普克或者普特南所声称的形而上学必然性或逻辑的必然性实际上不过是物理的必然性而已,这就意义不大了。毕竟,物理学或化学早已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知识,似乎不需要哲学家再来告诉我们一遍。如果他们所要指出的,仅仅是形如“如果x物质的确是y物质,那么,x物质同一于y物质就是必然的”这样的逻辑表述的话,那就仅仅是空洞地套用模态逻辑定理(x)(y)[(x=y)→□(x=y)]了。的确,“如果水是H2O,那么水同一于H2O是必然的”这话并没有错。但是,类似的模态陈述“如果大象是老鼠,那么大象同一于老鼠是必然的”自然也没有错,虽然我们明知该命题的前件是假的。关键问题是,自然种类词也好、科学上的摹状词也好,都会涉及到经验世界。而处理涉及经验内容的命题时,我们没法确保这个模态定理的前件绝对为真,这与25的非负平方根同一于3加2这种情况不一样,后者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内容。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根据科学理论可以使前件近似为真,但这样的近似性也无法确保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后验必然真理。
[1]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梅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2]克里普克.同一性与必然性[A].//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C].涂纪亮,编.北京:三联书店,1988:362.
[3]Putnam H.Is Water Necessarily H2O?[A].//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C].James Conant,ed.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4]普特南.“意义”的意义[A].//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C].陈波,韩林合,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普特南.语义学是可能的吗?[A].//语言哲学[C].马蒂尼奇A P,编.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陈原.语言和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6.
[8]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李步楼,俞宣孟,苑利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08.
[9]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M].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30.
[责任编辑 陈浩凯]
Is There Any Necessary A Posteriori Truth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Kind Terms?
WEN Gui-quan
(Graduate School of CASS,Beijing 102488,China)
Saul Kripke and Hilary Putnam present an viewpoint with the theory of rigid designator that the identity statements about natural kind terms and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are metaphysically necessary truths since they are rigid designators.With an analysis in detail,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both the natural kind terms and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could not be treated as rigid designators in the meaning of Kripke and Putnam.So,there is not any necessary a posteriori truth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kind terms.
natural kind term;rigid designator;truth;identity
B815.1
A
1672-934X(2014)01-0026-05
2013-11-06
文贵全(1980-),男,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