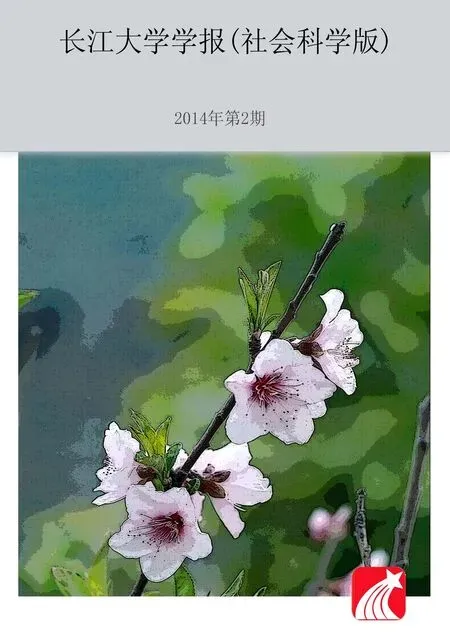从王尔德唯美艺术观看其童话中唯美的死亡①
祝传芳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童话的读者主要是孩子,但王尔德清楚地指出,“现在在写的《石榴之家》,我想像取悦孩子们一样取悦英国公众”[1](P113)。 因此,王尔德的童话故事有一定的独特性,读者须在两个不同的方面理解童话故事——孩子们的纯洁美丽的故事和一种直抵成人世界的精神漫游。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充满了明显的想象力,但对于孩子们来说,理解作家对贫穷、不公、苦难和死亡的诸多描述是困难的。王尔德试图逃离现实樊笼,希望在艺术中追求真善美。因此,在王尔德的童话故事中,很多角色只能在死后获得幸福、美丽和永恒的生命。从这一点上说,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是唯美主义的反映和实践。童话是表达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最适当的形式,或者说王尔德童话中唯美的死亡最能完美地表现他的唯美主义艺术观。
一、“艺术除了表现自身,不表现任何东西”——美而不真实的死亡
在王尔德看来,艺术家应该是一个骗子,应该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应该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却能写出迷人的游记的人。[2](P185)因此,在王尔德的童话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金属做的快乐王子,因爱上芦苇而错过飞往南方的燕子,努力送走灵魂的渔夫。这些都是虚构的、浪漫的。对于王尔德而言,童话创作是通过想象力来创造唯美的存在,它们越与现实保持距离,越能让人感受到美。王子和燕子死于爱和仁慈,他们帮助贫穷的母亲和生病的孩子、可怜的作家和卖火柴的小女孩。渔夫爱上年轻漂亮的美人鱼,但必须满足美人鱼失去灵魂的要求,在故事的结尾,他亲吻着嘴唇冰冷的美人鱼,然后走向死亡。在《自私的巨人》中,在神的指导下,巨人改正了缺点,但仍然死在美丽的花园。在《星孩》中,星孩经历那么多苦难,最后还是死了,这些死亡是如此的让人难以接受,人们不得不思考他们死亡的真正意义。其实,他们的死亡正是反映了艺术的自我性——艺术只表现自身,其审美情趣从不因为世俗道德而改变。死亡的结束打破了快乐的结局。所有死亡的描述显现出王尔德的艺术观点:“艺术除了表现自身,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3](P942)这种独特的唯美的死亡可能不被生活接受,但是艺术家不会只是因为公众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就改变写作。所有的人物都冰冷地死去,使读者不得不去考量、欣赏美丽梦幻叙事背后的这些美则美矣却不真实的死亡。而恰恰通过这种方式,王尔德强调了死亡的意象,让人们认识到只有死亡才能触摸到真善美;只有通过努力改变丑陋的现实生活或打破现实枷锁,人们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美和艺术的本质。王尔德的童话经常塑造大量优雅、美丽和诗意的人物,并通过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糅合到适当的情景中,从而形成唯美的画面,最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以死亡为结局,这使得死亡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他是想先通过唯美的叙述形成唯美的画面,然后再摧毁这种美丽,以加深死亡的悲剧效果,旨在坚持他的唯美主义的艺术创作。读者震惊或无法理解这些唯美的死亡,在王尔德看来并不重要,艺术家创造美的东西,不需要关注读者的观点或一定要准确表达现实。他认为艺术家应追求更具创意的艺术之美,他拒绝现实的平庸和琐碎,认为这些只能让人们讨厌,并不足以激发对美好事物的幻想。尽管唯美的死亡看起来是如此的美丽而不真实,但它真的可以存在于艺术世界。艺术是独立的,而不是模仿的。
二、“生活模仿艺术”——理想化的死亡
王尔德最原创、最具颠覆性的文学理论就是强调生活模仿艺术。在他看来,艺术有能力创造生活,并且有一种天生的模仿本能。死亡在王尔德的童话故事中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实际上,它不仅是表达一种艺术观点,还是王尔德指导现实生活的工具。通过描写人物的死亡,王尔德使这些死亡成为唯美的象征,这样就可以吸引和教育读者。快乐王子和小燕子因为帮助穷人而死,人们忽视了他们的善良,但神却将他们引入天堂。在王尔德的眼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善良和同情而死是一种理想的死亡——死者最终进入天堂,他们的死亡反映了唯美主义的观点。他们的善良和对爱的执着追求正是王尔德追求的目标。“白天,我和我的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晚上我在庭院里跳舞。我从来不去想背后还有什么。”[3](P318)这反映了快乐王子死亡之前对贫困和社会不公的冷漠。“现在我死了,他们把我竖这么高,我可以看到所有的丑陋和所有的痛苦。”[3](P318)这揭示出他死后发现了这一切。“我们所认为的现实,总是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可靠感,事实上它是非常脆弱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打破。”[3](P969)但快乐王子不放弃追求真正的幸福,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和燕子牺牲了自己,因为他们伟大无私的爱,天使带他们去了永恒的天堂,这恰恰意味着真正的幸福。通过这个故事,王尔德想告诉读者快乐王子和小燕子的死亡是高尚的。对唯美主义者来说,高尚的事物才是真正的美。快乐王子和小燕子这种理想的死亡可以为现实生活提供一些榜样,反映了艺术美可以间接纠正丑陋的现实。在《夜莺与玫瑰》中,夜莺唱“爱肯定是一件美妙的事,它比翡翠更珍贵,珍珠和榴石都买不到,他不是陈列在市场上的”[3](P327)。这种强烈的对比表明,在夜莺的眼里,爱是胜过一切的,也是值得永久珍惜的。它还表明,王尔德认为艺术比虚假、丑陋的现实更有价值。因此,当年轻人渴望得到爱情的红玫瑰,夜莺牺牲了自己。红玫瑰不仅是纯爱的象征,也象征着王尔德心中永远追求的至高无上的艺术美。夜莺为了追求至美的爱情,付出了生命。可以说,夜莺追求的就是美好的理想。夜莺的死是理想化的死亡,体现了王尔德追求美的理想和为现实生活苦寻指导的愿望。童话故事的最后,女孩觉得“和我的衣服配不上……而且御前大臣的侄儿送了我一些上等珠宝,谁都知道珠宝比花更值钱”[3](P331)。这表明,夜莺歌颂的纯洁爱情变成了只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的游戏。“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实现完美;同样,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抵御现实存在的可鄙的危险。”[3](P995)王尔德再次表明,丑陋的现实生活是不能容忍的,现实生活必须接受艺术的指导。尽管夜莺死了,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唯美的理想化死亡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深深的震撼,为人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从而达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鼓励人们去追求美,艺术应该指导生活,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动力,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一方面,角色们死后入天堂,意味着真正的美是独立于虚假的现实的,爱、善良和无私在现实中是脆弱的。只有在艺术中,这些东西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如此多高贵的灵魂为寻找永恒的美和智慧不惜牺牲生命,这种理想化的死亡因带有明显的道德和伦理的色彩而成为唯美的死亡。艺术的美可以间接纠正丑陋的现实,也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这不仅仅是生活的模仿本能,也因为生活的目标就是找到表现自身的方式,而艺术则为它提供了特定的美丽形式,让它得以实现。”[3](P46)
三、“艺术应当远离生活”——建立艺术乌托邦
如果说“艺术除了表现自身,不表现任何东西”反映的是艺术的自主性,“生活模仿艺术”反映的是艺术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艺术应当远离生活”则反映了艺术的独立性和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建立艺术乌托邦。王尔德认为艺术追求的是美而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快乐王子、少年国王和星孩如果生活在现实中的话,他们是很难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残酷的。而对于小汉斯、渔夫和小矮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死只是不用再挣扎求生罢了。但在王尔德的童话中,他们的死无一不是意义非凡的,无一不是在追求真善美。这恰恰表明王尔德的写作宗旨——艺术就是生活,是绝对的真理,对现实漠不关心。艺术使每个人的生活成为一种神圣,而不是反映,艺术使人生命不朽。也只有在王尔德的童话中,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这些人物形象才有了自我的意识和灵魂,才有了追求美与善的理想。他们的死亡才会如此的崇高、伟大和有意义。王尔德希望以艺术所营造的美的生活来构造理想化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如同宗教一般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一旦将其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理想的幻灭给人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弥补的。也就是说,王尔德在他的童话创作中,运用人物别具一格的唯美的死亡突破了传统童话模式和19世纪末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的束缚,试图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建立艺术乌托邦,以对抗庸俗市侩的现实生活。在这样一个脱离现实的艺术世界里,艺术家的自我得以强化和重建,艺术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具有最高品质的生存空间。正如王尔德所说:“谎言是有意识地掩盖真相,与现实保持距离,它更能得到艺术的精髓。”[3](P943)实际上,王尔德试图建立乌托邦的意义也不在于现实层面的实际操作,不在于它能否得以实现,而在于它对思想壁垒的挑战,对思维局限的超越,对想象力的张扬和对矛盾的揭示。[4](P23)乌托邦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拒绝和抗争、一种追求超越的激情。
四、结语
总之,在王尔德的童话故事中,绝妙的想象力和冰冷的死亡彼此和谐统一,这些死亡体现了美与丑、好与坏、生与死的矛盾,揭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强烈抗争的意图。也正是这些关于死亡的描写把王尔德的童话和传统童话区别开来,从而体现出他对传统艺术观的挑战。从这一点来说,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是唯美的死亡,这些唯美的死亡反映了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体现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人生观和艺术观 ——“唯美主义从来不在‘真’中求理想,而是以想象为媒介,把经验的事物转化为审美的存在。也就是在美和艺术中求理想,此所谓唯美是也。”[5](P103)在王尔德的童话故事中,浪漫的童话不再只有美丽的想象和快乐的结局,还揭示了丑陋和残忍,隐含着深层次的唯美主义意识。童话中对死亡的描述既能满足稚拙而富有想象力的儿童的心理需求,又能触动饱尝人生风雨的成年人的心境,体现了王尔德对终极美的追寻、对唯美主义思想的不断实践。
参考文献:
[1]Karl,Beckson.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0.
[2]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3]Wilde,Oscar.The Collected Works of Oscar Wilde[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7.
[4]李元.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张介明.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