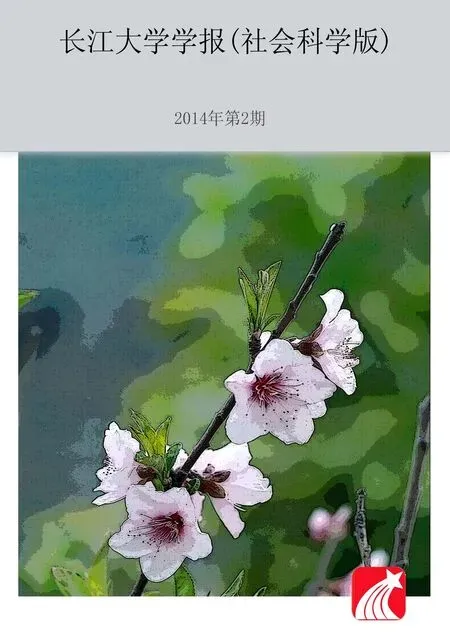楚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读徐文武教授新著《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
谭宝刚
(贵州民族大学 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25)
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大型学术丛书“世纪楚学”(12部)是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同时也是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该丛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新世纪楚学研究的面貌,是楚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该丛书中收入了徐文武教授的专著《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该书采取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引用了翔实的资料,尤其是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论证逻辑严密,观点颇为新颖,在这套丛书中极有分量。
徐文武教授在2003年曾出版过一部《楚国思想史》,在学术界引起过一定的反响。近10年来,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特别是一批楚简内容的整理发布,很多《楚国思想史》中的学术观点在《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被重新阐释。第一楚国为先秦时期南方思想与学术中心。第二楚国思想与学术的主流根柢是商、周王朝正统的王官之学。徐文武教授在引用了大量的战国楚简材料后指出:“楚国思想与学术的主流是与中原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这是完全不同于过去学界强调楚文化地域性特点的观点。第三儒家思想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徐文武先生指出:“儒家思想理应归入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中。”这是对过去“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归入楚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的新论。20世纪80年代,楚学大家张正明将楚文化的核心构成归纳为“六大要素”,也称为“六大支柱”。在“六大要素”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作为楚人在思想领域的最高成就,归入楚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然而,在出土的楚简中,儒家文献占据绝对的优势,道家文献并不多。仅从出土文献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儒家文献与道家文献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反映出了儒家和道家在楚国主流思想构成中所占比例的实际状况,从一个方面证明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道家思想居于其次。基于以上事实,作者提出关于楚文化核心构成的新观点:“既然儒家思想在楚国主流思想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那么,儒家思想理应归入楚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中。”作者主张把楚文化“六大要素”中“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改为“儒家和道家的哲学”,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在思想文化层面,中原思想文化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对楚文化所进行的渗透,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上述三点认识,尤其是后面二点非常有创见性。
《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除了观点颇为新颖外,还采取了全新的研究视角,逻辑严密,结论令人信服。作者继承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充分利用最新出土材料,把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典籍结合起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信度高。其一,在该书第三章“子张氏之儒在楚国的传播”中,作者在论述郭店楚简《忠信之道》和上博楚简《从政》为子张氏之儒的作品时,就从思想的一致性和语言的相沿性等方面与《论语·卫灵公》、《论语·子张》以及《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等三篇传世典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这两篇楚简都是子张氏之儒的作品的结论,非常有说服力。其二,该书在第三章中论述《诗、书、易的南传》时,也采用了相同的论证方法。在论述《易》的南传时,作者讨论了先秦时期易学在楚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并将帛书《易传》中提到的易学弟子与楚王族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得出易学在楚国贵族阶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结论,公允可信。其三,作者在论证“重生与贵民”时, 论证层层递进。开始提出“重视生命、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闪光的亮点”观点,然后引用郭店楚简《语丛三》、《语丛一》和传世典籍《孝经》、《孔子家语·六本》以及《荀子·王制》中的相关材料,得出“人为贵的思想是儒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继续阐述“基于‘天生百物人为贵’这一思想,楚简进一步提出了‘人道取先’的治国理念。”接着引用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和传世典籍《易·说卦》、《逸周书·史记》、《左传·昭公十八年》的相关材料,得出“‘人道取先’的价值取向与‘人为贵’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观点。最后作者进一步阐发:“如果说‘人为贵’是‘人道取先’的思想源头的话,那么‘人道取先’则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人道的重视,儒家要求执政者要以民为本,具体做到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与民同心……其二,宽政惠民……”。这样,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述,使论述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和核心领域。全书与此相似的论述至少还有“养性与修身”、“楚系兵学著作钩沉”、“民神同位与民神异业”、“信天命,疑天命,与反天命”和“春秋”是不是先秦各国史书通名的问题的阐发等五处的论述都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此外,在《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一书中,对某些问题的考证虽细小,但能于他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颇显其学术功力之深厚。这样的地方至少有3处。其一,子张“居陈”,实即“居楚”。《史记·儒林列传》载“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作者考证“子张居陈”的时间应在前476年之后,而公元前478年,楚公孙朝率师灭陈,此后陈国成为楚国的陈县,不再复国。由此看来,子张所居之陈,已非陈国,而是楚国陈县。由此得出子张“居陈”实即“居楚”的结论。子张“居陈”实即“居楚”最易为学者因不清楚而弄错,但对作者在论述“‘子张氏之儒’在楚国的传播”却极为有用。徐文武先生发现了它的价值,考证了子张“居陈”,实即“居楚”,从而为“‘子张氏之儒’在楚国的传播”做了很好的铺垫。 其二,疑《论语·尧曰》之“有司”,原为“贪”字讹误。上博楚简《从政》篇内容涉及从政的道德及行为标准,其中有“四毋”,即从政的大忌“虐、暴、贼、贪”。这“四毋”与传世典籍《论语·尧曰》的前三者相合,但是,《论语·尧曰》不见楚简里的“贪”,而作“有司”:“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与上文文理不合。因此徐文武先生说:“今疑《论语·尧曰》之‘有司’,原为‘贪’字讹误。‘贪’字因误读竖排‘又司’二字,因‘又’通‘有’,又将‘又司’转写为‘有司’,遂致误。另,‘出纳之吝’之‘吝’,本有‘贪’义,《后汉书·黄宪传》李贤注谓:‘吝,贪也。’由此,应据楚简《从政》,将‘有司’改为‘贪’。” 其三,考证楚庄王所提“武有七德”思想中“保大”之“大”应是“土”字,土、大因形近而讹。《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提出“武有七德”思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楚庄王的“武德”思想中,第三“德”是“保大”。“保大”一词,有人望文释义,认为“保大”是“保持强大”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是“安于大位”之意,如《文选·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有“保大全祚”之语,吕延济注曰:“安于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作者认为这两种解释与“武德”不符,“保大”之“大”应是“土”字,土、大因形近而讹。作者引唐黄滔《多宝塔碑记》云:“至如戢兵、保土、安民、和众之类,亦犹川陆之徂秦适洛焉。” “戢兵、保土、安民、和众”即引自楚庄王“武之七德”,“戢兵”之后即作“保土”,而不作“保大”。作者还在古文献中找到了“土”字讹为“大”字的其他例证进行进一步的佐证。如《汉乐府·孤儿行》:“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逯钦立所编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说:“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作者最后对“武德”中“保土”一词的本义作出解释,认为“保土”意即保卫国家疆土,这也是“武德”应有之义。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徐文武先生能在他人熟视无睹处进行学术考证,也是一大创新,颇能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以上是《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突出的优点,其他优点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望读者仔细体会。
——以中共与豫东南枪会关系为中心(1925—1930)
———楚简制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