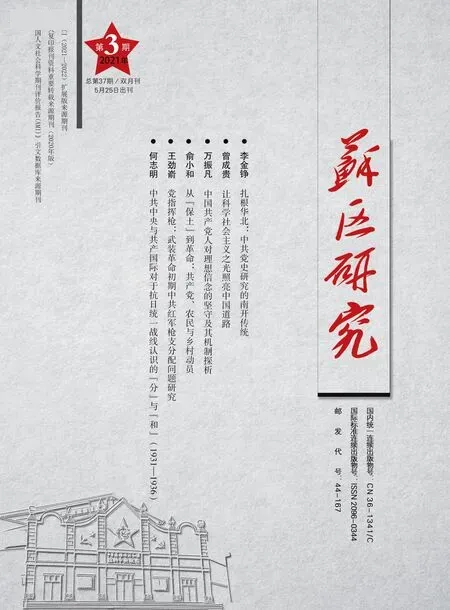从“保土”到革命:共产党、农民与乡村动员
——以中共与豫东南枪会关系为中心(1925—1930)
俞小和
提要:作为民间自卫团体,豫东南的枪会是为抵御军阀与土匪的掠夺,保护乡土而诞生的,带有浓厚的地方传统乡土意识。大革命期间,豫东南党组织与当地枪会上层展开合作,但并未掌握到枪会运动的主导权。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激发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中的革命因子,一方面,以革命枪会凝聚群众,在斗争中逐步以新式革命组织取代传统组织,整合农民,重构乡村的基层;另一方面,挖掘乡村历史中的反抗因子,注入阶级意识,在持续性的内外压力下,实现了农民思想从保卫乡土到阶级革命的转变。在豫东南,中共以传统组织为起点,从结构与思想上实现对乡村的再造与动员,使土地革命带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内涵。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河南枪会运动煊赫一时,(1)当时河南各地有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它们的性质与组织形式比较相近,本文统称为枪会。这些枪会又以红枪会最为普遍,因此当时的中共文件和报刊文章经常以红枪会指代一般枪会,对于“枪会”与“红枪会”这两个词并不作严格界定与区分。在抵御土匪、保卫乡土,以及反抗军阀统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有学者对河南枪会源流及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2)王天奖:《也谈本世纪20年代的枪会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近代河南枪会滋盛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李子龙:《试述红枪会的组织源流》,《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由于枪会本是自卫而生,因此对于河南枪会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的“保土”行为研究的较多。(3)罗宝轩:《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河南红枪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梁福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红枪会的活动》,《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吕书额:《国民军二军与红枪会关系述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3期。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在河南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与地方枪会运动联系密切,相关研究成果相对丰硕。(4)王少卿、朱金瑞:《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枪会的认识和改造》,《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乔培华:《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天门会的认识与争取》,《历史教学》1993年第7期;刘广明:《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河南红枪会的再认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永芳:《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述论》,《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河南枪会也是研究生选题热点,目前已有十数篇相关硕博论文,这些研究基本上以枪会运动兴衰为主轴安排内容,在论及中共与枪会关系时亦是如此。(5)王文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河南红枪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袁岿然:《河南红枪会研究(1913—1953)》,扬州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吕珂:《民国时期的河南红枪会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总的来说,目前现有成果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豫东南根据地发展壮大过程中枪会作用的探讨较少,特别是没有注意到豫东南枪会运动在大革命前后的断裂与承续,以及豫东南党组织在创建苏区时对地方枪会传统的运用。本文探讨了豫东南党组织自大革命后期到土地革命,紧紧抓住了这一反映乡村文化基因与权力关系的关键枢纽,通过联络、改造旧式枪会,创建红色枪会,中共对乡村和农民由隔膜到熟悉,从中掌握了组织动员乡村社会的钥匙,以豫东南的方式,发动与组织农民,再造乡村,掀起了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的高潮。
一、豫东南枪会的起源
关于枪会,学界一般认为起源于八卦教,与义和团、仁义会有某种组织上的传承关系,是一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清末开始在山东、河南秘密流传,具体时间不可考。(6)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在1922年1月,天津《益世报》报道了豫东的枪会,称其“羽党已有数万人”,(7)《豫东红枪会之可虑》,《益世报》1922年1月23日,第7版。到1923年底,即有豫东南固始、光山、息县等地枪会“势极猖獗”的报道。(8)《红枪会满豫境》,《顺天时报》1923年12月3日,第5版。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枪会迅速遍及河南全省,成为普遍现象,其中豫东南地区的枪会运动持久深入,而且在土地革命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缘于当地独特的历史人文和乡村社会结构。
豫东南,主要指今天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因稍偏离于全省的中轴线——京汉线以东,故有此名。清中期以后,豫东南地区长期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之中,捻军起义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次。捻军起于豫皖一带,常在河南流动作战,但豫东南既不是政治重心,也非财赋要地,清廷无心投入过多军事资源,仅多次通令地方士绅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修筑堡寨,训练团练,为此清廷特派团练大臣毛昶熙莅豫举办乡团,“成效卓著”,后“偶有匪患,率仿前制训练乡团以平之,有事则为兵,无事则归农。”(9)方廷汉等修纂:《重修信阳县志·乡团》,汉口洪兴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傍水为“圩”,依山为“寨”。圩寨在不同的地方,又称堡寨、围寨、寨堡、砦。参见牛贯杰:《十九世纪中期皖北的圩寨》,《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因此豫东南各县堡寨众多,“小者容纳数百人,大者可容万人”,这些堡寨建造坚固,多数保留至民国期间。(10)方廷汉等修纂:《重修信阳县志》,第75页。豫东南既有可以固守的寨堡,地主士绅又有办团练的历史传统,这都是枪会兴盛的历史资源,因而台湾学者戴玄之称枪会是“乡团的嫡孙”,是有一定道理的。(11)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商务印书馆(台北)1980年版,第280页。同时,晚清以降,豫东南屡历捻军、白莲教和教案之乱,“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百姓于乱世之中为求生存,不得不经常抱团斗争,形成了地方民众坚忍与强悍的民风。故《光州平贼纪略》载:“河南光州,疆域界处楚、皖之交,面山控淮,民俗狡悍。”(12)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94页。可以说,豫东南民众普遍团结斗争的意识较强,这也是枪会起源的群众民风基础。
豫东南乡村经济结构在河南别具一格。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河南农村土地集中程度并不高,普遍以中小地主为主,但豫东南却是河南大地主比例最高的地方,据调查达到4.08%,如罗山地主吕莘禄、刘楷堂均有田数万亩。(13)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版,第350页。豫东南因河流、大山阻隔,与中心城市相距较远,即使到了清末民初,受外界新思想影响较小,仍是一派传统田园牧歌景色:“富者多文,爱延宾客,气质驯雅,慕义乐善,……安土重迁,不善商贾技艺之事,其富商巨估挟重赀而游四方者,境内不闻其人也。”(14)许希之、晏兆平编纂:《光山县志约稿·风俗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1页。因为从事商业活动的比例小,与城市附近及铁路沿线农村相比,地主士绅乡居者占80—90%左右或更多,明显地高于河南其他地方。(15)曾鉴泉:《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光山》,《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第133页。这样以少数大地主为中心,中小地主与农民共同构成较为稳定的乡村秩序结构;同时,乡居的地主更为关注自身的财产与生命安全,愿意作为“学东”创立枪会,并提供相应的财力支持。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彻底破坏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传统关系。张仲礼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地方绅士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乡绅是政府在基层的利益代表者,政府一般会对绅士给予特别的照顾与尊重。(16)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1914年,在光山箭河附近,农民罗福太、熊润生秘密成立“哥老会”,联络了附近农民,准备将地主程瑞林的粮食分给穷人,“打富济贫”,后因有人告密,罗、熊被官府捉去,受到严刑拷打,后死于监狱。(1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新县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罗、熊之死正是这种合作的体现。
但是在袁世凯死后,河南兵燹不绝,成为军阀混战的主战场。各路军阀你来我往,无不涸泽而渔以养军队,即使地主士绅的财产也不得保全,国家权力与乡绅的这种默契关系不复存在。吴佩孚督豫时,豫南地亩附加捐每亩13元,花生捐每亩4角,有100亩土地的就被认定为富户,每户应摊捐100余元。(18)《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3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冯玉祥在河南,军队“(粮饷)统由各本军随地征办,……走到哪里吃到哪里”。(19)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99页。军阀混战与掠夺的后果是大量中小地主与农民破产,形成了规模惊人的土匪,“攻城掠地,所过一空……几乎无一村得免。”无论贫富,皆遭荼毒。(20)《河南匪势猖獗》,《申报》1922年8月26日,第11版。用贝思飞的话来形容,河南就是“土匪王国”,尤其是南部与西部诸县。(21)[英]贝思飞著,徐有威、李俊杰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地主士绅在面临军阀与土匪的双重危险时,被迫与农民联合起来保卫自己财富与生活,大部分农民也有抱团护家的思想,因此,1920年代之后,河南的地主士绅普遍出钱打造长矛(也有少数枪支),聚合自家佃户及当地的贫中农,请来外地“教师”训练枪会,保护乡土。当时豫东南各县无不有枪会,又以信阳、罗山、光山等县的红枪会势力最盛。其中信阳一县设红枪会即达500多堂,光山县青壮农民几乎全部都参加了红枪会。(22)董雷主编:《豫南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这样,大革命期间,中共干部在河南从事农民运动,就不得不面对遍地枪会这个现实问题。
二、大革命期间中共的豫东南枪会工作
中共介入河南红枪会运动较晚。1924年12月下旬,李大钊到达开封与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会谈。会谈之后,胡对河南的工农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李大钊也对枪会有了初步了解。(23)编写组:《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从1924年底开始,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人到河南开展农运,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及党的上层对枪会在河南乡村中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针对性地做好枪会的工作,因而农运的进展始终不愠不火。这一认识的转变发生在1926年初,在此前后,河南各地枪会在斗争中逐步联合起来,每次聚集的人数猛增,如1925年11月,信阳枪会已能聚集近5000人,“掘濠架炮(土炮),与军队对抗”。(24)《时局不靖中之豫省红枪会》,《申报》1925年11月20日,第11版。此时正是国民军第二军与吴佩孚争夺河南的关键时刻,吴佩孚入豫的基本部队较少,因此吴佩孚刻意笼络枪会首领,大肆封官许愿,将枪会改编为豫卫军协助吴军,迅速打败了岳维峻的国民军第二军。这是中共中央所未预料到的,震惊之余,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新审视河南的枪会。
1926年3月,《向导》刊文分析国民军第二军失败的原因,指出这与河南“数百万红枪会之组织”密切相关,首次承认枪会在河南政局变动中展现了巨大力量。(25)神州:《国民军第二军之失败(河南通信)》,《向导》周报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向导汇刊》第3集,向导周报社1927年版,第1369页。从1926年4月到6月,陈独秀、赵世炎、陈云等纷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河南的枪会,有的在文章中甚至将枪会运动抬高到与太平天国、义和团并列的地位,称其为二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此时,共产国际也开始重视河南的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自卫组织。(26)《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这种关注最终体现在1926年7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上。议决案对红枪会定性为:“真正民众的武装”,提出要“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在具体方法上,提出:一是仿照工运模式,建立红枪会通讯处,逐步使其成为指导机关;二是召集枪会领袖开会,形成一个简单的组织,议定共同的行动纲领。(27)《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218页。议决案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正视绝大多数枪会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这一事实,对于如何在农会与枪会关系中取得主导权完全没有论及,反映了中共在将传统农民组织引向革命的问题上缺乏理论指导与实际经验。这也为大革命期间中共枪会运动的无所建树埋下伏笔。
会后,河南党组织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红枪会的议决案,提出要“注重红运以发展农运并巩固农会”,“各地农工人员多半参加红枪会”。(28)《豫区关于军运、农运及国校工作的报告(摘录)》(1926年10月),《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第94页。也就是工人农民先加入枪会,再以枪会会员的身份加入农会。这一时期河南的政治局势也给了中共联络枪会创造了条件。吴佩孚利用枪会的帮助,取得河南的统治地位后,不仅没有兑现改编枪会的诺言,还于1926年3月宣布解散枪会,并大肆屠杀枪会成员,仅在杞县白塔寨一次就“洗剿”枪会成员约5000人。(29)《豫军洗剿红枪会》,《申报》1926年5月21日,第9版。吴佩孚的暴行彻底打消了枪会对他的幻想,因此,中共的枪会工作一开始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
信阳是豫东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区。在“打倒军阀”的大革命高潮中,经过中共干部(以国民党地方党部名义)的联络,信阳枪会纷纷整体加入县农会,并由农会改编为农民自卫团,至1926年6月,已编成南北2团,南团4000人,北团6000人。(30)《河南省农民运动报告(摘要)》(1926年6月),《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第85页。有的枪会领袖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信阳的曾澄清和刘顺,他们每人能指挥和号召数百上千的会众。(31)董雷主编:《豫南革命史》,第35页。1927年3月上旬,40多个信阳西南地区的枪会联合加入“信西南区武装人民团体联合会”,并举行盛大集会,“一致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参加反军阀战争”。(32)《信阳西南区武装人民团体通电与奉军决一死战》,《民国日报》1927年3月4日,第5版。1927年初,北伐进入高潮,信阳从事农运的共产党员与枪会领袖的关系也进入了最密切的时期,一时左右部分地区局势。第二次北伐前夕,信阳百姓痛恨奉军魏益三部队,枪会集合了数万人包围了魏军,但此前魏益三已与武汉接洽投诚,武汉国民政府也极力想保存这部分武装,遂派遣共产党员饶秉凡去调停。饶找到当时与革命方面有联系的枪会领袖张钦臣,以及大绅士仝静如,成功说服枪会撤围。(33)饶秉凡:《信阳风暴》,《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第420页。
当时,信阳的大革命氛围浓厚,共产党员联系枪会,组织农会与农民自卫团。虽然声势浩大,但这些农会与自卫团多数是枪会简单的改头换面,权力依旧掌握在枪会的领袖——地主豪绅手中。这些人对大革命未必有深刻认识,与中共合作的目的也仅仅是赶走军阀,恢复乡村旧有秩序,不可能接受中共的土地革命主张。一旦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自然也就迅速转变政治态度。1927年5月初,在北伐军胜利形势中,国民党信阳柳林党部处决了多名土豪劣绅,豫东南6县红枪会一致群起反击,杀害共产党员和农会领导人,史称“柳林事变”。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宁汉对峙局面形成。这些枪会领袖清楚政治走向,以拥护三民主义为名,广造舆论,污蔑中共,其中有一份在事变中散发的布告写道:“(中共)专执报复主义,异己任意残忍,愚弄无知农工,一言便遭死刑,……劝我父老兄弟,勿听党员横行。”(34)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375页。同时,信阳枪会破坏铁路,阻拦北伐军队。为减少北伐阻力,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给河南的农民运动降温。6月,武汉国民政府把河南地盘交给冯玉祥,命令北伐军回师武汉,河南农民运动迅速陷入低潮。
大革命期间,豫东南的枪会工作主要是联络其领袖,不过也有少数年青的共产党员在家乡筹资建立“革命枪会”,完全掌握了枪会的主导权。1926年夏,吴焕先依靠宗族的力量,打造武器,以“防匪”的名义在光山县箭厂河办起三堂红枪会,吸引贫苦群众入会。1926年底,吴焕先领导红枪会在箭厂河、泗店开展减租斗争,并迫使掌握庙产公田的族长士绅清理公产与捐款。在1927年初青黄不接的时期,革命枪会开展抗租、抗捐,并发动农民用武力向地主“借粮”,在箭厂河、田铺、泗店地区先后向12户大地主借粮千余石,分给家无余粮的贫困农民。(35)董雷主编:《豫南革命史》,第69页。革命枪会势力大涨引起了当地地主豪绅们的仇视,他们纠合自己的枪会与革命枪会为敌;同时,光山县靠近湖北的黄麻地区,黄麻地区的地主豪绅害怕湖北革命力量,纷纷跑到光山县,拉拢当地豪绅组建枪会,向革命枪会与农会反扑,因此,鄂豫边境革命枪会与地主领导下反动枪会的斗争极其激烈。1927年整个上半年,在光山东起癞痢寨、西迄木城寨连绵百余里的高山上,反动枪会与革命枪会激战半年之久。(36)吴先恩:《难忘的岁月》,《星火燎原》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473页。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光山县的革命枪会也被镇压下去。虽然光山县的革命枪会力量偏弱,无法主导整个豫东南的革命局势,在大革命期间也不是枪会工作的主流,但它提供了宝贵经验,锻炼了地方群众,为土地革命战争时豫东南的枪会工作开辟了道路。豫东南能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与这密切相关。
三、中共枪会工作与豫东南土地革命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河南的农民运动立刻陷入冷冷清清的状态。在信阳、荥阳、杞县等农民协会成绩最好的地区,据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其华回忆:“没有看到一个革命农民”,农民协会成为“没有群众的空机关”。(37)[日]三谷孝著,李恩民等译,《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河南省委也承认:“在农民中,没有我们的基础。现在简直谈不到农民有什么组织,有多少群众。农民工作简直要从新做起。”(38)《河南省委报告(节要)》(1927年9月4日),中央档案馆、河南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1925—1927)》,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85页。但是,这并不代表革命的条件不存在了:一方面,在豫东南,执政当局为应付军队所需,加大对一般贫民的税收,“物物有税,事事有捐”,钱粮预征到3年后,有的县在开春时80%农民没有饭吃,加之土匪的频繁骚扰,底层民众生活依旧困苦,对政府十分不满;另一方面,整个豫东南,从信阳到潢川,冯玉祥只驻扎了1个师,兵力严重不足,除县城及少数大的集市,在乡村完全看不见新军阀的势力。(39)《郭树勋关于豫东南政治和党组织状况、存在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2月11日),中央档案馆、河南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市委特委县委文件 1927—1934)》,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45、152页。最重要的是,豫东南光山等县的党员在大革命后期组织过革命枪会,并领导群众组织农会,与反动地主开展斗争,民众受到民主革命的启蒙,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验。
鉴于此,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14日、9月12日、9月30日连续给河南省委发数封指示信函,要求:“一切农民红枪、天门等会友起来组织真正的协会”“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者农民和兵士”,希望河南省委领导农民直接建立农会,在农村展开猛烈的阶级斗争。(40)《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的信——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形势与党的政策》(192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467页。不过,河南省委对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有着与中央不同的意见。这一意见正是源于对大革命后期河南农民运动失败原因的总结上。河南省委认为过去的农民运动是“枪会领袖接头运动”,最大的缺点:一是“只注意枪会首领之联络,未积极去抓取群众”;二是“没有积极领导农民,在乡村中实际作经济斗争”。(41)《河南农运报告——对枪会运动之分析》(1927年8月30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1925—1927)》,第78—79页。从这两点教训出发,河南省委认为目前河南农民受地主欺骗,觉悟较低,暂时不宜开展土地革命,当前最紧急的任务是:第一,放下我们党和农协的招牌,“切实按照农民之要求”,分别作抗租抗捐减租增资运动;第二,利用枪会首领与群众的矛盾,领导群众与首领斗争;第三,“择得几处根据地,去创造独立的枪会组织”。(42)《河南工作方针》(1927年8月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1925—1927》,第69页。这些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联络进步枪会,夺取其群众;独立组织有完全领导权的革命枪会;以枪会或其他传统组织的名义,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斗争,给予农民经济利益。
联络进步枪会方面,四望山斗争是个典型。1927年初,信阳附近的四望山何家湾农民因屡受大地主、红枪会头子张显卿的欺压,自己办了一堂红枪会,并协力于7月14日杀了张显卿,后受其妻兄陈少谟屠杀报复,被迫逃到四望山上,总人数约有三四百人。(43)信阳县委党史办:《四望山红色区域的开创》,中共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丰碑》第6辑,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46页。这些人在山上缺乏粮食,又想着下山种地,因此人心浮动,共产党员王伯鲁了解到情况,在8月份以同乡的身份上山,与他们多次长谈,取得信任,“每人喝口红鸡血酒”,结拜为生死弟兄,枪会农民表示愿意接受王伯鲁的指挥。(44)刘德福主编:《红色四望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9页。在经过复杂斗争,排除了其中一个“善于权变”的红枪会落后领袖王柳亭的干扰后,于11月下旬举行四望山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豫南工农革命军”。1928年2月初,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粟的指导下成立四望山特区苏维埃劳动政府,建立了河南第一块红色根据地。(45)方廷汉等修纂:《重修信阳县志》卷18,兵事,第779页。不久,在河南当局的“围剿”下,四望山斗争最终失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后来的红色暴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从对于枪会的运用来看,四望山党组织所依赖的核心军事力量由原枪会改编而来,结构复杂,未经过认真的成分甄别与政治教育,许多由枪会会员提拔的中层骨干非常动摇,外部压力大时即离心离德,普通会员在遇到敌人大部队时“一哄而散”。因此,在后来豫东南党所领导的暴动中,其主力基本上是共产党员主导创建的“革命枪会”,或者是经过较严格的思想改造和斗争考验的旧枪会队伍。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组建革命枪会成为豫东南共产党员的普遍行为。过去在地主所办的枪会中,会员就是本村农民,许多与地主有租佃关系,枪会“学东”“学董”往往是宗族族长或者房长,枪会内部隐藏着宗族关系与地主—农民关系,包含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最核心的元素与秩序。中共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必须打破地主对乡村秩序的垄断,建立由自己主导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从豫东南走出去的青年革命者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开展从事秘密发动群众的工作。当时正是赤白严重对立时期,河南地主豪绅与军阀对农会会员杀之而后快,农民不敢再行加入,但对于枪会,冯玉祥主要采取的是改编办法,尚有活动空间。这些本乡本土的青年革命者不少家族势大,有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于是他们充分利用本地优势,以防兵防匪的名义创立枪会。这既符合群众心理,也不容易引起地主豪绅怀疑。而且,枪会本身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以此为掩护,可以进行军事训练与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因此,土地革命初期,豫东南的革命枪会及其他类似的组织悄悄复兴。
1927年8月底,共产党员张相舟、徐智雨先后由外地回到家乡潢川,他们以家庭为掩护(张相舟的父亲是地主,拥有一个独立的土寨),用办枪会的名义,组织了7处农民协会,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大荒坡暴动的骨干。(46)梁声旺:《党开展农运的一支重要力量——“红枪会”》,潢川县文史资料研究会:《光州文史资料》1986年第3辑,第25—26页。1927年10月,郑新民在罗南的郑家湾办起第一堂黄枪会。以这一堂黄枪会为核心,郑新民号召每个党员都掌握一堂枪会,到1929年春,罗南党组织所掌握的黄学巳达40余堂,会众达1800余人。(47)中共罗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罗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7页。1929年9月,以黄枪会为主要武装依托,郑新民领导的罗南暴动爆发,建立了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罗南革命根据地。(48)《罗山革命史》,第50页。1928年春,黄麻起义后建立的鄂东军在吴光浩的带领下,来到光山县的柴山保。红军以柴山保为中心,在各村设立红枪会。到1928年11月,柴山保成立了“弦南红学司令部”,将整个光山县南部的枪会统一起来,巩固了根据地。(49)杨丽:《卡房暴动》,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中共新县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34页。在共产党组织自办的这些枪会中,由党员或积极分子担任会长(队长),也请当地有名望者担任“学董”,旧的“老师”仅负责技术方面,主要传授武术与宗教仪式等。在日常训练中,尽量降低迷信成分,至少不助长其迷信思想,但平时注意不要急切地去反对迷信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在民众心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同时,逐步加以政治教育,启发革命觉悟。通过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许多革命枪会与农会得以顺利建立起来,最后转化为革命武装。
无论是联络进步枪会,还是自己组建革命枪会,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斗争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反抗地主,是中国农民传统形式之一,也是豫东南农民的底层传统之一,正如瞿秋白指出:“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遏民变’”。(50)《大家都是良民,那里来的匪!》(1923年8月3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大多数农民习惯于在荒年到地主家去“吃大户”,如洪学智所说“晚上,成群结队到地主家里,呆到11点多钟,让地主管一顿饭,可以吃个饱肚子。”(51)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洪学智的家乡在安徽省金寨县黄鹄寺乡小河口村,新中国成立前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因此,豫东南党组织顺应民众的这种传统习惯心理,从组织“减租抗税”开始,与地主展开经济斗争。例如在四望山斗争中,王伯鲁等拟定详细计划,率领骨干打开地主寨子,将缴获的116石粮食,1.7万多斤铁有策略地分给山上的群众,巩固了他们对中共领导的信心。
在经济利益刺激下,农民革命热情高涨,“虽在新年大雨之夜,也要去打土豪”。(52)信阳县委党史办:《四望山红色区域的开创》,《丰碑》第6辑,第198页。剧烈的经济斗争一旦展开就没有回头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很快越过了“吃大户”的阶段,矛盾开始变得不可调和,实际上已与地主撕破脸,“结下大仇恨”。有的农民中途胆怯,脱离革命武装团体(如枪会、自卫军),就被地主豪绅找到杀害,结果“一般农民自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非起来去干不可。”(53)《豫南特委关于四望山目前工作纲要》(1927年10月21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市委特委县委文件 1927—1934)》,第72页。因此,到了1928年1月,四望山暴动趋于鼎盛的时候,农民大会上的气氛极其热烈,几个贫农激动地喊道:“反正二斤半(头)不要了,非和那些豪绅地主拼不可!”。(54)《豫南报告》(1928年6月25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1928)》,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238页。
通过组织革命枪会,乡村原有宗族与血缘界限逐步被打破,在频繁而剧烈的经济斗争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贫富怨恨转化为阶级对立,农民也不再受到地主的控制与压迫,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共产党员因势利导,以枪会为基础,建立农会与各种自卫军和保卫团,为保护农民的利益而斗争。以农会为权力基础,乡村新的结构与秩序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到1929年10月,在豫东南,仅光山有组织的农民就达三四万,商城有几千人,罗山有五六千。(55)《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巡视豫南的报告》(1929年10月22日),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 1929—1930)》上,内部发行,1983年版,第155页。到了这个时候,枪会也无形地消融于革命组织中,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条件成熟的地方开始发动暴动,形成小范围的苏区,最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分田分地。同时,军阀“围剿”的外部压力,反而成为增强根据地内部凝聚力的黏合剂,促使整个根据地形成秩序井然,各担其职的组织体系,从根本上重塑了乡村,传统乡村变成一个阶级化的农村革命策源地。
从保护乡土为宗旨的传统枪会运动到现代意义上的阶级革命,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仅仅强调是中共系统策划、组织和动员的结果,美国学者小萨克斯顿(Ralph A.Thaxton Jr.)认为这个回答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怀疑中共在革命动员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必须从农民的自身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农民并不是被动或者盲目地接受中共的动员,农民同样影响着中共,中共的动员只有与农村的社会结构、习俗与文化相协调,才会被农民所接受。(56)R.A.小萨克斯顿:《大地之盐:中国农民抗争与共产主义革命政治渊源》,潘世伟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页。从1927年到1930年,豫东南土地革命初期,中共的许多根据地开创工作都是围绕着枪会进行,其成功的原因在于豫东南党组织抓住了地方农村的传统习俗与文化。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群众运动决议案”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假使忽视了枪会运动或是策略的错误,就可影响到全部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到当地党的生命”。(57)《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1929年1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1930年后,根据地开辟工作基本完成,红军和苏区进入正规化发展阶段,中共枪会工作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枪会在根据地内部存在的基础不存在了,枪会也逐步消失。
余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创建了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其中鄂豫皖和由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最为著名。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为火种,从井冈山开始,逐步发展扩大形成的,根据地创建之初,外来的军队与干部起到了主要作用。这种根据地发展类型有人将其总结为“外力型”割据。(58)黄琨:《军队与乡村社会:革命根据地形成模式之比较研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而作为鄂豫皖苏区的一部分,豫东南根据地的形成过程有所不同。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当地知识分子从城市回到家乡,这些年青人在家乡利用宗族、同学、同乡的关系,组建枪会或其他传统组织,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农民开展斗争。这些年青的知识分子许多出身在地主士绅家庭,熟悉本地信仰习俗,掌握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为宣传与组织革命武装减轻了阻力。在革命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地方党组织举行暴动,组建半脱产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成为一个小的苏区,然后各小块苏区合并成较大的苏区,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根据地,革命武装也在在敌人的“围剿”中锤炼为强大的正规红军。这种红军和根据地成长方式可以称之为“内生型”割据。
革命枪会在缺乏足够社会力量的庇护下是难以建立的,“内生型”武装割据在发展的初始期主要依赖革命家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当地革命家所在的家族大多在当地有一定名望,或者有一定的资财,否则难以提供建立枪会所需装备及日常训练的费用,因此革命星火在豫东南地区初燃时,带有很多革命家的个人特质与地方色彩。同时,“内生型”割据在初期是用合法的形式来做非法的工作,必须进行较长时期的力量积累,只有在革命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通过红色暴动的形式打出革命旗帜。因此,相比外力型割据,内生型割据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潜伏过程,这个准备过程的长短影响了暴动的成功与否。
当然,无论是“外力型”割据,还是“内生型”割据,它们都抓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农民。“外力型”割据是以军队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吸收农民参加军队,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豫东南的“内生型”割据是以革命枪会或其他传统组织为依托,通过与地主展开经济斗争,提高农民觉悟,壮大革命队伍,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将革命枪会转化为农会和革命军队,在长期斗争中壮大革命根据地。“外力型”割据与“内生型”割据,都是中国革命发展逻辑的产物。
豫东南土地革命初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利用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中的革命因子,将蕴含革命性的地方传统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革命。将井冈山、湘鄂西根据地与鄂豫皖根据地略作比较,可知它们革命的起点与生长方式是不同的,革命的面貌也各不相同。由此不难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不断被“地方化”。在这个过程中,豫东南地区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特质的底层革命者参与形塑了革命的面貌,使豫东南的革命不同于其他根据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生动诠释。正是诸多根据地的多样化兴起构成了革命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不断地去探索中共革命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