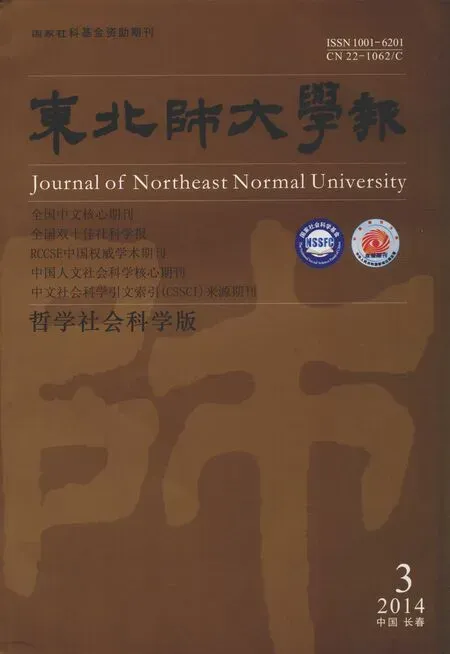历史与实践: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音乐哲学研究
王 磊
音乐哲学是探索人类在感知音乐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与体会的全部内容,与音乐美学的概念不同,音乐美学则是探究艺术传统中的音乐,音乐是美学研究的主体,而人类是哲学研究的主体。音乐哲学作为哲学范畴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主题,围绕音乐这个特殊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属于哲学范畴的研究。实际上,直到2001年,在新版的《格罗夫音乐词典》中才加入了音乐哲学的概念。音乐相比于其他艺术种类,确实具有着较高的神秘性,而这种特性让古往今来不少哲人展开思考,试图从思想的角度去探索音乐的本质和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一直伴随着音乐的历史发展,成为了音乐哲学的基础。我们并非是在单纯地讨论音乐的功能,我们坚信音乐哲学的基础是使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音乐产生并被人感知到的美学,让音乐的美学认识从音乐哲学的角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在更深刻的层面来探讨音乐以及感知音乐的对象——人类自身,进而推演到整个社会。
音乐哲学的发展是历史性的、是十分漫长的,正如《格罗夫音乐词典》在介绍音乐哲学的概念时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你想举出对此学科做出过贡献的哲学家们和音乐家们的话,那将是一个包含很多伟大名字的没有尽头的名录”[1]。按照现代的观点,毕达哥斯拉被称为音乐理论之父。毕达哥斯拉学派的菲洛劳斯创造了著名的古希腊自然音节。从毕达哥斯拉学派开始,音乐理论的研究就开始关注音乐的社会意义,音乐科学的研究也相应地展开,为音乐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以前的时代,音乐哲学从自然哲学研究过渡到了反思阶段,直到“神曲”打破了音乐哲学的自然发展,要求理性、禁欲、有节制的格里高利圣咏成为了音乐哲学的唯一思想出路。“音乐的美不过是上帝在音乐这个对象身上打下的烙印,是上帝自身性质的体现。人们可以通过音乐的美来观照上帝的美。音乐中表现的情感正是对上帝信仰的虔诚,对现世罪恶的鄙视和对彼岸世界的憧憬之情”[2]。从毕达哥斯拉学派的音乐理论基础学术研究开始以来,音乐哲学的研究方法就从未脱离过基本哲学的研究范畴,从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汉斯立克等较为古典的哲学流派,到语义学、符号学、阐释学、分析学、格式塔心理学、发生认识论、接受美学、比较音乐学、文化人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哲学研究方法都被用来阐释音乐哲学的相关内容。于润洋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提出了音乐哲学采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尝试,实际上是对中国早期音乐哲学传统的一种回归,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音乐哲学包含两个研究范畴,一个是中国传统音乐哲学思想的研究,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下的音乐哲学研究。后者显然没有被延续下来,尽管现在翻看早期的诸如《欧洲音乐史》(于润洋参编)采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下的分析方法,但是并没有被学界所意识与重视,音乐哲学研究随着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的介入,一度陷入了单纯的过度诗化。
一、音乐哲学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实际上在音乐哲学研究的领域内,对近代音乐哲学的诗化批判以及对音乐介质的资本性批判早已经展开,以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为代表,阿多诺从“否定的辩证法”出发,深入地研究了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的本质及其审美特性。尽管南京大学的方德生在《生产与意识形态批判——析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激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批判话语,阿多诺新音乐哲学强调的是音乐的认识功能而非审美功能,即它的批判性与革命性。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特色的理论,阿多诺透过勋伯格的新音乐革命把非同一性从同一性的压制下离析出来,由此开辟出否定辩证法与美学理论的建构之路,展开了继马克思之后对资本同一性最为深入的批判”[3]。但是,实际上阿多诺的研究方法依然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思想更多的是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出发,去批判性地看待现代音乐哲学。马克思主义对音乐哲学的批判应该是更为实在的,建构的音乐哲学方法是更为直接的,所以,应该批判的就是这种资本社会衍生出来的虚无思想,产生了极不负责任的音乐哲学。
首先,被过度诗化的音乐哲学体现出了音乐哲学发展动力的匮乏,即便不去追究诗化哲学在文字表达上充满了让人难以揣度的晦涩词语,单单是将音乐哲学集中于情感体验这一项,也让人不免觉得其研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移情”、“人格”、“自由意志”等掺杂在音乐当中的哲学研究不仅让音乐哲学的研究更脱离音乐本身,让音乐哲学的研究陷入了虚幻之地,更让真正的音乐哲学远离价值体系,我们相反更推荐瑞德莱的《音乐哲学》中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下的音乐哲学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一样,以实践做为其根本点和出发点,强调哲学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是能够作用于音乐本身发展的哲学,而不是像其他哲学思维一样,把音乐带到了“彼岸”,如仙子般远离尘世。也正是基于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哲学从此由疏离人生的超感性的天国下到了具有诗意的人世,西方现当代哲学正以不同形式实现着传统意义的哲学之非哲学化,以及哲学的现实化”[4]。
其次,音乐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原动力的共有产物,能够被科学主义所解释。科学表达的必须是客观真理,并取得人们的共识,艺术所表达的往往是个人感受到的强烈的审美体验,所以艺术表达需要鲜明的个性。实际上,作为人类共同的活动,科学与艺术一直都是对立统一的。然而,这种认识不断地被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科学主义所打破,在完全从音乐理论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我们不得不提到音乐结构主义——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观念下的对艺术的庸俗化处理。结构主义认为,音乐实际上如同建筑一样,音乐产生是一个功能系统在发挥作用,所以,在结构主义看来,主要将音乐的功能“键”都一一掌握,音乐表现才能够趋于真实和完美。如同机器生产一样,音乐在理论上也可以走向生产线。这让我们想起了黑格尔在论述哲学自身时所举的那个“动物听音乐”的例子,如同黑格尔所言:“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透进它们的头脑”[5],尽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功,但是这种发展和成功却建立在使主体意识沦为“动物”的基础上,我们除了被货币所操控以外,还被泛货币化的内容所操控着,从而简洁地丧失了主体地位,在“抛弃”神之后,创造了新的上帝,名字叫“Gold”。
最后,我们应该严肃看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发展的音乐工具主义。这其中也包括对结构主义的批判。音乐被视为人类情感的一种宣泄,被视为一种安慰。音乐作为娱乐工具出现在哲学思想内,看作是替代控制心绪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变相手段,被阿多诺称为“社会相面术”,音乐的功能仅仅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娱乐的手段,这种思想是建立在人本身的需求也仅仅就是娱乐的基础上。人们谈论音乐的娱乐功能似乎比音乐自身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变相的神学音乐,只不过它的存在方式被社会大众在默认的前提下悄然整合了。
二、音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在人与实践对象之间存在一个实践的过程,美是同人的状态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认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6]79。比如说音乐作为审美对象的存在,取决于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一方面是音乐的性质,另一方面是认识主体所具有的能力,“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来说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6]79。这说明在具有“发现美的耳朵”的前提下,在被激起乐感的同时,实践的过程是让二者结合到一处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告诉我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感性活动,音乐哲学本身就处于天然的实践活动中。实践矛盾产生物质及意识概念。物质与意识的认识是实践的规律性规定。实践的内在矛盾是意识本体与生命本体的自我解放必然。我们应该延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对实践活动的认识方法与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理解音乐,理解音乐这种实践活动中所带给我们的感性认识。
首先,现实的实践哲学要求我们认识音乐产生效果和作用的基本原理,从而祛除神秘哲学为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添加的虚幻外衣。音乐的作用原理恰如鸟鸣带给人耳产生的听觉现象,是自然的声音现象,完全可以用声音产生的科学理论进行解释,是耳膜震动产生的辅助效果。正如皮亚杰所说“在音乐之中,结构不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而言)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常的能力”[7]。也就是说,音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务,认识音乐要通过具体的音乐实践来完成。
其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增进了我们对音乐本身的了解。实践自身的矛盾性延伸到音乐上,解释了现实世界的二重化、人类自身的二重性和社会历史的二象性。音乐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当中被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解释,不同于传统哲学上对这种关系的解读,音乐本质上属于概念性的,这是十分荒谬的,按照“无人身的理性”和“逻辑规定”,仅仅是概念中介的单词意义,让我们似乎看到的是虚无主义倾向。尽管费尔巴哈在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作是“抽象的个人”与“感性的直观”来解释,但是依然无法充分对音乐的实质性内容做出充分的解释。“要理解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不应该从观念出发,而应该从有感觉的人和自然界出发;精神应能在物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物质在精神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及其思维、感觉和需要应该是这种统一的有机反映”[8]。马克思的实践观清楚地说明了,音乐应该是一种“现实的人”以“感性的活动”为基础的与“现实的世界”的关系问题。音乐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的感性活动,被现实的人所感知,同时被现实的人所创造和发展,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
最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我们指明了音乐哲学的发展目标,即改造和发展音乐,而不是如就事论事般地停留在音乐的美学欣赏上,这也是我们比较美学与哲学不同点的一个主要内容。音乐的实践哲学告诉我们不仅仅要能够解释音乐,更重要的是改变音乐,或者说发展音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给哲学领域带来的一个本质上的突破,即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以人为中介来解决近代哲学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实践转向的真正意义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名言当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音乐不能够脱离实践和历史两个范畴去单独理解,音乐哲学的发展也不能够摆脱历史与实践的约束,失去历史背景与实践过程,音乐就变成了自然属性的事物,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变为纯粹的声学内容,那些对音乐过分诗化的描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三、音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6]79。人在音乐上的感觉,同样是以往全部历史音乐文化的产物,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音乐美的发现和感悟,都是以该时代的人所能够继承下来的历史文化作为前提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音乐也不例外,音乐的发展史同样是人类的活动而已,脱离历史的主体,音乐不会产生“有过程的结果”。所以,学习和研究音乐哲学的角度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音乐学界最为常用和最为成熟的一种认识,然而,却被渐渐的忽略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分析音乐哲学和构建音乐哲学的基本框架可以说具有着非常有效的说服力。
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音乐发展分为古代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时期四个阶段,通过历史背景的分析来理解音乐在时代实践活动作用和影响下的发展以及独立成长的原因。在古代奴隶社会时期,就必须谈及古希腊时期十分盛行的戏剧艺术,是戏剧艺术的发展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悲剧”的发展,通过戏剧的形式来演绎那些大型的神话与史诗,则繁荣了音乐形式的种类。这就是时代背景下,音乐的发展原因。中世纪为教廷服务的格里哥利圣咏、城市的发展、剧院的产生、云游诗人、流浪艺人以及那些发自内心反抗精神束缚的民间艺术形式,不断地推动着音乐向前发展,贵族、巴黎、文艺复兴这些词汇对于音乐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歌谣、意大利的乐派,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音乐内容无一不在说明着音乐发展的具体性和现实性,能够说明这种分析方法的有效性的例子汗牛充栋。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地看待音乐的问题、看待音乐的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念,我们才能够更加成熟地抽象出音乐中的意境和美感,就像理性认识从来不曾影响到感性认识一样,我们依然可以追求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些“感觉”,但是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每个“感觉”上的认识正是在不断创造着历史。
四、马克思主义音乐哲学体系的重构
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音乐哲学现实发展进行批判,实际上也是揭示出了音乐哲学现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从某种层面上讲,我们不能将这种原因完全归结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还有诸如其他思潮的影响与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中肯的一种批判,这也是音乐哲学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比如音乐的现代化发展难免被商业化和货币化所冲击,资本在影响人自身的同时也损害了艺术的发展与纯粹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有力批判,正如音乐哲学发展到目前为止也不断地涌现出恢复传统的趋势。音乐哲学如同哲学等其他学术一样,一直都是在不断前进的,尽管出现了各种发展的问题和错误,但是总的趋势并没有出现倒退,实践哲学的出现到语言转向的回归本身是一种进步而非退步,音乐哲学从语义、符号到发生认识、接受美学再到实践的转向,我们同样认为这是一种前进,是一种超越,同时也是音乐哲学现实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再将思想禁锢在现代化的盲目当中,更应该吸收传统的、经典的以及后现代主义带来的种种反思,重新看待我们在音乐哲学领域内的认识,重新回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历史观引领下的音乐哲学体系当中,将现代化的过程拉长、拉细,充分沿着历史的、实践的内容来重新审视我们的音乐历程,重新认识音乐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音乐哲学体系的重构关键首先在于思维与方法的转变,只有重新认识延续马克思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逻辑,才能够建立感知主体与音乐客体之间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其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历史观下的音乐哲学一定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特征,音乐必然是属于人民的、大众的,然后才是作为历史的和实践的事务在哲学范畴内的意义,正如P·奥尔佩森说的那样,“真正的音乐听众是把音乐当成日常生活必要组成部分的业余爱好者,欣赏音乐是一种再创造,它具有自我赖以生存的共同感。鉴定音乐审美乐趣的标志非但不是我们消费审美对象,相反是成为音乐知识和表现主体的组成部分”[11]。最后,我们不一定完全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存在关系当中去,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转身再次了解一下克列姆辽夫与卓菲娅·丽萨的思想,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原理下的音乐哲学思想,重新认识杰出马克思主义学派音乐学家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重新回到历史分析与实践分析的传统当中去。
[1]牛龙菲.有关“音乐哲学”[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1):1.
[2]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7.
[3]方德生.生产与意识形态批判——析阿多诺新音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模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4):19.
[4]池瑾憬.论音乐哲学研究的历史擅变[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6):132.
[5][德]黑格尔.哲学演讲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2.
[8][匈]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5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9.
[11][英]P·奥佩尔森.评什么是音乐——音乐哲学导论[J].英国美学杂志,1989(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