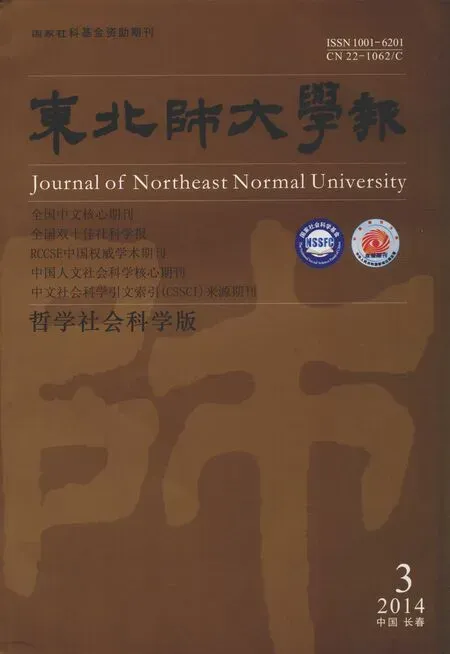论清末文学教育的转型
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不仅破坏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同时还对国人封闭僵化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社会性质的转变,儒家文化思想渐渐失去了信仰与崇拜的光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旧式教育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主要攻击的对象。此后,兴“博学”之实用科目,教“济世”之文学,育“时务”之新人才成为了文学教育改革的重点。
一
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在科举选士的“指挥”下,逐渐形成了八股“作”文与经义“述”学的交织,教育中的文学性和教育意义几乎被“有妨举业”的衡量标准遮蔽。再加之清朝中叶以来的文化高压政策,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与犯言直谏的品格投向了内敛沉闷的学术考校。然而,这种治学之风随着帝制末外敌入侵发生变化:战败,变法;国难,新政。为了挽救封建政权,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为近代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革新的大门。一批先觉者由质疑走向了反思,试图从兴新学入手,通过教育的革新举措有计划地挽救清廷的颓势。但此时的革新更多的是创造之意,虽有革除旧蔽的实际做法,如改八股为策论、办京师同文馆,但在文学教育领域奉行的则是一种“有限抽离”的策略。
吉登斯曾经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讨论中提道,“前现代社会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变得更为专门化,更为精确。”[1]19然而,其中还有一种更为内在的关联,“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的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接’”[1]19。对于“抽离”,吉登斯强调的是一种传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是理性思考的外化过程。事实上,清末的封建社会也处于“抽离”的阶段。此时文学被知识分子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挖”了出来,成为教育革新的对象。并且在19世纪末中、西文化传统互动中,掺杂了社会转型、现实需要、思想进化等多种因素的“再联接”:一方面,它借鉴了西方现代学术体制、非原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后,构成了文学教育转型的试验场;另一方面,为了维系封建统治秩序,文学教育在转型中保留了一部分传统文化思想。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清末文学教育开启了现代性的探索。
首先,中国古代的统治集团是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伦理教化中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而包含着经、史、诸子学等繁杂内容的文学,不过是教育的手段而并非目的,它不是成为举业的“附属产品”,就是成为“修身立德”的人生标签。虽然,清末的治学活动遗传了学海堂、诂经精舍“实事求是”的学风,但这种内容混杂、外延模糊的“泛文学”教育已然不符合晚清救亡的需要。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清末又处于中西思想碰撞的大时代,当“具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题材”[2]与传统的典章子集相遇时,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强烈反差,也成为了文学教育转型的巨大推手。
其次,文学教育的转型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清末的治学虽然囿于儒家的经典内容,但当它们遭遇“欲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3]的文化殖民活动后,文学在自我保护机制的驱使下,开始从国家制度层面思考“济时用”的文学革新。1902年,“文学科”一词出现在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中,随后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中国文学门”划出了“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等内容,设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等七门主课以及四库集部提要、各种纪事本末、西国文学史等九门补助课。自此,文学教育的合法地位得到官方话语的肯定。但是,清政府在《奏定学务纲要》中又特别指出,经籍古书有益德性,有助封建统治,所以学堂内不得废止。这就决定了清末文学教育的转型不可能是彻底的新生,它只能是以渐进的方式,协调文学与传统制度、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以学术研究的姿态参与清末的自救行动。
二
作为一种审美意识活动,清末的文学教育只能选择抽离的方式把握人与社会、古典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大体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伦理型人才。而清末在西方知识观、价值观的冲击下,在“启民智”的诉求下,文学教育开始了一番对世界重新理解和把握的活动。其中,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改良方式,虽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在情感、知识、价值观等方面的效度,却逐渐拉开了文学教育与封建制度的关系。
其一,言辞方面的探索,即“言文合一”的主张促进了白话文学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清末文学教育的转型。传统的文学以诗文典籍为主,“文言分离”保证了书面文的高雅、古朴。但清末的民族危机亟须便于认知、理解、记忆、应用的文学表达方式出现。因此,在裘廷梁、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倡导下,“言文合一”的白话通俗文体进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特别是19世纪末,迫于外交、商贸、翻译的需要,欧化的语体带着新思想、新知识、新词汇进入了新式学堂。这种借鉴西方语言、句式,又接近民众生活的表达拓宽了文学教育的空间,加快了文学革新的进程。周作人就认为,早期对《圣经》的中文译介就对近代文学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胡适更是指出,“欧化的白话文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4]因此,在社会需要的情况下,“言文分离”、排斥俚俗的文学开始新的尝试。如,早期黄遵宪尝试在诗歌创作中引入民间俗语,并提出了明白畅晓的文学变革设想。陈荣衮则认为只有白话文才能救亡图存,因而积极地创办白话报刊,编写白话文课本。再有,无锡三等公学以浅近通俗的文字编写了《蒙学读本》,意在传递普通知识,养成立宪国民之道德。直到1904年,《奏订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5]但是,这种较为接近日常生活的言辞探索,还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其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仍存在区别。
其二,新文体功能的凸显,即新小说、戏剧、诗歌的创作为清末文学教育的转型提供了直接的文学来源。经由不同文学体裁与主题的阅读和接受,有助于丰富读者的情感体验、提高智识、获得审美愉悦。但清末的学术研究钻精、考校八股,很少涉猎科举以外的文学作品。鉴于这种僵化、功利的治学风气,一种切合实用,又能传播智识的文体迅速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重点。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约》中提出了“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分类。他力主一种“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6]的写作。1902年《新民丛报》刊载《新小说》杂志的广告,强调小说文体具有的“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7]特质,并指出“本报文言俗语参用”的体例。另外,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下,西方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描写方式、审美标准等都参与到清末文学的转型中。古文虽美,但此时新文体的出现与流行打破了传统诗文歌赋的权威感。这种通俗易懂的体裁,强烈的语言感染力及文白夹杂的言说形式,以社会群体为启智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桐城文法、“同光”诗作的局限,为文学教育开辟了新的天地。此外,1905年科举停罢,俗语和官话进入了文学科的视野,加快了文学教育内容的转变。尽管此时诗歌、小说的创作还有依托古人的痕迹,《新中国未来记》《九命奇冤》还称不上白话文学的新生,但它们的确为文学教育的蜕变打下了基础。
除了以上两种途径之外,清末文学教育还在学科化的建构中展开了自我转型的探索。近代教育系统的完善与发展,需要更严谨的学科划分以及专业的学术研究。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并不是依照“性质的类别而组织成各自独立的系统”[8]。它更近似于一种学术“大拼盘”。余英时先生将这种情况归为“逻辑知识论意识”的缺失。然而19世纪末西方科学思想的输入,传统分斋而治的词章记诵、八股训练,转向了初、中、高以及大学堂各有侧重的文学认识活动。虽然,此时的文学教育仍然以古书经籍为主,但它毕竟迈开了学科独立探索的第一步,推动了内容混杂、外延模糊“泛文学”朝着专业化、精细化的学术系统转型。特别是文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应用,加快了清末文学教育转型的步伐。最初从模仿教会学校课本开始,知识分子在异质文化的对接中逐渐完成了文学教科书独立编纂的工作。这一阶段比较完备的课本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以及刘师培编辑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他们的编写是对旧式学堂内经书、文选的告别,在内容编排上由字、音、义入手,从简到繁。前者的编写以通俗语体配上插图,后者以文言体例为主,侧重小学的研究。而在大学堂内有林传甲、黄人的文学史讲义,这两本著述在文学界定、文体分类及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创新的思考。但是,清末文学教育的转型毕竟站在了封建残垣之上,虽然在开通智识和学科建构方面有所突破,它的本质仍然指向益德教化的封建立场。
三
总体来说,清末文学教育的转型是在封建体制内对思想启蒙的呼唤,它虽比不上新文化运动来得猛烈,但其借助异质文化碰撞的契机,还是对传统文教进行了一番形制的拆解。尽管在这一拆解过程中,政治指向与价值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文学与传统秩序建立的亲密关系已经在革新的教育语境中出现裂痕。儒家文化的权威性受到了学科化文学建构的冲击。白话文和新文体被知识分子从封建秩序中“挖”了出来,并与思想启蒙联接在一起。这种帝制末的文学转型,是对固有范式与规则的反抗,不仅为文学教育现代性发生开辟了教育的空间,也为新文学传播搭建了一个思想的平台。
[1]吉登斯,赵旭东,方文.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李春.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85.
[3]李清悚,顾岳中.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7.
[4]胡适.新文学的建设理论[M]//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再版.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42.
[5]奏订初等小学堂章程[G]//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璩鑫圭,唐良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05.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88.
[7]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N].新民丛报,1902-07-15(14).
[8]余英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M]//沈志佳.余英时文集: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