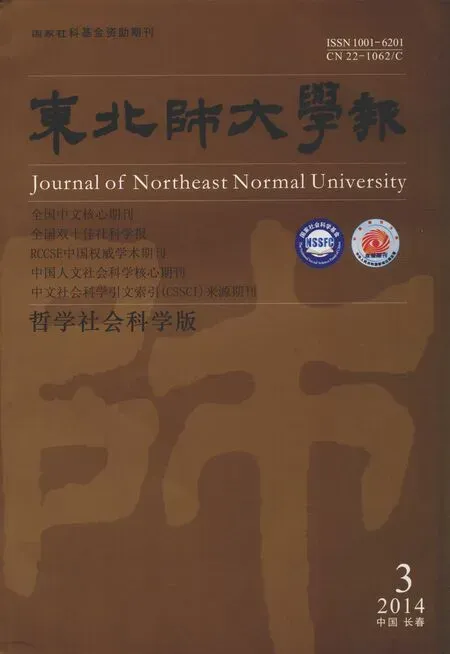回归生命的底色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奥丽芙·基特里奇》探论
柳 青,宫玉波
(1.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北京100091;2.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回归生命的底色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奥丽芙·基特里奇》探论
柳 青1,宫玉波2
(1.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北京100091;2.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44)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以新颖的创作形式、质朴的叙事风格和永恒的婚恋主题吸引了众多关注,而作品中表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更为可贵。通过13篇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的短篇小说,巧妙地将女性命运与大自然及其周遭男性相联系,揭示了现代女性遭受工业文明和男权文化双重压力的真相,并通过小镇众生的喜怒哀乐,审视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敬畏。小说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积极探索女性自我救赎的途径,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家园。
奥丽芙·基特里奇;生态女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
一、引 言
当代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1956—)凭借《奥丽芙·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摘得了200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与其前期的作品相比,这本小说不仅反映出令人心动的真挚人文情怀和细腻女性意识,而且又有了新的突破。首先在形式上构思独特,《纽约时报》评价它成功地结合了长篇小说持续交缠的手法和短篇小说灵光乍现的洞察力。13个似乎可独立成篇的故事暗通款曲,勾勒出一幅立体的小镇风情画。但如同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三寸象牙微雕”绝不简单囿于几户乡村人家的喜怒哀乐一般,《奥丽芙·基特里奇》引发出人们对于爱、孤独、悲伤、死亡等不朽命题的思考。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在形式和艺术上都颇具大师的潜质。不仅如此,透过女作家细腻、阴柔而略显残忍的笔触,女主人公们的生活境遇令人唏嘘无奈,人们不禁思忖: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女性寻求尊严和幸福的道路依然坎坷,工业的文明和野蛮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自然中的我们。作家借这部作品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1974年在《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中呼吁女性参与拯救地球的工作,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开创性地在人与自然、男性和女性之间假设了一种新的关系,将生态学和女性学融合在一起,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从20世纪80年代起,将哲学、妇女研究和环境研究相糅合逐渐成为女性主义者着力的新方向,从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作品中都能发现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自1990年以来,女性主义者开始自觉而有意识地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准则和阐述与现有的文学研究相联系。其中,欧美知名学者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等对生态文学批评做出了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研究。
简言之,生态女性主义已然成为当代西方环境运动和女性运动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在反思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更致力于建构一种生态的女性文化。这种文化无疑是对女性解放的新解。《奥丽芙·基特里奇》巧妙地融合了长篇的宏观视角和短篇从精微看普遍的特质,不动声色地表露出强烈的生态关怀,探索着女性的成长和幸福之路。
二、奥丽芙们与海湾特质的高度契合
整部小说发生在一个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缅因州的海滨小镇——克劳斯比,这里风景宜人、生活闲适,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风情。而那片波光粼粼的海湾便成为经常出现的景色,全文对其描述不下30处。女作家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感受力和略显随意的笔触描绘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这片海湾的依恋和情感变化。它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孕育愤怒,既惹人烦恼,又挥之不去。表面上它似乎缺乏大海深处磅礴的气势,只能给龙虾和寄居蟹提供栖居之处;但似乎又孕育着“前一分钟风平浪静,后一分钟暴跳如雷”[1]240的巨大潜力。细细思忖,这片海湾的意象与小镇女性形象有着多重相似之处。
首先,从位置来看,海湾属于边缘地带,虽然她具备巨大的生命力,对生物的繁衍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最容易遭受外界的侵入,这与广袤无垠的大海中央俨然不同。小镇女人的边缘化地位与之如出一辙,虽然担负着延续生命的重任,但似乎永远都处于被男性忽略和遗忘的境地。这里,“边缘”和“中心”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被作家巧妙地嵌入进来,为进一步探讨“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吸纳、相互排斥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功能来看,海湾是船舶停靠之地,它所拥有的安详和包容让人类的灵魂得以休憩,但他们似乎只能停留片刻,因为远处的世界更具挑战性。作品中,有些男人常年生活于此,他们期冀妻子有着海湾般的温柔,但私下里又渴望女人能激起自己大海般的狂野情欲。有些男人走了又回来,他们贪恋这里的静谧与温暖,看到了海湾就能想起站在岩石旁挥手的母亲,但明天终归还要回到喧嚣的纽约或别处。
最后,从本质来看,海湾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它所呈现的苦涩的味道,它所冲刷出凹凸嶙峋的海岸线,它对大地和海洋的双重依恋,既不动生色,又巧夺天工。而女性较之男性,具备更多贴近自然的属性,温润、坚忍、包容,并姿态万千,一方面寄托着男人们的无限遐想,也会残忍地撕下他们的所有伪装。
每每看到这片海湾,总让作品中的人物想到恋人、母亲和家园,也让人们想到爱与被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克劳斯比小镇的人们以这片海湾为家,以身边的海岸线为骄傲。但是,葆有一块自然和心灵的净土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便捷的通信、威猛的机器以及无尽的欲望已经让这个小镇的人们无处遁形。斯特劳特笔下曼妙的海湾风情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女性担忧和人类危机。与此同时,这片海湾寄托了作家对当代女性特质的全方位描绘。她巧妙地把这种生态女性主义情怀聚焦在主人公奥丽芙·基特里奇身上。这个性格稍显古怪的退休数学教师似乎没有什么女性魅力——身形高大、脾气暴躁、不拘小节,一心为家却得不到亲人的怜爱和尊重。但是,她如海湾般的直率坦白、乐观通达,以及隐藏在强悍外表下的脆弱和忧伤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不难看出,这位普通的小镇知识女性身上凝结了太多当代女性的苦乐人生,折射出家庭与社会、道德与理想、文明与蛮荒对女性个体施与的压力与提出的挑战。
三、处于男权中心的奥丽芙们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Karen J.Warren)从哲学的视角出发,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父权制是“压迫性的概念框架”。父权制代表着一种男性占统治地位、两性不平等的制度,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价值等级制和统治逻辑[2]。澳大利亚哲学家瓦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进一步反思了二元文化中的一些相互关联的范畴,比如“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认为“二元论的划分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鲜明对比的概念构成的。它由统治的和屈从的两组概念构成,形成了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3]。那么,与男性气质相关的概念总是与高贵与优雅分不开的,而低等或依附都是属于女性的代名词。
一般认为,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机会和男人抗衡的今天,像奥丽芙这样的女性应该凭借体面的职业和独到的见识赢来舒适的晚年生活。但是小说中隐隐透出的压抑氛围使人无法释怀,奥丽芙及小镇女人们对自己的幸福归宿变得无法掌控。
西方白人父权文化中的二元论思想在小镇中根深蒂固。男人、儿子、顺从、隐忍、安静、忠诚……构成了女性世界的全部。在开篇故事《药店》中,身为药剂师也是老板的亨利厌倦了和自己耳鬓厮磨的妻子奥丽芙,因为她的强势霸道和犀利言辞似乎让自己失去了对家庭的掌控权。而药店的雇员丹尼丝,一个带着单纯梦想和拥有雏菊气质的女孩,激起了他那略显病态的渴望。于是,“好人”亨利逃避着家里的繁琐纷争,眷恋着药店的祥和安宁。小说似乎勾勒了一个负责任、有担当、发乎情而止乎礼的丈夫形象,隐忍多年实属不易。但是细细解读下来却发现,亨利一直是奥丽芙的主宰,用或亲密或疏离的态度掌控这个女人的人生。在忙碌的职业、繁琐的家务、相互的熟悉磨去了这个女人的温柔、淡定和善解人意的时候,亨利却悠然地做着丹尼丝的人生导师。不难发现,亨利代表的俨然是具备理性判断、思想深邃的精神领袖,而奥丽芙就是受情绪左右、性格肤浅的物质女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女性具备了更多与自然相似的属性,所以只能与自然一样受男人的支配、改造和发落。根据格里芬的归纳,(女人与自然)同样地消极被动、逆来顺受、养育滋润[4]。
如果说奥丽芙受控于丈夫的事实还有她的犀利言辞加以伪装的话,那么在儿子面前,她着实成了一个卑微顺从,小心讨巧的角色。《小插曲》、《郁金香》和《安检》三个故事主要描述了奥丽芙与儿子和前后两任儿媳的关系问题。克劳斯比位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多数人家庭观念重,对子孙承欢膝下的场面极为向往。儿子克里斯托弗受够了母亲的敏感和坏脾气,断然地远走他乡。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娶了又高又壮的安,养着两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小孩,在纽约这个满是火药味的城市生活着,却不愿回到开满郁金香的海边小镇。当克里斯托弗说自己不想再活在对母亲的恐惧中时,奥丽芙惊诧万分,怎么可能会有人害怕自己,自己才是那个害怕的人。这个女人习惯去用唠叨、聒噪、大惊小怪去表现她的关爱、在乎和心疼的时候,最终却成为了最孤独的人。男性的生活模式和认知世界决定着周遭女性的行为是否符合标准,当发生冲撞和矛盾时,男性可以选择放弃和离开,而女性只能一辈子小心翼翼地活在取悦身边男人和担心不再被爱的惶恐中。
可以说,奥丽芙只是小镇女人的一个缩影。无论年龄大小、阅历深浅、性格如何,小镇女人的幸福和命运就是同孩子和男人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也许,经济的独立、口无遮拦的痛快、人前的亲密和谐掩盖了女性内心的恐惧、卑微和孤独。男性对女性价值的轻视,对女性审美的固化,对女性思想的禁锢,从古到今未曾消失,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
四、受人类摆布的海湾小镇
二元对立使得白人男性的人类身份分离并高于女性、有色人种、动物和自然世界[5]11。由此,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便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而格里芬和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都认为,女性与自然在西方男权文化中由于共同受到压迫,而绝非生物学或本质性身份才构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特殊的亲密感[6]。
克劳斯比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着许多家族的荣耀,亨利夫妇就坚信,自己的苏格兰祖上凭借顽强和坚韧曾在这里生存繁衍。对他们而言,小镇不仅有迷人的郁金香花海,有浓密原始的树林,更有平静威严的海湾。这样的环境赋予小镇居民心胸开阔、淳朴自然和乐观坚强的品质。这些特征无一不包含着人性的光辉和母性的情怀。《涨潮》讲述了功成名就的精神科医生凯文回归小镇寻找自我的故事。在辗转了纽约、达拉斯、芝加哥等许多城市后,他回到家乡。波光粼粼的海湾、巨大的花岗岩、山谷的野百合都在,更重要的是,穿着长裙的昔日女伴,依旧大嗓门的基特里奇太太,都回来了。于是,童年那些不快乐的事实现在却如同他记忆中的甜蜜恋情一般攫住了他的心。如果说这片海湾赋予了凯文重生的力量,那么同样赋予奥丽芙坦然面对死亡的力量。《河流》中,丈夫去世后的奥丽芙百无聊赖的生活着,生命之河似乎没有了流动的迹象。一次偶然机会,她帮助了患急症的孤独老人杰克。当被需要的感觉重新回到体内的时候,她重新审视这片海湾,找到了春的希望和味道。可以说,女性作为生命的孕育者和抚育者,她忠实于自己的身体经验,对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拥有贴肤般的感受,女性和大自然的完美融合是那么的神奇。因此,阿里尔·萨莱(Ariel Salleh)指出,尽管男性和女性都拥有历史塑造的身份,但在生态遭到破坏的时代,女性化的身份明显代表更为健康的人类态度[7]。
无论人们多留恋海滨小镇的淳朴和温暖,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份子,不可避免的遭到金钱和欲望的玷污与毁灭。奥丽芙曾经犀利的断言:“我们正像罗马人一样走向毁灭,美利坚是块发霉的大奶酪。”[1]9祖辈留下的清教传统代代相传,但经过岁月的洗礼,信仰渐趋衰微,连每周一次的礼拜仪式都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慰藉。伊拉克战争以及9.11事件似乎并没有给克劳斯比带来表面的变化,但内心的渴望、冲动夹杂着浮躁和恐惧使得小镇的每个家庭都充斥着不安的情绪。《瓶中船》中的四口之家可谓典型,多年质朴简单的渔民生活无法安抚躁动的心灵,柴米油盐的日子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安守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已属奢望。《殊途》讲述了奥丽芙夫妇遭遇的危机事件。情急之下的真实反应给双方留下了无可弥补的心灵伤痕。的确,美国发达的危机咨询行业可以帮助缓解交通事故、校园枪击带来的恐慌,但由此失去的人与人间的关爱、尊重和信任又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呢?
海滨小镇依旧带着清丽的风光,但住在这里的女人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她们担忧丈夫对自己的不忠,孩子长大后的远走高飞,现代人无法遏抑的欲望带来的种种生活危机。人类征服自然、创建文明的历史,同时就是征服、控制和改变女性的历史。女性就如同文中的海滨郁金香一般,尽管依旧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繁盛和旖旎,但在充满孤独、寥落和忧伤的人眼里,它竟盛开得如此“荒谬”。
在斯特劳特笔下,海湾小镇中非人类的自然景物莫不烙上了人类或干预、或破坏等种种自以为是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男性自私任性地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颐指气使如出一辙。对男性中心主义而言,为了构建独立的自我意识,一切异于“自我”的特征都被视为“他者”而加以贬抑、异化和控制。因此,自然和女性一样,被置于边缘的地位[8]。不可否认,在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统治早已根深蒂固。小说中描述的克劳斯比的变化必然对改变人与自然以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
五、回归海湾回归和谐
《旧金山纪事》曾这样评价女主人公奥丽芙:这位风趣、睿智而心怀伤感的女士是一股鲜活迫人的生命力,一位活力四射的奇人[9]。除了鲜活逼真的性格外,她更是一位经历了种种无奈、痛苦、纠结后,与生活握手言欢的智者,虽然笑中带泪,但不乏勇气和希望。海湾小镇虽然失去了可贵的纯真和自然,但依然是游子们眷恋的故乡,奥丽芙们得以终老的乐园。这是斯特劳特试图通过小镇女性和身边的这片海湾传递的可贵正能量。
女性在追求与男性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做出的反应、改变甚至抗争显得尤为重要。或许是沉默和逃避、或许是反抗和对立、或许是做出坚持下的改变。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意识带给女性的压力从未减少,在当代社会,似乎以更隐蔽但伤害性更大的形式迸发出来。身处弱势地位的女人需要以乐观和自嘲的心态来面对。奥丽芙在面对精神出轨的亨利时,用一贯的强势口吻和淡化处理的方式让亨利不得不放下这段无疾而终的情感;在发现亨利始终对经历的危机事件无法释怀时,她结婚以来第一次向亨利说抱歉;在经历了与第一任儿媳的不欢而散后,她讨巧地远赴纽约帮助第二任儿媳照看孩子。当然,期间遭受的煎熬、委屈和痛苦只有自己知晓,但退让似乎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如果说圆滑和迁就只能获得表面的平和,那么只有坚持和改变才能获得更深层次的幸福和权利。奥丽芙尽管性格直率,但她善良、真实、友爱,所以多年前的学生凯文归来后依然能从她身上找到故乡的淳朴气息,初次谋面的妮娜就信任地躺在她的腿上哭诉心事。相信人类共通的这些最宝贵的品质赋予了奥丽芙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而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改变,奥丽芙曾感慨自己是只田鼠,“而前面有个越转越快的球,她拼命地想爬到球顶,于是用尖利的爪子抓狂乱扯,但还是怎么也攀不上去”[1]127。当改变了自怨自艾的心态,豁然于短暂生命的当下,就可以恬淡、平静地去帮助他人,不去计较生活已然夺去了自己多少东西。于是,奥丽芙以这样的心态收获了自己的黄昏恋情。
生态女性主义的中心议程就是要实现个人、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改变——特别是这个改变能够提高女性与自然的文化地位[5]132。以奥丽芙为代表的当代女性经过痛苦的自我挣扎、自我认识和自我调整,收获了与男性平等对话和平等选择的自信和能力。期间,依仗生命中共通的底色——善良、信念、希望和爱,男性和女性有了相互珍惜、相互谅解的可能。当然,在试图克服二元论文化思想时,一定避免进入把女性/自然与男性对立起来的新误区。斯特劳特在这个问题上给了读者一个较为中肯而可行的出路。女性在对逝去的美好与纯真充满留恋和怅惘的间隙,也能真挚地去关注身边的一朵小花,一抹绿色。宽容但坦诚的海湾以无声的方式告诫人类,失去的已然失去,而未来却无法预见。这样看来,生态女性主义的确不像激进的女性主义那样过分强调女性视角的优势,而是以广阔的胸襟吸纳多样的声音并支持个性的张扬,以期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10]。
六、结 语
小说自始至终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但奥丽芙从未跳脱出大家的视线,她坐看潮起潮落,静观人生悲欢,品咂自家生活滋味的同时,对当代女性的生活处境和获得幸福的途径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这种通过女性视角在静默的人生中自发地去寻找自我救赎的意图令人赞赏。
身为女性作家的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在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母亲,她施与生活魔法,是我所认识的最会讲故事的人[1]。从更广泛意义而言,它可以献给所有自强而乐观,小心翼翼而又义无反顾的前行在追求平等、和谐的生存环境中的女性。
21世纪是倡导生态和谐的世纪,也是生态女性批评风起云涌的世纪,如《奥丽芙·基特里奇》般饱含人文情怀的作品必然给奔波的世人带来无限慰藉和希望。
[1]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奥丽芙·基特里奇[M].张芸,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
[2]Warren,K.J.Ecofeminist Philosophy: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Lanham:Rowman &Littlefield,2000.
[3]Lear,L.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M].New York:Henry Holt,1997:33.
[4]Griffin,S.Woman and Nature:the Roaring Inside Her[M].SFO:Sierra Club Books,2000.
[5]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M].蒋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King,Y.“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M].Ed.Judith Plant.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89.
[7]Salleh,A.“Class,Race,and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Ecofeminism/Deep Ecology Debate”[J].Environmental Ethics,1992,14(3).
[8]王文惠,曾敏.追寻生命和谐的精神家园——《又来了,爱情》的生态伦理启迪[J].外语教学,2012(1):93-95.
[9]Strout,E.Olive Kitteridge[M].New York:Random House,Inc,2008.
[10]陈伟华.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一种新的伦理秩序[J].湖北社会科学,2011(11):107-109.
Returning tothe Essential Life——An Eco-feminist Approach to Olive Kitteridge
LIU Qing1,GONG Yu-bo2
(1.Foreign Languages School,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 100091,China;2.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Elizabeth Strout's Olive Kitteridge has captured much critical attention with its novel form,plain style and universal theme of matrimony.Much 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novel deserves readers'special note.Thirteen seemingly independent short stories are actually interconnected,tying women's fate with men's and nature,and disclosing women's sufferings inherent in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patriarchal culture.The novel explores their inner respect and reverence towards life itself by depicting the sorrows and joys of common people.The author hopes to guide women in their pursuit of self-salvation and on their way to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gender relationship by deconstruct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androcentrism.
Olive Kitteridge;Ecofeminism;Androcentrism
I106
A
1001-6201(2014)03-0144-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2014-03-2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09JBZ022)。
柳青(1974-),女,天津人,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讲师;宫玉波(1967-)男,吉林白城人,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