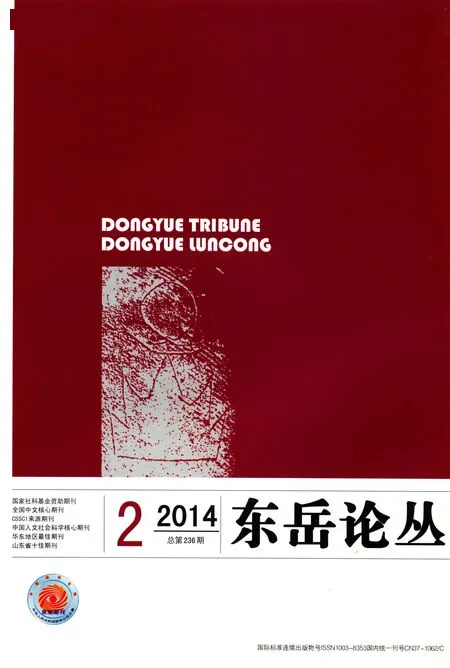早期客卿考论
王玉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客卿在战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对战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秦国完成统一,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①黄冬云:《战国客卿制度刍议》,《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秦国客卿作为战国客卿的典型代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翔实②丹秋:《秦客卿考》,《文化建设月刊》1936年6月第2卷第9期;严耕望:《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责善半月刊》1942年第20期(现已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李福泉:《秦国客卿议》,《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黄留珠:《秦客卿制度简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孙铁刚:《秦国与客卿》,《周秦文化研究》编委会:《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865页;袁礼华:《秦客卿制述论》,《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但是关于客卿制度的起源问题,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文章专门探讨。理论上,一项政治制度的形成一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演生过程,客卿制度当然也不例外。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究客卿制度的源头——早期客卿的发展形态问题,即早期客卿存在的理论依据、早期客卿形成的历史条件与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一、早期客卿存在的理论依据
(一)客卿广、狭两种定义的关系。讨论早期客卿存在的理论依据,首先要搞清楚客卿的概念。客卿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定义。对此,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中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说:“客卿有广狭二义。……客卿乃一特定之官名,专为位置某种诸侯人之来仕于秦者而设,而非泛指一切为客于秦之诸侯人甚明。……此狭义之客卿也。至广义之客卿,则不限于有无拜为客卿之事实,举凡诸侯之人不产于秦而来仕于秦者,皆得名之曰客卿。”③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1-942页。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以秦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因而他对客卿的定义也基本上以秦国客卿为主。事实上,通过《秦集史·秦客卿表》可以看出,客卿不仅存在于秦国,东方诸侯国如齐、燕、赵、韩也有客卿①马非百:《秦集史》,第941页。。马先生的狭义客卿定义和宋元之际胡三省对客卿的定义大致相同。胡三省认为“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显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页。若不拘泥于秦国,狭义的客卿就是本国对异国来仕之人专门设立的一种地位较高的官职,其位相当于卿一级官员。按照狭义的客卿定义,客卿就是为吸引外来人才而专门设立的一种官职,它只存在于战国时期。若以广义的客卿定义,举凡来本国做官的异国人都是客卿。若依后者,客卿就不仅存在于战国时期,起码,春秋时期广义的客卿数量就相当可观。单就春秋大批出奔贵族而言,绝大多数也属于广义的客卿。部分学者遵从客卿的狭义定义,主张客卿仅仅存在于战国时期,战国之前无客卿③黄留珠:《秦客卿制度简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孟繁峰《论客卿》,《史学集刊》,1987年第3期。。而大多数学者论及秦客卿之时,往往依据广义的客卿定义,将秦国客卿追溯到春秋时期。这种分歧的关键就是,没有处理好客卿广、狭两个定义的关系。实际上,两个定义非但不矛盾,而且还有一定的逻辑联系。狭义的客卿应该由广义客卿发展而来。广义客卿是客卿演生过程中的发展阶段,狭义的客卿乃是客卿发展的成熟阶段。较之狭义的客卿,早期客卿的发展形态肯定不成熟,概念上就应该遵循相对不太严谨的广义的客卿定义。
(二)客卿的二元因素。不论是广义的客卿还是狭义的客卿,客卿都具备二元因素:①于某一政治实体单位来说,必须具备“客”的属性;②“客”还要担任该政治实体单位的官员。前者是必要条件,没有客的属性就谈不上客卿;而后者则是充分条件,客还必须拥有一层政治身份——官员,客不是官员,则终究是客,而非客卿。狭义客卿的前身是广义的客卿。
古人称亲戚多指有共同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亲属,包括父族和母族④关于亲戚包括父子兄弟之论,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亲戚”条有较为缜密的论证,详参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6年版,第1347页。。上古之人多聚族而居,父子兄弟朝夕相处,其间往来,不应称为客。因此,“客”之中就排除了父族。那么,“客”就仅指具有婚姻关系的母族和朋友,即异姓群体。“客”最初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界限。质言之,父系以外的群体即是“客”。但是这种家族间交往的“客”仅仅是礼尚往来之“客”。“客”只有在具有政治属性的实体里才能具备客卿的二元属性。家族发展到宗族才有政治属性。晁福林先生指出“宗族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与政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⑤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此说极为精辟,因为宗族中原始的宗法制原则业已产生了凝聚宗族的作用。宗族有自己的祖先和姓氏,这两个特征足以证明宗族成员有自己的认同感⑥田昌五先生对宗族的五个基本特征曾有专文论述,详见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212页。又,田昌五、臧知非合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此亦有涉及,详见该书第23-26页。。但是,宗族诞生之初,客卿却很难产生。宗族诞生初期,规模较小,在地域上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有着共同经济单位的村落⑦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绪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最重要的是,早期宗族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官僚系统。因此,早期的宗族,仅有客,而没有客卿。宗族发展到部落(姓族)或部落联盟时,早期客卿也没有产生。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制虽有了早期国家的雏形,但是联盟的领导权并非一姓专有,而是采用具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禅让制,即首领由几个大的部落(姓族),如陶唐氏、有虞氏以及夏后氏轮流担任。联盟的部分官职也是由各个姓族的首领担任,如《尚书·尧典》中提到的舜命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禹为“司空”,皋陶为“士”等等。同在一个联盟之下,族与族之间的人员往来很难说是客卿。宗族只有发展到更高一级的一姓专有的早期国家,相对完备的官僚系统诞生之时,早期客卿才有可能诞生。
夏代是公认的第一个一姓专有的早期国家。夏后氏与其他姓族虽然也有联盟关系,但是这时期的姓族也有了独立性,即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套官僚系统。因此,这些姓族或部落又称为“方国”。其他异姓部落虽然服膺夏后氏,但是夏后氏对他们的控制却相对有限①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方国的独立性使得早期客卿有了诞生的可能。如陶唐氏后裔刘累曾学扰龙术,事夏后氏孔甲,孔甲赐其御龙氏。“命氏”也意味着“胙土”②《 左传·隐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而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可见胙土与命氏乃同一过程。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61页。,即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分封。被夏后氏命氏的刘累,显然是供职于夏后氏。夏、商都是方国联盟性质的国家,方国与夏后氏、殷商之间的政治属性的人员往来,不但规模小,而且还有不少的原始性。大规模、真正意义上具备客二元因素的早期客卿应该在西周初年,周公创立宗法分封制之后。
二、西周早期客卿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征
(一)早期客卿形成的历史条件。前已述及,夏、商时期的早期客卿还相当原始,真正具备二元因素的早期客卿在西周初年才得以形成。西周早期客卿的形成是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
第一,殷灭周兴,朝代更替,殷商旧政权中的异姓贵族纷纷投靠新兴的西周政权。殷周之际是剧烈变革的时代,殷商的覆灭使得许多为殷商服务的官员被新生的西周政权所吸收。胡新生先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一文详细考证了以史官为代表的殷商官员,在殷灭周兴之际,转而为西周政权服务,并为商周文化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史实③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这些原来服务于殷商政权的异姓史官,在殷商覆亡之后,继续在西周政权中担任史官。按照我们对早期客卿概念的界定,殷灭周兴之际的史官大多也属于此范畴。
殷灭周兴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独史官,原殷商政权中的其他官员,继续转而为周政权服务的,也必不在少数。比较典型的就是殷太师、少师在商纣淫乱不止、不听劝谏的情况下,“持其祭乐器奔周”④《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8页。。《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曰:“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⑤《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第2123页。“天下宗周”即暗含了原来服从、服务于殷商的异姓官员,转而为周政权服务的人数之多。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也反证了殷商旧官员纷纷投靠西周政权的事实。这一部分殷商旧官员,于姬周政权来说,多为异姓,明显地是以“客”的身份出仕西周政权。甚至到了春秋时期,微子建立的宋国仍然认为自己“于周为客”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第1459页。。种种迹象表明,殷商的覆灭,客观上催生了早期客卿。
第二,宗法分封制国家的形成。夏、商是方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方国或姓族与夏后氏、殷商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周初至武王时期亦然。晁福林先生指出,“武王所走的依然是传统的路子,竭力以周王朝为核心组成新的方国联盟”⑦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第397页。。武王以及殷商、夏后氏诸君与各方国之间的关系乃是“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⑧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6-467页。。而周公创立的宗法分封制使得周天子与诸侯形成了牢固的君臣关系。周公创立宗法分封制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才诞生。宗法分封制创立之后,原来服务殷商的异姓官员也被纳入宗法分封制当中,成为西周政权之下的卿大夫。异姓官员不仅具备了客的属性,宗法分封制最终使其成为广义上的客卿。
第三,“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得社会上只有贵族群体才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原来偏居一隅的西周姬姓贵族来说,无论在执政经验,还是文化知识上都无法与殷商的贵族官员相比。故周公在洛邑建成之后,对殷商之“多士”训话时,曾自称“我小国”,而称呼殷商为“天邑商”。“多士”即指殷商的上层贵族。周公在《尚书·多士》中明确表示:“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只有服从、臣服西周的殷商贵族,才能保有土地,安身立命。值得注意的是,周公还提出,对于这些殷商贵族,西周政权将“惟听用德”。对于优秀的殷商贵族,西周会像商汤任用夏后氏遗民一样“简迪在王庭,有服在百僚”①《尚书·多士》,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26页。。对于服从西周有德才的殷商贵族,周公明确要委以官职重用。这说明,早期客卿的形成有现实的需求。
(二)早期客卿的特征。与春秋客卿以及战国客卿相比,早期客卿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早期客卿主要是异姓贵族,且多与姬姓贵族有联姻现象。
除了异姓史官,以金文为主的出土文献还为我们提供不少异姓家族担任西周政权其他官职的例子。曹玮先生提出了判断金文中异姓或姬姓的三个标准,即①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是姬姓或者是异姓的属国或族;②按照古代“同姓不婚”的原则判定姓氏;③凡是祖、父以及作器者本人的名字为日名的便是异姓②曹玮:《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按照这个标准,曹玮先生从金文中列举了居住在周原的十个异姓家族。这十个异姓家族中大多是贵族身份。其中,梁其氏官至膳夫,为“邦君大正”,微氏家族为王朝史官。微氏家族世代为史官,胡新生先生已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克氏诸器与梁其氏诸器同出土于陕西扶风任家村,朱凤瀚认为“梁其当是克之后人”③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341页。。据师克盨铭文记载,克之“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捍)害王身,作爪牙”,周王令克“嗣左右虎臣”④《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师克盨》4467,第528页。。陈梦家先生认为此“虎臣”乃“侍于王左右之官”⑤陈梦家:《西周青铜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6页。,即周天子亲近侍卫之官。大克鼎铭文追述克之祖师华父“肆克 保厥辟恭王”⑥《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2卷,《大克鼎》2836,第409页。,华父曾在恭王时期担任师职。据周代世官世禄的原则,华父家族在周恭王以前极有可能也担任师职。同处于克家族窖藏的善(膳)夫吉父鬲曰:“膳夫吉父作京姬尊鬲。”⑦《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1卷,《善父吉父鬲》701,第535页。吉父属于克家族,克家族与姬姓存在世代通婚的现象。理论上,克家族属于早期客卿。与史墙盘同出一窖的还有商尊、商卣,商尊铭文曰:
隹五月,辰才(在)丁亥,帝后赏庚姬贝卅朋,……商用乍(作)文辟日鼎宝尊彝。⑧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符号乃商遗民族徽⑨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63页。,“庚姬”即谓嫁给庚氏之姬姓女子,庚为天干日名。显然,庚氏乃商族后裔。早期客卿相对于姬周贵族来说,皆是异姓贵族。宗法制行之同姓的同时,异姓则以联姻的形式,被纳入其中,作为宗法制的外延。金文资料还透露出一个关键的信息,即早期客卿大多与姬姓贵族存在世代通婚的现象。周原中的克家族、庚氏家族与姬姓贵族都存在联姻现象。至春秋时期,周王畿之内的阳人尚言阳邑之中“皆天子之父兄甥舅”⑩《国语·周语中》,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5页。。“甥舅”当指早期客卿与姬姓贵族联姻者。由此也可以看出,早期客卿与姬姓贵族的联姻具有普遍性。有学者就认为甥舅关系实际上也属于原始宗法制的内容之一⑪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世族制”,第148页。。此说颇有见地。甥舅关系是姬姓宗族与异姓宗族关系的外在表现,早期客卿以甥舅的身份架构在姬姓宗法制之上。周人将这些入仕西周的异姓贵族拉入宗法制系统之内,更强化了对早期客卿的控制。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创新。与战国客卿相比,早期客卿还保留着浓厚的血缘色彩,这也彰显了早期客卿的原始性。
第二,西周早期客卿的任用被纳入到分封制内爵系统。
周代分封制中的内外爵系统是由殷商内外服制发展而来。《尚书·酒诰》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⑫《尚书·酒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78页。内服百官中既有同姓贵族,亦有异姓贵族。显然,“百姓”中当即包括异姓贵族。换言之,商代将早期客卿的任用纳入到了内服制当中。周代宗法分封制吸收了商代的内外服制,发展成内外爵两套系统: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①《新书·阶级》,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页。。通过上文西周时期异姓贵族出仕早期客卿的例子可以看出,西周统治者将早期客卿的任用纳入到了内爵制系统当中。若我们的探讨仅停留在此的话,那么殷商对“百姓”的任用与西周早期客卿并无二致。但是殷周两代的更替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王国维先生著名的《殷周制度论》宗旨就在于揭橥殷周之际的巨变②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第451-480页。。周公创立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是西周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作为分封制的一翼,内爵公卿大夫士也寓于宗法制之中。对此,前文已经述及。以上金文中的克家族、庚氏家族不仅是西周政权的畿内诸侯,而且还大多与姬周贵族联姻。这是与殷商任用异姓贵族所不同之处。不仅如此,西周姬姓诸侯国同样也广泛任用异姓贵族担任官职。
早期客卿不仅仅服务于周王室,在姬姓诸侯国内担任官职的也不在少数。周公东征之后,周公将殷商遗民各宗族分封给鲁、卫、晋等国。《左传·定公四年》曰: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③《左传·定公四年》,第1536-1539页。
鲁、卫、晋所分配之殷商旧族都是以族为单位,宗族组织完整。这些殷商旧族当然会有不少贵族以及官员,其中分封给晋国的“职官五正”很可能就是殷商管理怀姓九宗的官职。至春秋初年《左传》中仍有“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的记载④《左传·隐公六年》,第49页。,这是九宗五正之官继续保留在晋国之明证。九宗五正本是管理殷人的组织,唐叔分封晋国后,九宗五正之官应当继续由殷人担任。若此,九宗五正之官在理论上也属于早期客卿。另外,周公在分封康叔时,告诫康叔赴卫国后,要“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广求“商耇成人”⑤《尚书·康诰》,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商耇成人”即殷商富有治民经验的族长或官员。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周公有意让康叔继续任用殷商旧族贤人担任卫国官职。若这个推断不错,理论上,卫国也有早期客卿。鲁国的殷民六族“职事于鲁”,意味着他们继续服事鲁国。殷民六族中的贵族出任鲁国官职,也可以算作早期客卿。鲁、卫、晋虽无出土文献证明早期客卿的存在,但燕国的早期客卿却存在于出土文献当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早期燕国墓葬中就有早期客卿出仕燕国的记载。复作乙鼎铭文曰:
匽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作父乙宝尊彝。⑥《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复作父乙鼎》5978,第527页。
同出一窖的复鼎铭曰:
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作父乙宝尊彝。⑦《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2卷,《复鼎》2507,第253页。
从出土地来看,匽侯当即燕侯,即燕国国君。复为其父亲父乙铸两鼎。从复父亲的名字上看,复家族当是殷商旧族,铭文末的“ ”字符号也证明了这一点。从铭文上看,复家族与燕侯关系密切,应该是燕侯属下的官员。再从墓葬的规模上看,更可以断定复家族的贵族身份。理论上,复是燕国的早期客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西周初年,西周政权以及姬姓诸侯国中的确存在着不少早期客卿的踪迹。
西周时期的早期客卿大多供职于两种机构:一是直接服务于宗周政权;二是供职于各姬姓诸侯国。前者可以视为服务于西周中央政府机构,后者大致也可以看作供职于地方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西周各级行政机构遍布早期客卿的活动踪迹。这一信息也透露出,西周政权大规模启用异姓贵族并非权益之策,很可能是独居匠心的安排。
三、早期客卿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首先,周人将早期客卿纳入宗法分封制,不但稳定了社会局势,而且还创造性地改造了社会组织结构。武王灭商之后,社会局势并不稳定。《逸周书·度邑》指出了武王担心的问题:“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成,用戾于今。”①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501页。“三百六十夫”指殷商贵族贤人众多。西周政权只有安抚好这一部分人,社会才能稳定。武王没来得及进行社会改革,即在灭殷之后不久去世。武庚以及东部徐、奄叛乱,即是西周政权没有安抚好殷商贵族的缘故。周公东征之后,开创宗法分封制,将服从西周的殷商贵族纳入其中。这些早期客卿大多世代担任王朝卿士或姬姓诸侯国公臣,并且多与姬姓贵族有联姻现象。因此,早期客卿及其宗族也被纳入到了西周宗法体系之内。从某种程度上说,早期客卿及其家族逐渐被周人的宗法制文化所同化。正如朱凤瀚先生所言,周人对殷商贵族的成功处置,“实是周人对旧有社会组织结构改造中的最重要一环”②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286页。。
其次,早期客卿促成了周代文化的融合。三代文化,周文化水平最高。故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③《论语·八佾》,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周代繁盛的文化并非自发生成,而是“监于二代”,即吸收了夏、殷二代的文化精华,祛除了糟粕性的方面,在“损益”的基础上诞生的。而担负周代文化融合使命的恰恰是那些曾经服务于殷商政权的异姓贵族,亦即本文所谓的早期客卿。胡新生先生探讨的周代异姓史官即是早期客卿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以异姓史官为例,早期客卿将先进的殷商文化甚至是夏代文化引入西周社会,在西周文化的交融下,两种文化相互“损益”,最终实现了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融合。套用胡新生先生的观点,早期客卿的家族在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的形势下,大规模迁徙各诸侯国,并将周代文化传播到各地,“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不再具有‘族类’外观的真正统一的华夏文化”④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再次,早期客卿是春秋战国客卿的源头,从早期客卿到春秋客卿,再到战国客卿,其间的发展脉络清晰可循。相对于春秋战国客卿,早期客卿具有原始性,即带有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浓厚的宗法血缘色彩。姓氏是区别早期客卿与姬姓官员的主要标准。早期客卿与春秋客卿一样,都没有专门的官职,属于广义上的客卿。但是与春秋客卿相比,早期客卿一旦被西周政权任用,其家族往往能够世代保有固定的职位,即所谓的“世官世禄”。到了西周末年,王纲解纽,随着诸侯国日趋独立,国与国之间的人才交流更加频繁。早期客卿的宗法血缘色彩逐渐淡薄,在春秋时期逐渐发展成以地缘差异——国别区分为主的春秋客卿。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早期客卿脱胎换骨,在春秋时期日渐带有集权官僚制的色彩,即春秋客卿已经不在世代居有固定的官职。正如学者所言,春秋客卿执政的时代背景就是列国君主引入客卿对抗国内宗法贵族⑤严耕望:《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载于《严耕望史学论文集》,第3-7页。。春秋客卿正是去宗法化的产物,列国大量启用春秋客卿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君权。但是,理论上,春秋客卿也是广义的客卿。从春秋到战国,客卿逐渐从广义客卿过渡到狭义客卿。到了战国,客卿才真正发展成一种专门为吸收外来人才而设立的官职。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春秋客卿还是战国客卿,其源头都是西周时期的早期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