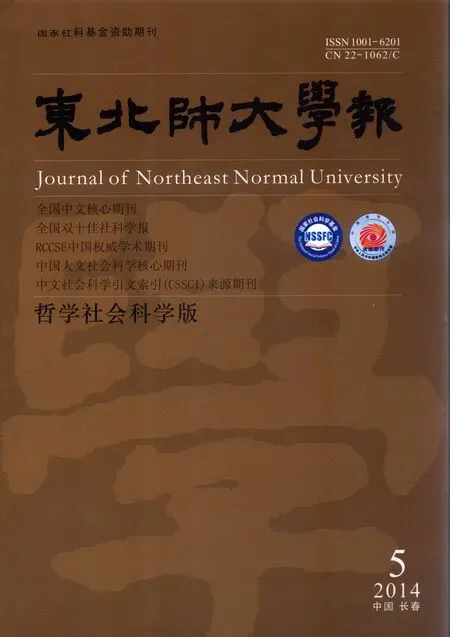改革文学中的代际冲突模式研究
苏 奎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一
父辈与子辈的代际冲突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不同时空背景下父、子分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代际冲突也承载了人类的不同情怀。出现在文学中的父与子之间的亲情关系,与他们相异的文化、历史价值负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父与子交流的平台虽然还是家庭,但他们之间的对话却超越了家长里短。“文学作品中的父子角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血缘上的父与子,在具体性的父子冲突背后往往蕴含着超越性的结构。”[1]父辈代表着一种先在的权力、既定的秩序与不可动摇的权威,子辈则是以秩序与权威的挑战者身份出现的,作为叛逆者他要打破一切业已僵化的思维、观念与制度,按照自己的价值理想建造一个新世界。其实,人类的文明史究其本质就是代际冲突的历史,如果在朝代的更迭、体制的变迁、价值观念的革新的进程中,缺少了否定质疑的勇气与力量,就不会有社会历史的前进。代际冲突“是人类发展的内驱力之一。如果没有代际差别,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难出现本质性的飞跃”[2]。所以作为可以永远阐释的话题,代际冲突会伴随文学的始终,尤其是在对转型期社会图景的建构上,这一隐喻模式有着明显的优势。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透视了男人在儿童时期,就具有的恋母弑父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导致了代际之间关系的紧张。所以,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只不过具有表现形式的隐显差异而已。在共同的心理机制下,作家的创作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使文本更容易被接受。同时,子一代对旧有东西的叛逆,也迎合了他们对新世界的渴望与梦想,这一模式的强烈鲜明的指向性为其赢得了受众的认同。
新文学的倡导者高举革命的大旗,上演了一出“弑父”的大戏,终结了古典文学的狭窄视野与单调题材,推动了文学思维观念的现代化。同时,用代际冲突来表述破旧立新的社会转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建构的普遍性选择,保守与革命、腐朽与新生、传统束缚与民主自由等等,在思维观念与价值立场冲突剧烈的时代,这一模式有着天然的表达优势。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与高觉民、高觉慧之间束缚与反抗、遵从礼教与封建叛逆的两极对立,是传统家族制度、家长制度、专制制度遭遇现代自由观念挑战的体现。高觉慧一类的叛逆者形象不仅宣告了旧有制度的反动,也昭示了开创一个新世界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逆子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生命力勃发的觉慧与行将入木的高老太爷之间的代际间的较量,虽然过程会充满曲折,但结果一定是子辈战胜父辈,僵化的体制与观念必然被现代化所取代。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寻求个体与阶级解放的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以代际冲突来展现革命斗争潮流,是左翼文学中常见的表述模式,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是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文学图景中的代际冲突“农民父亲最先怀疑甚至阻挠儿子们的革命行动而形成父子间的冲突,而最终又在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皈依了儿子的反抗道路,使父子间的冲突得到和解。”[4]这一叙事指向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特色,也基本能够涵盖革命潮流对中国人精神心理的革新,唯有如此才能由自发革命转向自觉革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有着决定民族走向的影响与意义。“文革”被视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重演,传统中的诸多负面力量借机复活,阻碍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只有革除掉这些负向的羁绊,承载民族复兴的梦想之舟,才能驶向现代化的彼岸。所以,改革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描述改革的文学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改革不仅要设计并论证现代化的行进路径,而且要摆脱旧有的沉重负担,后者往往要比前者更加消耗改革者的精力。相应地,在改革文学中,对于“沉重的翅膀”的叙述是一个普遍性的主题,甚至会占去作品大部分的篇幅。保守与改革、落后的现状与现代化的梦想之间构成了强烈的冲突,而在对两者斗争多样性的隐喻表达中,代际冲突被广泛地采用。“‘改革文学’常常以‘保守/改革’的对立模式来蕴含着‘传统/现代’的历史分野,显示出‘告别过去’的决绝。”[5]代际冲突成为改革文学的主要表述模式,一方面这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也展现出了转型社会的特有样貌,父辈的守成与子辈的创新,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二
改革是一场波及整个社会的运动,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集体都会在遭遇冲击与震荡后,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与方向,寻找新的坐标。个体选择的差异性会使家庭与集体分化,会使不同价值取向的思维观念剧烈地碰撞。即使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一旦对于改革的观念存在冲突,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立的价值立场,两者之间思想意识的异质性相当明显。
在改革语境中,子辈的价值内涵比革命叙事中体现出来的有所丰富,他们不仅有着符合社会前进方向的进步性、参与时代发展的热情与力量、执着的信仰与奉献精神,而且有着现代化的宽广视野。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亮色,也是民族复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代表着未来。如果说子一代形象较之既往并无太大变化,那么父辈形象的性格内涵则更为复杂,他们保守、落后,顽固地保持现状,甚至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代际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子辈胜利的结局模式清晰地体现了小说的立场与时代的希冀。张锲《改革者》中的魏寰不仅支持父亲的“政敌”,而且以告状的方式控诉父亲魏振国的保守与不作为。按照世俗眼光看,魏寰似乎算不上一个“正常”的人,然而,对于现代化事业的信仰,使他超越了亲情的局限,把改革与民族复兴作为自己行为的唯一旨归。《竞争者》中两代人——同为工厂领导者的叔叔季国雄与侄子季明——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表现在领导组织现代化生产的能力上。在小说展现的这场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结局的竞争中,父辈因为过时而被淘汰,子辈因为新锐而被肯定。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充满了对新的渴望,其中,新人是改革极力呼唤与期待的。能不能以新人代替“旧人”关系社会转型的走向、改革的成败与民族的未来。所以出现在改革文学中的新人形象,虽然都有旧时代的成长经历,但是他们有能力摆脱历史的阴影,成为被寄予改革希望的群体。在改革文学中,老一代成为赞赏肯定新一代的背景,子辈在克服父辈的压制下成长起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是对代际冲突模式的一种泛化。虽然作家没有把冲突双方直接标示为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但是无论在年龄、观念,还是在价值立场等各个方面,他们之间都具备了构成代际冲突的要素。
没有对“出身”及生命道路的否定,就不会获得新生,转型时代为子一代提供了叛逆的契机。蒋子龙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描述了青年人解净与老一代祝同康之间的代际冲突。解净信服、认同,甚至崇拜过祝同康,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曾经是她精神上的父亲。在这一情境下,解净以实际行动对保守落后的祝同康的背弃,也就具有了“弑父”的象征意义。父辈总是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框式去培养子一代,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强烈的自我认同,一方面也是他们顽固地保持现状、维护权威的体现。父辈僵化的意识本身就决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当然,这种矛盾纠葛会因为双方身份地位的悬殊而表现出复杂性来。父辈的权威一时还难以动摇,在民主机制尚不完善之际,子一代的叛逆挑战之路必然会坎坷不断。子一代的成长、壮大,以及获得群体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享有权威的父辈与有待成熟的年轻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注定了改革起步的难度。
在代际冲突中,权力成为一个焦点,没有权力的保障,改革便显得举步维艰。乔光朴之所以能大刀阔斧地厉行革新,莫不在于他的厂长身份。同样的,《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与顾荣构成的代际冲突中,显出了对后者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态势。李向南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古陵县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并改变了顾荣多年精心建造起来的官场生态。在这场代际冲突中,顾荣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这种一边倒局面的形成,虽然有李向南作风硬朗、改革之心坚决、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等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是县委书记,是古陵县的一把手,手中有权。李向南对顾荣的胜利,最终还是权力使然,而一旦李向南碰到地委书记郑达理,他的困境马上就出现了。对于李向南来说,顾、郑两个人的唯一区别是官阶的高低,这一差异决定了他与这两人分别形成的代际冲突,必然会以不同结果而告终。与李向南回北京向外部寻求战胜郑达理的力量不同,《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只想依靠“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蒋子龙的叙事中,父辈与子辈之间具有社会性的冲突,却以解决家庭矛盾的方式平息,现代问题用传统方式解决,这明显地带上了转型期的时代特色。
三
随着改革文学的日趋成熟,代际冲突叙事逐渐摆脱保守与改革、落后与先进、一己之私欲与克己奉公等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对于生活复杂性的还原也使作家避免了明确单一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父与子作为家庭内部的个体,他们之间并非单纯的观念对立、权力争夺,血缘亲情、尊卑伦常等元素也影响着他们的冲突与融合。作为隐喻意义上的父辈与子辈之间,他们所代表的传统与现代本身就包蕴了复杂的特性,传统确实意味着保守、落后,但传统也有需要承继的东西,比如向善的人心与道德;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以商业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势必会使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加剧,从而使人、人际关系被异化。所以,在历史判断之外,还需要道德判断、文化判断等多元的衡量方式来看待代际冲突。这是符合现实的文学表达,是改革文学走向深入的明证,也体现了中国人对改革的态度已经由初期的狂热转为冷静的审视。
王润滋1983年发表的《鲁班的子孙》,是改革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代际冲突的形式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纠葛。首先,作为矛盾双方的老木匠黄志亮与小木匠秀川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秀川并非老木匠亲生,而是被后者收养的孤儿,两人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父子之实。如果说老木匠代表传统,小木匠象征了现代,那么在王润滋看来,这个现代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自身所生发出来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生活在一起的两者“相处”多年,但是因为没有共同的基因,无法从根本上做到血脉上的无间融合,现代身上的异质性因素从来都未曾被传统所同化。所以,一旦在传统的“母体”中“寄生”的现代遇到适宜的阳光、水分,就必然会脱离传统、背离传统,甚至颠覆传统。进城打工,对于小木匠秀川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此过程中,他寻找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那就是现代。在他的生命中,必然要有这样一个逃离乡村“养父”,寻找现代“父亲”的行为,舍此秀川便无法获得现代“父亲”的基因血脉,也不会获得与传统乡村相冲突的意识观念。所以,离乡——还乡对于秀川来说不仅仅是生活空间的变迁,行为理念与价值取向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更新。王润滋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了对现代化的理解,以及他的忧虑——没有传统的基因血脉且置传统于不顾的现代,会走向何方,又能走多远。
老木匠黄志亮从传统中走来,他把传统的道德良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作为社会个体虽然必然会有利益追求,但是当利益与道义相抵触的时候,黄志亮们会选择舍利取义。然而,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背景下,道德圆满的追求遭逢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现实的冲击,依然固守“道义”的老木匠的处境窘迫而尴尬。黄志亮和徒弟们经营的木匠铺的破产,一方面在体现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形式的破产,一方面也昭示了不做变通的道义观念的不合时宜。秀川毫无疑问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有见识有锐气,对于新工具新工艺敢于大胆地使用,能够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跟上改革的潮流。作家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展示了现代经营理念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农村想跟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需要有敢于打破传统僵化局面的弄潮儿。当然,秀川抛弃了道德良心的现代是残缺的,或者说他对现代的理解是生吞活剥的,只学到了皮毛而忽视了现代的精神内核。秀川与黄志亮之间的冲突,是文化的、道德观念的、时代更迭的冲突,究其根本是两种社会形态的冲突。秀川要打破老木匠坚守的那种最终会陷入集体贫穷的原始社会形态,并以商业关系建构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本质的关系是交换关系,检验劳动生产有效性的核心尺度是利益的获取,无法实现赢利,即使赢得了更多的口碑也是失败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生产目的来看,秀川的诸多行为就有了合理性。
商业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只是一个进程快慢的问题,就像暖锋与冷锋相遇必然会使天气异常一样,然而两种经济观念的更迭,势必引发观念领域的风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有景观。“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何看待经济活动,如何看待经济利益,这对一个社会的文明,不仅不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是整个价值观念系统的一个核心问题。”[6]王润滋并没有站在任何一边,在叙事中没有做简单下判断的意图,不论是老木匠还是小木匠都长短夹杂,同时这又使作家一直在理智与情感冲突中挣扎。王润滋创作意识中的这种矛盾特色,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斑驳复杂现实的浓重投影,也是民族整体心理的写照。作家选择以代际冲突的形式来表达对改革的认知,其实他的理想恰恰是父辈与子辈的融合,既保持讲求道德良心的传统取向,又要以现代来促动发展;既要摒弃保守落后的故步自封,又要对人罔顾诚信的贪欲加以约束。这种理想社会形态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律、制度,以及理想、信仰等等,都必不可少。重新思考王润滋提出的问题,在商品生产与交易的诚信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结 语
代际冲突模式,因为契合了改革文学的格局而被普遍采用,成为隐喻改革的一种主要方式。代际冲突表述内容的不断丰富是改革文学走向深入的一个表征。父辈与子辈对应的价值内涵,冲突的焦点、方式,以及作家情感偏向的变化,都标示了社会转型与改革文学的进程。当改革成为社会共识之后,那种以父辈与子辈的矛盾简单表述保守与改革冲突的叙事,就被作家抛弃了;当改革渴望遇到体制的障碍,权力便成了代际冲突的焦点;而一旦作家意识到即使赋予改革者以权力,似乎也无法解决所有阻碍改革的沉疴,关于代际冲突的叙事就会深入到精神心理、思维观念的层面;当改革在现代化轨道上的推进,越来越表现出割裂传统,甚至在利益的刺激下泯灭良心违背道德,《鲁班的子孙》这样的作品也就应时而生。对于转型社会来说,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对于改革文学来说,代际冲突是永远有效的表达模式。
[1] 陆雪琴.审父与训子的两难[J].浙江学刊,2000(6):95.
[2] 洪治纲.代际差别的凸现与文学的多元化[J].文艺争鸣,2013(8):38.
[3] 张伟忠.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J].东方论坛,1999(1):26.
[4] 王爱松,贺仲明.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78.
[5] 韦丽华.“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反思[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2):102.
[6] 宇文华生.论新时期小说中的经济意识[J].齐鲁学刊,198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