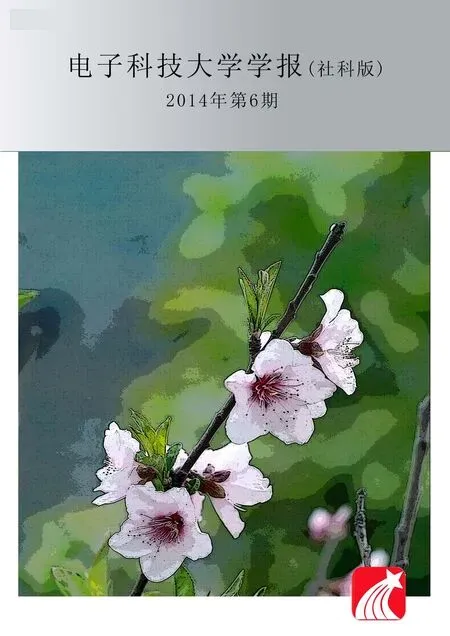论对失独者“代孕”行为的法律保护
□王 鹏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引言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各类突发事件和灾害对国家与家庭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其他国家相比,风险社会对家庭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的“计划生育”制度产生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这些子女一旦因风险性事件或疾病去世,常常会破坏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安定幸福,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据统计,我国每年约产生数十万个失独家庭[1],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安置等问题业已成为政府和社会亟待解决的议题。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对失独者关注的中心主要是“制度性帮扶”,而对失独者的“代孕”问题则研究不多。前者固然重要,但制度建设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政府的制度性帮扶与经济状况和财政收支有密切关联,所以缺乏稳定性。况且这也无法解决此类家庭长久的精神与心理问题,对当前“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造成了冲击。与此相比,更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予失独者以更多选择权,即在从经济上保障其生活与养老的同时,让其拥有更宽泛的“生育权”,尤其是对于无法生育的失独者而言,允许其代孕无疑是最好的出路,“给失独者留下后代才是最好的慰藉[2]”。但可惜的是,尽管当前学界对代孕已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讨论,但却对我国特有的、因计划生育而导致的大量失独者的代孕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以“失独”(或一孩,单核等类似词汇)和“代孕”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仅能得到8个结果;以“代孕”为关键词检索,并在其检索结果中以“失独”等进行全文检索,也仅能得到16个结果。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也基本上是把失独者作为代孕的众多研究对象之一对待,其解决方法也基本都是从改革代孕的整体法律制度入手。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方法的思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式”“出售”代孕权,未能根据代孕人群的特殊性进行分类,对失独者的特殊法律地位缺乏足够的关注。
从当前我国规范体系看,失独者相比其他特殊群体在代孕方面有更强的合法性,能够更好地得到法律的支持与合法性的证成。而且与上述“捆绑式”的思路相比,首先使对代孕有迫切需求的失独者的相关活动合法化,不仅能减少这一制度推行的阻力,也能为未来扩大该制度的适用人群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另外从实践中看,使失独者代孕行为合法化也有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当前已有大量失独者进行了“代孕”,但由于相关协议未能得到法律和司法支持,给其带来了重大财产损失[3]。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看,失独者的代孕行为都应合法化,其正当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一、失独者的特殊法律地位
如上所诉,在代孕方面,失独者与其他主体相比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法律地位是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综合”[4],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法律地位的表现,据此,可从失独者在法律上所应享有的权利来探讨其法律地位。具体看来,失独者与代孕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主要有再生育权、生存照顾权和继承权三种。
(一)再生育权
再生育权是失独者享有的首要权利。以“再生育”全文检索北大法宝“中央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数据库,能得到六十部中央法律法规和一千余部地方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对失独者的再生育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总体来看中央法律法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行政管理角度对失独者进行适当的照顾,如简化再生育行政审批手续、为再生育提供资金支持以及进一步明确再生育的条件等;二是从医疗科技角度规定对失独者进行技术支持,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第五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规定政府应提高相关技术水平;《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3条第2款规定政府应“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第八章序言规定政府应“免费提供再生育技术服务”,该章第二节更是将“再生育技术服务”细化为再生育医学检查等技术。地方法规规章则多为与中央规定相对应的具体的执行规范和细化规则。
尽管没有直接规定“代孕”二字,但这些规范在本质上包含了代孕这一行为,因为:首先从代孕的性质看,尽管其严格受制于国家,但根据公民“法无禁止即可行”的行政法基本原理,失独者有委托他人代孕的权利。尽管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办法》)第3条和第22条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并规定了处罚措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禁止商业化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以及商业化等限制性词汇反而为代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从立法目的和语义学角度看,上述法律是为了“优生优育”和科学管理人口,在此行政目标的涵摄下,“计划生育技术”就不可能仅仅是避孕技术,而应是对出生婴儿质量有利的人工受精、胚胎移植以及代孕等多项技术之和。总之,国家不能否定公民的再生育权利[5],而代孕是失独者再生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法律的内涵与要求。
(二)生存照顾权
根据我国《宪法》第14和第45条,任何公民都有权获得“生存权或者说是生存照顾权的保护”[6],失独者作为公民中的弱势群体,其生存照顾权更是受到了法律的特别关照。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和实施、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扶助对象具体条件的确认、失独者医保社保解决办法等法律和制度规范均表明了国家对失独者所履行的生存照顾义务。但相比其他弱势群体,当前对失独者的生存照顾义务还远远不够,这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补偿条件过高与标准过低等缺陷方面(如《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者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相关规定),还体现在失独者的精神问题无法解决等问题上[7]。“‘失独’作为重大的家庭生活事件”,“必然导致家庭功能受损”[8],即便是给予其充分的经济补偿,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合适的方式是明确失独者享有代孕的权利,以重建家庭的基本功能。
(三)继承权
从失独者的继承权来看,在实践中,由于独生子女父母往往在其存活时将房产等重要财物登记于其名下,在其离世后,失独者往往会因离婚及子女配偶再婚等事由而对财产分配产生争议,虽然对此可根据《民法通则》和《继承法》等进行司法处理,但由于证据混乱、手续复杂及亲情纠缠等原因,极易导致“夫妻反目”、“翁婿反目”等严重问题。此外,由于法律未能明确代孕的合法性,使代孕的工具,如胚胎等仅能作为法律上的“物”对待,忽视了其对失独者的重大意义,导致司法中出现较多不利于失独者利益、但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出现。因此,失独者的继承权本身不仅是一项简单的民事权利,而是被赋予了更多“人”的属性,只有法律明确允许其为代孕之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定纷止争。
我国规范体系所承认的失独者上述权利的独特内涵,决定了其特殊的法律地位,也使其代孕活动能为法律所保护。但由于法律法规毕竟没有基于这些权利直接规定失独者的代孕权,因此其权利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伸张。吊诡的是,同样是“再生育技术”,与“代孕”有较多交叉的“人工授精”受到了《关于开展供精人工授精技术实施情况调查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和《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等司法解释的较为全面系统的保护,而代孕行为却不为法律所提倡。这样的规范体系还意味着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公民如果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代孕,其人工授精的过程和子女受到规范的保护,而代孕过程却缺少立法和司法支持,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
因此,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权利角度看,失独者相比其他需要代孕的群体,有更强的合法性和紧迫性。对其代孕权的立法保护不仅有助于完善当前法律体系,填补规范的漏洞,而且有助于维护失独者的基本权利。从实践看,目前实现其该权利的主要阻力在于立法和司法方面[9]:立法上的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可执行性,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范从反面“暗示”了代孕的“非法性”,地方规范性文件也因无上位法授权而无权保护代孕行为;司法上由于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和成熟的做法,实践中做出的判决常常引起当事人的激烈反对。为此,下文将着重探讨破解这些困难的可行路径。
二、立法的改进
由于规范体系的漏洞,使行政和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往往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其无论作出何种行政或司法决定,都会引起较大争议。因此首先需要从规范层面进行完善,以建立较为系统和可执行性强的规则体系,为后续的执法活动提供指引。
(一)明确法律内涵
首先应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内涵。由于失独者享有代孕权是再生育权的要求,而再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应首先由法律对其进行保护。《宪法》第25和第49条明确规定了计划生育制度,同时第37与第38条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体现了对生育权(包括再生育权)保护和限制两方面的含义。为此,我国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第38和第51条对妇女的生育权进行了保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主要是对其进行了限制。但遍观两法内容,其对何为生育权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答,这种笼统的规定仅是“对国际社会关于生育权认识的尊重,但不意味着我国在立法上将生育权赋予任何有生育能力的公民。”[10]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通过立法解释,对失独者生育权的范围做出更为清晰的说明,并且对实现该权利的技术手段做列举性规定,明确代孕可作为失独者实现其生育权的合法技术手段。这样既能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又能满足失独者由于年龄增长、生殖能力丧失而对代孕的急迫需求。
(二)完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在法律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代孕作为涉及到委托和亲子关系等多重法律利益的行为[11],尚需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配合,对此可从规范的主体和内容两方面展开。
在规范主体方面,国务院与其下属行政部门应合理分配各自权限。当前我国规范代孕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通过《办法》等部门规章对相关行为进行管制。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方面,部门规章的层级较低,与法律衔接的权威性不够;另一方面,难以有效处罚违法的代孕行为。因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7条,对违法代孕的处罚仅为责令停业、没收非法所得及罚款等,威慑力度较小,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条和第12条,部门规章仅能在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的范围内进行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卫计委难以有效管理代孕行为。因此在规制代孕过程中,必须重视国务院的作用,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对失独者代孕行为的指导原则、行政处罚范围和监督等问题进行规定。
在规范内容方面,除应加强行政处罚力度外,还应规定具体的代孕审批办法,并“明确规定禁止有偿代孕[12]”。在代孕审批方面,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应就六个方面作出规定:失独者的认定标准;代孕实施机构必须为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专门性医院;代孕和医疗人员的资质;管理、监督和指导机关;违法代孕的法律责任;代孕纠纷的解决机制。此外,由于商业性代孕会产生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和法律纠纷,故应明确禁止商业性代孕和有偿代孕,取缔相关代孕中介,以尽量减少失独者在代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的伦理和法律阻力。
(三)革新地方规范性文件
在上述规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也应出台对应的执行措施。上述规范由于其较高的层级,决定了不可能对失独者代孕这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行为作出过于详细的规定,因此给地方政府预留了较大的立法空间。为此地方政府应出台具体的执行标准和细则,并应进行法规清理,及时废止之前出台的大量禁止性规定。此外,地方政府还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当地经济状况,自行规定财政补贴等优惠措施,对确有困难但又有代孕意愿的失独者进行经济帮扶。
总之,应建立“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三级的立法保护,从而使失独者代孕权系统地纳入法律的范围内。另外,由于失独者仅是需要代孕群体的一部分,因此前两个层级的立法仅需以法律解释或更正个别条文的方式进行修改即可,以尽量保持法律的完整性。
三、司法的支持
在司法方面,实践中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围绕代孕合同的有效性展开,法官往往认为这类合同将代孕人与婴儿作为“物”对待,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与《合同法》第7条,判决合同因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而无效[13]。
然而,在失独者语境中,代孕合同能够通过公序良俗原则的检验,得到合法性的证成。有学者在总结德、法、日等国司法实践后指出,公序良俗原则有危害家庭关系、违反人格尊严、违反性道德及暴利行为等十种内涵[14],当前学界和实践中常将前两者作为代孕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然而从失独者的特殊法定权利来看,其订立的代孕合同没有危害这两者。就家庭关系来看,正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创造了“失独者”这一特殊群体,预设了家庭关系破坏的可能性,失独者履行了法律义务。但义务是与权利对应的,该法第1条还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促进家庭幸福”,对失独者来说,其代孕行为以及作为其手段的代孕合同都是恢复家庭关系的重要努力,理应得到国家的尊重,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就人格尊严来看,实践中的主要担忧是代孕合同将代孕人和婴儿作为“物”对待。但实际并非如此:从婴儿看,失独者代孕是其法律上再生育权和继承权的体现,尽管婴儿不是失独者所生,但失独者在法律上与婴儿存在亲权,这与收养关系是类似的;从代孕人看,由于法律禁止有偿代孕行为,因此只要失独者给予其的物质利益不明显超过代孕所需的必要限度,则代孕人就可被看作是失独者实现其再生育权的义务履行者,作为失独者权利的相对方而存在。由此可见,在代孕合同非有偿合同,且约定失独者为胎儿父母的前提下,代孕合同是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的。
因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肯定失独者订立代孕合同的效力,并进一步依照《合同法》和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代孕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包括:合同委托方是否为失独者;合同是否为有偿合同、有无明示代孕者为子女父母、合同是否为要式合同,即以书面方式订立的合同[15];合同履行方的资质;履行的方式是否恰当或有瑕疵等。此外,最高院也可以批复、专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明确该类合同的审查标准,以为下级法院的判决提供指导和帮助。
[1]王小平.失独者的精神抚慰与制度保障[N].光明日报,2013-10-6(06).
[2]杨国栋.给失独者留下后代才是最好的慰藉[EB/OL].(2014-8-18).http://hlj.rednet.cn/c/2014/05/19/3352945.htm.
[3]失独老人起诉争夺冷冻胚胎 法院判决不能继承[EB/OL].(2014-8-18).http://china.cnr.cn/yxw/201405/ t20140520_515554864.shtml.
[4]青井和夫.社会学原理[M].刘振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5.
[5]张荣芳.论生育权[J].福州大学学报,2001(4):36-38.
[6]刘丽.税权的宪法控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
[7]宋强玲.失独者养老问题及对策研究[J].人民论坛,2013(5):126-127.
[8]杨宏伟,汪闻涛.失独者的缺失与重构[J].重庆社会科学,2012(11):21-26.
[9]任巍,王倩.我国代孕的合法化及其边界研究[J].河北法学,2014(2):191-199.
[10]杨遂全.婚姻家庭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34-135.
[11]任汝平,唐华琳.“代孕”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7):161-165.
[12]王贵松.中国代孕规制的模式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118-127.
[13]吴亚东,杨长平.“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被判无效[N].法制日报,2012-11-1(08).
[14]梁慧星.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6):21-31.
[15]曹新明.现代生殖技术的民法学思考[J].法商研究,2003(4):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