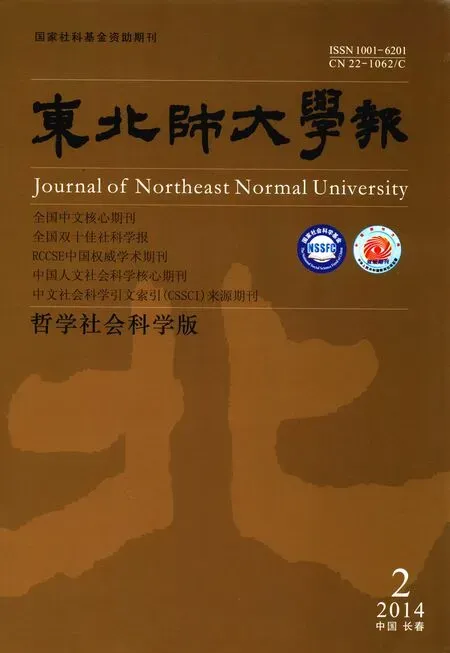中西差异视角下外语思维构建的本质探析
贺 莉
(1.黑龙江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2.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117)
一、引 言
长期以来,外语教学界对于提倡外语思维的做法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外语思维构建的本质内涵及构建的模式、途径却始终未能进行深刻而有效地阐释。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外语思维进行了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蒋楠从言语产出过程中概念提取的视角将外语思维界定为“不经过母语的转换和翻译而直接使用外语,其实质是概念和外语直接联系”[1],即用外语所特有的概念系统来进行认知活动;另外,姜孟、王德春从心理、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外语思维“是指按照外语概念化模式的要求将要表达的体验概念化,它不是一种随意、可选的外语使用策略”[2],即外语思维是一种概念化模式的构建。两种观点都侧重于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揭示外语思维的内涵,偏向于认为外语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种概念模式的转换。那么外语思维究竟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思维能力?外语思维究竟是在方式上的转换抑或是内容上的构建?外语思维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概念体系还是在原有概念体系基础上的重构或者互构?本文认为,要回答上述问题还需从语言哲学的本源问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加以分析。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一)相互作用
语言与思维二者不可分割,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载体,语言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对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成与导向作用;反过来,语言又从属于思维,语言能力的发展不能先于思维能力的发展,思维方式必然影响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结构的形成。爱因斯坦指出,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概念形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3]。中国汉字的象形特征和构词方式使得中国人拥有着独特的类推能力,也有资料显示,中国学生在理解和运用数的概念上占有优势。而俄罗斯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分析抽象的逻辑思维模式与其复杂多变、具有理性色彩的语言结构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此外,思维和语言都是在人类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均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思维方式之形成和发展有所影响,各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形成对同一客观事物不同的语言传达模式和语序变化程度,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语言的民族性。俄语语法是俄罗斯民族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而汉语语法是汉族人长期进行形象思维的结果。维果茨基曾说过:“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过程,是从思维到言语和从言语到思维的连续往复运动。在这个过程里,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经历了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在功能意义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发展。”[4]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果茨基也肯定了思维与语言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二)动态变化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二者的相互作用通过言语活动中概念或词义的形成而体现并发生动态变化。
概念是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单位。概念的形成是一个由低至高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概念混合、复合思维和潜在概念三个基本方面,每个方面又相应地分为若干阶段。在概念形成的初期,人们会以堆积的方式把若干毫不相关的物体聚在一起,而词语的意义也毫无方向地延伸到人的知觉中偶然联系起来的原本无关的物体上面。在此阶段,词的意义除了指把各个个别物体予以含糊的概念混合的聚集之外,并不指其他任何东西。概念形成的第二个方面是复合思维,它是由思维的许多变式组成的,这是摆脱概念混合而朝向客观思维的决定性一步,复合思维已经属于一种客观的思维。在复合思维阶段,会相继出现联想型复合、聚集的复合、连锁复合、扩散性复合和假概念五种基本的复合形式。复合思维通过把经验的互不关联的各个要素组成一个类别,从而开始将分类的印象统合起来,为后来的概括创造基础,它是概念形成的一个根源,而另一个根源则是潜在概念的形成。潜在概念导源于一种孤立的抽象作用,人们通过抽取事物的某一特征,并依据这一属性进行分类,通过综合与分析的方法,当抽象的特征重新综合,而且产生的抽象综合物成为思维的主要工具时,真正的概念才得以形成。在概念形成的过程里,概念通过一种智力操作使一切基本心理功能都参与到特定的结合之中,词语则作为一种工具动态引导着概念的发展方向。因此,词语的使用是概念形成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往复运动
言语中的词通过概念来反映事物和现象,词义是对现实的概括反映,它既是思维又是言语,既属于思维范畴又属于语言范畴。言语最本质的标志是声音和意义的紧密联系,没有意义的词是一种空洞的声音。意义是“词”的标准,是词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看,它可被视为一种言语现象。言语的原始功能是交际和社交,交际的手段是信号(词或音),但是,真正的交流需要意义,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将反映概念化现实的人类思想简化、类化和概括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否认地是一种思维活动,概念是思维的单位,是词义的基础,由此来说,词的意义又可以看作是一种思维现象。词义作为言语和思维的单位,促成思维与语言融合为言语思维,使人类的交往成为可能,而词义随着思维功能的多样化导致自身涵义不断发展,使得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从思维到言语和从言语到思维的连续往复运动的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经历了变化和发展。
以上通过分析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得出结论:语言与思维二者相互作用,思维既需要通过言语来表达,还需要通过言语开始产生并存在和发展,词义概念作为概括化思维和言语交际的单位维系并推动着思维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和动态发展。
三、母语思维与外语思维
各民族语言思维的概念化模式既有普遍性又有差异性,这是因为概念化模式的构建受到各民族认识、观察和理解客观世界的角度所影响,这种认知视角的差异会造成各语言所对应词语的语义范围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语言反映着该民族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既然思维只有在某种语言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那么本族语思维与外语思维是否完全相同?回答是否定的,二者在思维方式、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的形成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一)思维方式的差异
就思维方式而言,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比较、分析、综合等思维过程,对于操任何语言的民族来说都是共同的,差别主要在于中、西方民族所倾向使用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
1.天人合一与主客两分——哲学探源
徐通锵认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通过它所崇尚的哲学理论反映出来,因而不同语言社团思维方式的差异自然会与不同的哲学理论相联系[5]。汉语民族受儒、释、道三种哲学的思想影响最深,崇尚万物皆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言行合一,注重整体思维、形象思维和悟性思维。因此,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综合的、整体的、非线性的推理方式,强调主观感受和意念抒发,将理性、功能和交流目的溶于直觉,不注重抽象、逻辑,不执著于形式结构规范,因而思维概念倾向于笼统甚至模棱两可,讲求主体性。这种思维特点直接影响了汉字的形成和发展。汉字属于象形文字,受古代人的“寻象以观意”的形象思维的影响,起源于原始图画,经演变转换为线条,形成象形文字,在此基础上配以偏旁、部首等符号进行排列组合发展成现在的形声字;语法上呈隐性,讲求含蓄,注重语言的内在联系,隐含关系和模糊关系等,不注重形式上的统一;在句子结构上表现为主题显性,即句子的主题往往就是句子的主语;在语篇层面则表现为叙述全面、周到,语义连贯即意合性。
西方民族由于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崇尚以自然为认知对象、神凡两分、主客两分,习惯于因果线性论,典型的线性逻辑结构体现为三段论的演绎特征,注重系统化和逻辑化,思维方式上表现为:重理性、重逻辑分析和推理,重形式论证,讲求客观,主张主客体分明;语言结构相对严谨,语法呈显性、刚性;段落和语篇结构模式一般表现为:主题句(段)、支持句(段)以及结尾句(段),注重语言形式结构的完整和衔接手段的运用,体现语义逻辑的一致性和形式逻辑的严密性。
2.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语言是思维最有效的工具,思维活动需要借助语言来进行,思维成果也需要依赖语言来表达,语言结构特点是与思维方式的特点相一致的[6]。汉语起源于象形文字,直接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取向于物,以形达意,因此,具有直观性、具体性;汉语语法重意合不重形合,是汉人思维长期形象化的结果,他们不倾向于把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的关系较直接地表达出来,不倾向把逻辑分析的结果展现在语言的表层,而习惯于将抽象思维隐藏在形象后面或形象之中,实质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和手段,其目的是使对事物的描写更直接,更接近事物本身。汉语思维在形成概念时也往往是与那些与表象联系得紧密的概念,从直观感受出发,运用表象进行具象化,从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感受上整体把握事物的特征。
俄语起源于西里尔字母,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取向于语音,字形与字的读音具有一致性,但与其所指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因此,字母文字与汉字相比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俄语句法中的屈折变化和复合句句法结构等语法手段就是俄罗斯人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他们在认知客观事物时,不仅描写事物,还借助一定的语法手段,如屈折变化、复合句句法结构等语法规则将对事物间关系的分析也表现出来,使俄语语法表现出理性、注重分析的色彩,性、数、格、时、体、态的存在使分析成为俄语语法的重要或本质的特色,在涉及语言现象时对其所作的分析是一个对语言符号解码的过程,这种分析实质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分析,与汉语的直观与意合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俄语语法的各种规则反映着思维的逻辑规律,文字和语法都适合抽象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另外抽象思维在西方民族思维模式中占主要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哲学家一般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始终把追寻事物的本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透过表象、层层深入、挖掘本质,长久以来形成了纯思维的抽象思维模式。
3.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
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主客体的融合统一,注重意合;而西方民族注重分析推理式逻辑,强调主客体分离,因此在语言上注重形合。
汉民族长于运用直觉——联想体悟——比喻例证的方法,实质是直觉整体式思维。汉语句子间注重隐性连贯和逻辑顺序,功能意义领先,“以神统形”,采用意合法。汉语语法注重以词达意,习惯于直接描写事物,并用意向组合来使句子更生动,是汉语的具体思维在语言组织上的反映。中国人重悟性与汉语语法偏向隐性有关,因此,汉语体现的是一种悟性思维,以言简意赅为特征,重意义的整体组合而轻形式结构。汉民族整体思维的特征在生理学上也得到了证实,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于大脑右半球,所以右脑主管的具体性、综合性、类推性、直觉性的能力占优势。
西方民族惯用假设——逻辑推理——演绎论证的方法,实质是分析推理式思维,因此使用的语言严密而明确。俄语句子受制于主谓一致的形态框架之中,注重“以形统意”,常采用形合法,习惯于用一些形态标记,比如词尾的屈折变化、连接词和从句等语法手段,把各种成分连接起来,组合长短句子,表达一定的语法关系和逻辑联系,形式较为严谨,以形显义。俄语是一种逻辑化的语言,俄语语法偏向显性,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重理性,擅长分析推理思维,能更好地理解语言单位间的关系。
4.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思维
李约瑟曾经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辩证思想注重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是以两点论的思维方式把握客观世界,这种辩证的哲学思想反映在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中。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语词使用往往言简意赅,行文讲究辞约而意丰,具体表现在:汉语词语双声叠韵的对立统一、词的语法意义的双向推导、句法意识与词句的对照映衬、汉语语义派生的反训现象等,这种语言结构中“偶意”的独特特征正是汉民族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
西方民族的语言思维特征是严密机械的二项式形式逻辑,强调非此即彼的排中律[8]。印欧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单体精确型”的语言,它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及其表述总是从某一个逻辑主语出发,以动词为核心构建复杂的关系网络,使其进一步精确化、抽象化,它关注的是实体,论断的是事物的属性。以俄语为例,俄语词类、词性界限分明、词形变化严格、句法的抽象逻辑分析等,这些都说明,俄语语法与对事物的逻辑分析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语法的各种规则反映着俄罗斯人思维的逻辑规律。
汉语与外语语言体现在思维方式上的种种差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学习一门外语,除了要学习它外在的语言形式,还要学习隐藏在语言形式背后的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语思维就是思维模式的转换。
(二)思维内容的差异
概念是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单位,而概念的形成途径、概念的对应单位以及概念范畴的划分在不同语言中都有很大差异。
思维的核心是通过语言的概念来反映、表达客观世界,每一种语言都是该语言民族认识并反映客观世界的结果,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切分方式,因此,概念的形成必然也受到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汉语民族重直觉、重体悟和妙悟,因此概念的形成是通过直觉的思维方式,运用联想和体悟挖掘并建立事物间的联系获得;西方民族重逻辑推理、重演绎论证,因此概念的形成是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获得的。语言关联性的发展性理论认为,语言对客观经验的编码方式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倾向于按他们语言所提供的不同范畴去区别和辨认经验[9]。
由于概念形成的途径有假设和直觉之别,因而概念的对应单位也有很大差异,印欧语社团语言中概念的对应单位是词,而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是字。可以这样认为,汉语的字和西欧语社团语言的词不能完全对应,也很难有确切的对应物,但是试图在所学外语中去寻找词汇上的等价物是完全不可能的,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掌握了外语词汇的能指的全部和所指概念中与汉语概念相对应的那一部分而并非全部所指。
在概念范畴上的界限划分也有所差异。不同的语言按照不同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切割”,并按切割后的小单位之间的相似性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即范畴化。汉语语法结构是以字为基础,层层扩展生成语句。字是中心主题,词则是辅助性的副题,因此,没有像印欧语那样明确的词类划分,只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而印欧语中词类划分明确,句子的概念也很明确——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正因为中国和西方各民族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不可能形成完全相同的概念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语思维就是用所学语言来构建对世界的概念化体系。
每种语言都是一套庞大的概念系统,学习者需要充分认识外语概念系统,了解其与母语概念系统的差异,尤其是在概念内涵、外延和概念隐喻方面的差异。通过概念重组的方式,学习者把头脑中的概念体系按照与外语文化相适应的方式进行重新组合,达致概念地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外语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词汇和语法规则的学习,而在于如何通过外语将世界重新概念化。
(三)思维形成途径的差异
学习母语时是从口语到书面语,先学会用口头表达思维,而后是书面语表达思维,语言表达能力随着思维能力的加深而加深,就是说,母语学习是某一民族思维和思维能力的再现和延续。因此,母语者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和思维是同步的,交际双方都在不停地进行编码(说)和解码(听),且编码和解码的速度和正确率很高。
母语习得过程中,对于儿童来说最难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如何将声音和所指的概念结合起来,使声音转化为客观概念,因此母语习得的过程就是不断将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的过程。在掌握外部言语过程中,儿童往往从一个词开始,然后联结两个词或三个词;稍后,儿童从简单句子发展到较复杂的句子,最后达到由一系列句子构成的连贯言语,以上过程可以解释为:儿童在语音方面的发展是从部分进展到整体。而在涉及词义概念时,儿童说出的第一个词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随后才开始掌握一些独立的语义单位,如一些语块、词汇等的意义,并将他先前尚未分化的思维分配给这些单位。从语义学角度来看,儿童从整体开始发展到特殊。综上所述,儿童母语习得过程中语义的发展过程和语音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在于两者相反的方向:言语的外部方面从特殊发展到整体,从单词发展到句子,而语义发展则是从整体发展到特殊,从句子发展到单词。
而外语学习不同于母语习得,也不同于在目的语环境下的二语习得,是一种处于无自然环境下的外语学习。进行外语学习时,由于学习者头脑中已经完整地建立了一套母语的知识结构和概念系统,大脑的语言侧化功能已经完成,可塑性大大降低,因此,在初级阶段,学习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母语的影响,他们大多是翻译式地掌握外语,依赖于把所学的外语词汇用母语“复制”下来这种语码转换的翻译过程,使之与一个最为接近的母语概念相联系,即用母语思维、外语表述,这样的后果是思维与语言产生分离、不完全同步,具有滞后性,因为交际者始终忙于找寻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对等关系,进行语码互换,使输出和接受的信息更接近母语思维。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语言使用量的增加,与外语词汇相联结的语义会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概念。外语学习的过程就是母语的知识结构和概念系统与外语的知识结构和概念系统不断相互排斥及同化适应并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外语概念的形成依赖于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以及对目标语民族文化的深刻了解,甚至是在外语环境中长期生活才能获得。
四、外语思维构建的本质及途径
(一)外语思维的本质
外语思维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模式?对于此问题,以往的语言理论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维能力是人类认识现实规律的能力,具有全人类性的特点,能力的高低决定人在执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等一系列任务时完成质量的好坏;思维方式是实现和运用思维能力的一种偏好,即人采用何种方式以完成这些任务。思维能力有高低之分,思维方式却没有优劣之异,它与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体现该民族语言社团特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本文认为,外语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又是一种思维内容的重构,既体现思维构建的过程也是思维构建的结果,是方式和能力的双重体现,是外语教学的最高目标。
(二)外语思维构建的途径
至于外语思维是一种新概念体系的构建还是在原有概念体系基础上的重构?本文认为,对于俄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基于俄语与汉语、英语在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上的差异,外语学习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地用一套概念系统来取代另一套概念系统,而是使三套概念系统的意义同时纳入学习者的头脑。外语思维的实质就是母语概念结构和外语概念系统不断地进行对比、互动、转换和重组的过程,这种以三种语言为思维方式的知识与认知的三元结构构成了外语学习过程中的特殊语言和思维方式。这种三元结构分别受制于母语和外语的知识结构和概念系统,在三种语言的概念原型发生分歧和冲突时通过概念转换和概念重组并遵循接近的两种语言相互借鉴的原则最终达到理解的目的。
从心理语言学视角来看,在外语思维概念构建的认知操作过程中,大脑会随机构建四个空间:概念输入空间、概念类比空间、概念整合空间和概念输出空间,通过概念间的相互映射,连接形成一个概念网络系统,输入空间中三种语言的共核结构被投射到类比空间,再有选择地投射到输出空间,而三种语言中的非共有信息则通过进一步的比较和分类在类比空间进行筛选,并投射到整合空间,经过组合、重构和拓展形成新的概念结构再映射到输出空间。任何信息都可以回到网络的其他空间中去,实现信息在交互网络的循环往复。
语言与思维相互依存,语言结构规律的民族性与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外语教学也就是要帮助学习者能够从语言的表面深入到内里,在深刻了解汉语与外语各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学会用重新构建的概念体系和文化体系去观察世界和体验世界。外语教学应注重对学生思维模式的培养,逐渐培养学习者在语言编码过程中的“心理模型意识”,以思维为取向来转变外语教学,系统的外语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应成为外语教学的重要途径。
[1]蒋楠.外语概念的形成和外语思维[J].现代外语,2004(4):378-385.
[2]姜孟,王德春.外语思维的再思考——论外语思维的概念化模式内涵[J].外语研究,2006(4):38-44.
[3]申小龙.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6.
[4]列夫·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M].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5.
[5]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6.
[6]徐通锵.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的方法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1):45-53.
[7]汪成慧.俄汉语言文字的差异与思维方式[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68-72.
[8]晋荣东.近现代名辩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10):49-51.
[9]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