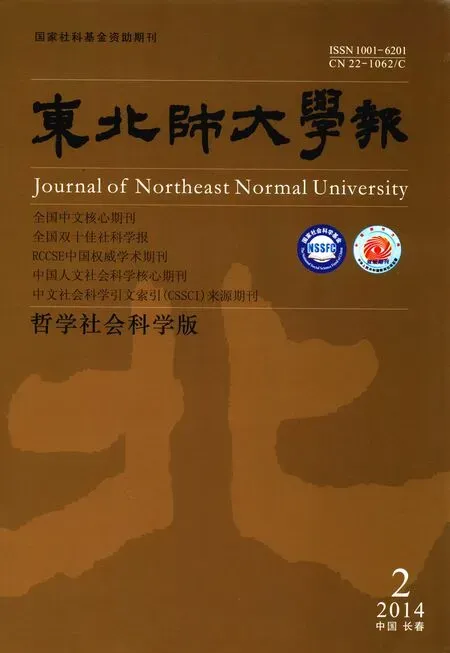弗朗西斯·杰弗利对华兹华斯《诗,两卷》的批评
许 鹏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2.长春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22)
1807年5月8日,华兹华斯(Wordsworth)出版了首部完全是他自己作品的短诗集——《诗,两卷》(Poems,in Two Volumes),因为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中,都有他的朋友柯勒律治(Coleridge)的作品。但这部诗集并没有给他带来《抒情歌谣集》般的光环,却让他遭受到了一场措辞严厉、历时持久的抨击。《英国评论家》、《诗界》以及《每年评论》等几乎所有的文学评论期刊都将华兹华斯的《诗,两卷》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正如《爱丁堡评论》资深评论家弗朗西斯·杰弗利(Francis Jeffrey)所说,华兹华斯的关键问题是所选取的主题,“绝大多数读者都会认为这些主题没有品位、愚蠢、令人生厌”,他还强烈指责,华兹华斯这是在公然亵渎“已经建立起来的作诗法则”[1]。1807年,华兹华斯遭受了他成为诗人以来最屈辱的折磨。《抒情歌谣集》在7年中出版了4个版本,而同样在7年中,《诗,两卷》第1版的1/4还没有售完,这让华兹华斯刚刚建立起来的诗人声誉受到重创。
其实,杰弗利对华兹华斯的偏见早在《抒情歌谣集》发表时就存在了,他认为华兹华斯的观念是一种对传统的冒犯,女佣和绅士的情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相同的,而对于华兹华斯在《坎伯兰的老乞丐》(Old Cumberland Beggar)中的宣言:“我们共有一颗人类的心灵(We have all of us one human heart)”[2]15,杰弗利个人认为那是一种侮辱。只不过在《抒情歌谣集》发表时《爱丁堡评论》还没有创办,所以直到1802年该刊始创,杰弗利才有机会公开发泄他对华兹华斯的强烈不满,他借评论骚塞(Southey)的《萨拉达》(Thalada)之机,开始了对华兹华斯长达十多年的批评,正如他自己所说,从那时开始,他就“没有错过一次可以批评华兹华斯的机会”[3]89,他不仅将华兹华斯自己的作品作为长期嘲讽的对象,而且借评论克莱布(Crabb)、彭斯(Burns)、骚塞等其他诗人的作品之机,对华兹华斯进行抨击。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说他没有尽到一个评论家应尽的职责,相反,他对待评论是非常认真的。
一
或许有人会认为华兹华斯和杰弗利天生就是一对死对头,但是大量的研究资料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对杰弗利旅游日记研究工作的深入,更多的事实表明,杰弗利也像华兹华斯一样,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的人。在旅行中,杰弗利常常趴到草地上看不同花朵的细微差别,他也会像华兹华斯一样,在别人认为不好的天气中获得快乐,在他1882年的一封信中,他是这样描绘苏格兰的:“……下了一整夜的雨后,山间的急流在宁静的清晨中轰鸣着,我喜欢听这欢腾的响声。”[4]212这不仅让人想起华兹华斯在《作于格莱斯米尔》(Lines Composed at Grasmere)和《决心与独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中的诗句。可见,杰弗利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华兹华斯还是有很多相像之处的。
在政治观点上,杰弗利认为《亚眠和平条约》(The Peace of Amiens)迟迟没有签成,英法双方都有责任,而最近两国之间的敌意又有上升的势头,这让杰弗利很是担忧,所以,像他的朋友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一样,杰弗利在苏格兰也参加了地方武装,随时准备对法作战,而华兹华斯在格莱斯米尔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当西班牙抗战爆发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位长期讥讽华兹华斯的杰弗利先生,竟然也写出了与华兹华斯类似的话语,“正是这些没有什么财产与权利,被上层阶级鄙视的劳苦大众成为了战争的主力军。”[5]可见,无论是华兹华斯那动人的诗歌,还是杰弗利那意味深长的散文,都表达了对西班牙普通民众的同情。而当1814年滑铁卢战役结束时,我们从杰弗利的散文中也看到了华兹华斯般的爱国主义。
对于文学,杰弗利认为是诗歌让我们不再忽视熟视无睹的事物,是诗歌唤起人们心中那种共有的却极力去逃避的情感,而这种观点在华兹华斯写给约翰·威尔森(John Wilson)的信中几乎可以被逐字逐句地找到。就凭这一点,我们足可以相信杰弗利并不是读不懂华兹华斯的诗歌,他一定有能力品鉴出华兹华斯在《诗,两卷》中所表现出的睿智与勇敢,但他却非要把华兹华斯作为长期嘲讽的对象。杰弗利1810年评论克莱布的《城镇》时,刻意极力赞赏他用诗歌来描写日常的生活,这无疑更加彰显了其对华兹华斯的不满与偏见。
二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观点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之间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呢?这就要求我们来看看杰弗利先生的审美观了。
首先,杰弗利和很多大城市里的文学评论家一样,认为华兹华斯脱离城市而隐居乡村的这种生活方式会影响他的诗歌艺术,因为诗歌本该拥有社会的属性,但它不是与整个社会有关,而是只与上层社会有关。这种观点与杰弗利所处的时代有关,他是在苏格兰文学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在理论上他很可能同意大卫·休姆(David Hume)的观点,认为人类在行为举止上存在着一种通性,而且人类的本性是不变的。但他也可能同意托马斯·瑞德(Thomas Reid)的观点,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保持荒蛮和独处的状态,而是要生活在社会之中。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观点也可能对他有影响,亚当认为如果富丽堂皇的豪宅是非自然的产物,那么简单朴素的村舍也一样不是。自然的固有状态是透过客厅的大玻璃窗观察到的,而不是在杂草丛中见到的。
其次,杰弗利本人一直坚决反对尝试新事物,这在他1802年评论骚塞的《萨拉达》时就表露无遗。他指责骚塞怎么可以把诗歌写成和宗教信仰一样,并重申创作诗歌的标准早都已经确立下来了,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在做评论时多次强调传统诗歌标准的不可挑战性,然而他自己是否始终遵从这种审美标准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在写给乌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意大利诗人,文艺评论家)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许多不太好的事情却能得到公众的认可……但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有把握说我看好的事情就真的是好的,因为它们很可能带有我的冲动或是个人偏见。”[6]28由于缺乏足够的坚持己见的勇气,杰弗利最后还是选择了从众。
再者,像柯勒律治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杰弗利也不相信用社会中下层人的语言来写诗有任何的价值。他认为社会上层人物的语言以及受过良好教育人的语言就是比社会中下层人的语言要好。他并不认为出身低微的人不能作诗,但为了去写诗,这个人就得提升他自身的语言,还要学习作诗法、韵律学等等,等他都学完了这些知识,也就很难再看出他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了。这不仅让我们想起1809年杰弗利评论《罗伯特·彭斯的遗作》,他不同意有些评论家认为彭斯的诗歌就是一个农民信手拈来的作品,他认为这样评论一位诗人不免有些草率,但同时他也不否认,彭斯的诗歌确实有他的特别之处,不免让人想起他“低微的出身”[3]392。对于杰弗利来说,文学是有身份的人的追求,他虽然没有称彭斯为下层人(a low man),但也没有称呼他为绅士(gentleman)。
最后,在诗歌的艺术技巧上,杰弗利非常不赞同华兹华斯的做法,尤其是像《诗,两卷》这样的处理方式,他是根本就接受不了的。他认为一个人若想写作的话,就必须谨慎选题,就应该能让大多数的人受感动。如果超出了大众所能接受的审美标准,那么他的文学品味就只能是低下的,错误的。杰弗利几乎每次评论华兹华斯的诗歌时都会重申这样的观点,他对华兹华斯的这种指责,很可能是借用了华兹华斯发表于1800年《抒情歌谣集》前言中的观点,他在前言中是这样说的:“……我自己非常清楚,一些诗歌的联想是很特别,不够常见,常常会让人觉得我写了没有意义的东西……”[7]165。
但是当华兹华斯看到杰弗利对《诗,两卷》的评论后,他写信给骚塞说,他是不会因为个别权威的指责而改变这种表达方式的,他也不会因别人的非议而失去信心,他提醒某个批评家,别忘了他自己就很有可能也犯这样的“错误”。他在信中还说,其实杰弗利是懂得联想的艺术作用的。但是杰弗利却不欣赏华兹华斯的联想,他始终认为华兹华斯把他自己那崇高的、细腻的情感竟然与那些看起来荒唐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像麻雀窝、雏菊、捉水蛭的老人等,这些事物在多数人看来一直都不可能是有品位的,都不应该入诗。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华兹华斯和杰弗利两人在审美上的巨大差异了,这种分歧一直存在于杰弗利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评论中,可想而知,除了抨击和贬低之外,杰弗利对于华兹华斯还能评论些什么。当他1809年借评论彭斯的诗歌之机来打击华兹华斯时,他把《诗,两卷》中的《爱丽丝·菲尔》(Alice Fell)作为了抨击的对象。他认为这是一首无聊的作品,这样的垃圾作品对于公众的鉴赏品味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它竟然将穷人的生活作为主题,还用了平淡无奇的语言,更假想了一种根本就不可能的情景——一位绅士竟然会对一件破斗篷感兴趣——最主要的是,这首诗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德教育意义,也没有任何的讽刺作用。杰弗利的这种批评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多年后才有学者分析这首诗的艺术性和技巧性,指出不该如此谴责这位诗人[8]。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杰弗利非常喜欢《诗,两卷》中那首显然是描绘安妮的诗歌——《曾经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Once in a lonely hamlet)。他很欣赏里面那些描绘这位法国女子和她自己的孩子分离的诗行,他认为这些诗句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位女子的情感。其实,华兹华斯探索母爱的诗歌是开始于1798年的那首《一位被遗弃的印第安妇女的抱怨》(The Complaint of a Forsaken Indian Woman),接下来的《她的目光疯狂》(Her Eyes are Wild)和《玛格丽特的痛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也都属于这一主题。可以说,《曾经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是华兹华斯同情母亲的诗篇中情感最丰富的一首。但是对于当时评论华兹华斯的杰弗利来说,他并不知道他所喜爱的这首小诗是华兹华斯母爱主题的四重奏之一,他也更不能理解这些诗是如何表达了华兹华斯本人那种失去的痛楚。战争,对于华兹华斯来说就意味着和他心爱的女人以及他们未曾谋面的孩子的长久分离,在英吉利海峡的那一端,有着他无尽的思念和牵挂,这也就造成了他心中一直萦绕着的想念,也解释了他心中缘何会有那种无名的情感矛盾。懂得了这些,也就能理解《诗,两卷》中的很多诗篇了,可惜,与华兹华斯生活在同时代的杰弗利先生是无法了解到这些的,更何况华兹华斯技高一筹,借用了女性之手来表达他这个大男人的思女之痛。
三
著名华兹华斯研究家、评论家乔纳森·华兹华斯(Jonathan Wordsworth)在介绍《诗,两卷》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杰弗利在评论《诗,两卷》时,为什么没有提及那些弥尔顿式的十四行诗和那两篇精美的颂体诗呢?他怎么可能对这些诗视而不见呢?这是一个被评论界常常问及的问题。事实上,除了那首《布鲁厄姆城堡晚宴的歌声》(Song at the Feast of Brougham)外,杰弗利对《诗,两卷》中的其他十四行诗只字未提,而他之所以谈这首十四行诗,还是因为好友司各特的极力推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杰弗利对这些十四行诗和颂体诗避而不谈呢?难道他真的看不出这些诗歌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杰弗利在他的评论中也曾暗示过,他认为华兹华斯的这些十四行诗和颂体诗确实使他的诗歌水平有所提高,他也曾引用过一些十四行诗中的优美诗句来贬低那些他认为“幼稚的”、女人般“矫揉造作”的抒情诗,只不过他并没有指出那些优美的诗句是他引用华兹华斯自己的诗行而已。
至于《诗,两卷》中的挽歌,今天的读者都知道,那字里行间浸满了华兹华斯对兄弟约翰的悼念,没有人能知道,华兹华斯在1805年海难发生后,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才写成了这些如诉如泣的诗行:(我仿佛看见)“那微笑的海洋”和那“漂浮着劳工浮肿尸体的笨重沉船”,(我)渴望拥有“古时那冷酷的铠甲”,可以勇敢地面对“闪电、狂风和惊涛骇浪”[9]315-318。而面对如此感人的诗行,杰弗利依然保持视而不见。
可见,杰弗利如此批评《诗,两卷》,根本就无法理解华兹华斯所要表达的本意,更何况《诗,两卷》是这样一部诗人精心设计的诗集。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主题上,它都是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蝴蝶与大海的对立统一,孩子与祖国的对立统一,甚至它给批评界带来的震惊也是对立统一的,既有人抨击它过于多愁善感,矫揉造作,也有人赞赏它的豪迈气概[10]。总之,无论这部充满了内心情感的诗集带给当时评论界的是什么,我们都不能否认,对于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英国社会来说,它都是一支强心剂;而对于现代诗歌来说,它无疑就是那冲锋的号角。
[1]Edinburgh Review[J].June 12,1807.
[2]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Francis Jeffrey.Contributions to the Edinburgh Review[Z].4vols.Edinburgh,1844.
[4]Henry Lord Cockburn.Life of Lord Jeffrey With a Selection From His Correspondence[M].2vols.Edinburgh,1842.
[5]Edinburgh Review[J].13Oct,1808.
[6]The Letters of Francis Jeffrey to Ugo Foscolo[M].ed.J Purves.London:Oliver and Boyd,1934.
[7]William Wordsworth.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William Wordsworth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M].ed.Philip Hobsbau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
[8]马修·阿诺德.评华兹华斯//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M].易漱泉,曹让庭,王远,译.张贴天,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9]William Wordsworth.Poems,in Two Volumes1807[M].London:Humphrey Wilford,1934.
[10]王向峰.对现象学几个关键词的是非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