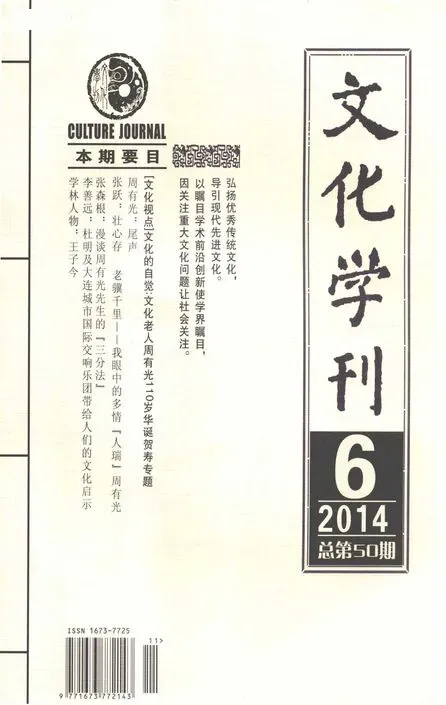乡村集市的“民俗文化空间性”
董丽娟
(辽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一、 “民俗文化空间”理论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的兴起和深入,“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别被提出,用于更准确地定位“与各种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一些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空间和反复定期出现的时间密切相关的传统节日、民俗信仰、民俗崇拜现象等。这也引发了民俗学者对“文化空间”的讨论,进而提出了“民俗文化空间” “民俗空间”的理论。本文借鉴“民俗文化空间”理论对乡村集市这一经济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意在揭示这一“民俗文化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定期聚集进行产品交换和交易的市场,多是民间自发的经济行为,主要存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在我国,集市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历史传承性。乡村集市从产生之初,承载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交换的经济功能,它还联系着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是“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汇聚集中的场所,或某种民间文化表达方式有规律性地进行的地方”,具有“节律性、集聚性、流动性”等特点,是农村民俗生活展演的一个“民俗文化空间”。[1]
二、乡村集市的“民俗文化空间性”
“民俗文化空间”大体具有以下几种特征,说乡村集市具有“民俗文化空间性”,就是说乡村集市也具有“民俗文化空间”的特性。
(一)建构性和符号性。建构性是指“民俗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人的行为作用的痕迹,这种行为最初是不自觉的,直到“民俗成为学科对象以后,它的建构就表现为文化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了,广大民众视民俗为一个民族或地方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从中挖掘、发展传统和利用传统”。[2]乡村集市在建构的最初,参与者往往也是自发的、无意识的。欧洲中世纪的集市常常出现在宗教节庆、集会上,中国古代的集市也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是源于小农家庭余缺调剂的需要而在熟人之间进行的“有无相通”。乡村集市的集期是对时间的建构。“赶集”是民众在集体协商好的日子的一个“赴会”。集期的确定可以和农村的生活、生产有关,也可以和季节、时令的更替有关。符号性是约定俗成的标志物。乡村集市的集期和地点都是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成员所认可和长期约定俗成的符号。
(二)日常性和公共性。日常性是指“民俗文化空间”作为民俗文化活动的载体,最终都是指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俗活动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乡村集市作为乡村生活中带有传承性和模式化的文化生活和生活文化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常性是其基本特征。与日常性相呼应的,是它的公共性。公共性指民俗活动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所共享的广泛性。乡村集市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所公有的民俗空间,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交易和交际等活动得以展开,物质的和精神的“交际”功能得到发挥,从而也给这个空间带来了“公共性”的色彩。
(三)伦理性和社会性。伦理性表达了“民俗文化空间”的礼俗功能,它规定了在特定的民俗文化空间的长幼尊卑和秩序伦常。乡村集市也是如此,在乡村集市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遵守着各自的价值观念、乡规传统,共同维护这个民俗文化空间的秩序。社会性是指在交换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交换双方的社会交往、民间信仰等社会性行为。
三、民俗文化空间:乡村集市在乡村民俗生活中的功能
乡村集市作为农村经济民俗生活的展演空间,一方面有其经济功能,同时,也承载着展演乡村民俗、映射地区文化传统的文化功能。施坚雅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3]生活在这个范围内的乡民在多少个世纪里世代遵守着同样的交易习俗。他们通过集市场所进行互动,并在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类似的民俗行为,受到共同的民俗观念、民间伦理道德的支配,最终形成本集市区域所独有的民俗文化。所以,集市不仅构成空间交易体系,其本身也是民俗文化体系。
(一)乡村集市与岁时节日习俗。中国传统岁时节日大多源于气候变化或月的圆缺变化,乡民们的生活、生产也大多依据于此。岁时节日的物质需求带动了乡村集市的发展繁荣。集市所采用的集期、集市规模大小、集市商品种类多寡一般都受岁时节日等季节规律影响。生活在同一集市所覆盖的乡村范围的乡民们遵守大致一致的生产、生活规律,所以,农忙的季节,集市就会处于少人光顾的萧条期;而年终岁尾、春种秋收之前的农闲时节,也是各种岁时节日扎堆的时间,节日的物质需求、生产需求都促使这段时间的乡村集市格外热闹繁荣。如春节的集市、春耕前的集市,秋收后的集市都体现了乡村集市受岁时节日习俗影响、与乡村社会的生活、生产相呼应的特点。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赶集是乡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作为基层市场,它满足了乡民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它也是各种岁时节日习俗进行的重要场所。在娱乐活动贫乏的广大农村,集市充当了娱乐场所的作用。在节日的集市,乡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丰富见闻,了解时事,活跃生活。
(二)乡村集市与商业习俗。作为农村经济交换和交易的场所,诸如市声、隐语等商业习俗也在乡村集市中有所体现。市声可以说是有声的招幌,是一种靠听觉符号传播招徕信息的非言语的商业习俗,有叫卖吆喝、韵语说唱和器乐音响三种形式。[4]叫卖吆喝是古今都常见的最简便的招徕市声,韵语说唱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富艺术性的招徕市声。最有趣的当属器乐招徕市声。过去的集市上卖杂货的使用“货郎鼓”、理发匠使用“唤头”、磨刀剪的手摇“串铁”、吹糖人的手敲小锣来招徕顾客。这些招徕市声构成了乡村商业习俗的完整体系,同时,也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除了市声,还有一种颇具民间文化特征的常见的议价习俗就是“袖里吞金”。所谓“袖里吞金”,是一种商业隐语,主要用于牲口市。即交易双方通过不公开口头议价,而是通过中间人(牙纪)在长袖里或衣襟下“摸手”的方式议价,交易的价格是保密的。这种议价方式已渐渐少见。
(三)乡村集市与社会交往习俗。乡村集市是乡村社会人际交际的重要场所。由于乡村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性,使乡民们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囿于地域和血缘关系而更趋向于一个封闭的、有边界的空间,人们在经济上习惯于自给自足,在社会关系处理上习惯于家庭或家族内部解决,在信息上更是处于相对闭塞的空间内的共享,而集市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在这里人们“经济往来” “信息共享”,因此也成为乡村社会人际交往的一个主要空间。在乡村集市中,社会交往主要表现为经济和非经济两方面的交往。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构成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的物质的交换多是基于互通有无,是一种相互馈赠行为,而集市上交换行为则是抛开地缘和血缘关系不论、基于陌生人之间进行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它是把人情排除在外的。但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在乡村集市的经济交往中,完全不考虑这种“人情”的情况是少见的。一般在集市上如果交易双方是“熟人”,卖主会选择不收钱或少收钱,买主则会不好意思讨价还价或多给零头。除此,还有两种极端现象:一是买主为了避免卖主损失,还会主动选择不买“熟人”卖主的货物,这叫“避熟”;一是个别卖主故意利用“熟人”关系而缺斤短两或抬高价钱,而买主又不好说明,这叫“杀熟”。总体来说,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人情”还是会参与到集市上的经济交往中去,体现着商品交换以外的社会文化内涵。
除了经济交往,乡村集市还承载了乡村娱乐、交友、信息分享等非经济的文化功能。“乡村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的圈子有地域的限制,在区域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5]因此,其娱乐资源有限、交友范围狭窄、知识和信息匮乏。“赶集”使乡民们无意间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接触到的人不再局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突破了以往的走亲访友或相邻之间互助的交往形式,增加见闻,愉悦身心,分享信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集市还增加了科学知识普及、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法规宣传的功能,各种“文化大集” “科技大集”应运而生,农民们在集市上可以购买到高产的种子、优质的化肥,学习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交流农业生产经验,提高了素质。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乡村集市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空间所承载的功能也在悄然改变,现代发达的商业网络、多元的交际方式、丰富的娱乐生活都对乡村集市的“存在感”构成了冲击,但乡村集市并没有因此衰落或消失,仍然保留和发挥着其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展演和保留地的功能。
[1]蔡丰明.上海传统民俗文化空间[J]. 民间文化论坛,2005,(5) .
[2]林继福,王丹.解释民俗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3.
[3][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
[4]曲彦斌.民俗语言学[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431-432.
[5]费孝通.乡土中国[A].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