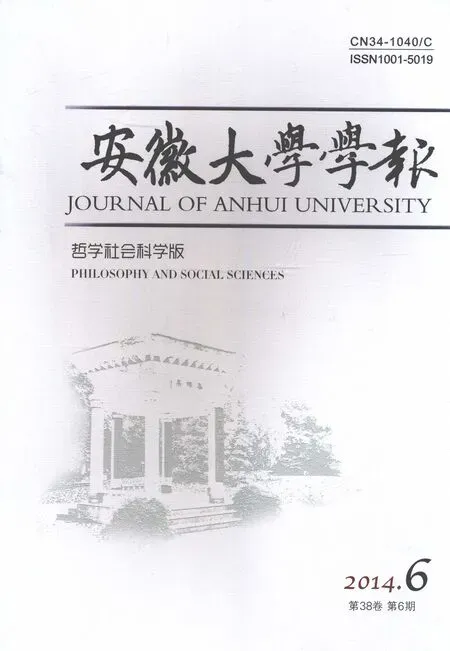“诉讼不及时”问题的理论解构
——治理诉讼迟滞与诉讼冒进的解释性工具
郭 晶
一、引 言
观察我国刑事司法现状,案件办理过于迟滞或者过于快速的情形,屡屡见诸报端。诉讼过于迟缓,不仅让被告人承受过多压力和痛苦,而且使被害人生活难得安定、愤怒难获平息。此外,诉讼迟缓也导致证据流失、证人记忆减退,致使大量额外的时间、精力、财力被付诸调查取证,造成对有限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相反,诉讼过于快速,控辩双方难以充分准备,无法从容参与诉讼,极易造成诉讼流于形式,既难以准确发现真相,也无法正确适用法律。
总体来看,我国刑事司法难以使诉讼的运行普遍性地维持在一个相对正当的速度,致使畸快、畸慢的案例频发。该种情况屡屡引发法学界、法律界乃至一般公众对案件程序公正性与实体正确性的质疑,持续挑战着人们承受能力的底限。诉讼速度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刑事案件,实体案情、证据状况相异,其运行速度必然各有特点。仅从办理时间的长短,难以评价其妥当性。然而,这却不能允许我们将下述问题诉诸无知:诉讼过于快速或过于缓慢的现象,究竟侵害了何种权利和利益,致使该种现象为人们所厌弃?在一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谁在为这种权利、利益的损害而埋单,谁又是损害的始作俑者?如何确认利益的损害,并救济利益受损者?如何追究利益侵害者的责任,对其实施制裁?什么是刑事诉讼的妥当速度,其合理性标准与合法性标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诉讼过快或过缓的司法现象,与程序性违法的关系为何?
二、“诉讼不及时”范畴的初提炼
刑事诉讼的妥速有序,是启蒙运动以来保障被告人权利、维护司法裁判公正的重要追求。这不仅是我国刑事司法的重大问题,也为全世界所关注。
(一)两大法系对诉讼速度妥当性问题的共同关注
大陆法系以诉讼及时性原则为基点调控程序速度。及时原则,又称迅速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之进行,务必摒除一切不必要或者不正当之延搁①[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赵海峰:《欧洲法通讯》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随着《欧洲保护人权与自由基本公约》的签订,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审理活动的推动,大陆法系诉讼及时原则越来越突出地在《公约》第6条所确立的“合理期间审判”条款的制定和实施中获得体现②参见《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与义务或在决定对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与公正的法庭之公平与公开的审讯。”,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大量判例,成为解释和适用该条款的重要依据③重要判例如1968年6月27日的诺伊枚斯特诉奥地利案(Neumeister v Austria)和1968年温霍夫诉德国案(Wemhoff v Germany),构建了“合理期间审判”条款适用的基本模式。还如1981年的巴克霍尔兹诉德国案(Buchholz v Germany),明确了合理期间的具体衡量审查标准。。
英美法系对刑事诉讼速度的关注,主要从保障被告人迅速审判权这一角度展开。1776年,美国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规定了被告人的迅速审判权,之后的1791年美国第六宪法修正案④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享有由犯罪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及迅速审判法令的颁布,都进一步确立了对被告人迅速审判权的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05年“比斯威尔诉郝伯特案”(Beavers v.Haubert)是第一个涉及迅速审判权的判决,此后又积累了大量判例。
基于诉讼及时原则与被告人迅速审判权,两大法系分别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制定法和判例,彰显了不同法系语境下对诉讼妥当速度的共同追求。然而,恰如美国Beavers v.Haubert案大法官所指出:“对于任何侵犯迅速审判权案件的调查,都必须在依据具体案情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该权利本身很难进行定义。”⑤See Beavers v.Haubert,198U.S.77,87(1905).我国学者在对刑事审限的研究中也提出:“刑事诉讼程序的进程,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无视个案的具体情形,强行设置一个一体遵行的审限制度,是不符合诉讼规律的形而上学的做法。”⑥万毅:《底限正义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8~239页。可见,如何界定诉讼速度的妥当性,存在先天性的疑难。
(二)诉讼的妥当速度与诉讼不及时
刑事司法由控、辩、审等多方刑事诉讼主体共同参与,其运行速度的快或慢,系多方刑事诉讼主体各自诉讼行为交互影响的自然性结果。然而,过于快速或者过于缓慢的程序速度,却有可能对刑事诉讼制度所保护的诸如人权保障、犯罪控制、真相发现、成本节约等重大权利、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制度措施,对过快或过慢的速度进行干预。
诉讼及时原则与被告人迅速审判权,虽然处于不同的法系语境,但都是对失妥的诉讼速度进行干预的理论工具,有着共同的功能和价值。具体来说,包括三方面:1.判断何种程度的快速或迟缓将会损害刑事诉讼的制度利益;2.判断制度利益的损害严重到何种程度,需要将相应的速度状态界定为诉讼迟滞或者诉讼冒进;3.判断应当为诉讼迟滞或诉讼冒进设定何种法律效果,从而对程序速度施加干预。
正义就像普罗透斯的脸,变幻莫测。相较之下,不正义的现象却更容易为人们所感知与识别。由于程序速度的妥当性标准难以正面说清,两大法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界定何为程序速度的不妥,即界定何为对诉讼及时性原则的违反,何为对被告人迅速审判权的侵犯。借由此种反向思路,逐步通过司法案例的积累,反向明晰诉讼速度妥当性标准的内涵。
因此,笔者拟将世界各国共通性的诉讼迟滞问题和诉讼冒进问题,共同纳入“诉讼不及时”这一理论范畴,进一步吸纳诉讼及时原则与迅速审判权的相关原理,提炼“诉讼不及时”现象的理论模型,试求为诉讼迟滞和诉讼冒进的识别和治理,提供一个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笔者所界定的“诉讼不及时”,即,刑事诉讼在运行过程中,背离诉讼及时原则和被告人迅速审判权对诉讼速度的妥当性要求,速度过快或过缓,进而对刑事诉讼所保护的权利、利益造成损害的现象。
(三)诉讼冒进的解释性意义
“迅速审判的核心要素是有序的迅速,而不仅仅是速度”①Charles H.Whitebread,Criminal Procedure:An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s and Concept,New York:Foundation Press,1980,p.475.。综览两大法系就诉讼及时原则和被告人迅速审判权等两大主题的研究,虽然均强调及时和迅速,但并不是绝对的求快,而是在过快和过缓之间追求相对妥当的速度。然而,既有研究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研究如何保障和提高诉讼效率,侧重于对遏制诉讼迟滞的研究。相较之下,诉讼过快现象则并非重点。即使诉讼冒进在部分研究中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研究者往往也仅是关注过快的程序可能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伤害。
笔者之所以并不遵循传统研究的偏向性,而是提炼“诉讼不及时”范畴,将研究范围从诉讼迟滞扩展到诉讼冒进,原因有两点:
第一,不同的制度利益,并非一概求快,也并非一概求慢,其对程序速度的要求具有复杂性。仅关注诉讼迟滞,逻辑不周延,难以充分揭示程序速度与其所关联的重要制度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制度利益之间,不同诉讼主体的利益倾向及其对诉讼速度的要求是互有差异的,仅关注诉讼迟滞也难阐明不同诉讼主体围绕程序速度变化的损害或受益;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即使诉讼冒进问题与具体诉讼权利的救济问题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但是,具体诉讼权利的受损有时难以获得证明与确认,而程序速度的过快,至少从时间角度,可以提供一个在外观上易于识别与操作的标准。若能借助时间因素而识别出诉讼程序的冒进,并将其作为引发对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线索,该种方式,或许能够成为当事人受损利益获得关注和救济的重要手段。
三、诉讼速度关涉的多元利益与程序推进的主导者
(一)界定诉讼不及时的三重困难
对“诉讼不及时”现象进行理论层面的提炼,存在三方面的困难。首先,诉讼速度所关联的制度利益的复杂性。刑事诉讼速度关联真相发现、人权保障、成本节约等多元利益,且不同利益对程序速度的要求是不同的,不能说某一种或几种利益一概求快或求慢,都受具体情况影响。因此如何确定诉讼速度对特定制度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极其复杂。
其次,受到损害的制度利益,其归属者的多变性。多元化的制度利益考量,分别关联不同刑事诉讼主体。控诉方、辩护方、裁判方甚至被害方,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因某一制度利益的损害而受害,但也可能因某一制度利益的损害而获利。很难说某一方刑事诉讼主体就必定倾向于追求某种利益,也难以机械地认定该方主体就应当基于该种利益的损害而获得救济。
最后,侵害制度利益的责任主体的模糊性。由于刑事诉讼速度由多方刑事诉讼主体的行为共同影响,即使程序速度丧失妥当性,也很难将速度过快或过缓现象,及其所引发的利益损害,明晰地归责于特定的一方或多方刑事诉讼主体。
突破上述三方面困难,是提升“诉讼不及时”范畴解释力的关键,现分别研讨如下。
(二)制度利益的四元划分
对制度利益的保障,是对刑事诉讼速度进行干预的正当性基础。同时,制度利益的相对明晰化,既是界定诉讼不及时的第一要点,也是其首要疑难。综览国内外研究状况可知,刑事诉讼速度所关联的制度利益,基本不会超出下述四方面:
首先,真实发现。诉讼速度过于迟滞,很可能导致证据灭失、证人记忆淡化,致使案件事实原貌难获还原②[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并且,司法必须建立在通过审判得来的生动印象的基础之上,所以不能被长时间隔断,以免裁判者淡忘了在审理中的所见所审③[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然而,倘若一味求快,又可能会导致侦控、审判人员因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忽视收集一些细微的但是对认定案情又至关重要的证据,或者因过分匆忙而无法仔细认真地审查判断证据,进而从纷繁杂乱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以查清案件事实①参见瓮怡洁《论刑事程序中的诉讼及时原则》,《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6期。。
其次,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受到强大的国家机关追诉的一方当事人,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侦控机关或审判人员的侵害。因此,有必要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承受的程序痛苦,尽快结束冗长的诉讼过程。如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迅速审判权旨在防止审判前的不公正和暴虐性的监禁,并将伴随公诉同时发生的担心和顾虑减少到最低限度,减少由于长期推迟审判对被告人所造成的自我保护能力损害的可能性”②[美]卡尔威因、帕尔德森:《美国宪法释义》,徐一东、吴新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同时,也要避免过快的速度损害辩方防御权③在United States v.Ewell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拜伦·怀特列举了迅速审判条款意图保护的三种利益:1.避免审前过度和难以忍受的监禁;2.减少被告对于案件结果的焦虑和担心,以及由于公诉带来的精神压力;3.减少对被告辩护权侵害的可能性,即因长期迟滞导致证人或者证据的缺失而致使被告不能有效辩护。See Po H.Chiu,Doggett v.United States:Adapting the Barker Speedy Trial Test to Due Process Violations,14Whittier L.Rev.893(1993).at898.。就被害人来说,诉讼速度过慢,会使其复仇的愿望难以及时实现,受犯罪损害的权利、利益也难以获得及时的救济。并且,冗长的诉讼同时也会加大被害人的负担和程序痛苦。但倘若诉讼速度过于快速,也不利于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有效参与。
再者,犯罪控制。迅速审判的重要性除了保障个人自由之外,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和震慑潜在犯罪的目的,国家和社会同样期待迅速审判④[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二卷·刑事审判)》,魏晓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倘若被追诉人实然上有罪,刑法和刑罚的及时实施,有利于威慑犯罪,及时矫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社会公众也是一种安抚。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推迟刑罚尽管也给人以惩罚犯罪的印象,然而,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惩罚,倒像是表演⑤参见[意]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47~48页。。倘若被追诉人实然上无罪,也有必要及时终结既有诉讼。然而,过于快速的诉讼速度,也不利于犯罪控制的实现。一方面,诉讼过快会阻碍真实发现,连带贬损犯罪控制的准确度。另一方面,随着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和多元诉讼价值的萌发,刑事诉讼的运行过程,越来越体现出矫治、教育的功能倾向。该种程序功能需要时间成本,过快的速度会使其无的放矢。
最后,成本节约。诉讼过程的迟滞可能会导致未决羁押时间延长,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行政负担压力,耗费国帑而难获实益。然而,如若过分求速,也可能加大诉讼过程中发生程序错误和实体错误的风险,对错误的修正和救济,将会引发更高昂的成本耗费。在我国目前越来越重视程序性制裁的大趋势下,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补正程序性违法的成本耗费。
(三)程序推进的主导角色与协助角色
就诉讼不及时所造成的制度利益损害,需要关注的是制度利益的受损者与侵害者。诉讼不及时在获得识别后,重要的功能在于引发救济或制裁的法律效果。诉讼主体所倾向的制度利益如果受到侵害,那么此诉讼主体一般是救济的获得者,而引发这种侵害的诉讼主体则往往是被制裁者。因此,对两者进行识别,是界定诉讼不及时内涵的关键性要点。对于程序速度影响力较小的一方诉讼主体,即程序推进的协助角色,两大法系尤其关注如何降低其利益倾向受侵害的可能性。以此为基础,采取一系列的救济措施对其利益予以关照。对于诉讼速度影响力较大的诉讼主体,即程序推进的主导角色,两大法系则侧重于考量其是否善意、勤勉、理性地推进诉讼。进而,为其设定了义务性规范和违反义务后的制裁性措施。
鉴于大陆法系采取审问制诉讼构造,诉讼的推进主要由审、控等官方刑事诉讼主体依职权主导,当事人的诉权影响较小。因此,大陆法系的诉讼及时原则,在制度层面侧重于设定官方义务,强调法官、检察官等官方诉讼主体的勤勉义务,分外关注官方刑事诉讼主体是否对诉讼速度进行了妥当、有力的调控。《欧洲人权公约》甚至为法院设定了由其保证诉讼中所有人员都要尽最大努力避免不必要拖延的特殊义务。
英美法系秉持对抗制传统,因此,其不仅极为强调官方诉讼主体的勤勉义务①欧洲对程序速度妥当性的判断标准是以“政府是否尽到勤勉义务”为中心,是一种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正向证明;英美判断标准以“被告人迅速审判权”是否被侵犯为中心,是一种站在公民立场上的反向证明,实际上也是反向强化对官方刑事诉讼主体勤勉义务的要求。为此,英美法系甚至不惜将被告人迅速审判权上升到宪法高度,并以此为基础审查实体法、判例法的公正性。,而且额外关注当事人较为强大的诉权影响。因此,英美法系在强调对官方诉讼主体进行制约的同时,将制裁的触角向辩护方做出了适度的延伸②美国《联邦迅速审判法》针对具有四种拖延诉讼行为的公诉人或辩方律师,设定了惩戒措施。详情参见[美]伟恩·拉费弗:《刑事诉讼法》(下册),卞建林、沙丽金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9页。。另外,日本《刑事诉讼规则》也有规定,在检察官或者律师辩护人违反有关诉讼程序的法律或者法院规则而妨碍审理迅速进行时,法院可以要求该检察官或辩护人说明理由。在前款的场合,法院认为特别有必要时,对于检察官应当向对该检察官有指挥监督权的人,对于辩护人应当向该律师所属的律师协会或者日本律师联合会,请求予以适当的处分。在该种理念下,对诉讼速度妥当性的追求,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而且也是其义务。比如,在被告人采取延宕辩护策略干扰诉讼的情况下,为遏制被告人的辩护权滥用,美国法甚至发展出了针对被告人的失权制裁③在Carruthers判例中,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判定,贫穷的被告人如果使用律师辩护权来操纵、延误或者阻碍审理程序,那么他可能被认定为默示弃权或者失权。See State v.Carruthers.35S.W.3d516,549(Tenn.2000),cert.denied,533U.S.953(2001).。该种理念认为:“律师帮助权是一个盾牌,而不是一把剑。被告人没有权利操纵他的权利以达到延误和阻碍审理的目的。”④参见 United States v.White,529F.2d1390,1393(8th Cir.1976).
刑事诉讼活动,实质上是由一系列的阶段、手续等程序片段构成的,且每一程序片段的速度均受控、辩、审等多方刑事诉讼主体诉讼行为的影响。虽然诉讼整体上的速度很难有绝对的主导者,但就每一程序片段而言,则可区分出何方刑事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对该程序片段存在主导性的影响,扮演程序主导者的角色;何方刑事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仅有协助性影响,扮演着程序协助者的角色。随着整体诉讼活动的推进,两种角色在控、辩、审甚至被害人等多方刑事诉讼主体之间动态游走。
程序主导者对特定程序片段的开始、运行、终止有制约力,是程序推进的强势一方,一般积极借由这种主导性而保障、追求其所倾向的制度利益,同时也往往成为对他方所倾向制度利益的侵犯者,以及诉讼不及时的责任主体和被制裁对象;而程序协助者,一般仅有协助角色,是程序推进的弱势一方,其所倾向的制度利益多受侵害,因而往往是受到关照与救济的对象。
四、诉讼不及时的双层逻辑构造
刑事诉讼速度所关联的制度利益,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片段的主导权归属,是解释诉讼不及时现象的两个前提,也是提炼诉讼不及时逻辑构造的两个基本点。在此基础上,以诉讼不及时范畴的功能为线索,可以抽象出诉讼不及时的逻辑构造。诉讼不及时这一范畴的应用,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制度利益的损害,确定侵害者和受损者,进而引发救济或者制裁的法律效果。因此,“救济”或“制裁”的法律效果,作为诉讼不及时的功能指向,反向影响着对诉讼不及时内涵的界定。
然而,引发救济的诉讼不及时和引发制裁的诉讼不及时,在实体规则层面,却体现了两种互有差异的构成标准。这也导致了诉讼不及时的逻辑构造,呈现出“损害认定标准+责任追究标准”的双层次递进形态。
(一)第一层:损害认定标准中的诉讼不及时
对刑事诉讼速度予以评价,其正当性基础在于过快或过缓的速度将会引发特定制度利益的损害。因此,无论该损害归责于何方,确定损害的存在是界定诉讼不及时的第一步。而且,认定损害的存在并衡量其程度,这与后续救济措施的引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损害的识别与认定,也构成了诉讼不及时在第一个层次的界定标准。这一层次,关注的要点是:何种速度状态引发了何方刑事诉讼主体所倾向的何种程度的制度利益损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2年在巴克诉温果(Barker v.Wingo)案中,确立了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迅速审判权条款的司法判断标准。抛弃了将“迅速”量化为特定的天数或月数的僵化做法,确立了一个由四个因素组成的平衡检验,即著名的“巴克平衡测试”。该测试通过分析“迟滞的时间、迟滞的理由、被告人对迅速审判权的主张和迟滞对被告人造成的损害”这四个因素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被告人的迅速审判权是否受到侵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救济措施,为迅速审判权的实践操作提供了依据①See generally Darren Allen,The Constitutional Floor Doctrine and the Right to a Speedy Trial,26Campbell L.Rev.108-116(2004);Justin Daraie,Criminal Law—The Road not Taken:Parameters of the Speedy Trial Right and How Due Process Can Limit Prosecutorial Delay,9Wyo.L.Rev.175-179(2009);Anthony L.Ciuca,The Right to A Speedy Trial—The Montana Supreme Court Realigns Itself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s Balancing Test,39Rutgers L.J.911-916(2007-2008).。其中,对诉讼迟滞时间要件的考量、对被告人受损状况的考量,均是损害认定层面界定诉讼不及时的标准②依据美国法,迟滞的时间作为损害存在的推定性因素发挥作用,单纯其长短,并不必然构成对被告人的侵害。此外,拖延对被告人的不利影响,是确定迅速审判权的关键性要件,若无不利影响,被告人任何主张皆无基础。相较之下,被告人对迅速审判权的主张则作为证明性因素发挥作用,只是将被告人反对拖延的频度和力度作为考虑要点之一,如果被告人没有正式主张这项权利,并不能推认其放弃。。
大陆法系对诉讼及时性原则的追求,集中体现在《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6条所确立的“合理期间审判”规则之中③《欧洲人权与自由保障公约》第6条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与义务或在决定对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与公正的法庭之公平与公开的审讯。”。对诉讼速度并非设立抽象期限,也是在个案斟酌前提下的综合判断,最重要的标准是欧洲人权法院1981年在巴克霍尔兹诉德国案判决中所提出的3+1要件衡量标准。具体包括四方面要件:第一,案件在法律及事实层面的复杂性;第二,案件对于被告的严重性,主要是指程序结果的严重性;第三,被告人本人的行为和态度是否为可归责与被告行为和态度所导致的诉讼迟滞;第四,国家机关的行为与态度④林钰雄:《刑事诉讼法(总论篇)》,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42页。。其中的第二要件,就诉讼迟滞对被告人利益重要性的考虑,也体现了损害认定层面界定诉讼不及时的标准。即,案件可能的结果对于被告权益的剥夺程度,影响诉讼迟滞的认定。
两大法系对刑事诉讼程序速度的关注主要侧重于诉讼迟滞问题。关注其界定标准可以发现,美国的判断标准以“被告人迅速审判权利是否被侵犯”为中心,而欧洲的判断标准则侧重于判断“政府是否尽到勤勉义务”。但这仅是相对而言,由于上述两种界定标准,皆以试求评价是否有必要对特定的案件和判决施以否定性评价,作为其终局性的目的,因此,无论是欧洲人权法院还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司法活动不仅重视制度利益损害的存在及程度,而且更为关注损害造成者的过错和可归责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损害认定标准层面的诉讼不及时,貌似仅是引发后续制裁措施和否定性评价的前提条件而已。
然而,损害认定标准层面上的诉讼不及时,相对于后面将要进一步论及的责任追究标准来说,有其相对独立的重要制度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其与救济措施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原则上来说,只要损害认定标准达成,程序协助者即有获得救济的正当性,该种正当性并不以损害可归责于程序主导者为必然前提。损害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之间的差异,根源于救济与制裁之间的法理差异。即,救济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遭受了损害,救济的实现并不必然性地附着于对责任者的制裁而发生。这在各国的制度层面也有多方面体现①利益损害获得认定后,一般涉及预防性救济与补偿性救济等两类救济,其均与制裁的思路截然有异。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预防性救济,该种救济有利于即时调整诉讼速度,降低损害程度。预防性救济是一种事中救济,并不必然关联对责任主体的惩戒。典型如《奥地利法院组织法》第91条设定的加速抗告程序,即,在事实审法院程序延宕时,赋予诉讼当事人直接向上级法院就程序速度问题提起抗告的权利,目的是由上级法院直接诫命事实审法院加速裁判的进行,具体措施如指定期日、追捕鉴定、裁判预备等。相较之下,制度利益受损后的补偿性救济,则是一种事后救济,该种救济虽然往往与对责任主体的制裁密切相关,但也呈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如德国实务对程序被拖延的被告,采取量刑减轻和以延迟期间折抵刑期(类推适用羁押折抵规定)的补偿方案。上述两种独立于制裁的救济措施,均系损害认定标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不必然与责任的追究相关联。,支持与印证着损害认定标准的独立性意义。
(二)第二层:责任追究标准中的诉讼不及时
诉讼速度的过快或过缓造成了制度利益的损害,这是识别诉讼不及时并对诉讼速度进行干预的根源性原因。因此,损害认定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是第一性的。另外,倘若该种损害因程序主导者的过错(故意、过失)所致,则确有必要追究程序主导者的责任。通过引发某种形式的制裁方式,为诉讼不及时的治理提供长效性的制度保障。因此,以程序主导者的责任为核心,诉讼不及时也密切关联对责任主体的制裁问题,体现为诉讼不及时在责任追究层面的界定标准。
典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对诉讼迟滞原因的探讨,具体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控方或者辩方基于诉讼策略而故意造成的拖延;第二种是法院积案严重、日程紧张造成的拖延;第三种是正当拖延理由,如证人无法出庭造成的拖延。前两种情况均构成责任追究标准意义下构成诉讼不及时的要件。鉴于美国确定迅速审判权受侵犯的标准,主要是用于判断是否需要实施撤销起诉等程序性制裁。因此,其关键性的衡量因素,系案件拖延的事由是否是故意的、违宪的,任何偶然的、超出检方控制能力范围的拖延都是合宪的;又如欧洲人权法院对诉讼迟滞所采取的“3+1”标准,案件的复杂性、被告人的态度和行为、案件对申请人的重要程度等三方面因素,最终汇集到一个根本性的最终要素的衡量——被诉国家的态度和行为。即,审查有无可归责于国家的懈怠事由(比如,频频发回重审),以及法院是否恪尽加速审理的特别勤勉义务②尤其需要注意,因司法政策不当而导致的制度性延迟,整体责任在国家,不得作为个别诉讼迟滞的合理化事由。。将被诉国家态度和行为作为认定诉讼不及时的终局性要素,无疑也体现了责任追究标准意义上诉讼不及时。制裁诉讼不及时的制度措施具有多样性,且均以利益损害标准和责任追究标准同时成立为其适用前提。并且,很多制裁措施,往往同时兼具救济功能③如德国的终止诉讼和美国的驳回起诉,均既有制裁效果,也有救济功能。分别参见[德]克劳斯·罗科信著《德国刑事诉讼法》,台北:台湾地区三民书局,1998年,第150页;卞建林《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损害的确定与救济,责任的追究与制裁,两者实际上是两种方向的思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受制于其终局性的裁决地位与程序性制裁实施者角色,实际上忽视了利益损害标准的独立意义。倘若不对诉讼不及时在损害认定层面和责任追究层面的界定标准进行适当分离的话,那么将意味着:两层次任何一层次的标准不具备,则均不能认定诉讼不及时的存在。在这种逻辑下,诉讼不及时的责任追究标准吞噬了损害认定标准的独立性。即使制度利益确实发生了损害,如若不能将原因明确地归责于程序主导者,那么制裁将难以成立,救济的机会也会随着制裁的不成立而同时葬送。由此可见,为了对诉讼不及时现象做出较为精细的解释,损害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绝对不能混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获得进一步阐明。
(三)双层标准之间的四种逻辑关系
诉讼不及时现象的损害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之间的划分,初步形成了解释诉讼不及时现象的双重逻辑构造。两层次标准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存在四种情况:第一,如果损害可被归责于程序主导者,那么对程序主导者的追责与制裁,一般可以同时构成对受损主体的救济。这是较为通常的一种情况。比如说美国的撤销起诉制度,既是制裁,也有降低制度利益损害的救济效果;第二,损害不可归责于程序主导者,损害系利益受损者自身原因所致。此时,利益受损者对损害有容忍义务,不具备获得救济的正当性,程序主导者因而也就无须承担责任。这是两种标准绝对分离的情形。如欧洲人权法院“3+1”标准中对被告人行为和态度的考量,即用于分析迟滞是否可归责于被告人;其三,损害既不可归责于程序主导者,也非利益受损主体一方的原因所致。此时,利益受损主体无法借助对程序主导者的制裁而获得救济。针对此种情况,国家有可能作为第三方为制度利益损害提供最终救济①如就法院案件积压所导致的诉讼迟滞,大致属于该种类型。积案所致的诉讼迟滞,虽然并非控方责任所致,但美国有时仍会将其认定为诉讼迟滞,由控方承担被驳回起诉的不利益。控方仅是代替国家为救济的提供而承担附属性成本。另外,因为该种原因的驳回起诉不是制裁,故而美国司法实务的操作方式较有弹性。两相比较之下,欧洲则更倾向于国家负责,原则上不能将案件积压作为国家免责的依据。。最复杂的是第四种情况,利益损害非因利益受损者自身原因所致,本因程序主导者的行为失妥所致。但是,司法政策对程序主导者予以较大的宽容,就该种损害为利益受损者设定容忍义务,剥夺其寻求救济、主张对责任者施以制裁的权利。
诉讼不及时的双重界定标准实际上是对各方刑事诉讼主体善意、勤勉义务的统筹性关注。鉴于上述损害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之间的不同逻辑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用于识别损害的存在及其程度的损害认定标准是第一性的,无损害就无界定“诉讼不及时”以干预刑事诉讼速度的必要,从而也就不涉及救济或制裁;有损害却不一定有救济;再如一国政府出于司法政策考虑,为特定利益损害设定容忍义务,此时,受损方也难以获得救济或者制裁,即使有救济,也未见得一定构成制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有些情况下,确实救济和制裁是一体的,制裁同时也构成救济。然而,切不可混同两种理念倾向的差异,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制度风险。比如,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设定,即混淆了救济与制裁的法理界限,致使损害救济和责任制裁均难以实现。因此,有意识地区分诉讼不及时的双重界定标准,能对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提供更加充分的解释力。
五、诉讼不及时与程序性违法
程序性违法②我国学界常用的“程序性违法”概念,由于以程序性制裁为其目的和归宿,故指的是官方诉讼主体的违法行为,其主体并不涉及被告人。与程序性制裁密切相关,是确定诉讼行为主体有责性的关键性概念。一般认为,程序性违法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可以具有侦查违法、公诉违法和审判违法等具体形式③陈瑞华著:《程序性制裁理论》(第二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405页。。但是,什么是“违反法律程序”,却存在解析的空间。基于上述界定诉讼不及时的双层逻辑构造,很多理论问题可迎刃而解,如诉讼不及时与程序性违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合法性标准:程序性违法意义下的诉讼不及时
就刑事诉讼专门机关适用诉讼法的行为,存在裁量性违法与执行性违法之区分。前者涉及对刑事诉讼法实体性条件④参见锁正杰著《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及以下。的理解与适用,在裁量空间内不宜过分压制行为人主观理性,一定程度上的不妥甚至错误均可予以容忍,仅在行为人滥用裁量权,严重超出裁量范围,方可归入裁量性违法而遭受谴责,这是保障职权获得积极有效行使的前提。相对而言,执行性违法仅涉及对程序性规则的严格执行,并不具有裁量空间,因而其具有显著的可谴责性。
判断诉讼不及时与程序性违法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考量诉讼不及时所违反规范的性质。诉讼不及时既是对诉讼及时性原则的违反,也是对被告人迅速审判权的侵犯,因而其所触犯的规范形态,一般来说应为法律原则。虽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诉讼及时性原则与迅速审判权,目前已从原则性规范具体化为了规则性规范⑤典型的立法例如美国的《联邦迅速审判法》、日本的《裁判迅速化法》等等。,但是,鉴于程序速度所牵涉的因素过于复杂,原则性规范即使在一国已经获得法定化、具体化,其所形成的规则一般也较为抽象,往往保留了较大的裁量空间。由此可见,诉讼不及时问题,格外地呈现出合理性与合法性相交织的特征。
在特定国家,某种诉讼不及时现象是否构成程序性违法,密切受该国法律层面对诉讼迅速要求的法定化程度影响。举例而论,有些国家将对诉讼速度的要求机械性地规定为对诉讼期间时点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特定的时间点要求即为诉讼不及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界点,超过时间点即构成程序性违法①当然,也有程序片段没有超期,但是整体上速度过缓,也可能构成合法性问题,引发制裁,比如说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有对被告人羁押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八年的规定。2012年5月,该“八年羁押上限”条款已在刑事诉讼中首度获得适用,详情参见中国新闻网:“台湾‘速审法’首例8度判死刑因羁押逾8年获释。”访问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tw/2012/05-19/3900410.shtml,网页发布时间:2012年5月19日,访问时间2013年12月1日。。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诉讼不及时现象,确实可以表现为程序性违法的形态,进而引发程序性制裁。并且,其大多会体现为程序性违法中的裁量性违法,其认定过程中具有较大的裁量性空间。然而,在某些法定化程度较高、操作弹性不足的国家,诉讼不及时也可能体现为执行性违法。
(二)合理性标准:程序性违法之外的诉讼不及时
程序性违法范畴有其局限性,一般来说,程序性违法往往更趋向于责任追究标准层面的诉讼不及时。由于其与程序性制裁的关联性过于密切,因而也就往往欠缺对损害认定标准的统筹考虑。受不同国家法治化程度差异的影响,仅关注程序性违法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举例而言,倘若一国将特定程序的期限规定为30天,耗费31天即构成程序性违法。该期限点,对程序性违法的认定和制裁的启动无疑很有意义,但是,从对损害进行救济的角度来看,却存在明显的解释力缺陷。毕竟,无论时间耗费是30日或是31日,对制度利益的损害程度无甚差别。
对此,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在于:程序主导者不构成程序性违法,是否能够当然地成为制度利益受损方对利益损害应当承担容忍义务的理由?这是问题的要害。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无论一国对诉讼速度的妥当性要求,在立法上的法定化程度如何,真正有解释力的诉讼不及时概念,必须突破“程序性违法”范畴的限制,应当是合理性标准(基于损害认定标准)和合法性标准(基于责任追究标准)的结合。诉讼不及时,既有合理性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也有合法性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
合理性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虽未见得引发违法性宣告和程序性制裁,但却是一系列救济和督促措施的基础。尤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程序速度方面的要求极为弹性,特别是为官方刑事诉讼主体诉讼行为所设定的时限,不仅标准极为宽松,且缺乏制裁性后果。因此,程序性违法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在我国的存在范围实然上极其狭小。在此情况下,合理性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由于不依赖合法性标准,其解释性意义分外重要,不仅可以作为检讨程序主导者(尤其是官方诉讼主体)勤勉义务的理论坐标,而且可以成为评估其业务质量的实务线索,故而可以密切联系对法律人职业惩戒机制的理论探究。除此之外,对合理性层面和合法性层面诉讼不及时认定标准的分别关注,可以有效解释制度利益受损者的容忍义务范围与利益侵害者行为合法性之间的关系。程序违法意义上的诉讼不及时,并不必然等同于利益受损者的容忍义务范围。合法,不一定就应当被容忍,也不一定就当然剥夺利益受损者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程序性合法”的范畴,有必要在程序性制裁的框架之外,向制裁与救济的双重方向扩展其内涵。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