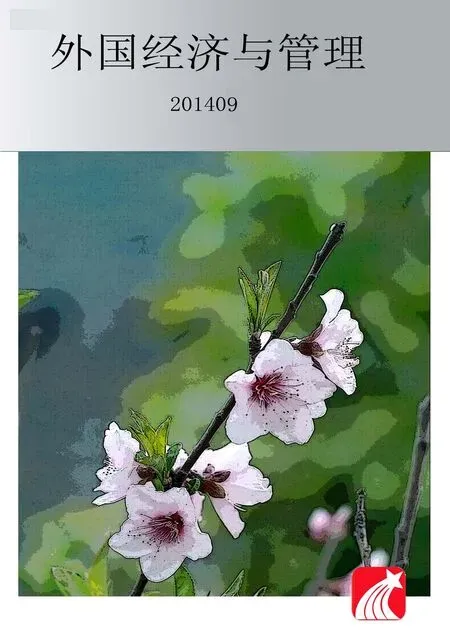补偿性消费研究回顾与展望
柳武妹,王海忠,陈增祥
(1.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3.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 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消费行为背后的动机往往是复杂的,很难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解释。比如,遭遇社会排斥(如考试失败、与恋人分手、婚姻破裂等)后,人们既会非常亲社会(如向慈善机构捐钱)(Ward和Broniarczyk,2011),又会降低对他人的同情心,并且变得更加怀旧(Twenge等,2007);缺乏权力与金钱时,人们反而会购买昂贵的奢侈品和稀缺的物品(Rucker和Galinsky,2008;Rucker等,2012);经历大的灾难与事故后,人们往往会购买国货(Friese和Hofmann,2008;Liu和Smeesters,2010),并且会有更强的物质主义倾向(Arndt等,2004;Rindfleisch和Burroughs,2004);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和不够自信时,人们会选择能够提升自信与智力的产品(Gao等,2009)。鉴于面临社会排斥、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工作碌碌无为等是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活常态,因此,对于营销者而言,关注消费者在这些状态下的心理和行为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只有洞察消费者相关心理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需求,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战略,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财务回报。本文认为,消费者的慈善捐助行为、对奢侈品和稀缺物品的购买、对国货的偏爱、对提升智力的产品的过度关注等,都可以从补偿性消费的视角来解释,即消费者之所以表现出这些行为,是为了应对威胁,获取内心的平和与自我价值感。本文将从需求受威胁和自我概念受威胁这两个角度,对补偿性消费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期促进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探讨,并为企业的营销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二、补偿性消费的概念界定
关于补偿性消费(compensatory consumption)概念的界定,学者们至今未达成一致。早期的研究常从需求未得到满足的角度来界定补偿性消费,而近几年的研究常从自我概念(self-concept,即对自己的多维认识)受威胁的视角来看待补偿性消费。“补偿性消费”一词最早由Gronmo(1988)提出。Gronmo发现,人们的很多消费行为(如成瘾消费、强迫性购物等)是为了寻求生活现状与内心需求的一致。由于现状和需求往往很难一致,因此人们会通过消费来补偿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这种消费即被称为补偿性消费。之后,Grunert(1993)进一步解释了补偿性消费概念。Grunert认为,人们的需求可以通过多种资源来满足,这些资源可以是与需求相对应的资源x,也可以是表面上与需求没有关系的资源y。比如,当人们的人际归属需求未得到满足,感到孤独时,他们既可以直接去和亲密的朋友约会,也可以去看一场喜剧电影。因此,Grunert指出,缺乏x既可以通过获取资源x来进行治愈,也可以通过获取资源y来进行治愈,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过程就被称为补偿(compensation)。
基于学者Belk(1988)提出的产品能够反映消费者延伸的自我这一观点,近期的补偿性消费研究开始从自我概念受威胁的角度来定义补偿性消费。由于产品自身具有象征含义,能够向消费者自己(Solomon,1983)和他人(Belk等,1982)传递信息(如收藏画作的人常被认为很有创造力,开宝马车的人常被认为很有财富与地位),因此,产品是Grunert(1993)提及的资源中的一种。基于这一理解,学者Rucker在2009年的北美消费者研究会议(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Research)上对补偿性消费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他认为,补偿性消费是指消费者在其自我概念(如自我价值感、自尊等)受到威胁时,通过偏爱和选择能够应对这种威胁的产品来进行补偿(Rucker,2009)。最新的补偿性消费研究认为,补偿性消费所涉及的产品既可以表面上与自我概念受到的威胁无关,也可以与自我概念受到的威胁相关(Kim和Rucker,2012)。这一观点虽与Grunert(1993)对补偿性资源的界定相冲突,但被很多学者采纳。同时,Kim和Rucker(2012)认为,补偿性消费包括先行性补偿性消费(proactive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和反抗性补偿性消费(reactive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两类。前者发生在威胁尚未出现时,是消费者的一种具有预见性的事前消费,目的是预防未来自我概念可能受到的威胁;而后者发生在威胁出现后,是消费者的一种事后应对,目的是减轻或消除所体验到的自我概念受到的威胁。Kim和Rucker(2012)指出,反抗性补偿性消费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现,分别是象征性自我完成(symbolic self-completion)(如缺乏成就时,人们会在自己的简历中写上一大串头衔)和转移对威胁的注意。在现实生活中,属于先行性补偿性消费的例子有,在参加重要宴会前试穿或试戴珠宝首饰,以避免自己在宴会上丢丑等;属于反抗性补偿性消费的例子有,在感到自尊受威胁时暴饮暴食,以转移对威胁的注意等。
本文认为,需求受威胁与自我概念受威胁这两个视角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有重叠之处。比如,自尊既是消费者的基本需求(Pyszczynski等,1997),又涉及消费者的自我概念(Lisjak等,2012);同样,对人际归属的渴望是消费者的一种基本需求(Pyszczynski等,1997),而这一需求的满足又能让消费者感受到自我价值(Pettit和Sivanathan,2011)。但是,为了脉络清晰起见,本文将分别从需求受威胁和自我概念受威胁这两个角度来阐释补偿性消费。结合学者们对补偿性消费的定义,本文将补偿性消费定义为,消费者在其基本需求(求生、人际归属、控制等需求)或自我概念受到威胁时,通过消费来应对威胁的一种策略。鉴于已有的补偿性消费研究对Kim和Rucker(2012)提出的先行性补偿性消费的关注非常少,本文着重回顾反抗性补偿性消费相关研究。
三、 需求受威胁视角的补偿性消费研究
对生命永恒的需求、对控制外界的需求、对人际归属的需求等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Pyszczynski等,1997)。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很难长生不老、很难改变和影响环境中的人和事,且常常遭到他人的拒绝和社会的忽视。研究表明,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控制的缺乏以及社会排斥时,个体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并会产生强烈的摆脱这种焦虑和不安的渴望(Sheldon和Kasser,2008)。由于消费行为具有象征含义,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焦虑和不安,获取内心的平和(Wattansuwan, 2005),因此,人们常常会通过消费来对自己进行补偿。下文将具体阐述生存需求、控制需求以及人际归属需求等受威胁时,消费者的具体补偿方式。
(一)应对生存需求所受威胁的补偿性消费
媒体对死亡新闻的报道以及亲友的离世等都会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死亡。在想到死亡时,人们常会陷入恐慌和焦虑状态(Beck,1973)。学者Rosenblatt等(1989)提出了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来预测人们应对死亡恐惧和焦虑的方式。TMT认为支持文化世界观(supporting cultural worldviews)可以起到缓解死亡恐惧和焦虑的作用(Rosenblatt等,1989),因为支持文化世界观会让人感到虽然自己的肉体会从世界上消失,但精神和思想却会被持有相同文化世界观的其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后代)延续和传承下去(Rosenblatt等,1989;Pyszczynski等,1997)。TMT的这一观点启发了营销学者Maheswaran和Agrawal,他们在2004年将TMT引入消费行为研究。鉴于国家内群体(ingroup)是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Rosenblatt等,1989),而国货又能反映消费者的国家内群体身份(Elliott和Wattanasuwan,1998),因此,Maheswaran和Agrawal(2004)提出了死亡威胁会增强国货偏好的命题。后续实证研究显示,当提及与死亡相关的信息时,人们倾向于偏爱和支持本国(相对于外国)产品(如软饮料和巧克力)(Friese和Hofmann,2008;Fransen等,2008;Liu和Smeesters,2010),因为死亡信息激发了消费者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死亡信息增强国货偏爱的现象会持续24小时之久(Liu和Smeesters,2010)。
死亡威胁除了影响国货消费外,还能塑造消费者的其他消费观念,如放纵性消费、奢侈品消费、物质主义、风险寻求和多样化寻求等。具体而言,Mandel和Smeesters(2008)研究发现,让消费者想象自己的死亡能促使他们超出经济预算去购买物品(如杂货店的食物),并且能促使他们过量饮食以转移对死亡的注意。死亡威胁增加放纵性消费的现象在Friese和Hofmann(2008)以及Ferraro等(2005)的研究中也被提及。但Ferraro等(2005)认为,死亡威胁导致放纵性消费的原因是,死亡威胁会让消费者感到自己可调控的资源有限,因此会选择放纵自己以节省精力。除放纵性消费外,死亡威胁还会增加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增强消费者的物质主义倾向,让消费者在临死前拼命地积攒财富以便不枉度一生(Mandel和Heine,1999;Arndt等,2004)。死亡威胁增强物质主义的另一种解释是消费者能够从拥有物中获得安全感,得到心理慰藉(Rindfleisch和Burroughs,2004;Rindfleisch等,2009)。此外,死亡威胁还会影响消费者的风险寻求和多样化寻求倾向,但关于具体的影响方向,学者们观点不一。有些学者认为,死亡威胁会增强消费者的风险寻求倾向(如进行鲁莽和超速驾驶),其内在机理是冒险行为能够增强自尊和人生掌控感(Ben-Ari等,1999;Miller和Mulligan,2002);有些学者则认为,死亡威胁会降低多样化寻求和风险寻求倾向,促使消费者选择熟悉的产品(如薯片),因为熟悉的产品有助于消费者体验到归属感和减轻死亡焦虑(柯学,2009)。
(二)应对控制需求所受威胁的补偿性消费
本部分将首先阐述广义层面的个人控制感缺乏与应对理论,接下来简述权力(即对他人施加影响和控制)的缺乏所导致的补偿性消费。由于自由和控制紧密相关,缺乏自由时人们很难对环境中的人和物施加控制,因此我们还将简述消费者的自由受限与补偿性反应。
1.个人控制感的缺乏与补偿性消费。个人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影响、预测和解释外部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信念(Burger,1989)。获取较高的个人控制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Burger和Cooper,1979),但单独的个体往往能力有限,很难完全掌控外部事件(如地震、金融危机、产品在市场上遭遇失败等)的发生与发展,因此人们常会感到自己缺乏个人控制感,并有强烈的控制需求(Burger,1989)。学者Rothbaum等(1982)提出了双过程模型,认为在控制需求受到威胁时,人们会经历初级控制(primary control)和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两种应对过程。初级控制指的是控制外部环境以满足自己的期望,但个体一般很难控制环境,因此初级控制往往会失败;在失败后,人们会转向次级控制,即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人们可以寻求的次级控制源有四类,分别是预测控制(即将不能掌控的事件归因于自己能力有限,以避免自我失望)、幻觉控制(即将不能掌控的事件归因于运气、偶然和命运)、代理控制(即将不能掌控的事件归因于强有力的他人或机构)和解释控制(即上述三种控制源的结合)。
上述双过程模型,尤其是次级控制的观点,对消费行为研究影响深远。学者们发现,次级控制可以解释许多消费心理和行为。比如,Cutright(2012)认为,缺乏个人控制感会促使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寻求结构与秩序,由于边框象征着结构和秩序,因此缺乏控制感的消费者会偏爱外围有边框的品牌标识、带有边框的画作以及便利店中有边框和隔板的货架,以增强预测控制。Cutright等(2013)进一步将控制感受威胁与品牌延伸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缺乏控制感的消费者和产品经理都偏爱可以理解和预测的品牌延伸(如一家汽车公司想开办一个小型赛车中心),而非不能理解和较难预测的品牌延伸(如一家汽车公司想开办一个旅游度假中心),感知匹配度在这一现象中起中介作用。此外,控制感的缺乏会增强人们的助人和慈善捐助倾向,促使人们相信帮助他人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从而实现幻觉控制(Converse等,2012)。控制感的缺乏还会增强人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使个体认为自己所处的种族或民族比其他种族或民族优越(Agroskin和Jonas,2010),从而体验到代理控制。
2.权力缺乏与补偿性消费。权力(power)作为一种反映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信号,令很多人极为向往。但权力常常掌握在少数人(如老板、领导等)手中,大多数人(如员工、下属等)处于权力缺乏状态。研究表明,权力匮乏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让消费者变得更加看重社会赞赏和他人的注意。具体而言,当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权力来影响他人时,他们会倾向于购买能够显示身份与地位的声望产品(Rucker和Galinsky,2008;Rucker等,2012),以获取代理权力(Mazzocco等,2012)并保护自我的完整(Sivanathan和Pettit,2010);会倾向于购买外观漂亮但不实用的产品,以引起他人的注意(Rucker等,2012);会偏爱大号产品、喜欢用大的餐盘,原因是大的尺寸象征着显眼的身份与地位(Dubois等,2012);会喜欢从大的选择集中进行选择,因为大的选择集和权力具有相互替代性,两者都能增强消费者的个人控制感(Inesi等,2011)。
3.自由缺乏与补偿性消费。与权力缺乏相比,学者们对自由缺乏与补偿性消费间关系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空间自由和选择自由上。以Rui Zhu为代表的学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Meyers-Levy和Zhu(2007)发现,让消费者处在一间天花板离地面较近的房间时,他们会感到自己的空间自由受限,并认为面前的产品(咖啡桌和放葡萄酒的架子)与常见的同类产品更加不同。Levav和Zhu(2009)将这一实验结果放在真实的超市购物环境中进行检验,发现当超市的走廊变窄时,消费者会感到其空间自由受限,并会选择独特的、多样化的产品,以获取更多的选择自由。关于消费者为什么如此渴望选择自由,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消费者相信自己选择(而非他人代选)的产品性能更好(Botti和Hsee,2008),并且自己做选择时更不容易受外界说服信息的影响(Yuan和Dhar,2008)。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限制选择自由时消费者是否会渴望空间自由,是否选择自由越大(即消费者的选择集越大)越有利于消费者做选择等话题。
(三)应对人际归属需求所受威胁的补偿性消费
在现实生活中,获取人际归属感并非易事,人们在社交圈或工作场所常常会遭到他人的拒绝或忽视,比如与恋人分手、婚姻破裂、考试失败、被辞退等,这些现象也被称为社会排斥(Kim和Rucker,2012)。学者Lee和Shrum(2012)将社会排斥分为被忽视和被拒绝两类。他们认为,在被他人忽视时,消费者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引起他人的注意;在被他人拒绝时,消费者会通过助人和慈善捐助等亲社会行为来获取人际归属感。无独有偶,Mead等(2011)也观察到遭遇社会排斥者强烈的获取他人注意和认可的心理。他们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促使消费者购买象征群体身份的产品(即使该产品并不实用)、依据交往对方的消费偏好来调整自己的消费偏好,甚至为了提高人际亲密性而尝试非法药物。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发现,社会排斥会降低消费者对他人的同情心、增加消费者对怀旧产品的购买(Twenge等,2007)、增强消费者的宗教信仰(原因是宗教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缓解由社会排斥带来的痛苦)(Aydin等,2010)、降低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具体表现为吃更多的饼干)(Burson等,2012)。可见,社会排斥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能促使消费者通过主动迎合他人和炫耀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来获取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消费者通过寻求精神慰藉(如宗教信仰和怀旧)和放纵自己(如过量饮食)来逃避社会接触。
上文依次梳理了生存需求、控制需求以及人际归属需求等受威胁后消费者的应对反应及其理论机制。尽管每类威胁所引发的具体应对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目的性——试图通过消费来缩短现状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实现内心的平衡。可见,消费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其终极目的在于补偿内心未得到满足的生存渴望、控制渴望和人际归属渴望。接下来,我们将从自我概念受威胁的视角来继续阐释补偿性消费。
四、 自我概念受威胁视角的补偿性消费研究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一种动态的知识结构,包含多个与自我(self)相关的个体特点、特质以及社会角色,这些成分相互连接,组成一个多维的网络,以指导人们的行为(Markus和Wurf,1987;McConnell,2011)。Epstein(1973)认为,自我概念是关于自我的一种理论,它具备成为一个理论的特征(如广延性、简洁性、可测性等)。因此,自心理学泰斗Williams James在1890年提出“自我”这一概念后,学者们对自我概念持续探讨了上百年,至今仍兴趣不减。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具有双重性(大多数情况下是稳定的,但会因重大事件而发生改变)(Markus和Kunda,1986)和无穷性(具有多个可能的自我,可以无限发展)(Markus和Nurius,1986)。回顾以往有关自我概念受威胁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股分支,分别是社会身份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个体身份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以及拥有物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接下来,本文将对各股分支进行梳理。
(一)社会身份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
人处于社会环境中,通过与环境中的人和物发生联系来形成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社会身份是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它来自于人们对自己在社会群体中身份的感知(Tajfel和Turner,1986)。White和Argo(2009)将那些重视和认同自己社会身份的个体称为高集体自尊者,将那些不愿意与社会群体发生联系、不认同自己社会身份的个体称为低集体自尊者。研究显示,高集体自尊者和低集体自尊者在其社会身份面临威胁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反应。具体而言,学者Ellemers等(2002)认为,对于高集体自尊者,社会身份受到威胁会促使其更加忠实于自己所处的集体,并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对于低集体自尊者,社会身份受到威胁反而会促使其脱离所处的群体。学者White和Argo(2009)将这一研究结论应用在了消费情境中。他们指出,当社会身份(如女性形象)受到威胁时,低集体自尊者倾向于避免选择与其社会身份相联系的产品(如女性专用笔),当该产品具有负性效价、会引起负面联想(如女性的智商较低)时,低集体自尊者的产品回避倾向更为明显;相反,当社会身份(如女性形象)受到威胁时,高集体自尊者更加偏爱与其社会身份相联系的产品。
(二)个体身份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
与社会身份相比,学者们对消费者个体身份(personal identity)的关注更多。个体身份和社会身份处在同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上,因此,对自己社会身份认同度低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个体身份感知(Ellemers等,2002)。高个体自尊者往往集体自尊较弱,个体意识较强。下文将具体阐述消费者在其个体身份受到威胁时的应对反应。
1.自尊主要成分受威胁时的应对反应。自尊是一个多维概念,由自信、能力、成就、创造力等多种成分构成。学者们常通过探讨自尊的组成部分受到威胁时人们的应对反应来了解人们如何应对自尊所受的威胁。具体而言,当消费者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不够自信时,他们会选择能够提升智力与自信的产品(Gao等,2009);当消费者认为自己能力不强时,他们会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加友善,以维持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Holoien和Fiske,2013);当消费者缺乏成就时,他们会在写给他人的邮件末尾添加自己的一大串头衔,以便象征性地表明自己很有成就(Harmon-Jones等,2009);当限制消费者完成创造性任务所需的时间和材料时,他们会更具创造力(Moreau和Dahl,2005)。综上,消费者自尊的主要成分受到威胁会促使消费者极力向他人证实这些成分的完好,以获取虚假的内心平衡。
2.自我价值受威胁时的应对反应。高自尊会让消费者体验到自我价值(self-worth),但人们的自尊经常会受到威胁,此时人们会怀疑自我价值。研究表明,自我价值的匮乏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支付方式。具体而言,强迫性消费(如强迫购物、成瘾购物)尽管长期来看会让消费者产生负债,并体验到自责、愧疚等负面情绪,但在短期内却有助于消费者获取售货员的赞赏,从而增强自我价值感(O’Guinn和Faber,1989)。除强迫性消费外,自我价值受到威胁还会促使消费者偏爱信用卡支付而非现金支付(因为相比现金支付,信用卡支付时人们不会直接看到钱币的减少,不会体验到心理痛苦),同时会促使消费者用信用卡来超额购买奢侈品,以炫耀自己的财富并获取他人的注意(Pettit和Sivanathan,2011)。自我价值受威胁与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在Sivanathan和Pettit(2010)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
(三)拥有物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
消费者的自我不仅包含自己的身体、容貌、个体特征和特质等,还包含自己所拥有的房子、家具、宠物等拥有物(James,1890)。实质上,拥有物组成了消费者延伸的自我(Belk,1988)。以往探讨拥有物受威胁(如丢失、受到负面攻击等)与随后的补偿性消费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分支:第一,钟爱的品牌受到攻击。来自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研究已经证实,消费者会将钟爱的品牌视作自己亲密的伙伴、伴侣甚至自己的一部分(Fournier,1998),然而消费者所钟爱的品牌有时会受到威胁(如发生丑闻)。Lisjak等(2012)认为,当消费者所钟爱的品牌受到丑闻威胁时,消费者会感到自我受到了威胁,此时,他们会提升对该品牌的评价,但当消费者事先证实了自己的内群体身份时,他们会感到自我威胁得到了缓解,因此将不再提升品牌评价。第二,拥有物的非自愿损毁。尽管探讨消费者在自己所钟爱的拥有物遭到非自愿损毁(如因火灾、地震等而损毁)时会如何应对这一话题极为有趣,但目前仅Delorme等(2004)开展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遭遇火灾时,消费者会特别重视三类拥有物,即房子和宠物、日常通信必需品(如手机),以及不可替代的物件(如老照片、纪念册等),当这三类拥有物被损毁时,消费者会依次经历选择性地保存、悲伤和痛哭,以及财产和自我重建三个心理过程。
五、补偿性消费研究不足与展望
通过上文的文献梳理和回顾可以发现,补偿性消费研究关注的是消费者如何应对其基本需求和自我概念受到的威胁。尽管这一话题理论价值丰富,但国内鲜有学者对其加以关注。更重要的是,虽然已有的补偿性消费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仍有很大的拓展和探索空间。接下来,我们将剖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提炼未来可行的研究方向。
(一)关于需求受威胁与补充性消费的进一步思考
1.生存需求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目前有关生存需求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的研究都基于TMT,也即都基于提及死亡会让消费者感到焦虑和恐惧这一假定。但是,最新的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该假定进行了反驳。具体而言,该研究表明,当提及死亡时,人们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死亡焦虑和恐惧,而更多的是对人生稀缺、很多事情没做完的遗憾;死亡和人生稀缺是因果关系,提及死亡会促使人们在第一时间想到生命只有一次,提及人生的稀缺也会促使人们在第一时间想到死亡(King等,2009)。这一结论意味着,当消费者对人生稀缺的感知被削弱(如让消费者觉得人还有来生)时,死亡威胁导致的补偿性消费(如物质主义、放纵性消费、奢侈品消费、鲁莽驾驶等)现象可能会消失。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信徒往往相信人生是循环往复的,有今生必有来世。这可以解释为何佛教信仰者会清心寡欲、物质主义倾向较弱。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在启动死亡威胁时,强化人生不稀缺这一信念是否能减少消费者的物质主义倾向、放纵性消费以及奢侈品购买等。
此外,Liu和Smeesters(2010)发现死亡威胁能激发消费者的爱国主义情绪(爱国作为文化世界观防御的表现可以缓解死亡焦虑和恐惧),进而促使消费者偏爱国货(相对于外国货)。本文认为死亡威胁增强国货偏好这一现象还可以从补偿个人控制感的缺失这一视角来解释。我们的推测依据如下:学者Snyder(1997)认为控制感的缺乏可以解释死亡暴露下人们的文化世界观防御行为(如内群体支持行为);学者Martin(1999)进一步发现,在暴露于死亡信息时,人们之所以更加遵守内群体规范,是为了补偿个人控制感的缺失;而且Fritsche和Jonas(2008)也报告了相似的发现,即内群体支持和偏爱行为仅发生在人们无法控制死亡的前提下,当人们可以主动控制死亡方式(如自杀)时,这种行为会消失。可见,面临死亡威胁时,消费者之所以偏爱国货,是为了补偿个人控制感的缺失。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个人控制感的降低是否在死亡威胁对消费者国货偏好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控制需求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已有的有关个人控制感缺乏与补偿性消费的研究表明,缺乏控制感会促使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寻求结构和秩序,具体表现为偏爱可理解的品牌延伸(Cutright等,2013)和有边框的产品(Cutright,2012)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结论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是Rothbaum等(1982)提出的次级控制(即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假定。目前,尚未有学者从初级控制(即向环境施加控制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角度来探讨补偿性消费。鉴于触摸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身体来移动和抓举产品,也即对产品施加控制(Peck等,2013),而产品又是消费者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因此本文猜测,与拥有个人控制感的消费者相比,缺乏个人控制感的消费者更想触摸产品,因而也更加偏好实体店购物。未来的研究可以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
3.归属需求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已有的有关归属需求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的研究大多从社会排斥究竟是导致人们亲社会还是逃避社会这一角度展开。本文认为,在遭遇社会排斥后,个体的注意力不一定完全放在亲近他人或逃避社会上,相反,个体可能会更加专注于积累财富和变得更加独立。比如,已有研究显示,在遭遇社会排斥后,个体会对金钱更加看重,会寻求收益高的投资(Duclos等,2013)。一般来说,金钱能让人变得更加独立和独特,因此社会排斥和消费者的独特性寻求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未来的研究可以检验社会排斥是否会促使人们寻求独特的产品(如外观独特的产品、定位与众不同的产品)。此外,Ijzerman等(2012)发现,在遭遇社会排斥后,人们的皮肤会变冷;而Tai等(2011)发现,触摸产品(如泰迪熊)可以缓解遭遇社会排斥的伤痛。在现实生活中,单身人群以及老年人更喜欢触摸和饲养宠物,这可能是因为触摸能给予他们心理温暖,缓解其社会孤独感。由此可以推测,触摸能够满足遭遇社会排斥者对温暖的渴望,所以遭遇社会排斥的消费者对触摸的需求更高,尤其是更想触摸外表柔软的产品。未来的研究可以对这一命题加以探讨。
(二)关于自我概念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的进一步思考
1.自尊组成成分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有关自信受威胁的研究表明,降低消费者的自信(让消费者认为自己能力欠佳)后,消费者会购买能提升能力的产品(Gao等,2009)。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提升自信的产品不可得时,消费者又会如何应对?本文认为,自尊的各个组成部分(创造力、能力、成就、智力等)之间存在相互补偿的关系,能力受到威胁的消费者会倾向于证实自己其他自尊成分的完好。因此我们推测,当认为自己能力有限的消费者在环境中找不到能提升能力的产品时,他们会转而购买能够提升自己的创造力或智力的产品。此外,已有的探讨创造力受限与应对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如Moreau和Dahl,2005)仅关注了创造力受限后消费者的创造力会提升还是降低,而未触及产品消费领域。本文认为,创造力在受到限制后反而会提升这一现象属于Kim和Rucker(2012)提及的反抗性应对,而除了反抗性应对外,我们认为认识到自己创造力不足还会促使消费者通过放纵性消费等转移注意力。感兴趣的学者可以探讨创造力受威胁与放纵性消费之间的关系。
2.拥有物受威胁与补偿性消费。Lisjak等(2012)研究发现,当所钟爱的品牌受到负面丑闻攻击时,消费者会提升对该品牌的评价,然而当消费者事先证实了自己的内群体身份时,这一现象会消失。这一研究结论非常有趣,说明品牌和所处内群体都可以帮助消费者应对自我威胁,同时也说明消费者之所以钟爱某品牌,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可以归属和依恋的群体。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这一结论,比如可以探讨除了强化群体归属感外,还有哪些因素能使消费者不受品牌负面丑闻的影响?学者Einwiller等(2006)指出,品牌丑闻的严重程度会影响消费者的应对反应,当面临中等严重程度的负面丑闻时,消费者会捍卫该品牌,而当负面丑闻极度严重时,消费者则会拒绝该品牌。因此,品牌丑闻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影响品牌钟爱者的应对反应。此外,目前仅学者Delorme等(2004)探讨了消费者在自然灾难中失去钟爱的拥有物后所经历的心理过程。但是Delorme等(2004)的研究是以对火灾经历者的定性访谈为基础的,选择性地保存、悲伤和痛哭、重建财产和自我这三种心理过程是否能够通过定量数据得到验证仍不得而知。同时,在自然灾难中,消费者除了失去物质上的拥有物外,还可能失去亲人、朋友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失去拥有物和失去亲友对消费者的打击是否相同,失去亲友是否会促使消费者更加重视拥有物,这方面反应又是否有个体差异(如物质主义倾向)等问题。
[1]Arndt J, Solomon S, Kasser T and Sheldon K M. The urge to splurge: A terror management account of materialism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4, 14(3): 198-212.
[2]Burger J M. Negative reactions to increases in perceived personal contro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6(2): 246-256.
[3]Cutright K M. The beauty of boundaries: When and why we seek structure in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 38(5): 775-790.
[4]Cutright K M, Bettman J R and Fitzsimons G J. Putting brands in their place: How a lack of control keeps brands contained[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3, 50(4): 365-377.
[5]Delorme D, Zinhan G M and Hagen S C. The process if consumer reactions to possession threats and losses in a natural disaster[J]. Marketing Letters, 2004, 15(4): 185-199.
[6]Dubois D, Rucker D D and Galinsky A D. Super size me: Product size as a signal of statu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 38(6): 1047-1062.
[7]Ellemers N, Spears R and Doosje B.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 161-186.
[8]Epstein S. The self-concept revisited or a theory of a theo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s, 1973, 28(5): 404-416.
[9]Fournier S. Consumers and their brands: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theory in consumer research[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8, 24(4): 343-373.
[10]Gao L, Wheeler S C and Shiv B. The “shaken self”:Product choices as a means of restoring self-view confidenc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9, 36(1):29-38.
[11]Gronmo S. Compensatory consumer behaviour: Elements of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R].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Consumer Behavior, Salt Lake City, 1988.
[12]Grunert S.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ating behaviour as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R]. Proceedings of the 2nd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Consumer Behavior, University of Utah, USA, 1993.
[13]Harmon-Jones C, Schmeichel B J and Harmon-Jones E.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in academia: Evidence from department web pages and email signature file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9, 39(2): 311-316.
[14]Ijzerman H, Gallucci M, Pouw W T,et al. Cold-blooded loneliness: Social exclusion leads to lower skin temperatures[J]. Acta Psychol, 2012, 140(3): 283-288.
[15]Kim S and Rucker D D. Bracing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orm: Proactive versus reactive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 39(4): 815-830.
[16]King L A, Hicks J A and Abdelkhalik J. Death, life, scarcity, and value: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meaning of death[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12): 1459-1462.
[17]Lee J and Shrum L J.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versus charitabl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A differential needs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 39(3): 530-544.
[18]Levav J and Zhu R. Seeking freedom through varie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9, 36(4): 600-610.
[19]Liu J and Smeesters D.Have you seen the news today? The effect of death-related media contexts on brand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0, 47(2):251-262.
[20]Maheswaran D. Country of origin as a stereotype:Effects of consumer expertise and attribute strength on product evaluation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4, 21(2): 354-365.
[21]Markus H and Wurf E.The dynamic self-concept: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7, 38: 299-337.
[22]Meyers-Levy J and Zhu R.The influence of ceiling height:The effect of priming on the type of processing that people use[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7,34(2):174-186.
[23]Moreau C P and Dahl D W. Designing the solution:The impact of constraints on consumers’ creativity[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5,32(1):13-22.
[24]O’Guinn T C and Faber R J. Compulsive buying: A phenomenological explora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9,16(2):147-157.
[25]Peck J, Barger V A and Webb A. In search of a surrogate for touch: The effect of haptic imagery on perceived ownership[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3, 23(2): 189-196.
[26]Pettit N and Sivanathan N. The plastic trap: Self-threat drives credit usage and status consumption[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1, 2(2): 146-153.
[27]Pyszczynski T, Greenberg T J and Solomon S. Why do we need what we need? A terror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the roots of human social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7, 8(1): 1-20.
[28]Rosenblatt A, Greenberg J, Solomon S, Pyszczynski T and Lyon D.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violate or uphold cultural valu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4): 681-690.
[29]Rothbaum F, Weisz J R and Snyder S S. Chang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self: A 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2, 42(1): 5-37.
[30]Rucker D D and Galinsky A D. Desire to acquire: Powerlessness and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8, 35(2): 257-267.
[31]White K and Argo J J. Social identity threat and consumer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9, 19(3): 312-325.
[32]Van Tongeren D R and Green J D. Combating meaninglessness: On the automatic defense of meaning[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0, 36(10): 1372-1384.
[33]柯学. 大灾难可以减少消费者的多样化寻求行为: 一个基于恐怖管理理论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11: 12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