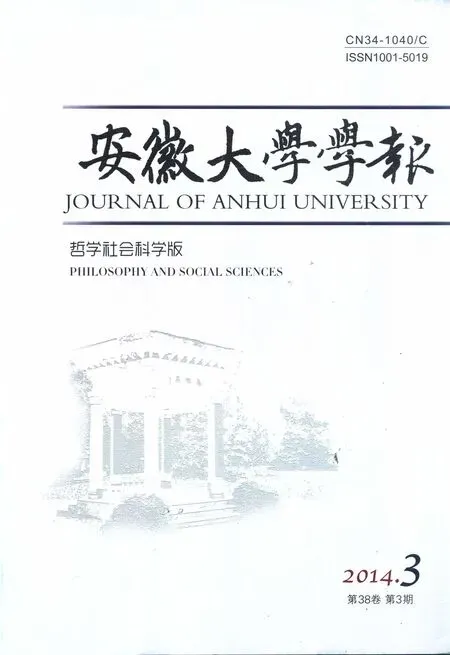北平沦陷时期翻译状况初探①
付文慧,王恩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为日本占领区。尽管大批知识分子和主要文教机构迫于时局已陆续撤离,但北平的各项文化活动并未就此停滞。一批留守北平的文人学者以及从台湾、东北移居而来的文化人士坚持文学创作,从事文艺活动。当地的报刊书籍出版发行也得以在经历短暂沉寂后继续繁荣,小说、诗歌、话剧等文学形式进一步发展,文艺界思想依旧活跃,关于“色情文学”、乡土文学、木刻等话题的论证交锋激烈,凡此种种构建了一幅特殊时期的别样文化风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之后,已经有不少国内外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北平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进行了研究②如:E.Gunn,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 -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2000年。,遗憾的是,鲜有学者对当时的译介活动进行全面的专题研究,相关篇什偶见于关于沦陷区作家、丛书以及报纸杂志的实绩梳理中③如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王申:《沦陷时期旅平台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动与身份表述——以张深切、张我军、洪炎秋、钟理和为考察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年,第37~43页。,且多以寥寥几语带过,可谓面貌不清、特征不明,目前仅有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论述》一文尝试从翻译角度初步梳理抗战时期的译介成果,但北平的译介情况仅在其“沦陷区的翻译文学”一节略有涉及④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惜乎止步于有限的译作篇目罗列层面。这种研究状况与彼时北平译介活动的普遍存在状况不甚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初步分析北平沦陷时期(1937—1945)的译介活动,探究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梳理包括单行本和合集在内的译著状况,主要以《中国文艺》为例,分类考察官办文学刊物的译介特色,借以管窥本土知识分子在译介活动中疏离日伪政治、秉承“五四”新文学旨趣的独立姿态。
一、北平沦陷时期译介活动概观
北平沦陷后,多数留守知识分子虑及失节之虞,不愿出任伪职。为筹谋生计,翻译著述、教书糊口成为极为普遍的谋生手段。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忆及沦陷之初时言道:“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以后,华北沦陷于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处于俘虏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隐忍的勉强过活。头两年如上两章所说的总算借了翻译与教书混过去了。”①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下),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5页。
在当时逼仄的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迂回消极的抵抗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北平沦陷时期译介活动的兴盛。当时举凡报纸杂志,多开设译作栏目或零星发表译作,如《中国文艺》、《东亚联盟》、《国民杂志》、《北华月刊》、《万人文库》、《艺文杂志》、《新光》等具有日伪背景的官办杂志,《沙漠画报》、《朔风》、《长城》、《艺术与生活》、《读书青年》、《逸文》等民办杂志,《辅仁文苑》、《燕京新闻》等校园出版物,《晨报》、《新民报》等报纸及文艺副刊或多或少均有译文刊登。在部分刊物中,译文甚至占据相当篇幅,如《中国文艺》每期必刊登文学译作,长篇翻译小说与戏剧连载为常规内容,还时常以“海外文学别辑”等形式集中推介外国作品;《沙漠画报》容量较《中国文艺》略小,但译作亦是每期都见诸报端,且比例不低。有关两刊的译介特色,将在下节及另文详细考察,此不赘述。
除了杂志报刊等连续性出版物,印行书籍是北平沦陷时期面世译作的另一载体。由于战争因素导致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纸张油墨奇缺,加之日军占领北平之后,一直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文艺,在文艺政策上体现为严格控制新闻出版自由和各项文化活动,导致北平翻译出版事业严重受阻。就笔者目前统计来看,得以面世的文艺译著仅有十余种,且其中译自日本者近半②出于严谨考虑,本文此节纳入考察范围的译著均为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且具有明确出版时间、出版机构者。其余在概述或索引文献中亦有提及,但存在以下情形者未予收录:存在未刊行之虞,如魏敷训翻译小说集《平凡》、周丰一翻译小说集《银茶匙》、尤炳圻翻译小说集《我是猫》等;因遭查禁之故未曾面市,如董绍明、蔡咏裳合译小说《士敏土》、赵景深译介诗集《儿童的诗园》等;其他语焉不详者。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张克明:《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禁书览要》,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出版史志》第4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209~218页。。
沦陷初期,在日伪奴化宣传政策干预下,图书出版主要集中在印行奴化教育教科书,编行日伪政府法令书籍,发行日语教学书籍等方面③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101页。,文艺图书的出版工作几乎完全停滞。直至1939年,华北战局趋于稳定,北平出版业逐渐解冻,一系列文艺书籍才得以陆续出现,其中参与机构既有新民印书馆等官办出版社,及北京曲艺出版社等私人出版机构,也有《沙漠画报》等报纸杂志出版的单行本和丛书,相关译著的面貌也因参与方文化身份以及翻译动机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比如,1939年北京东方书店出版的《土与兵》(金谷译)是一部站在军国主义立场,美化、歌颂侵华日军的作品。该作由日本从军作家火野苇平于1938年写就,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以书信体书写作者在中国的见闻,为侵华战争宣传造势。此译著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日本以“国策文学”为武力侵华推波助澜的险恶企图,另一方面亦可洞见沦陷区文艺生存环境之恶劣。类似译著还有北京中国留日同学会出版的《樱花国歌话》(1942,钱稻孙译),译书从立意选题乃至篇目选择无不烙有日伪干预的痕迹。该作原名为《日本爱国百人一首》,为日本和歌合集,以镰仓初期(我国南宋时)和歌宗师藤原定家所选的《小仓百人一首》为最早且最通行。而日伪“文学报国会”嫌旧有的百人一首“言情各半,亦或写景,失之太柔”,重新调整篇目形成新的《爱国百人一首》,并于1942年11月20日公布,钱稻孙译本即据此完成①参见卞琪斌《周作人作序的〈樱花国歌话〉》,《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该书正文前有周作人作序称:“日本之国体特殊,因地理历史种种关系,人民特具尊王爱国之热诚与别国不同,其发现于文学正是当然。”②周作人:《樱花国歌话》小序,《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由此可见,其时刊行该译著的初衷当是弘扬所谓的“日本爱国精神”,与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图谋不无干系。
但是,1939年由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印行的《转生》虽然亦为钱稻孙所译,却呈现出强化文学旨趣、淡化政治色彩的特点。该小说集的作者志贺直哉为日本现代文学“白桦派”代表作家,因其精练的语言和敏锐的观察力而被誉为近代日本文坛的“小说之神”。他对日本对外侵略持否定态度,卢沟桥事变后曾封笔直到日本战败,以示不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态度。与此类似的还有:1940年由未名出版社推出的《千人针》(罗玉波编译),收录浅井花子等作家的短篇小说;1942年由新民艺术馆推出的《现代日本短篇名作集》(张深切编译),收录横光利一的《秋》等小说。这两种图书内容均与政治时局无关。除此之外,1941年北京曲园出版社刊行的《猴子与螃蟹》(沙文编译)为日本民间童话故事,在题材上与上述传统文学门类的图书又有所不同。
北平沦陷时期除了日本译著,还出现了少量其他国别译著,题材、内容亦相对庞杂,具体包括苏联柯静米夫等合著的《维堡区的故事》(1939,司马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M.盖尔生松撰写的少儿读物《伤脑筋博士》(1940,符基珣译),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美国女性杂志《真实的故事》(True Story)作品选《女人们的故事》(1940,赵今吾译)、通俗读物《择偶术》(1940,李木译)以及《吾家》(1941,李木译),均由沙漠画报社发行;德国赖普著作中德对照版《海上魔旗》(1943,崔亮译),由北京中德学会推出;英国克利福德(W.Kclifford)等合著小说集《贼及其他》(1944,毕树棠译),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刊行;多国小说集《新世纪小说选》(1941,海藻编),由北京益智书店出版,具体选目为芥川龙之介的《秋》、中河与一的《结冰的跳舞场》、苏德曼的《挽歌》、霍普特曼的《管栅门的第尔》、塞梨奥的《露露的胜利》、布罗基的《幻》以及阿耶拉的《黎蒙家的没落》③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萧山县志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中国文艺》译介活动概览
北平沦陷时期,报纸杂志成为译事发声的主要场域,无论是校园出版物,还是官办刊物,概不例外。这些刊物的运作模式、办刊宗旨、栏目设置、选文标准等风格迥异,译事特色各有不同。由于这一时期的杂志刊物多达百余种④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第15页。,品类繁多,不胜枚举,本文仅以《中国文艺》为例,详细勾勒官办文学刊物之译事轮廓轨迹,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该时期译介活动的更多思考。
《中国文艺》创刊于1939年9月,迄1943年11月出至九卷三期后一度停刊,1944年1月与《华北作家月报》合并组建《中国文学》。该大型月刊是抗战中期华北沦陷区最主要的综合性文艺刊物⑤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第72页。,从性质上而言为官办刊物,隶属于武德报社,间接受控于日本华北驻屯军报道部,主编先后由张深切、张铁笙、王石子、林榕等担任。
该刊自创刊起就对外国文学重视有加,不但每期均有译作刊载,而且时常设立“海外文学别辑”或“翻译”专栏,四年间共刊登外国文学作品超过140篇次⑥冯昊:《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年,第92页。,译介成绩可圈可点。就译介内容而言,覆盖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电影、传评、文学评论等几乎所有重要文艺门类,译源国包括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其中译自日本和英国的作品最多。
译自日本的作品品类杂多,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戏剧理论、随笔杂文、文学评论、学术论作、作家年谱、剧社介绍等。其中“笔部队”作家①本文参照王向远教授的界定,将所有“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统称为“笔部队”作家。参见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昆仑出版社,第2页。占一小部分,入选作品的内容部分集中于文化交流方面,如近藤春雄的《在日本现代中国的文学》(黄荣生译,4:1)、木村毅的《翻译界漫谈——日本翻译史话》(马云超译,5:4)和林房雄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岳蓬译,9:1)等;其他如石川达三的小说《转落的诗集》(克人译,5:1;5:2)、林芙美子的小说《勿忘草》(凌冰译,8:2)以及菊池宽的戏剧《某兄弟》(冯幼竹译,4:3)和《恋爱病患者》(王石子译,4:12)等,虽为文学创作,但与为日本侵略战争推波助澜的“侵华文学”没有直接关联。
其余入选作家的作品则以近代为主,内容亦多呈现出纯粹的文学鉴赏倾向。小说包括日本汉学家饭塚朗的《院内雨》(梅娘译,7:4),“二战”前著名作家森鸥外的历史小说《高濑舟》(真夫译,8:2),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古典题材小说《杜子春》(真夫译,8:5),以及诗人、小说家岛崎藤村的《东方之门》(崔正译,9:2)等;诗歌包括杉村楚人冠的《春水》(鲁灵译,3:5),田中冬二的《菊》(杨须明译,4:4),高桥新吉的《视》(杨须明译,4:4)以及石川啄木的《旷野》(5:5)等。
另有哲学家桑木严翼的《没有意思》(云将译,2:2),舞台美术家伊藤熹朔的《舞台构思的基础条件》(方原译,5:2),矢田津世子的随笔《祖父》(亦茄译 7:7),石田义男的《孟子之母与其教育作》(于廷文译,7:7),升屋治三郎的《戏剧协社与南国剧社——上海新剧史的一节》(张铭三译,8:3)以及缱田研一的《岛崎藤村年谱》(章明译,9:2)等。
译自英国的作品堪与日本比肩,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散文等方面俱有佳作入选,时代跨度从18世纪直至20世纪。小说方面的译作包括:19世纪女小说家爱密黎·朗明特(Emily Bronte)的《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林栖译,连载)②抗战时期的作家及作品中文译名标注范式与当代不同,兼之部分作家或作品因缺少线索难以追溯至源语,为免讹误,本文仍沿用考察刊物所用译名,部分能够确切追溯源语者在括号内标注源语名,以利于读者辨识。,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兄弟》(何漫译,连载)和《太阳》(卢荻译,5:4),20世纪“两性爱”作家劳伦斯(D.H.Lawrence)的《落雨之谷》(张蕾译,4:1)和《落花生》(陈砺译,8:5)等。诗歌译作有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歌》(梅娘译,4:1)和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湖上佳人》(The Lady of the Lake,晓勃译,6:1)等。文学评论译作有19世纪新浪漫主义作家斯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携带着灯笼的人们》(林栖译,7:4)和20世纪评论家T.S.艾略特(T.S.Eliot)的《批评之尝试》(塔扬译,4:3)等。
散文随笔是英国文学的一大特色,《中国文艺》对该门类尤为重视,入选篇目颇多。如18—19世纪著名散文家查理斯·兰姆(Charles Lamb)的《古磁器》(Old China,林栖译,6:3)和《梦幻的孩童》(DD译,2:2),19世纪弥提佛(M.R.Mitford)的《散步乡野》(何漫译,5:4)和《乡景》(何漫译,7:4),19—20世纪散文家露加斯(E.V.Lucas)的作品《失去的手杖》(林栖译,8:2)和《修女及其它》(林栖译,6:3),20世纪 Robert Lynad的《谈写作》(若云译,8:4)以及希莱尔·白劳克(年代未知)的《白劳克随笔》(先夏译,3:3)等。不仅如此,《中国文艺》还在“编者小记”中对这一在国内“刊物上还不多见”的文学门类予以推介,而且着意厘清其与国内论文及散文随笔的差异③《编者小记》,《中国文艺》第8卷第4期,第63页。。于此不难窥见该刊物“纯文学”的艺术定位和推动塑造国内文坛新风的努力。
译自美国的作品以20世纪小说为主,入选作品多为名家之作,如:短篇小说大师奥·亨利(O.Henry)的《青色的门》(鲁风译,4:2)、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雨中的猫》(秋星译,4:4)、朵斯·帕索士(Dos Passos)的《一个美国人的尸体》(祁乐为译,8:3)、斯坦培克(John Steinbeck)的《蛇》(祁乐为译,9:1)、伊尔文(Ir-ving Stone)的《雨天的小店》(成伯华译,2:2)、犹利·奥略的《嫉妒—爱尔玳蓓兰》(王若云译,4:4)和亚尔伯特·马尔兹的《游戏》(祁乐为译,8:5)等。另外还译有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的戏剧《画十字的地方》(庐荻译,6:2)、Mark Van Doren散文随笔《什么是诗人》(维本译,8:4)、William J.Long的评论《关于文学》(成伯华译,3:3)、海明威的《写小说的基本三原则》(哲西译,4:4),以及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的《朗费劳给他父亲的信》(成伯华译,3:4)等。
译自法国的作品则以戏剧为主,主要是《群鸦》(讯鸽译)和《白里松先生的旅行》(闻青译)两部戏剧的连载,前者是十九世纪剧作家亨利·贝克的自然主义名作,后者为拉比什(Eugène Labiche)的哲理性戏剧。另外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纪德的小说《有关个人道德的记录》(雪萤译,3:5),浪漫主义巨匠嚣俄(Victor Marie Hugo)的诗歌《拿破仑》(白桦译,3:5)以及曼达的《失去的星星》(朱利译,2:2)
译自德国的作品门类亦较杂,文学性相对较弱,有《席勒尔与哥德书札》(谨铭译,2:2),里尔克作品《布里格随笔》(丙子译,2:2),爱西黑特的报告文学《巴拿马运河之由来》(金谷译,7:2;7:3)以及《噶贝尔斯日记》(山风译,5:4)。
除以上主要译源国之外,《中国文艺》亦零星刊载译自其他国家的作品,如西班牙的《唐·吉诃德》(4:3)、加拿大 Stephen Leacock的《谁决定古典作品?》(野萍译,8:4)以及罗马尼亚 M.Sadoveanu的《侠盗库兹》(沉雷译,9:3)等。
三、《中国文艺》译介特色辨析
综观《中国文艺》的译事行为,有两大特征可谓一以贯之。
其一是继承五四时期新文学传统,力图坚持“纯文学”本位。这一文学本位的办刊理念自创刊时就已确立,首任主编张深切在入主之初明确提出的办刊要求之一,就是“保持纯文艺杂志的形态,不作主义思想的宣传”①张泉:《张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国”实践》,《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尽管后来时局艰难,《中国文艺》不得不在周旋委蛇中求得生存发展,但继任主编张铁笙仍然坚守理念,并具体指出:“中国的文艺思潮,是已经经过一个热烈的文艺革命阶段,达到自由反悔和具有新形态的时期了,所以在思想上,泥古的,迷古的,或者说自认为仿古的或复古的作品,请自动不必送来,本刊不负责这个返古的任务。我们觉着我们即使不能前进,也不必后退,至低限度停留在已经达到的那个阶段而徘徊不前,也比向后转开步走有意义得多。”②《卷头语——关于今后本刊》,《中国文艺》第3卷第1期,第3页。《中国文艺》的译介活动堪为历任编者苦心经营的绝佳注脚。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它以广博的视野引进名家名作,选目跨越18至20世纪三百余年,涉及欧美日诸多国家;以雅致的趣味推介散文随笔等异域文体及创作新潮,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发展;以积极热切的心态展现文学魅力(如选取朗费罗之信以展现其幼时萌发的文学兴趣),激发读者的文学热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遴选作家及篇章,确保刊物的文学品味。当然,由于期刊的篇幅限制,入选作品未必是作家最著名之作,但编者依然用心良苦,尽量选择能够体现作家典型风格的作品,如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其短篇小说《蛇》的入选理由是因其“结构严谨,作风洗炼,颇可算为斯坦培克手法的代表”③见《中国文艺》第9卷第1期,第49页。。
其二是竭力抵御文化殖民同化,守护民族立场。《中国文艺》作为官办刊物,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气候下,不配合形势显然难以立足。尽管如此,历任编者仍然“以最大可能,维护这个刊物的坦白性和纯洁性”④《卷头语——关于今后本刊》,《中国文艺》第3卷第1期,第3页。。这主要体现在对日本作品的译介上。尽管从总体数量来看,日本作品的数量几乎与英国持平,但在创刊前期,入选数量甚为有限,直至1941年日伪控制收紧,从第四卷起日本作品的比重才逐渐增大,并出现了一些“笔部队”作家作品。单纯以这些作家的政治身份而论,《中国文艺》似有“附逆”之嫌,但值得玩味的是,从入选篇目的具体内容而言,并无为日军侵华行径辩护的即时作品,而是多为关注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学、学术评论,或为相关作家的早期创作。如菊池宽的《恋爱病患者》写于二战之前,无关政治,是反映日本家庭中新旧两代人婚恋观冲突的剧作;石川达三的《转落的诗集》则是以针砭日本时弊为内容的风俗派作品。由此我们不难体会《中国文艺》规避沦为日伪官方宣传工具、尽量淡化时局色彩的特别用心。除此之外,部分译作还在类似形式的掩盖下,迂回表达了国人强国图存的真实愿望。正如学者张泉指出的,沦陷区文学的呈现形式错综复杂,“既存在当局利用某种观点的情况,也有作家借助当局的提法大作自己文章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双方看似都在说同一个问题,但结论和寓意却大相径庭”①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18页。。上文提及的《噶贝尔斯日记》就存在着所谓“名”与“实”之间的张力,作者姚赛夫·噶贝尔斯为德国纳粹成员,选题表面看来似乎意在顺应当时潮流,“译者言”却揭示了《中国文艺》选文的真实初衷。译者山风将此文视为德国“复兴与奋斗”的见证,从中可看到德意志在受“一战”打击“濒于支离破碎的危境”之时,如何“重整海陆空三军,雪掉了凡尔赛条约之耻”,他认为德意志成功的因素在于“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住的奋斗”,因此希望借此文给国人“一个启迪”、“一点‘力’的赠品”②山风:《〈噶贝尔斯日记〉译者言》,《中国文艺》第5卷第4期,第23页。。可见此文的真正目的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希冀国人振奋。
在具体译介规范方面,《中国文艺》的表现亦值得称道。尽管由于资金、人员紧张,出刊时间仓促,排版工人外文水平有限等原因,出现了部分外文人名、题名及其单词误印等问题,但《中国文艺》严肃的译介态度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当被铭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刊载要求,促进翻译行为规范化。刊物强调原作的权威性及译作的原创性,以“编者话”的形式明确规定,译稿须详注原作出处,鼓励附带原文,不刊载转译作品及剽窃讲义③《编者话》,《中国文艺》第5卷第1期,第95页。。
2.鼓励翻译论争,推动译文质量改进。针对尤炳圻所译日本名著《我是猫》(夏目漱石),《中国文艺》先后两次刊发真夫的商榷文章《谈尤译我是猫》和《再谈尤翻译我是猫》,内容既涉及“一只”、“这一点”、“那时”、“可是”、“的事”、“东西”等微观的词语译介问题,又关乎“直译”、“死译”等宏观的翻译理念之争④参见真夫《谈尤译我是猫》,《中国文艺》第7卷第4期;真夫:〈再谈尤翻译我是猫〉,《中国文艺》第8卷第1期,第49~56页。。
3.译中做注,确保翻译严谨性。刊物中附加译注的译文不在少数,文中及文末加注的现象都有出现。如祁乐为在译作《一个美国人的尸体》的文中加注解释了“铜帽子”(高级将校)、“老光荣”(美国国旗)等美国俚语俗语⑤朵斯·帕索士作,祁乐为译:《一个美国人的尸体》,《中国文艺》第8卷第3期,第47~48页。。克人译作《转落的诗集》的文末附注解释了“刑事”(侦探警察或刑事警察)、下宿(纯日本式的公寓)等专有名词以及日本食品、跪礼姿势等特有文化风俗⑥石川达三作,克人译:《转落的诗集》,《中国文艺》第5卷第2期,第81页。。林栖译的《古磁器》篇幅仅有4页,注释就达25个之多,涉及人名、地名、尺度名、名著及文学人物等多方面内容⑦查理斯兰姆作,林栖译:《古磁器》,《中国文艺》第6卷第3期,第6~10页。。
4.添加副文本,全面补充背景文化信息。刊物充分利用编后记、译者序跋等副文本提供译文背景信息,或介绍作品,或推荐作家,或阐释作品渊源,或详述选文动机,如纪德、雨果、雪莱、噶贝尔斯、拉比什等作家作品均是如此,为读者更为深入了解外国文学文化提供了便利。
四、结语
本文简述了北平沦陷时期的译事活动,并深入考察了官办杂志《中国文艺》的译介成果及风格。由于政治局势和译介主体(包括机构及个人)文化立场、艺术趣味之间的交织纠葛,无论是译著书籍的出版还是连续出版物译作的刊行,都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之特征。
丰富性在于来自欧美诸国的译作未因日军法西斯统治而彻底阻断,日译文学畸形繁荣、一家独大的现象并未出现。尽管日本占领当局为达到推行殖民文化统治的目的,极力宣扬日本文化优越论,排斥欧美文化,并将“消除排日抗日及依存欧美之思想,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营造亲日气氛”①井上久士:《华中宣抚工作资料》,东京:不二出版社,1989年,第51页。作为重要的“宣抚”内容,但这一企图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以至于日方官员林房雄在1944年不得不无奈承认,中国高校学生所阅读的文学书除了“重庆或延安系作家的作品,其余的大部分是英美系的翻译小说”,而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没有②林房雄:《中国新文学运动》,岳蓬译,《中国文艺》第9卷第1期,第40页。。林氏此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本文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吻合。
复杂性在于知识分子的抵抗性言说是在“合法”的外衣包装下,以特殊、隐蔽的形式迂曲表达出来的。北平沦陷区不存在地下文学和公开的对抗性文学,译介活动也在日伪官方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尽管该时期的部分刊物得到了日伪政权的资助,编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伪政策的制约,但决不可因其隶属关系就草率得出“伪刊”结论,对某些文学性刊物及版面的评判和定性则更需谨慎。《中国文艺》的译事活动就表明了,它并未遵循日伪旨意,在其译作风格多元化的努力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本土知识分子疏离日伪政治、秉承“五四”新文学旨趣的独立姿态。
北平沦陷区的译事形态分析表明,无论政治环境如何恶劣,文学(包括文学翻译)的演进都有其自身的必然路径,多种文化间的交流势不可挡。无视民族情怀和客观规律,以政治乃至武力干预文艺的图谋必定会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