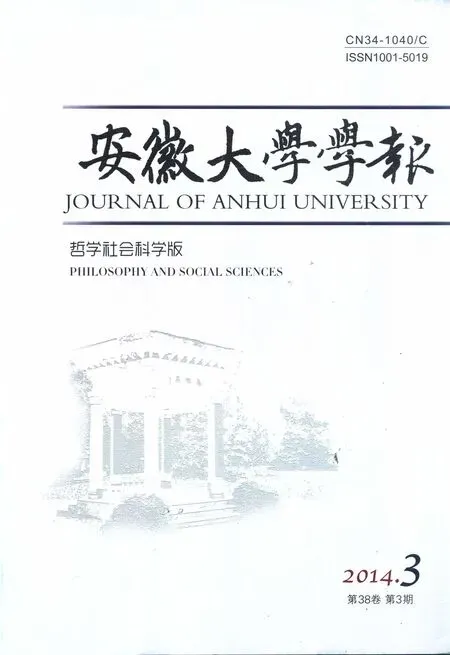论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暴力关怀
于元元
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在其作品中表现了暴力关怀。然而,读者们往往惊异于其中的暴力,对作家表达关怀的暴力叙事动机却忽视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她公开发表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1955)卜一问世,便激怒同乡,有人质疑说南方的本貌并非罪犯大行其道,或是圣经推销员携姑娘木腿逃跑①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112.。评论界赞赏她才华的同时,有的指责“她太惯于写灾难故事,以至于没有道德判断”②R.N.Scott,I.H.Streight.Flannery O’Connor:The Contemporary Review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33.,还有的称她的十篇故事如“一只毒镖在肋骨上捅了十下”③R.N.Scott,I.H.Streight.Flannery O’Connor:The Contemporary Reviews.p.42.。针对这些误解,奥康纳在不同场合解释她写暴力畸人是为自己的天主教意图服务。受此影响,1971年,评论界在她逝后六年出版的《弗兰纳里·奥康纳故事全集》中,同时注意到她笔下的暴力和“不确定的救赎前景”④R.N.Scott,I.H.Streight.Flannery O’Connor:The Contemporary Reviews.p.443.,却未厘清二者关系。至上世纪90年代,仍有不少美国论者仅聚焦于她作品中的暴力和堕落的美国南方。进入21世纪,美国论者则多偏离神学视角另辟蹊径,如从种族主义切入论述奥康纳作品中黑人对白人主人公的精神蜕变所起的催化作用⑤Nicholas Crawford.An Africanist Impasse:Race,Return,and Revelation in the Short Fiction of Flannery O'Connor.South Atlantic Review,Vol.68,No.2,Spring,2003,pp.1-25.,或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其中“救赎的暴力”⑥Doreen Fowler.Flannery O’Connor’s Productive Violence.Arizona Quarterly,Vol.67,No.2,Summer 2011,pp.127 -154.。但是,笔者以为,奥康纳不是心理学家,她所有关于精神蜕变、“救赎的暴力”等理念均生发于天主教信仰,尤其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救赎教义。因此,离开奥康纳的天主教视角谈其人其作则不得要领。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奥康纳研究走向繁荣,至今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她作品中的暴力与宗教救赎,以及二者关系,即暴力是手段,救赎为目的。然而,这一研究尚有三点不足:第一,将天主教关于炼狱、神恩、救赎的特殊含义误解为基督教的普遍教义;第二,仅述及纯粹天主教意义上的救赎,未细解它反映的作家天主教的人文关怀;第三,未涉及奥康纳的样本寓言①寓言的一种,也有人译作“说教故事”,但笔者认为此汉译不够准确,且易在文学作品赏析中引起误解。(exemplum)式暴力叙事。鉴于此,本文将从思想、主题和相关叙事三个方面论述奥康纳的暴力关怀。
一、奥康纳的暴力关怀思想
奥康纳的暴力关怀思想有三个根源:天主教义、南方文化和作家的狼疮经历。天主教义为之提供宗教理论依据;美国南方为之提供文化支撑;长期罹患狼疮的个人经历则被她视作上帝暴力关怀的实证。她暴力关怀的实质是天主教理念包裹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包括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其终极关怀基于天主教义,现实关怀则主涉美国南方文化和她的狼疮经历。
读者对奥康纳暴力关怀思想截肢般的曲解常缘于缺乏对其天主教信仰的了解。她1925年生于佐治亚州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笃信天主教。美国南方新教势力强大。作为夹在新教徒中的天主教徒,她于1963年在题为“新教南方的天主教小说家”的演说中,号召天主教小说家提醒自己“天主教徒有什么,应保留什么”②F.O’Connor.Mystery and Manners.Eds.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1,p.209.。天主教关于炼狱、神恩和救赎的教义有别于新教③本文关于天主教和新教的信息源自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Volume 6,p.23-55和Volume 22,pp.679-693.Danbury,Connecticut:Grolier Incorporated,1988.。新教教派众多,说法不一,但一般说来,多数新教否认炼狱,而天主教徒相信炼狱是天堂的前庭,人只有在炼狱中涤罪方能入天堂。新教徒相信预定论(Predestination),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承载神恩,只有上帝的选民才会被救赎。天主教徒相信三位一体(Trinity),认为上帝爱人,通过耶稣拯救世人。神恩对世人开放,世人接受神恩,则获救赎;拒绝神恩,则下地狱。至于耶稣如何复生,如何拯救世人,则属于天主教徒笃信的、超越理解的神秘主义。奥康纳在其作品中刻意保留并突出有别于新教的天主教关于炼狱、神恩和救赎的思想。
奥康纳暴力关怀的思想源出圣经。据天主教徒推崇的圣经杜埃英译本(The Douay Bible)中《马太福音》,“自受洗者约翰时代以降,天国就盛行暴力。暴力夺取它”(11:12)。暴力仿佛上帝之剑,用以检验人的信德。约伯屡遭大难,家破人亡,贫病交迫,却痴心不改,仍笃信上帝,因而获得救赎。亚伯拉罕因着信,将亲子摆上祭坛,终获救赎。显见,暴力是上帝关怀信徒的手段。此外,上帝也用暴力之剑惩治背弃他的罪人。他的两大诫命是信德和“爱人如己”。据《马太福音》,“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22:37-40)他数次用洪水、血灾、旱灾、蝗灾等显示神迹,警告世人遵守诫命。就此而言,他关怀的是读懂上帝之道的世人。
受《圣经》影响,奥康纳也视暴力为炼狱的一部分。她笔下的暴力既有常与死亡相随的肢体冲突,又有令人感到屈辱、挫败,或被抛弃,乃至丧子之痛的非肢体冲突。但是,一切暴力仅是手段,关怀方为目的。她认为人因原罪和个人的罪(personal sins)而“不健全”,需要神恩④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32.。所以,她的故事里经常出现生理或心理畸人。她在故事中将这些畸人置于炼狱般的极端暴力环境,使其受苦:一则剥除浮华,露其本性;二则,使他们在山穷水尽时,不得不依靠上帝,坚振信仰,接受神恩,获得救赎。至于那些在暴力环境下仍拒绝神恩的,则下地狱。她指出:“对于一位严肃作家,暴力从来不是目的。”⑤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134.暴力对她而言只是关怀与救赎的手段。她的关怀对象是信徒,或是领悟她天主教意图的读者。
奥康纳基于天主教义的暴力关怀带有终极关怀特性。终极关怀命题包括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我希望什么”和“将来的人会变成怎样”,以及画家高更之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等所拷问的关于人类生命状况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奥康纳首先以“人来自伊甸园”回答“从哪里来”的问题,表明上帝爱人,继而以人因原罪而成为“不健全”的罪人回答“我们是谁”,最终以是否获得救赎回答“往哪里去”的追问。
奥康纳的暴力关怀不仅带有天主教终极关怀的特性,而且,因她进步南方作家的身份也具有天主教现实关怀的特性。现实关怀一般表现为“作家对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现实处境与悲惨命运的关切,还表现为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社会黑暗陈腐势力的揭露与鞭笞,总之表现为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和批判”①顾祖钊:《论文学批评的三大原则》,《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在奥康纳的作品中,南方奴隶制残余的种族歧视、等级观念是她频频炮轰的目标;南方绅士淑女风范是她揶揄的对象;南方濒危的农牧经济则是她极力挽救的传统。从《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的黑人母亲向自高自大的朱利安母亲抡起的拳头,到《最后审判日》(Judgment Day,1965)中北方黑人演员对擅于驾驭黑人的南方老人坦纳的愤怒推搡,从《启示》中丑姑娘对特平太太的暴袭到《格林利夫》中公牛对压迫雇工的梅太太的顶撞,奥康纳笔下的暴力如上帝的正义之剑,斩向不公的种族歧视和等级陈念。她在《眺望林景》中安排的祖孙暴力冲突,代表工业进步与农牧传统的冲突,体现了她对濒危的南方农牧传统和自然生态的留恋与关怀。总之,南方成为她暴力关怀思想的文化载体。抽象的天主教暴力关怀被她具体化为有美国南方特色的暴力关怀。
奥康纳暴力关怀的南方特色缘起于20世纪中叶南方文学“现代性”(modernity)转向,而这一转向是二十年代开始的南方文艺复兴(Southern Renaissance)的余波。一战后,当美国北方沉浸在“喧嚣的二十年代”(the roaring 20s)的享乐气氛时,南方一批精英作家却毅然割断与旧南方文学的联系。他们抛弃缅怀南方骑士精神的传统,冷静面对美国内战中南方的战败经历、南方浓重的宗教、家庭和社区氛围,以及南方的种族问题,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各领域实现了南方文学的复兴。这些作家包括福克纳、罗伯特·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卡罗琳·高登(Caroline Gordon,1895—1981)、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等。他们对后辈南方作家奥康纳、沃克·珀西(Walker Percy 1916—1990)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一代南方作家关注的焦点同样是定义南方身份的“三个 R”——种族(race)、农村(rurality)、宗教(religion)。不过,随着争取种族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的节节胜利、农牧经济的衰退和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他们记录的是“三个R”向“现代性”的位移过程。奥康纳和珀西从天主教视角描述这一过程,被称作上世纪中期为南方天主教文学复兴定步调的两位作家②Bryan A.Giemza.Catholic Minds of the South:A New Concert.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Volume 39,No.1,Fall 2006,pp.133-136.。
“三个R”中的宗教问题是南方身份最稳定、最核心的部分。作为天主教作家的带头人之一,奥康纳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天主教,而是放眼整个南方的基督教根基。在“新教南方的天主教小说家”的演说里,她号召天主教作家扎根富含宗教的南方土壤进行艺术创作。南方又称“圣经地带”(The Bible Belt),基督徒甚众。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南方人都惯以基督教义解释生活现象,南方作家也惯于把作品嵌入圣经框架,将基督教义阐释得鲜活具体是他们自觉承担的先知般的重任。因南方身份而自然生成的基督教视角令他们易于甄别背离上帝的畸人,这也是南方作品畸人多的要因。显然,这种文学传统和宗教土壤都是南方天主教作家宝贵的资源与财富。
南方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与作为“现代性”标志之一日益显露的信仰危机之间产生强大张力,最终催生了奥康纳具有南方特色的暴力关怀思想与实践。对于一些信仰丧失或不坚定的读者而言,他们对上帝之道已不再敏感,反而代之以与它相抵的世俗价值观(如有悖于“爱人如己”诫命的等级观、种族观等),以至于他们无法辨识基督教话语体系中显而易见的畸形,故而显得麻木不仁。对于此类读者,及以他们为原型的人物,奥康纳予以暴力关怀。1963年,她在霍林斯大学的演讲中曾说:“我发现暴力很奇怪地能够令我的人物回归现实(即宗教现实),并且使他们接受神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的头脑太顽固。”①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134.她的名言是:“对耳背者要大声喊,对弱视者要画大而惊人的形体。”②F.O’Connor.Mystery and Manners.Eds.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1,p.34.在作品中,她试图以惊人的暴力撼醒他们,使他们反思自己的世俗价值观,重归“现实”,即基督教道德轨道,接受神恩,获得救赎。
如果说南方为奥康纳的暴力关怀打上了区域文化标签,那么“狼疮”则为其刻上个人印章。奥康纳不满16岁时,父亲患狼疮去世。25岁时,她也被诊断出狼疮。她视狼疮为上帝暴力关怀的实证,说:“生前害病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错过了上帝的恩惠。”③鹿金:《善于用变形手法塑造人物的艺术家》,见弗·奥康纳:《公园深处》,主万、屠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前言第5页。狼疮在奥康纳的天主教视界里有如约伯身上的毒疮,既是上帝所行的暴力,又是他赐予的神恩。它所带来的病痛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令她更加深入思考人生和宗教,使她获得敏锐非凡的洞察力。因此,在她短促的一生,佳作迭出,屡摘奖项。她曾数次折桂“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作品多次入选《全美最佳短篇故事集》。1964年,狼疮夺取了她的生命。她逝后不到十年,作品开始入选美国大学文学读本。1972年,《弗兰纳里·奥康纳故事全集》(1971)获全美图书奖,2009年被网民评为“最佳全美图书奖作品”,1983年,“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设立。狼疮经历对她文学创作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以此为暴力关怀的蓝本,使作品中的苦难人蒙神恩,得救赎。《瘸子应该先进去》中心理残疾、为追随在天堂里的妈妈而自杀的主人公之子小诺顿,以及《启示》中特平太太先前看不起的黑人、穷人、丑人、怪人都是饱经苦难,却坚守信德,故而先得福的。“狼疮”作为苦难的代名词,以及信德与神恩间的纽点,成为暴力关怀的隐喻。它透出作家对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等边缘人物苦难的现实关怀,成为奥康纳暴力关怀的个色。由于同时具有了天主教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奥康纳暴力关怀的本质是天主教果肉中的人文关怀内核。事实上,正是独特的狼疮经历促使她在熟稔的天主教认知体系中苦求解读,从而产生了她独具个色的天主教暴力关怀思想。在创作实践中,她将这一思想化作主题,统驭南方现实题材。
二、奥康纳的暴力关怀主题
“暴力-神恩”是奥康纳作品里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它体现了作家的暴力关怀思想。前已述及,在天主教视野,世人因罪而“不健全”,需要在暴力的炼狱里涤罪,接受神恩,获得救赎。至于那些冥顽不化、拒绝神恩的人,则遭上帝遗弃。显见,暴力-神恩主题有两个变体:暴力-接受神恩、暴力-拒绝神恩。
这一主题的两个变体在奥康纳入选选本最多的故事《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1953)里均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奶奶”随家人赴佛罗里达度假途中,想探访一座南方庄园,故意骗得全家拐上佐治亚州的崎岖山路。他们不幸遭遇逃犯“不合时宜的人”(Misfit)团伙,一家六口命丧黄泉。淑女打扮的“老奶奶”死前曾百般说求逃犯饶她一命。但是,当她看到对方郁结于“耶稣是否重生”的疑惑时,忽生怜悯,低声道:“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儿,我亲生的儿哟!”④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132.她伸手轻抚他的肩膀,胸口却被连射三枪。奥康纳认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是获得神恩与救赎”①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134.。“老奶奶”中枪后孩童般的蜷曲姿势和仰天微笑意味着已接受神恩,得到救赎。故事中的施暴者和受暴者都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心理畸人。受暴者“老奶奶”惯以“南方淑女”的世俗风范代替基督教道德准则,加之她自私的个性,强烈的控制欲、虚荣心和表现欲,显示她的心理畸形。对这样一位畸人,奥康纳说:“也许新教徒看不到她承载神恩,天主教作家却能看到。”②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222.奥康纳给予她天主教的现实关怀。于是,暴力的极端场景令她回归本性,顿悟耶稣的仁爱精神,接受神恩,获得救赎。施暴者“不合时宜的人”被奥康纳称为“迷途的先知”③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77.。暴力环境使他的恶源袒露无疑,即“耶稣是否重生”的心头之堵。他长期纠结于斯,以致精神错乱,深陷暴力与痛苦的泥潭。天主教的善恶分别以耶稣和魔鬼为中心,标题“好人难寻”亦指“耶稣难寻”。“耶稣难寻”正是他的病灶。但是,他却比其他人物更接近上帝的“神秘王国”,因为他知道如果老奶奶天天遭枪击,暴力会令她醒悟耶稣的仁爱精神,成为“好人”;他同时清楚,人生如炼狱,没有乐趣。遗憾的是,他因不接受天主教关于耶稣复生的神秘主义而无法相信救赎,自然也就无法看到炼狱的终点便是天堂,所以始终拒绝神恩。
《启示》(Revelation,1964)里的暴力-接受神恩主题昭然若揭。特平太太自觉受上帝眷顾,有房有产,容貌富态,性情慈善,而且婚姻美满。她在候诊室里与一位妇人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抖出这些资本,不料却被那妇人的丑女儿一本厚书砸中头部。丑女嚎叫着扑过来,掐住她的脖子;被制服后,仍然骂:“你个老疣猪,回你的地狱去!”④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500.颇具戏剧性的是,特平太太在委屈、困惑、愤怒之后,猛然悟到自己没什么了不起。以前,她的等级观念是,“最底层的是大多数有色人……然后在他们旁边——不是在上面一层,只是同他们稍微隔开一点——是那些下等的穷白人;然后他们上面一层是有房产的人,再上面一层是又有房产又有地产的人,她和克劳德就属于这一等级。她和克劳德上面的一层是拥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土地、钱多得不得了的阔人。”⑤见弗·奥康纳著《公园深处》,主万、屠珍等译,第424页。如今,恍惚中,她看到通往天堂的路上,她一向鄙夷的穷白人、黑人、疯子和怪人居然站到了有产阶级的前面。她所谓的资本和人为划分的等级在上帝面前一文不值,因为上帝爱人,且一视同仁。认识到这一点,便是开始悔罪,而悔罪正是接受神恩的标志。所以,她听到了向星空攀登的众灵魂喊着赞美神的“哈利路亚”。在天主教徒奥康纳的眼中,受暴者特平太太因固守南方等级观念及由此滋生的骄傲炫耀心理而“不健全”,原因是这一世俗观念有悖于平等谦卑的基督教道德。显见,丑女的暴力是令特平太太接受神恩,成为“健全人”的极端手段。
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1961)凸显了暴力-拒绝神恩主题。故事的创作背景是二十世纪中期高歌猛进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经过黑人和进步白人的不懈抗争,公立学校、城市餐馆、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先后被推翻。然而,制度虽已取消,观念尚难转变。故事主人公朱利安的母亲出身南方世家。她秉承南方淑女惯有的乐善好施的高姿态,赏给一黑人小男孩一枚硬币,不料男孩母亲怒吼一声:“他不要别人给的钢镚儿!”⑥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418.一拳将她抡倒在地。这一拳打出了两条真理:第一条从进步白人青年朱利安口中道出:“别以为您就是碰到一个没心没肺的黑女人。这意味着整个有色人种再也不愿接受您施舍的小钱。她是一个黑色的您。她也可以戴一顶您那样的帽子。”⑦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419.一句话,黑人母亲和白人母亲是平等的,她们同样有伟大的母爱、独立的人格和被尊重的权利。第二条真理是,只有诉诸暴力,才能加速平等进程。故事标题典自天主教神学家德日进(Père Teihard de Chardin 1881—1955)的理论:“真诚地对待自己,但是要永远向上朝着更伟大的良知和更伟大的爱攀登!抵达顶峰时,你就会发现自己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攀登者会合。因为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①C.A.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61.这一标题仿佛奥康纳的战斗呐喊,号召进步白人与激进黑人联合起来,共同为了爱而消灭种族主义观念。那一拳打得朱利安母亲神志丧失,缩回奴隶制时期的儿时记忆,标志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使她无法接受神恩。然而,暴力与缺失的神恩更如开刃的刀锋,足以刺醒读者,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南方读者,使他们响应她的呐喊。正如上帝以暴力关怀读懂上帝之道的世人,奥康纳此番暴力关怀的对象是能够听到她呐喊的读者。
《善良的乡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1955)也环绕暴力-拒绝神恩主题。跛腿姑娘乔伊是位高学历的无神论者。她欲以虚无主义哲学点化“善良的乡下人”——卖圣经的小伙儿波因特,不料却被他一通狂吻后骗去木腿,被弃于偏僻谷仓里的高高阁楼上。她所承受的暴力虽非激烈的肢体冲突,却充满了难以名状的侮辱性和破坏性。在天主教视域,这位“善良的乡下人”显为魔鬼的化身。从假圣经到假眼球到假肢,他装圣经的提箱有如潘多拉的盒子盛满了邪恶的赝品。然而,背离上帝者如盲人,乔伊枉有高学历,以为哲学可使她洞察世界,却辨不清真正“善良的乡下人”和魔鬼。因此,她的心理畸形甚于生理畸形。她拒绝神恩,自然会被上帝遗弃,因而遭受暴力。奥康纳以其天主教逻辑揭示这一道理,目的是关怀并警醒读者:只有信德才是透视善恶的灵光和获得救赎的条件。
在奥康纳的其余佳作里,暴力与神恩如孪生双子频繁出现,共同沿着接受神恩和拒绝神恩两条主线,实施她源于天主教、面向南方现实的暴力关怀。《格林利夫》(Greenleaf,1956)中的梅太太因固守等级观念,背离“爱人如己”的诫命而拒绝神恩,成为上帝弃儿。《眺望林景》(A View of the Woods,1957)中的玛丽为保卫原生态草场,在与追求工业进步的外公的暴力冲突中死去。她接受了神恩。限于篇幅,不再罗列。总之,暴力-神恩主题在奥康纳作品中如万花筒般变幻出各种花样,却始终如一地表达作家的暴力关怀。
三、奥康纳的样本寓言式暴力叙事
奥康纳声称:“我用我的方式写作,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②C.A.Kirk.Introduction.In 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xi.她认为“作为天主教会成员,无论多微不足道,也是救赎的一部分。”③F.O’Connor.The Habit of Being.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9,p.92.本着这份天主教的道义担当,她在作品中以上帝的暴力关怀为蓝本,并对上帝暴力关怀作寓言般提示,因此,其作品具有样本寓言的特性。样本寓言原指宗教布道中作为一个概括的宗教主题的具体事例而讲述的一则寓言故事。这种样式盛行于中世纪。它很快跳出“布道”的窠臼,适用于多种场合。乔叟的《教会赎罪券推销人的故事》(The Pardoner's Tale)例证“贪婪是万恶之源”,便是一个范例。乔叟同时将这种样式外延扩大,使之也可以包含非宗教主题的故事④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7theditio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6年,第5~8页。。本文仅研究宗教样本寓言,其主要特性有二:其一,表现概括的宗教主题;其二,故事有本体之外的宗教象征意义。奥康纳的故事基本满足这两点。
前已述及,奥康纳的故事表现天主教的暴力关怀主题。神恩、救赎和上帝的暴力关怀归根到底都是超验的,所以,她并没有在故事中明确这一主题,而是留给作品人物和读者参悟。她采用乔伊斯在《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中运用的现代主义技巧“精神顿悟”,让读者高度参与,使之和作品人物在“精神顿悟”中领悟这一主题。“精神顿悟”既是一帧微妙的心理升华画面,又是一种叙事技巧。它由作者精心策划,人物心理在经历了有意无意的准备后,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配合下,发生了化学反应般的质的腾跃①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1~112页。。奥康纳故事中的暴力就是具有强刺激性的外部条件,它起两种作用:1.阻断世俗逻辑;2.联通天主教逻辑。她故事中的暴力总是突如其来。这种突发性不是来自暴力美学常用的动静急速切换,而是缘于更深层次的世俗逻辑的猛然断裂。例如,《好人难寻》中的“老奶奶”听到匪首痛苦而狂乱地嚷出对耶稣是否重生的困惑,不由心生怜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伸手抚慰。但是,“不合时宜的人猛地闪开,象是被蛇咬了一口,冲她心口连射三枪”②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132.。再如,《启示》中自认为受宠于上帝的特平太太正在候诊室里与邻座欢谈时,忽遭丑姑娘暴袭。《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的朱利安母亲赏钱后却遭到黑人母亲的一记老拳。暴力来得不合常理,令受暴者和众读者的常规认知与理解顷刻处于茫然失重状态。由于世俗逻辑为暴力所阻断,受暴者要么如朱利安母亲一般精神错乱,要么如“老奶奶”和特平太太,以及有基督教意识的读者,诉诸天主教逻辑。于是,暴力打通了天主教逻辑,使作品人物和读者得以从头沿着奥康纳貌似无意实则精心设置的天主教路标(如表现畸形),反思整个事件和自己的价值体系,达到如“老奶奶”所经历的天主教的“精神顿悟”,接受神恩,获得救赎。由是,奥康纳实施了对受暴者和读者的暴力关怀。
奥康纳的故事可被纳入圣经的象征体系。大量圣经意象被奥康纳信手拈来,象征神恩、救赎、耶稣或魔鬼等。例如,《好人难寻》中,老奶奶中枪后孩子般盘腿蜷着,象征接受神恩,获得救赎。因为耶稣曾告诫使徒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18:3)《背井离乡的人》中吃苦耐劳,惨遭碾死的吉扎克象征受难的耶稣,而蛇一般窜到门口的钱塞则显然是魔鬼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象征主义中个人意象的应用令奥康纳的暴力叙事个性鲜明。鸟是奥康纳作品中一个典型的个人意象,往往象征耶稣或天使。奥康纳幼时爱与禽鸟为伴。五岁时,她训练一只卷毛鸡倒着走的新闻影片作为电影前放映的短片,曾风靡三十年代的美国。身患狼疮后,她在安达鲁西亚农场里养孔雀,盛时达四十余只。《马太福音》中,耶稣曾变形(17:1-2)。鸟作为奥康纳苦难一生的伴侣,被她视为耶稣或天使的变形。《背井离乡的人》中的孔雀被神父看作变形的耶稣,而任劳任怨工作,却即将被解雇的吉扎克也被他认作是耶稣的化身。于是,作家在耶稣、孔雀、吉扎克之间建立了交互象征关系。三者在故事中互映频现,组成网络,勾连耶稣变形、受难和上帝暴力关怀的内容,使整个故事进入圣经象征系统。同样,《好人难寻》中“老奶奶”的儿子贝利的双眼如他衬衫上的鹦鹉颜色一样蓝;《你救的也许是自己》(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1953)中的聋哑女的双眼也如孔雀脖子一般蓝,饭店伙计一语道破:“她看起来象个上帝的天使。”③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154.在暴力叙事中,奥康纳通过强化鸟、神、人三者互为象征的关系,链接圣经象征系统,暗示行恶之人必得不到救赎,从而唤醒读者的基督教善心与谦卑,达到她暴力关怀的目的。如是,奥康纳的圣经意象在文本中网结组合,于文本外勾连圣经相关内容,使她的故事具有本体以外的象征意义。从而,读者能够在圣经框架中解读奥康纳故事,并理解她暴力叙事的关怀主旨。
暴力关怀如一剂苦药,为表达现实关怀,并使暴力关怀主题更易为读者接受,奥康纳在暴力叙事中为这剂“苦药”包上糖衣,即黑色幽默。黑色幽默,简言之,是一种恐怖中蕴含幽默的现当代文学形式,其讽刺对象是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残酷、浅薄、混乱④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7theditio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6年,第278、332 页。。奥康纳故事常被引为黑色幽默的范本,主要原因是她讽刺双重对象,即表面上揶揄作品人物,深层里却嘲讽人物背后的陈规陋习,如等级观念、南方淑女绅士风范等。例如,《启示》中自命不凡的特平太太竟被她看不起的丑姑娘骂作“地狱来的疣猪”;《好人难寻》中的“老奶奶”穿戴齐整,目的是死了也要被认作南方淑女。她甚而拿淑女身份作挡箭牌,哭问“不合时宜的人”:“你不会杀淑女吧?”①F.O’Connor.Flannery O’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127.南方淑女曾被认为是南方的象征,圣洁虔敬、温柔守礼,是南方男人显示勇武与殷勤的保护对象。然而时过境迁,风尚陡转。老奶奶的淑女帽在身穿睡衣旅行的儿媳眼里怕是颇显另类,以淑女身份作免死牌则令人发笑。无独有偶,《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的朱利安母亲也戴一顶淑女帽。她未料到淑女帽早已不是白人妇女的专利,戴在黑人母亲头上倒更好看。她“乐善好施”的淑女美德换来的竟是一记代表自尊的黑人拳头。《最后审判日》中在屋内还戴着绅士帽的南方老人坦纳试图对北方黑人演员使出驾驭黑人的老套路,却被觉醒了的黑人愤怒推搡。显然,南方传统价值观在新形势下已全线崩溃,陈念使南方绅士淑女们反而成了“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们竟以不公且过时的世俗观念代替奥康纳眼里永恒的宗教道德。奥康纳的黑色幽默凭借反讽与戏剧冲突,向这些“不合时宜的人”及其背后的陈念射出了子母弹,实施其现实关怀。她讥笑世人的浅薄和世俗陈念的荒谬,也使世人在会心的笑中领悟并认同其关怀主旨。黑色幽默作为“恐怖中的幽默”(humor in horror),在奥康纳故事中与恐怖的暴力形成合力。二者合力,不仅令作家的暴力叙事张弛有度,五味杂陈,而且契合其暴力关怀的理念,显然比纯粹的暴力文字更易令读者接受。
奥康纳视自身的绝症狼疮为上帝暴力关怀的实证,以此为蓝本,不断重复暴力-神恩的主题,对作品中人物和读者予以暴力关怀。借助“精神顿悟”、象征主义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她创作出一个个宗教样本寓言式的警世故事,寓说暴力关怀。她传承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南方文艺复兴传统,引领20世纪中叶的天主教文学复兴潮流,而且影响了理查德·鲍希(Richard Bausch,1945—)、鲍比·梅森(Bobbie Ann Mason,1940)等后代天主教作家。尽管读者和论者对她独树一帜的暴力关怀思想褒贬不一,但是她的暴力叙事技巧和人文关怀的内核使她的作品成为令人难忘的美国文学经典。当今流行的暴力美学,作为现于电影和武侠小说等流行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纯粹趣味追求中发展起来的形式体系,提供给受众道德教化以外的形式快感②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它在获得广大受众的同时,也因摒弃道义担当而产生日益明显的社会副作用,例如,模仿影视暴力情节的青少年暴力犯罪屡见不鲜。笔者以为,我们无须认同奥康纳的宗教理念,却可以借鉴她在暴力叙事中的道义担当和包裹在宗教理念中的关于平等博爱的人文关怀,以及一些相关暴力叙事方法。我们不妨有选择地以此为参照,对暴力美学予以修正,如控制血腥色情场面,转而深挖思想道德内涵,使之掮负一定的道义责任,而不是将道德取舍的重任推诿给受众,特别是一些尚无明辨是非能力、极易受环境影响的青少年受众。
责任编校:刘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