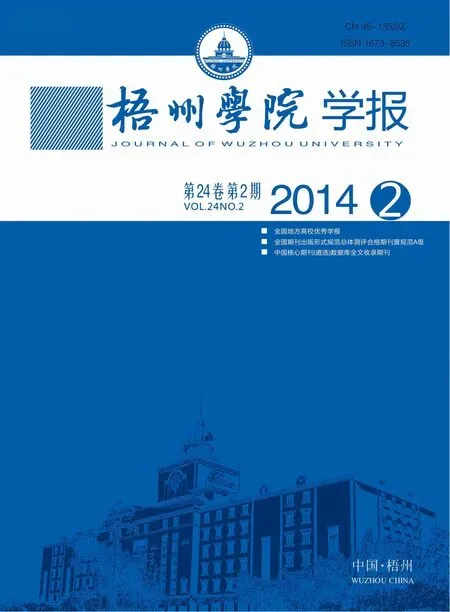从中国视角看文化产业的“西方经验”
李江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从中国视角看文化产业的“西方经验”
李江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文化产业的“西方经验”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是系统完备的理论认识,二是丰富的产业经验。理论认识是更多地侧重于学术层面上的批判性研究,产业经验则更多地关注实用性的产业手段的运用。总体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文化产业如果要为进一步跨国经营做准备,就有必要在全面把握西方文化产业的社会历史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基础、发展方式以及社会贡献的基础上,更好地兼顾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和产业化经验。
文化产业;西方经验;文化产业理论;产业化经验
一、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
从思想背景和理论影响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技术媒介学派对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深入研究过文化工业的机制、特点、作用和影响。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很多富于警策性的见解,令人目眩地打开了一条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所不同的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思路。
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进步和人的解放逻辑不同,阿多诺深刻地继承和发扬了一种方法论上以及基本立场上的批判传统,对文化产业保持了一种清醒而不妥协的批判姿态,集中而不是目标宽泛地探讨了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并把这些思考转换成了认知表述,从而使他揭示的文化产业的相关认识系统而又深入。根据阿多诺的观察,文化产业明显不同于自发生长的大众文化。“在文化工业的所有部门中,为了大众的消费而制作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消费本质的产品,多少是按计划而生产的。各个个别的部分在结构上都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相互适应的,把自己组织为一个几乎没有裂隙的系统。做到这一点是借助了当代的技术能力以及经济和行政上的集中化。”[1]在阿多诺看来,文化产业是由文化生产商控制、按照严格的生产程序、为满足利润欲望和消费欲望而兴起的产业。生产的标准化导致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创造方式决定了产品的特点,这也就是文化产品为什么不具备真正艺术品那种真实的风格以及丰富的韵味的原因。文化产品具备的只是独特而新颖的虚假性,它带给消费者的并不是由衷的心满意足,而是一种充分而虚假的快感。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娱乐形式,对消费者而言,现代文化产品相对无害,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产业化是对消费者要求的一种民主化反应,但西奥多·阿多诺坚持认为文化工业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文化工业培养的是空虚、平庸和顺从。如果忽视文化工业的性质,就是屈从于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腐败的和操纵性的,它巩固了市场和商品拜物教的统治。它同样是使人顺从和使人头脑麻木,强迫人们普遍接受资本主义秩序。文化工业经营各种谎言,而不是真理。经营各种虚假需求和虚假解决办法,而不是现实的需求和现实的解决办法。它‘仅仅在表面上’解决各种问题,不是按照在现实世界中应当解决它们的那样去做。它提供解决各种问题的伪装,而不是实质,把对各种虚假需求的虚假满足当做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办法的替代物。在这样做时,它把大众的意识接管了。”[2]7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跟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理论特征不同,而且实际上跟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之间分歧也很大。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基础,来开展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辩证法》,他们采取的是拒绝工业文明进步的思路。同样,本雅明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而阿多诺不是。阿多诺一直在坚定地预警,提示人们注意新技术中的经济动机和意识形态动机。如果忽视商品拜物教和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关系,人类就将很难摆脱发展中的危机。他语重心长地写道:“文化工业总体的作用是反启蒙的,如霍克海默和我所评论的。其中,启蒙即先进的技术的统治,它完成了大众骗术,变成了约束意识的手段。它妨碍自主、独立、为了自己而自觉做出判断和决定的个体的发展。它阻止时代生产力所允许的、人类为之准备着的解放。”[2]65通过对文化工业生产过程和生产特点的观察,阿多诺注意到经过标准化的过程,文化产品具有了所有商品的共同形式。“文化工业虽然无可否认地反思过它所针对的成千上万的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况,但大众却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件。与文化工业要我们相信的不一样,消费者不是国王,不是消费的主体,而是消费的客体。”[2]72文化工业把文化变成了娱乐,这样的娱乐再造了虚假的幸福感,压制了消费者的思考,防范了人们对现实的否定以及解放冲动。在这里,阿多诺明确地指认出文化工业在生产方式上的标准化和同质化的的特点和后果,更不隐讳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意识或思想的管控,他把消费者设想为“文化呆子”。联系商品社会中文化产业的拜物性,阿多诺认为进入文化产业过程产出的文化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市场流通环节中交换或销售。它是商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已经失去文化的某些本性。既然不是艺术品,那么它主要是为了迎合消费需求而不是或不能满足真正的精神需求或灵魂的需求。严格说来,艺术创作是自由的精神创造。艺术让灵魂飞升,完成对人类的精神表现或精神引领。在产业化时代,把艺术文化的创造视为轻而易举的行为,把艺术文化作品的鉴赏理解为一种易如反掌的娱乐。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滋生享乐主义的温床,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审美能力的萎顿、批判能力的退化、反思能力的闲置。
法兰克福学派敏锐地注意到当文化产业服务于有组织的资本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必然会引发的后遗症。从更深层次的现实来看,阿多诺具有一种类似于宗教救赎那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在他看来,艺术文化一旦屈从于产业秩序,放弃作为文化艺术品的“以太”(ether)那样的精神之光,那么人类的心灵将万劫不复。所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阿多诺对日益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还保持着坚定的抵抗和批判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阿多诺敌视的或坚决拒绝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还具体针对工具理性向人的社会生活的扩展。张一兵曾经敏锐地注意到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那个准确概括现代技术社会特征的概念:“被管理的世界。”在阐释这个概念所表征的“工具理性的进步就是人类文化的铲除”时,张一兵做出了这样的联想:“这也是启蒙思想无意识自反性更具象的方面。我认为这一批判性指认对于中国学界面对‘科学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的无反思性的受动状态,一定是一种强劲的震撼。”[3]
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在完成对文化工业和技术社会的批判时,也巧妙地发现文化产业在物化社会和意识方面并不是万能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存在着某种虚弱的一面。在警惕技术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同时,阿多诺相信艺术并不是凝滞不变的,而是会在运动中完成自我调节的“变数”。在他看来,新的文化、新的艺术,也就是他所说的“尚无人知的审美形式”有可能产生于这种与技术统治之间的许多密切关联中。从这些表述来看,阿多诺既不悲观,也不守旧,更不僵化。在《电影的透明性》中,阿多诺明确地宣称:“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本身在操纵大众的尝试中,已经变得与它想要控制的社会一样内在地含有了对抗性。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含有自己的谎言的解毒剂。”[4]由此看来,深邃而辩证的阿多诺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工业时留下的大量言论对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而言,其意义就绝不是单一的。对接受者或借鉴者而言,对此不能断章取义,把握其表层含义和具体细节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更重要的是把握其具体论断之下的深层思想。不能只是刻板地援引阿多诺的理论文本,而是更全面更自主地接受。中国文化产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潜力、发展规模、发展节奏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情况都大不相同。对中国文化产业而言,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逐步扩大,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可能性都变得越来越坚定,也愈来愈明确。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都显得越来越迫切。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积极回应国内需求,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参与和主导激烈的国际竞争。从适应国际需求和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有秩序地良性地发展,也许比单纯的宣传更能有效地完成意识形态的使命。相对而言,媒介传播比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在效果上更深入,也更内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也许是文化产业最基本的现实国际职能。不过有必要注意的是,文化产业也是一种双刃的兵器。如果不充分尊重文化规律和产业发展的规律,不能有效处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从中产生的问题有可能会远远超过发展制造业引发的环境污染以及在大中型企业重组时国有资产的流失。
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工业所做的研究及其论断,作为前车之覆,对我们提供的是至关重要的警醒。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产业战略或决策,还是企业层面的可行性战略制订、资源整合的方式、商业模式的调整,实际上都需要认真关注价值观的作用。如果价值观体系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必将稳步发展。这也许是我们在解读阿多诺时获得的主要收获。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马里亚诺·格龙多纳(Mariano Grondona)教授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做出正确决策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实现持续的、迅速的发展。他提出:“价值观有两大类:一类是内在的,一类是工具主义性的。内在的价值观是指我们不计个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例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要求人们做出牺牲,有时就个人得失而言,它是‘不利的’。然而自古以来,千百万人都为捍卫祖国而献出了生命。相形之下,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是指那种因为它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价值观。假定一国致力于经济增长,为此而强调努力工作、提高生产率和进行投资。倘若有利于发展的决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工具主义性价值观,所以要发财致富,那么人们富到一定程度时,努力就会减退。”[5]实际上,从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对价值观体系的特点和作用的阐释中,恰好包含着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工业中指出的那些主要问题的原因。工具主义价值观的暂时性并不足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作为工具,一旦实现它的使用价值,人们也就不会再充分注意它的作用。但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所说的那种“内在的价值观”就大不相同,它不会随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而失去作用。如果说因为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经济价值观并不足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内在价值观与此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引领人们,使人们不至于误入歧途。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等理论家为代表,在文化立场、文化态度、文化研究方法以及文化理论认识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与文学》等著述来看,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非常宽泛。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即“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这就是说,仅仅把“文化”局限在观念或价值体系方面来理解,或局限在某些部分的生活或个别的生活方式来认识,都是存在着偏颇的。高雅文化是文化,低俗文化也是。严肃文化是文化,大众文学也是。从存在形态上看,文化有可能已经凝结为概念化的范畴,也有可能弥散在或渗透于日常行为和经验之中。雷蒙德·威廉斯甚至认为,从价值层面看,这些文化形态没有也不应该有高下优劣之分,因为这些复杂多样的文化形式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或成长的条件。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在如下几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认识重点和认识特点。
第一,伯明翰学派也坚持文化产业研究的社会批判性,但跟法兰克福学派有所不同的是,伯明翰学派更重视把大众文化作为文化产业形式来开展严肃的研究。由于消解了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低俗之间的对立,所以伯明翰学派在他们的理论工作中敞开了消费者的创造性以及发生在消费中的生产性阅读或阐释是怎样改变生产者的初衷或某种预先设定。这就是说,文化产品一旦进入传播或消费环节,它就具备了或体现出某种不以生产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
无论是斯图亚特·霍尔、霍加特、汤普森,还是雷蒙德·威廉斯、托尼·本内特,在他们对“大众”“人民”“流行文化”等概念的阐述中,都是试图彰显某种“文化平民主义”或“文化民粹主义”。对“大众”“人民”的关注,对“大众文化”的观察,有助于推动对文化研究中真实而具体的消费情况的研究,在密切注意有选择的消费行为、生产性的接受行为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的原有意图之间的差异时,还可以更细致地探寻接受中或消费中的吸收、抵抗、协商、曲解等各种具体的情况。那些批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大众”视角的意见则认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研究视野狭隘,完全有可能把研究工作引入一种不加批判的解释模式中。吉姆·麦圭根这样写道:“我赞成理解和评价各种日常意义的愿望,但是这样一种愿望,会产生对于塑造普通民众间接体验的物质生活景况和权力关系的不恰当解释。”[2]278对伯明翰学派持批评意见的人们认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缺乏一种必要的批判力量。实际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更明显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它的意识形态立场上,也许将其视作一种政治策略比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产业理论更符合实际。在各种文化产业理论中,真正切实的受众研究或许正是从伯明翰学派开始。虽然看起来迄今为止他们只是替消费者代言,或者替消费者立言,还没有朗声向消费者发言,但显而易见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并不仅仅像大多数文化理论那样,只是把文化消费当作经济行为或生产行为,重点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而不在于消费者心理和消费过程,伯明翰学派还关注消费的文化本性。在对文化产业的本体认知中,虽然他们也注意到产业手段以及产业方法,但他们更重视文化目的。由于他们不会把目的当手段,也不至于把手段当目的,所以可以希望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来实施某些认识纠偏。
第二,伯明翰学派把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从关注生产过程向关注消费过程的位移,在现在看来不仅仅是一种研究重心的转移,而且更是对某种消费主体性的强调。伯明翰学派在研究中注意到,文化产业的消费者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断言的那样,完全是一批空虚、平庸、不动脑筋、经不住诱惑的上当受骗者。伯明翰学派认为,把消费者设想为受控于大众媒介和它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完全被文化产业所算计,这样的判断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至少是过分夸大了权力对文化生产的控制,夸大到这些因素的力量足以决定文化消费模式的地步了,那就明显地出现偏差了。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在传统媒介研究中,受众总是以受影响的形象出现,一直是广播组织以及广告机构调查的需要。而我们要用一种更活泛、主动的受动概念代替了这些过于简单的概念。在这些概念中,读解、媒介信息如何被编码、编了码的文本的重要性和不同的受众的解码之间的关系都是活泛的。”[6]斯图亚特·霍尔等对阅读策略或大众解码策略的研究,强调了受众在消费行为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可以表明伯明翰学派并不否认民众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某种弱势处境,但与此同时他们把理论兴趣集中在对符号权力的研究方面,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权力虽然很强大,但符号权力却是受众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他们可以通过对文化产品的解码,来实现预期的对媒介权力意识形态的抵抗、颠覆或者重构。更重要的是,伯明翰学派对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意义改变、意义追加、意义歪曲、意义挪用等解码行为的细致研究,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文化消费的特点和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科学地认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
伯明翰学派重视文化那种作为社会经验的属性。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文化存在于日常行为和经验之中,是一种和真实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其物质性和实践性意味着文化创造是凝结群体智慧的方式,它是民主的、开放的、动态的,也是充满活力的。也就是说,由于创造和消费的广泛性,文化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某种难以垄断的、无法预测的、不断更新的同时也是前景广阔的形式。这些形形色色的创造意义的形式,充分体现出不可忽略的创造过程的某些“共同性”,或类似消费过程中那种共享的“民主性”以及参与者自我成长的某种“家园感”。消费模式对文化生产具有某种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不过对文化消费模式的研究仅仅停留于对消费行为的关注,那就太表面也太浅近了。从这方面来看,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显得深入得多。
(三)媒介技术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
媒介技术学派在解魅作为讯息的媒介对人的感知方式、感知系统以及认识和心理的深刻影响方面,以其独特的认识贡献,启发人们更及时更准确地关注新技术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电脑、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互联网以及通讯技术在为文化产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迅速地引发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媒介技术学派以技术演变为基础和认识线索,广泛吸纳新的理论资源,建构起富有阐释力和前瞻性的理论体系。
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研究媒介技术理论的先驱。由于对媒介技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机制、方式和效果的研究,他开创的麦克卢汉主义或麦克卢汉学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研究领域获得过很好的评价。他提出的“媒介讯息论”“冷媒介与热媒介”“媒介环境学”等论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麦克卢汉至为关切的媒介技术对社会和心理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然是媒介技术研究中一个广受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让人们对媒介技术变革不得不保持足够的重视。
作为传播学先驱,麦克卢汉理论体系的前提就是“媒介讯息论”。在他看来,媒介之所以能影响人,是因为它能把需要传通的东西处理成了能让受众接受的“讯息”。对“讯息”的理解,可以彰显他的“媒介讯息论”的要旨。他认为,单纯的信息,是一种不带讯息(message)的媒介。“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7]228在很大程度上,麦克卢汉早年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经历使他在用语上也体现出某种散文风格,这种非连续性并置的方式适合深度研究的表达,也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媒介即讯息”至少包含着三种相互联系的含义:一,讯息的样式或规格必须适合传媒的要求,便于让受众接受。二,媒介的性质是第一位的,远胜于传播的内容。三,理解媒介就意味着理解其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性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交流的内容。因此,他更重视研究媒介的性质,因为媒介成分和内容的研究绝不可能揭示媒介影响的动力学。
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属性的研究,其目的正在于深究媒介对人的感官的影响。在他看来,“热媒介”清晰度高,媒介感知者不需要深度介入,也不需要进一步地大量补充信息。如电视、电话、象形文字、卡通片、手抄本、口语等。“冷媒介”与此不同,其信息清晰度低,信息接受者必须深度卷入,并补充信息。麦克卢汉把这一类媒介称之为“冷媒介”,如电影、照片、印刷品、拼音文字等,并进一步就媒介的“冷热”特性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因为“热媒介”可以提供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可以剥夺信息接受者深度卷入的机会,那么信息接受者的感官机能降低。“冷媒介”邀请信息接受者深度卷入,那就需要感官提高感觉机能。麦克卢汉对媒介冷热属性模式的识别或者区分,其实已经暗含着对信息接受者的某种“分众”处理。显然,“冷媒介”适合媒介与精英阶层的信息交流,“热媒介”则可以大量用于社会中的普通受众。在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或伺服中,麦克卢汉认为由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对心理的影响已经可以让接受者浑然不觉。对信息接受者而言,那已经是一种隐形的环境,就像“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7]70。当新技术内化时,就会很快发生文化的新型转换。
从媒介史或媒介变革的角度,麦克卢汉乐观地预言,电子媒介时代将通过感知系统的重塑,人将会成为感官平衡、具有整体思维能力、能够整体把握世界的“部落人”。在原始部落时代,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味觉都可以接受信息,感知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在那个“口语媒介”时代,不凭借文本,也不发生感知方式的分割。书面媒介时代是由视觉感知主导的时代,拼音文字把信息进行视角编码,人类的眼睛在讯息感知中代替了耳朵,感官平衡被打破。在感知方式上人成了残缺的人。电子媒介缩小了地球空间,成了“地球村”,由于感知方式在更高层次上的“返祖”,在信息接受中感官平衡,人也许可以成为人格健全的人。这是新媒介带给人类的最振奋人心的福祉。
麦克卢汉对新媒介的环境作用的重视,使他有机会具体地探究媒介是怎样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的。他认为:“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觉察的。这似乎是种系发育过程的必然结果。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都成为此前一切阶段的环境。然而我们直觉到过去的阶段,或者说只觉察到环境的内容。”[7]412媒介形式对人的感知、认识、思考、理解,其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外在于人的感知方式。环境是可以避开人的感知的,并用一种奇怪的力量传播着关键而主导的讯息。既然新媒介就是一种新环境,新媒介传播的讯息又是根据新媒介的规范完成的新编码,那么在媒介与人的互动中,就必须重视具有主导性的新媒介的变革。媒介史从口语到书写、从书写到印刷、从印刷到电子媒介的转化表明,只有在媒介技术和人的回应能力之间保持某种必不可少的平衡,现代社会才有值得期待的未来,人类才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文化创造或文化生产的积极作用和建设意义在这里可以获得集中的体现。
从总体上看,媒介技术是麦克卢汉认识现实的视角。围绕媒介技术建构起来的认识体系,以富于历史性和反思性的阐述方式表达了具有启示性的文化民主观。也许,他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还原论者或技术决定论者。其理论认识的宏观性表明,麦克卢汉主义不像布迪厄的媒介批判理论和波德里亚的“仿真”理论那样,更多直接而具体地面对文化生产现实或文化产业现实,因此,它也因为这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间距而显得要全面得多,也显得更深刻。
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实践的基本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理性、完整、全面,具有战略认识的宏观性和前瞻性。从策略层面看,跟文化产业实践之间距离遥远,缺乏直接的可操作性。这也许是由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在目标和效用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
中国文化产业当前具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正处在加强学习和积蓄力量的重要阶段。自从2008年纳入国家产业振兴计划,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后,现在的状态也并没有急流猛进,一路高歌,而是“尽可能地从容前行,不断调整发展方式,完善管理方式,在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和研发资金等方面积累经验”[8]。这种现实要求中国文化产业在面对西方经验时要更有整体性、前瞻性地借鉴,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地利用。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产业重视投资,但忽略消费对产业的推动力量,大量民间资本被闲置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在管理方面采取的分业发展和行业分层管理也暴露出管理理念滞后的问题。所以,面对西方经验,我们不仅要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理论方面的丰厚积累,更要认真学习他们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实践经验。如果我们不充分注意以产业链结构为核心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整合,就有可能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具体地看,由于西方各国文化产业基础不同,所以在政策支持方式、产业发展方式以及产业管理方式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美国重视电影业和旅游业,他们的电影业、家庭电视、录制音乐等娱乐也获得了充分发展,所以其体制、市场、产值的成长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重视美国电影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业绩,希望并鼓励那些海外子公司在销售方面充分发展市场开拓能力。美国的旅游业是零售业中第三大零售产业,在支持和解决就业方面,功勋卓著。德国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戏剧业和电影业,并千方百计增加经费投入。德国公共剧院和私人剧院基本上不为经费问题发愁,因为各州以及地方政府把公共娱乐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三都投给了剧院。政府专门设置电影促进署来推动电影业的发展,媒体公司和国际电影集团负责在影片制作和电影院基础设施建设或改造方面投资支持。这些措施不仅支持了国内电影生产,也加强了德国电影业和欧洲电影业以及国际电影界的合作。瑞典跟美国和德国的情况不同,瑞典政府在文化环境建设、文化旅游以及群众文化活动等三个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但在经费投入方面并不太多。在瑞典,广播、电视、书刊、音像以及报业都是文化产业,所以就要按市场机制来运作,也就是需要消费者来投资了[9]。瑞典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主要用于交响乐团、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等方面,这里体现的也许是一种立足文化国情、脚踏实地、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
从以上欧美诸国的情况来看,共同之处在于:一、政府在战略层面上的政策支持,具有主导性和推动作用。二、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体现为面面俱到或平均使用力气,而是有重点、分主次、立足实际地被引导。三、依法管理文化产业,广泛利用民营资本来推动产业化。四、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加强了国际产业合作,组建跨国公司,有助于有效把握机会,利用对方的市场、渠道、机制,既可以保持一定的产业发展规模,又可以充分发挥灵活性。作为具体的文化企业或企业负责人,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一定要急于经营跨国公司,但从确保国家文化利益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文化产业的跨国经营,势在必行。
[1]Theodor 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J].New German Critique6,Fall1975.
[2][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2.
[3]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M].北京:三联书店2001:32.
[4]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6.
[5][美]塞缪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1.
[6]StuartHall,Dorothy Hobson,Andrew lowe and paul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M].London:Hutchinson and Co.(publishers)Ltd,1980:117.
[7][加]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8.
[8]李思屈,等.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效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3).
[9]陈忱.文化产业的思考与对话[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41.
On the“W estern Experience”in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Li Jia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GuangxiNorm 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The“western experience”in cultural industry consists of two inseparable parts:one is systematical knowledge of theory and another is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The systematical knowledge of theory ismainly about critical research atan academic leve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ten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industrial approaches.I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still in a natural state needs to prepare the experience for furthermultinationalmanagement,it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factor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bases,developingmodes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of the western advanced countries so as tomake better use of the theories and experience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industry;Western experience;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Experi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G114
A
1673-8535(2014)02-0037-08
李江(1964-),男,重庆市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4-01-12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