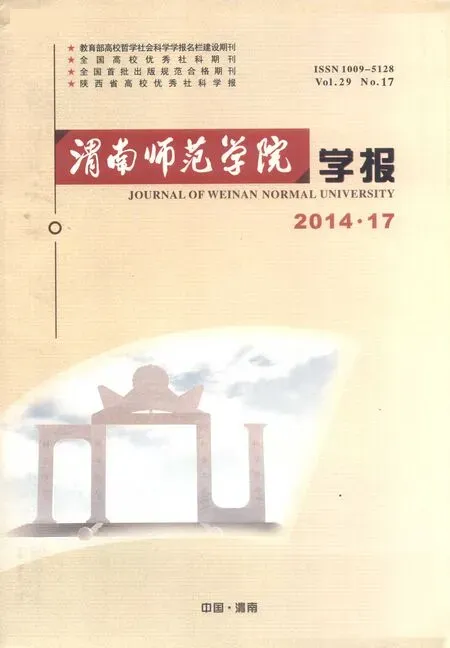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初探
王 锐,王明利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 712082)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初探
王 锐,王明利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 712082)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有的统治方式。它是在统一的国家内,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其采用的一种符合本民族地区实际的管理模式。自古以来,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时期,对整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以“羁縻政策”为主。待到大局已定、国力殷实之后,便从稳定边疆局势的实际出发,设法推行边疆与内地一致的政治体制。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就是清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四川边地的统治力度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它是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土司制度;川边;改土归流;巴塘事件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对原有制度的继承和创新。它来源于对原有制度的深刻反思,并使之与现实的境况结合起来,达到其理想的效果。当这种制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时,人们又会重新思索,代之以更好的社会组织形态,或者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修补。推行于川边的土司制度至清末,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灾难、边疆危机四起的情况下,只有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才能巩固统治。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也是对于中国自古以来只有边疆而无边界观念的一种挑战,面对列强对边疆地区的不断蚕食,也迫切需要对边疆体制进行改革。
先秦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以轻蔑、带有侮辱性的词语来称呼边疆的少数民族,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也。正统观念中的“华夷之别”,表现出尊崇中原地区的主体民族,轻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明显倾向。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中央政府承认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然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地方;各土司之间争权夺利,甚至出兵对抗朝廷。清末,面对内外危机,这种有损于封建王朝内部稳定的土司制度,也越来越不合时宜。
一、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原因
清朝统一中国后,基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点,继续沿用明朝的土司制度。《清史稿·土司传一》载:“西南诸省……迥殊华风。曰苗,曰蛮……无君长统属之为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为蛮。……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皆蛮之类”;“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隶吏部”。[1]2308长期以来,川边地区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清末,随着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直接威胁到四川与云南的安全,西南边境危机四伏。鉴于川边地区与川、藏间的特殊关系,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挽救西藏危局,不得不积极经营川边地区。笔者拟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具体原因:
1.列强环伺之下的川边危机
甲午一役,中国一败涂地。“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2]319世纪以来,英国借助其在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先后侵占了尼泊尔、锡金、不丹,同时也打开了入侵西藏的通道。1888年和1904年两次入侵西藏,迫使西藏噶厦政府与之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在其庞大的“巴德玛耶夫计划”中,就是要将西藏地方并入俄国版图,不断派间谍分子拉拢达赖及拉萨的大贵族,以达到分裂西藏地方的目的。中日战争的结局,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争夺,不仅造成西藏出现严重的危机,也造成了川边藏区的不稳定。川边主要是指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青海玉树和云南迪庆等各省区的藏族居住区,历史上称为康区。康区作为四川通向西藏的官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康为川藏通衢”。假若西藏有失,则川省门户洞开,岌岌可危。欲“固川图藏”,则“必先安康”。“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也,岂等藏为藩篱,而康为门户已哉,政府及川滇人士,于藏固不可忽于康,尤当念念不忘”[3]2-3。可见,“安康”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
2.川边梗塞,影响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
有清一代,川边实行的政治体制是既不同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不同于内地的郡县制度,而是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土司制度。各土司之间互相对抗、互相仇杀,影响了川边地区的稳定。处于川边中心地位的瞻对土司(今四川甘孜新龙县内)则让清政府屡次用兵。“瞻对距打箭炉七日程,东连明正,单东,麻书,孔撒,章谷五土司之界;南接里塘、毛丫、崇喜三土司之疆,西北与德格土司毗连”。[3]45该土司纵横四五百里,地势险要,民风强悍,时常兴兵作乱,扰及川藏大道。同治元年,瞻对土司工布郎杰发动叛乱,“欲拥康部全境以抗川拒藏……至是藏人怒,求四川出兵……派道员史致康率师会藏西讨,致康怯……藏蕃需茶急,弛兵击之……藏蕃索兵费银16万两”[4]14223。清政府因忙于四川战事,经费紧张,就将瞻对赏予西藏地方,以充兵费。随着西藏分裂势力的不断抬头,瞻对问题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清代藏事辑要续编》云:“瞻对…插入内属土司之中。本系川境内地,一旦弃归藏中,值此时艰,设西藏有事,瞻对之地,不问而即属他人,川省且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不能不及早图维,预筹布置……则不独川省之幸,实大局之幸也。”[5]101收回瞻对并将其改流,直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即可以清除川藏大道的障碍,也可以在西藏有失的情况下,举以援手,更可确保西藏有失,川省有门户可守,此一举三得。
3.清末新政为川边改革提供了相应的便利条件
1900—1901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一系列变故之后,清王朝不得不重新举起维新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避祸西安的清政府发布上谕:“诏议变法,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直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条举以闻。”[6]937深陷危机的清王朝痛下决心:“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治、吏治民主、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切实施行。”[7]4602这次新政是清政府极力挽救其腐朽统治的一剂猛药,但值得后人赞许的还是其筹边改制的政策。在敌强我弱、弱肉强食的国际格局中,中国传统的“以夷治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再也不能满足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改土归流和建立行省乃大势所趋。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在《请建西康行省折》中指出:“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焉,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领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为定之故,兹边地即为康地,康藏原有攸分,应将疆界照旧划定,以康建省。”[7]77在边疆地区改革行政体制,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直接行政权力,以稳边圉。这为川边改革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4.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是川边改土归流的又一原因
古代中国往往把一个朝代作为一个国家,甚至把一个政权也看作一个国家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无可厚非。古代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家概念,更没有国家主权意识。中国传统的边疆政策,只要对方年年来贡,岁岁来朝,即认为其是王朝的一份子。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睡梦之中的中国人。西方国家的入侵,使这种本就模糊的边疆政策再也不能应对时局的需要,列强不断向边疆推进,蚕食国土。国家主权遭到极大破坏。近代国家观念中的人口、领土、政府、主权、边界等因素开始影响当时的人们。清政府在与列强的相互碰撞与冲突中,逐渐认识到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开始积极地经营边疆地区,并将边界概念纳入到边疆的治理之中,在新疆和台湾建立行省,就是清政府经营边疆的最好证明,也为川边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依据。
二、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从川督鹿传霖“留心边事”到傅嵩炑上《请建西康行省折》为止,改土归流前后历经十余年。鹿传霖任川督时,于光绪二十二年《密陈瞻对亟应收回改设流官疏》云:“臣稔知藏事岌岌……实以瞻对为川省藩篱,其地本属川省土司,去藏远而距川近……当年瞻酋叛乱,川藏会剿,藏兵先克,借索兵费三十万……前督臣奏请赏给达赖,原一时权宜之计,光绪十五年,群起叛逐番官,恳求内附。彼时又未乘时收回……以至愈肆强横,瞻民更遭荼毒,而且威胁各土司。数年以来巴、里塘及霍尔等十余土司,皆以川省威令不行,依附瞻对,该番日益骄恣……寻衅构兵。”[8]15此番言语无非是要将瞻对收归川省,改设流官,以加强川藏通道,便于中央施政西藏。光绪二十二年,瞻对干预朱窝与章谷土司争袭,川督借机将其收回,拟行改流,但朝廷考虑达赖因素,又因成都将军寻机阻拦,瞻对改流乃作罢。光绪二十九年,驻藏大臣上了一份关于川藏情况的奏折,云:“此辈番僧…干预地方,肆无忌惮,若不早为箝制,窃恐一朝尾大,收拾更难……拟请与察木多(今昌都)地方,添设重镇,安驻大员,筹防练兵……庶几外可以慑藩服,内可以靖蜀疆……请驻藏帮办大臣驻扎察木多,居中策应。”[8]8于是,清廷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途径巴塘,因感时局艰辛,奏请暂留巴塘募勇训练,屯垦田地,以增实力。由于其政策过于激进,不能与人虚以委蛇,结果被杀,史称“巴塘事件”。“巴塘事件”后,川督锡良奏派四川提督、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赵尔丰被任命为炉边善后督办,统兵留驻,处理善后。从此,川边改土归流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阶段。
光绪三十二年,川督锡良奏请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充之。赵尔丰曾于光绪二十九年提出“平康三策”:“是将倮地收入版图,设官治理;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山为界,扩充疆域,以保西陲;光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仿东三省之例设西三省,以杜英俄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8]90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改变了川边隶属四川而遥制不易的弊端,极大地推动了清廷对川边的经营和管理。锡良在奏设川滇边务大臣的奏折中道出了这一职位的重要性:“窃查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噶岭,北至霍尔五家,纵横各数千里……如隶属于川,断非设一道员能所统治。现在改流地方……若以道员分巡,一举一动均须于数千里处远承总督命令,深恐贻误边计。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重大……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9]2赵尔丰的川边改革,不单是政治上,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每县设委员一人,管理全县事务,每县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每路设保正一人,协助委员管理地方事务。每路又分为若干村,以百人为一大村,设村长一人;不足百家者合数村或数十村设村长一人;由于人口居住分散,有数家、十数家或二三十家为一村的地方,设小村长一人。村长专管百姓上粮、催备乌拉及递送诉讼传票等,小村长协助村长办事。保正、村长由百姓公举,三年一任,连选连任。如办事不公,得随时予以更换。社会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矿。川边地区多以牧业为主,少耕作。加之原有土司不准民间私垦,所以各处都有许多的可耕荒地。川边垦荒主要以官垦方式为主,官府从内地招募农民出关开垦,途中所需路费由公家发给。垦民房屋,制备农具以及种子耕牛则由公家垫支。垦民收获粮食后,分年尝还。赵尔丰曾在内地招募兵勇,带出关外,一面试行开垦,一面防守地方,寓兵于民。为了扩大垦荒面积,各县不同程度地修建了小型水利工程,有的县还设立了农业研究会,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指导。川边矿产富饶,内地商人以道路艰险,不愿投资开厂;边地民众又怕惊动神山圣水。自赵尔丰川边新政以来,多种矿产得以开发。光绪三十四年赵委托四川劝业道聘请留美工程师刘轼轮到川边勘查矿苗。在基本探清全区的金矿情况后,于宣统元年开始在德格一带开办金矿。还招收附近的民众到工厂学习挖淘砂金技术,由公家按月供给口粮,学得技术后,即自备口粮在矿地开采,“为尔百姓辟一利源……得金只准卖与本厂委员,不准在外偷卖,委员皆照价收买。总期尔等获利,可以养家口,可以有存余。”[9]382赵尔丰还改革川边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将土司、头人、喇嘛多余的土地、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农奴可以领种一块土地,向封建国家纳税,成为国家的自耕农。废除了土司、头人、喇嘛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这些措施减轻了农牧民的负担,使他们能够重新生产和生活。在交通、通讯上,川边地区地势险峻,崇山阻隔,交通运输极为困难,这也成为治理川边地区的重大问题。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由边务经费下拨5000两作为修建沿途的旅店之用。次年,又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请修筑川藏大车路,由川、边、藏分段负责修筑。他在雅州设车务处,制造大车,并派人到陕西雇觅造车工匠和采购架车骡马。川边道路崎岖,路程遥远,往来文书、信息主要靠驿站传递。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策划并着手架设成都至康定的电话线。又架设了从康定至巴塘的线路。宣统元年,赵尔丰又提出在川边设立邮政,指令四川邮局就近速行安设,这不仅可以增加邮传部的收入,也可以方便商民。这些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信息不灵,联系困难的局面。在文教卫生上,由于边民不熟悉汉语,看不懂布告。为了使民众了解改革的各项措施,就必须建立学堂,从语言文字入手。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上奏在打箭炉设立学务局1所,作为兴学的总汇之区,管理筹拨学费,考查规划,采购图书、仪器,派员劝学等事。后来又设立了教育会,作为厅属教育行政的辅助机关。学堂教育中尤以爱国心最为重要,所以以修身、伦理为先,以《三字经》的形式编定了川边地区儿童的启蒙读物。并变革原有落后的风俗习惯,提倡孝敬父母,提倡一夫一妻制,改变丧葬方法。鉴于川边地区得痘症的人较多的情况,赵尔丰先后在里塘、巴塘等地设立了医药局,诊治施药,对患痘症的民众免收费用,使数以千计的病人解除了痛苦。宣统三年,赵尔丰因川边改土归流之功而署理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一职由傅嵩炑接任,继续进行改土归流的善后工作。傅嵩炑统筹川边全局,总结赵尔丰经营川边之策略,奏请清廷建立西康省,以达到卫川图藏御英的目的。
三、对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认识
1.改土归流巩固了中国的西南国防
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狼烟四起,边疆也自然成了列强蚕食的对象。英国通过不断蚕食中国周边邻国的办法来接近西藏地方,不仅从印度而且企图从缅甸侵入西藏,还不断派探险队进入云南探路。之后,英国两次武装侵略西藏,迫使清政府与英印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造成西藏出现严重的危险局面,这一现象导致了毗邻西藏地方的其他藏区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清政府在那里原本就脆弱的统治。
沙皇俄国的野心并不亚于英国,沙皇俄国多次派遣所谓的“科学考察队”进入青藏地区进行探路活动,并且派间谍分子入藏收集情报。其中臭名昭著的沙俄间谍德尔智,就曾以僧人的身份,通过积极钻营,进入僧官系统,拉拢达赖喇嘛联俄拒英,以期分裂西藏。1904年达赖喇嘛出走蒙古,企图去沙俄寻求支持,无不与德尔智的积极活动有关。英俄交窥西藏,使西南局势岌岌可危,清政府为“内固滇蜀”“外杜英俄”,就必须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川边地区加强统治力度,进行整顿,改土归流,将其地直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改土归流的实施,加强了清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内地与西藏地方的联系,防止了帝国主义的触角伸向川边,伸入内地。改土归流后,军队驻扎边地,招抚沿边部落、族人,人们皆愿内附。这对阻止英国企图由缅甸侵入川、藏,实现其独霸长江流域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巩固了中国的西南国防,也遏制了英俄两国的不轨之图。
2.改土归流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这一地区原有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由于边疆地区社会生产水平的不发达,其社会制度往往介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土司世代为土司,土司统治下的属民永远是土民。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将收获的物产大部分上缴给土司,而自己一年的辛苦却所剩无几,这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况且土司借各种机会对土民进行盘剥,“凡民间发生纠纷,审理之前,不论案情如何,原告被告均须向土官送礼,如无钱贿赂土司,即使有理也不能胜诉,案断后,胜者必送谢恩礼,负责亦送赎罪钱,甚有家贫无力出办者,即籍没其家产,折卖人口”[10]92。不少土民因此沦为土司的家奴,供土司驱使。土司对土民任意杀戮,也不会受任何惩罚。川边地区的土司,既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又是寺院集团的保护者。他们共同压迫和剥削其统治下的属民。属民还要为土司提供各种杂役。寺院的农奴,主要承担劳役地租,为寺院种庄园、砍柴、修建房屋和制造日用品。土司制度的日趋没落,严重阻碍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废除土司制度,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土司制度废除后,土民摆脱了长期以来的人身依附,负担有所减轻,提高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改流后,清政府鼓励土民开垦土地,并吸收贫苦的汉民进入原土司地区,给予各种政策的优惠。他们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带进落后地区,大大提高了当地原本落后的社会生产力。
3.废除土司制度有利于改善长期以来不和谐的民族关系
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成为统治边疆民族政策中一整套系统的规章制度。“因鄙夷在夷……未及经营,仅以羁縻之方,官其酋长,作为土司,俾之世守……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7]74各土司之间经常为承袭、土地问题而诉诸战争,土司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以蛮治蛮”,达到各土司势力的基本均衡,从而达到统治目的。这必然形成各土司你争我夺互相兼并的局面,造成各土司地区民族关系的不和谐。清末川边改革之际,瞻对藏官对瞻民横征暴敛,其民不胜其苦,几次奋起反抗。清政府改流瞻对后,“瞻民欢舞出迎”[4]14247。有些大土司在羽翼未丰之前,还能容忍中央王朝对他们的控制和约束,一旦有了资本,他们便有恃无恐,不时发动反抗中央政府的斗争,掠夺附近的汉民作为其奴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清兵两次攻打大小金川,大小金川土司以联姻之计,相互勾结,势力日益强大,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势力均衡,也影响了内地通往西藏的大道。清廷前后发兵四十余万,“官兵前后所杀番兵番民实不下二万人”[11]295,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土司之间的相互仇杀规模巨大,双方都有结盟者,持续时间长,所谓“一世结仇,九世不休”。这种种现象,不仅影响了社会安定,也影响了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改土归流后,官吏由中央统一任免,隶属于朝廷。各个兄弟民族也不会为了上层统治者的恩恩怨怨而卷进相互的冲突之中。人民可以自由往来,不受人身的束缚。德格土司在改流之际,泣曰:“德格地广人稀,窥伺者众,终恐不自保,愿招汉民开垦,使地开民聚,乃可图存。”[4]14245改土归流后,客观上为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
4.川边改土归流是在血与火中匍匐前进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对原有制度、原有统治方式、原有统治政策的调整,都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前提,任何腐朽的、没落的统治阶级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的大舞台,他们必然要在灭亡之际,作一番垂死的挣扎。土司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与地位,煽动寺院番僧对川边改革进行阻挠,如巴塘丁林寺喇嘛破坏川边开垦。赵尔丰平定巴塘、里塘后,诛两土司并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血祭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川边的改土归流,以武力改流者居多,自愿改流者极少,无不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这充分说明了川边改革的艰难。鲁迅先生说,在中国要想改变某一传统状况实在太难了,甚至更改标点符号和搬动椅子都要达到流血的激烈程度。那么,要想在政治上有所更改,其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赵尔丰为了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实施新政,大开杀戒,有“赵屠户”之称,但他推行的改革符合时代的要求。所谓“……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12]35。也许我们对过去的文明破坏得相当严重,但那是因为我们要在旧的文明上建立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文明的缘故。我们如果没有对原有的、传统的旧建筑、旧势力予以清除,就不能建立起崭新的、现代的新建筑和新文化。
5.川边改土归流带有强烈的大民族主义色彩
清政府对川边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以挽救其腐朽的封建统治为根本出发点。封建王朝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制度没有变,对少数民族推行的大民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也不会改变,他们用“蛮”“夷”“野人”“野番”等侮辱性的词语来称呼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个兄弟民族,把汉族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强加于各个民族,实行强迫同化的反动政策,企图达到“以夷变夏”的目的。赵尔丰经营川边“计所收边地纵横三四千里,设治者三十余区,一时皆慑于兵力,不敢抗”[13]12788,就是其高压政策的反映。赵尔丰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推行改流,采取大民族主义的强迫同化政策,以易其俗,而不顾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风俗习惯,坚决主张易其俗:“父母之死……关外蛮俗,则或弃尸于河,而谓之水葬;或焚其尸为灰,而为之火葬;或舂碎其骨,扬洒以喂鸟雀,而谓之天葬。此等恶俗,毫无人理,实堪痛恨……自示禁之后,务宜改此恶习……。”[8]673这些极端的措施,既不能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反而容易激化原有的矛盾。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无论民族大小,人数多少,应该一视同仁。赵尔丰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官僚,不可能正确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他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6.川边改土归流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清末川边的改革是诸多矛盾的总爆发。它似乎起源于偶然的“巴塘事件”,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所支配着的。[12]35各土司常常兴兵作乱,“视王朝德政之盛衰,兵力之强弱,以为叛附”[10]1,再加上土司地区固有的封闭性、保守性,致使它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生产力的传入受到限制,从而使这一地区落后的社会制度得以长期存在,阻碍了历史车轮不断向前运动的必然趋势。西藏分裂势力的不断抬头和列强的觊觎,加剧了川边的不稳定。川边土司的废除,既能消除土司之间的兼并,也能遏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巩固国防。而“巴塘事件”就是川边改土归流的催化剂,它加快了改土归流的步伐。
四、结语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当时一切矛盾的总爆发,它适应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要求,挽救了中国的西南国防。土司制度的废除,也为川边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土司制度退出历史的大舞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仅要看到今日的辉煌,更要铭记昨日的耻辱。我们广袤的国土是大清帝国疆域的继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清的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和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庞大帝国血脉相连。
[1][明]宋濂.元史·百官志七:卷91[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谭合成,江山.世纪档案1895—1995年[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3]傅嵩炑.西康建省记[M].上海:中华印刷公司发行,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4]赵尔巽.清史稿·土司二:卷513[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5]吴丰培.清代藏事辑要续编[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6]赵尔巽.清史稿·德宗本纪二:卷24[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写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9]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赵尔丰传[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10]王承尧,罗午.土家族土司简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11]彭陟焱.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2][德]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3]赵尔巽.清史稿·赵尔丰传:卷469[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朱正平】
The Reaserch about Gaituguiliu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NG Rui,WANG Ming-li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stitute,Xizang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 712082,China)
Tusi Policy is a uniqueway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ule theminority in the border areas.It is in the reunified country,due to the special politic,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border areas,it's an efficient and practicalmode of management for the local nationalities.Since the ancient times,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every dynasty,"Jimi"Policy was used basically in the entire borderminority areas.When the national power was strong and everythingwentwell,the governmentwould try tomake the border areas system the samewith themainland political system.The Gaituguili in Sichuan border ar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fer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that the Qing central government took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dynamics.It is the extrememeasures that the country took in internal disorder and foreign invasion difficult situation,and it has its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in history.
Tusi policy;Sichuan border area;Gaituguiliu;Batang Event
K249
A
1009-5128(2014)17-0065-06
2014-06-14
王锐(1987—),男,山西吕梁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王明利(1984—),男,陕西富平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