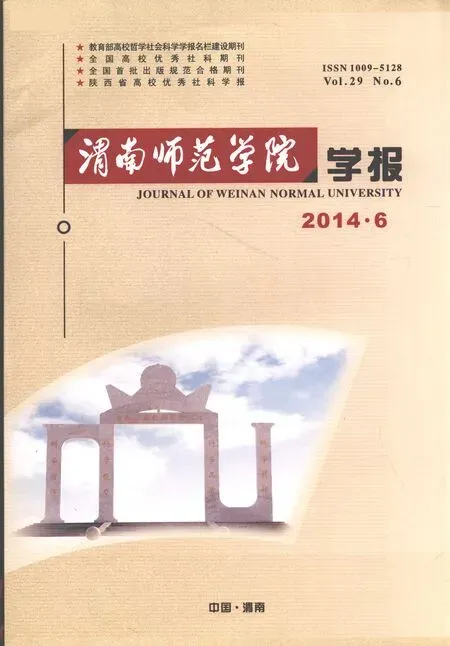艺人悲剧、情礼纠葛与地域文化的交响
——党益民《阿宫》散论
李险峰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714099)
艺人悲剧、情礼纠葛与地域文化的交响
——党益民《阿宫》散论
李险峰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714099)
《阿宫》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创作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集中叙述了秦末以降阿宫艺人的悲剧人生,揭示了艺人生命悲剧产生的根源,即情欲与伦理的激烈冲突,在叙事过程中融入了以方言和风俗为主要形态的渭北地域文化元素,凸显了人性的光芒和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党益民;《阿宫》;艺人悲剧;情欲;伦理;地域文化
《阿宫》是21世纪以来在国内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陕籍军旅作家党益民创作的一部小说,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部小说由13个故事构成,故事发生的时间从秦末延续至今,大致呈现出顺流而下的历史脉络,而且各个故事之间人物关系有或疏或近的牵连,但又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主线,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作的声明:“各章相对独立,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1]181国内影响较大的文学期刊《北京文学》杂志曾将其中的《桃花刀》和《墨面客》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由此可见,《阿宫》并非长篇,而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作者迄今为止出版最晚的文学作品,在笔者看来,它是作者所有小说文本中故事讲得最轻松自如的一部。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就是讲故事的艺术,倘若故事叙述得很“挣人”(作者家乡陕西富平方言,“吃力”“费劲”的意思),那么读者阅读时也会感到很“挣人”,小说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就会被削弱。翻阅《阿宫》,仿佛倾听一部交响乐,阿宫艺人的人生悲剧是这部乐曲的主旋律,其中拨动着情欲与伦理冲破与压制的和弦,点缀着渭北地域文化的多重变奏。
一、难逃厄运:阿宫艺人的悲剧宿命
历史上,从遥远的上古时期直到20世纪初,作为一种行当或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向来十分尴尬。上自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论繁华的都会还是僻远的村落,各个阶层、各种社群都有观赏艺术活动的内在诉求,人们的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艺人。艺人的存在如此合乎社会的需要,按说他(她)们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他(她)们的社会地位也理应不那么卑贱。但事实上艺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他(她)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常常成为被鄙视的对象,甚至陷于死后不能安葬祖坟的可悲境地。社会地位的卑下为他们的生命涂上了暗淡悲凉的色彩,这些常常被蔑称“戏子”的艺人大多沦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作为汉民族独有的艺术品类,戏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至今依然焕发着艺术生命力,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成百上千年里,悲剧几乎是大多数梨园弟子的命运归宿。戏曲艺人俗称优伶,这种带有贬义的称谓源于商周之际,那时的宫廷艺人——倡优“多为侏儒一类生理发育不完的畸形人”[2]14,生为侏儒本已不幸,而利用相貌的滑稽取悦君主就更可悲了,就连司马迁在抨击人文知识分子(“文史星历”)不被当朝眷顾不被世人尊重时也用“倡优所蓄”相类比。[3]399藉此,戏曲艺人的生命悲剧似乎蒙上了与生俱来的意味,他(她)们命中注定的种种不幸在《阿宫》中得到了形象的诠释。
首篇《宫女》中的大娥和小娥可以说是阿宫腔的影子鼻祖,她们“噫咽”“哪噫呀唉”“矣焉也”的唱腔至今还飘荡在阿宫舞台上。秦末项羽纵火烧了阿房宫,掳掠宫女,大娥和小娥只好逃离,慌乱中大娥被熊熊燃烧的门楣烫伤,她们化妆成夫妻逃到乡下借宿朱鹳家,不料身份暴露,小娥被求子心切的朱鹳强奸。为了报仇大娥将匕首刺向朱鹳(事后得知并未刺死),逃到东乡(今富平美原)后大娥为了阻止官军抓走小娥被军爷一刀砍掉了脑袋。得知小娥怀了自己的孩子,朱鹳因竭力阻挡军爷侮辱小娥先被割掉了一只耳朵,后被剜掉了命根子。作为第一个故事,《宫女》给《阿宫》定下了悲凄的情调。第三个故事《桃花刀》叙述了“刀子客”严奎一生中两段刻骨铭心的情爱悲剧。第一段悲剧发生在化州,严奎跟待嫁憨子的桃花一见钟情,在去县城的途中因突遇暴雨,在避雨的草房中情不可遏地走入了情欲的福地,没想到被疑心重重跟踪而来的憨子窥探了究竟,结果桃花惨遭毒手,严奎在深深的愧疚、沉沉的压抑和对桃花绵绵的思念中备受情感的煎熬。化州成了严奎的伤心地,他逃到频阳,遭逢了第二段情爱与生命的大悲剧。他将养女柳叶许配给没有性能力的徒弟石头,柳叶出于性欲的餍足挑逗养父严奎,唤醒了严奎的生命欲望,这对儿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女经历了生命历程中唯一的一次乱伦。为了求得精神的解脱,严奎手刃了柳叶然后自杀身亡。《桃花刀》将阿宫艺人的人生悲剧刻画得惊心动魄,敲骨击髓。
其余的11个故事中,除了《半分地》中的主人公徐跃进算不得梨园弟子——他只是曾在频阳阿宫剧团看过大门,剩下的主人公都是阿宫艺人,而且他(她)们的生命历程或结局皆氤氲着令人唏嘘不已的悲情。墨面客(一支义军)暗探顺子——阿宫腔的实际鼻祖在寻找李闯王的过程中屡遭坎坷,渭南之战中他英勇顽强,结果身首异处(《墨面客》);莲子先沦为娼妓后被警察冤杀(《莲子》);来旺因拒绝独守空房的女人的“一夜情”诉求遭诬陷被革命组织正法(《银簪子》);张青生逢乱世屡遭不测备尝艰辛遁入空门,“文革”中因阻止红卫兵砍伐仓颉庙里的古树被活活打死(《小生张青》);上官云秀因与同父异母的弟弟朱子良相爱并同居,知道真相后投护城河溺水而亡(《上官云秀》);老齐被三根金条折磨得食不安寝,夜不能寐,“大跃进”那阵儿为了把口粮留给儿孙自身被饿死(《三根金条》)。这些阿宫艺人的非正常死亡使小说的悲剧氛围得到充分渲染。其他故事中的主人公生命虽未终止,却饱尝活着的苦涩与辛辣。香草先被金班主强奸,后遭未婚夫田喜退婚,一气之下落草为匪(《观音土匪》);牛娃子“文革”中不惧专案组的淫威坚守正义被打断了一条腿(《牛娃子》);赵喜新婚之夜遭伙计恶作剧颜面扫地,漂亮胆小的新娘子悬梁自尽(《伙计》);曹老师面对为自己生了孩子的情人的接济和捐赠,性情变得郁郁寡欢(《曹老师》)。读罢《阿宫》,我们会聆听到,艺人的生命悲剧汇成了小说的主旋律。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指出:“正如人的伟大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显露出来一样,只有与命运观念相联接才会产生悲剧;但纯粹的宿命论并不能产生悲剧,悲剧的生命决不能消除我们的人类尊严感。”[4]184在《阿宫》中,民间艺人虽然卑微渺小,但大多表现出与命运的抗争;虽然他(她)们的抗争在远强于自己的势力或礼教面前不堪一击,但(她)们悲剧的命运结局彰显了人类的尊严和作者的悲悯情怀,这是《阿宫》存在的价值之一。
二、悲剧渊源:情欲与伦理的激烈冲突
情欲是人类的两大本能欲望之一,正如《礼记》中所指出的那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5]607情欲的生发不仅是人类得以生息繁衍的前提,也是旺盛生命活力的昭示。然而,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的个体存在,情欲的生发和表达又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民族特定社群伦理规范的约束,原本发自自然生命本能的男欢女爱就必须在社会伦理的监督下富有理性地中规中矩地实施,于是“发乎情,止乎礼义”[6]15成为人类情欲生发与表达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人的自然欲望在多数情况下先天性地具有躁动性,面对社会伦理的高压和威吓时,情欲往往不会自觉地遵守规约,总是情不自禁地试图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总是极不安分地期冀从伦理城堡中突围而出。这样,情欲与伦理之间就构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矛盾纠葛,从而酝酿出一幕幕人间悲剧。《阿宫》民间艺人的生命悲剧大多便是由情与礼的对立冲突而酿成的,其中以《桃花刀》和《银簪子》两个故事表现得尤为突出。
《桃花刀》中的严奎生命中经历了两次情欲洪水对伦理堤坝的冲决。第一次主要表现了严奎自然情欲的勃发历程。严奎是个制作皮影的刀子客,他到有着祖传打铁绝活的邵镢头那里去打刀,“发现桃花出落得跟水蜜桃一样。天气很热,又有火炉烤着,桃花穿的蓝布褂后背湿了一片,胸前湿了两片,紧贴在鼓鼓囊囊的奶子上。这还不算,一抡铁锤,两个奶子还上下乱颤”[1]39。此情此景让严奎“心里直发毛”,浮想联翩。更让严奎情欲飞涨的是,桃花在擦汗的当儿,扭头看一眼严奎,她不仅没有对两眼发直的严奎表示出反感生气愠怒,反而“红着脸膛,无声笑笑,露出两个酒窝,满口白牙”。这样,一见钟情的严奎和桃花便在此后严奎各种借口的造访中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后来两人心照不宣地找到合适的理由一起去县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情欲的魅惑下把本已两情相悦的他们诱入路旁打麦场里的草房,伴随着狂风暴雨实现了自然情欲的人性表达,没想到被尾随而来的桃花的未婚夫——邵镢头的徒弟憨子发觉,使得桃花惨遭毒手。邵镢头已将女儿桃花许配给徒弟憨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严奎和桃花的行为显然是有违于当时的伦理规范的,他和桃花“发乎情”却未能“止乎礼义”,造成桃花年轻生命的悲惨结局,也使自己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对桃花无尽的思念之中,背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第二次主要表现了严奎的生命挣扎。避难逃到频阳后,严奎一直孑然一身,正直壮年的他常常受到生命原欲的催逼而倍感压抑,为了实现自我的解脱,他将养女柳叶许配给身患性无能症(严奎当然不了解这个秘密)的徒弟石头,从而激起了柳叶畸形的的生命抗争,屡屡超越伦理规范,多次偷欢,当严奎出于捍卫社会伦理对她予以当头棒喝的时候,她把情欲的抗争推向极致,肆无忌惮地撩拨挑逗养父,刹那间唤醒了严奎久已尘封的生命欲望,跟柳叶行了苟且之事。这种乱伦行为即使在多少有些纵欲主义倾向的当下也难以为世俗所容,更不要说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宋明理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时代。为了求得彻底解脱,严奎自导自演了一出毁灭柳叶并自我毁灭的生命大悲剧。
如果说严奎式的悲剧显示的是人欲与传统价值观的尖锐冲突,这种文学表达的经典笔法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价值坐标,那么,《银簪子》中来旺的悲剧就很值得咀嚼。来旺在对金凤的爱慕(虽然在金凤去县城上中学后,他们的恋情在金凤那里渐渐稀释从而使来旺的倾慕变得有点单相思)与陈炉镇寂寞女人的欲望逗引之间非理性地选择了前者,结果遭到女人的诬陷,被革命组织钢铁般的纪律草率地正法。因此,与其说来旺死于他人的诬陷和组织近乎禁欲主义的戒律的惩处,还不如说死于自己高度的伦理自觉,换句话说来旺是自杀而非他杀。倘若来旺在那个怨妇的挑逗下跟她媾合了“一夜情”——“我看你是个厚道男人,才愿意跟你。你不用怕,咱俩睡一夜,明天你走你的,日后见面谁也不认识谁。”[1]89这样做并不稀释他对金凤的爱恋,也不妨碍他继续寻找心上人,那来旺的人生就不致于朝着悲剧的方向跌滑而去。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来旺的悲剧暗含着作者对前现代伦理价值和现代禁欲主义的思考与批判,渗溢出发人深省的当下意识。
此外,金家戏班的台柱子莲子与革命党人私通脱离戏班只身前往汉口千里寻“夫”,后迫于生计沦落风尘(《莲子》);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张青明知道田班主欲以女儿相许配,却跟曹娟子暗地里相恋并实现了情欲的表达,“奸情”败露后两人私奔,途中娟子遭土匪掳掠自杀身亡(《小生张青》);县剧团的名旦上官云秀与同父异母的弟弟朱子良“发乎情”而未能“止乎礼义”——20世纪50年代初婚前同居是被社会伦理规范所不允许的,当从未来的婆婆那里知道二人的血缘关系真相后羞愤难当投河而亡(《上官云秀》);20世纪80年代初频阳县阿宫剧团的曹老师跟学生刘爽相恋同居生下孩子却一直未领结婚证——在当时乡间的礼法中师生恋是不被社会接受的,刘爽去深圳打工傍了大款,曹老师做了贼似的不愿见人,郁郁寡欢(《曹老师》)。跟严奎、来旺一样,这几个故事主人公的人生悲剧都是因为情欲的生发和实现不合乎他们所处时代的伦理规约所导致的。
三、走向地域:渭北文化的镜像显现
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存在,渭北泛指陕西关中中东部渭河以北、由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过度的地带。阿宫腔是渭北一种古老的戏曲艺术,目前主要存活于富平县,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宫》的作者党益民是一位有着深厚的故乡文化情结的军旅作家,他出生成长于富平,入伍前他在故乡生活了近20年,为他带来较大声誉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表面上弥散着党项后裔的物态景观,内里实则是一部地道的民国富平叙事,曾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的《一路格桑花》虽然属于西藏边地书写,也摄入零星的富平元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域文化酝酿成风格特异的地方艺术,作为关于渭北民间戏曲艺人在历史更替中的人生百态的文学想象,作为一部纯粹的渭北叙事,地域文化的介入和呈现无疑是作者创作的内在诉求,阿宫腔的形态、阿宫艺人的秉性都跟渭北一带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紧密相联。《阿宫》所显示的渭北地域文化主要由方言俗语和民风民俗来呈现。
语言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分支,然而,相较而言,民族共同语更多地体现着语言的本质属性即交际的工具性,而方言则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交际功能,而且是地域文化的显性标志。早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7]33一种方言的形成跟使用这种方言的族群以及该族群的生活环境紧密相联,使用相同或者相近方言的人们,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情趣、气质特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甚至在体型外貌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阿宫》中极富渭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俗语主要存在于人物语言中,基本由方言词汇来凸显。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在骂人时常常涉及男女生殖器,“你还会表演皮影,我看是B影!”中的“B”与“你少避干!”中的“避”在渭北方言中其实是同一个字,读“pi”,声调为弱降,其本字应是“屄”,指女性生殖器。“你能把我球咬了!”中的“球”指男性生殖器,“狗松”中的“松”渭北人念作“sóng”,其本字应是“”,指精液,显然是挖苦被骂者祖上基因劣质或非其父所生,相当于四川话的“龟儿子”。“瓷松”“熊样”中的“松”和“熊”在渭北方言中也读“sóng”,其本字应是“倯”,有愚蠢懒惰等意。这种不堪入耳的骂人脏话一方面显示了渭北人的彪悍粗野,另一方面应视为远古生殖崇拜的遗存。但是,渭北人也有文明文雅的一面:“酒席没散,莲子就感觉肚子不舒服。到了半夜,就开始‘跑后'。”“跑后”是渭北人对拉肚子的委婉表达,因厕所一般建在后院,接二连三地往后院跑,肯定是拉肚子。“狗日的,敢跟老子动手,活泼烦了你!”[1]85“泼烦”在渭北方言中指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其中的“泼”本字应写作“颇”,该词富有文言色彩,是程度副词,相当于“很”“非常”等。此外,憨厚朴野的渭北人的方言俗语还在委婉中带有些许幽默,“你看你那鞋,大舅二舅都跑出来了”,“大舅二舅”分别指大拇趾和二拇趾。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显然意识到了方言词汇在凸显渭北文化特色中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为了方便那些对渭北方言比较陌生的读者,他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在方言词后加上括号,然后在括号里予以解释,如“砌墙当然没麻达(没问题)”“两人边干边谝着闲传(说闲话)”。二是先用“渭北农村把××不叫××,叫××”这样的句式引出方言俗语,随即对这一方言产生的背景或原因作出猜想式的诠释。如“渭北农村把嫁女不叫嫁女,叫‘打发娃'。”“在渭北农村,结婚随礼不叫随礼,叫‘行门户'。”“渭北把赴宴叫‘吃汤水'。”尽管由于作者不是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专家,在文字符号的使用上难免有所差失,但方言词的自觉运用无疑对凸显渭北历史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学史上,倾倒于风俗画的大作家不乏其人。因为风俗是与社会发展,与民族性格和精神密切相连的。从风俗的变化,可以发现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变化的轨迹。”[8]203就地域文学创作而言,欲显示浓重的地方情调和独特的小文化环境,除了无可替代的方言之外,民风民俗的叙述描绘是又一个必须且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国小说艺术的一大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应与中国幅员之辽阔、民族之众多、文化之多样相关。在《阿宫》里,富有渭北情调的风俗民情比比皆是。比如《墨面客》中对顺子以补锅作掩护挑着担子游走渭北时所携带工具及补锅准备过程的展示;《桃花刀》中对清末关中刀客随身携带的“关山刀子”模样的勾勒,对“刀子客”严奎制作皮影所使刀具和乳驴皮的描摹,对严奎高超的选皮、泡皮、刮皮技艺的精雕细刻;《莲子》中对阿宫名旦莲子活灵活现的千般眉眼儿和行云流水般的手上功夫(这里表面上摹写莲子的高超演技,实则是阿宫旦角眼神和手上功夫的汇总)的刻画;《银簪子》中对渭北名特产琼锅糖制作过程的介绍;《牛娃子》中对皮影演出的基本套路及操作技巧的罗列;《上官云秀》中对青衣表演动作集束式的描绘;《三根金条》中对阿宫剧团乐器的说明;《伙计》中对渭北赴宴风俗、婚俗的叙述等等。上述种种风俗民情汇成了一幅渭北的“清明上河图”,加上简洁明快的语言,很容易叫人联想到汪曾祺小说的风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民风民俗和作坊工艺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从文明演进的规律上看也只能如此,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突出症候就是对地方化、民间化、民族化的不断消解。
[1]党益民.阿宫[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
[2]张燕瑾.中国古代戏曲专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李学勤.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8]曹文轩.古朴、明净的风俗美学[M]//温儒敏,姜涛.北大文学讲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詹歆睿】
The Integration of Artists'Tragedies, Their Contradictory Minds and the Local Culture——On Dang Yimin's E Pang Palace
LI Xian-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99,China)
E Pang Palace,written by Dang Yimin,winner of Lu Xun literature scholarship,narrates the miserable lives of the artists in E Pang Palace,showing the origins of the tragedies of the artists,that is,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artists'passion and their ethics.During the narration,the local culture in the form of dialect and unique customs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Weihe river is presented to the readers.
Dang Yimin;E Pang Palace;the tragedies of the artists;passion;ethics;local culture
I206
A
1009-5128(2014)06-0051-05
2014-01-02
渭南师范学院2013年人文社科育苗项目: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关中叙事研究(13SKYM030)
李险峰(1968—),男,陕西富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林皋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