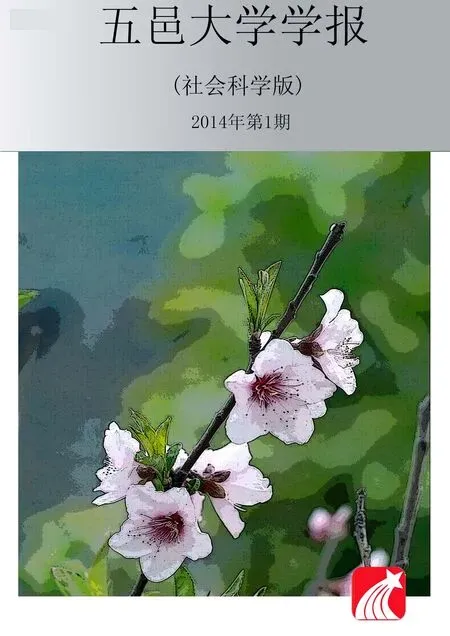论容闳西学东渐的价值理念及实践
马 波
(广州大学 华软软件学院,广东 广州 510990)
容闳为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生于1828年11月,卒于1912年4月。关于容闳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国内学者对容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容闳阶级属性的讨论上。尽管当时也出版了一些容闳的传记,但只是通俗读物。改革开放后,对容闳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有关容闳研究的成果表现在:其一,有三部容闳的传记相继出版, 即顾长声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李喜所的《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刘中国和黄晓东的《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 年),并依次都有新突破;其二,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发现,关于容闳的研究论文已达百余篇;其三,1998年和2004年,珠海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科教兴国》论文集, 对容闳的研究有了新进展、新成果。容闳是近代华侨爱国典范, 如何将容闳的爱国思想研究引向深入, 提升其学术水准, 是笔者选题的目的所在。
本文主要探讨容闳在留学事业有成的情境下毅然回国推动祖国近代化进程的相关活动,及其内心世界和精神品质,同时进一步论证容闳坚定践行“强国梦”的思想基础和客观依据。选题与研究对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及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把握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祖国至上,“强国梦”支配着容闳一生的行为方向
容闳是中国近代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首位留学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我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在美国学习8年,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其遭遇、感悟催生了他振兴祖国的“强国梦”。1854年回国后,自觉参与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做出了积极贡献。
容闳从7岁入西塾起, 先后将近9 年在澳门和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 接着赴美国留学8 年, 接受长达17年的西方教育。对于西方文明,容闳积极学习和融入,如剪发易服、入美国籍、娶美国妻等,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冲淡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曾这样吐露心声:“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1]31对于容闳的爱国行为,其美国友人特韦契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2]15梁启超在1903 年访问美国时亲自拜访了容闳,称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2]46
从封闭落后的中国走出去的容闳,“强国梦”是他一生奋斗、前行的精神动力。
1847年1月,容闳随布朗牧师一起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远赴美国。在异国他乡,容闳对美国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光怪陆离的西方生活感到惊奇和钦佩,与此同时,他时时记挂着被侵略的祖国及被西方列强烧杀淫掠的同胞,常常夜不能寐,每念及祖国与同胞的不幸遭遇,辄为之怏怏不乐。他说:“盖既受教育, 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遂觉此身负荷极重。”[1]31对比落后的祖国,美国的生活犹如天堂,而这更激起容闳刻苦学习先进知识、立志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决心。他说:“尚忆在第一年级时, 读书恒至夜半, 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2]21在孟松中学毕业后,1850年他报考耶鲁大学,但当时学校资助他学习的期限已到,学校相关组织提出条件,如果他大学毕业后从事传教士职业,校方可资助学费供他深造,并希望他在合同上签字。毕业做传教士,这与容闳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23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他断然拒绝了。通过半工半读形式和朋友的帮助,容闳终于如愿考上了耶鲁大学。容闳入大学时英语水平一般,但他通过刻苦学习,到大学二年级时,他的英语作文竟连续获得一等奖,博得师生们称赞。
在美国的学习岁月,可以说是艰苦奋斗的8年。异国的环境、文化、制度、教育等使容闳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经过博览群书的学习,他认识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需要先进的工业文明,更需要掌握这些文明知识的人才。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舍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和发展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决心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
二、西学东渐,设法推进祖国近代化
西学东渐,这是容闳构筑“强国梦”的重要途径。容闳回国后,从实业和教育两方面开始拯救国家。
(一)忍辱负重,推动实业强国之策。容闳深感祖国的落后在于工商文明的缺失,政府应当大力促进实业发展。容闳于1854年学成归国。由于他没有经过科举考试,没有获得功名,因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更没有什么影响力。但为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他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的海关、司法等机关打过工,做过书记员、译员等职业。根据晚清社会现状,他选择通过洋人影响政府官员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心中蕴藏的治国蓝图,但都未能如愿。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 这为容闳施展“西学东渐”志向提供了机会。经李善兰等好友的引荐,容闳终于进入洋务派大臣曾国藩的视野。1863年,得知曾国藩拟设立一规模较大的“ 西式机械厂”,容闳建议说: “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1]98。容闳的思路深合曾国藩之意,他也因此受曾国藩托付前往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 他经过多重艰难把所订购的机器运到上海, 作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江南制造局是专门制造枪炮、弹药、火轮等军工产品的工厂。该厂的选址,起初也是容闳和华若汀、徐雪村等人共同研究, 选定在上海高昌庙建厂的。在容闳的建议下,该厂附近还建立了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等机构。1873年, 容闳又受托订购美国先进武器——格特林炮50门运送回国。此外,洋务派代表郑观应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是在容闳的支持和帮助下而建成的。
对于水运发展,容闳也有着独到的思考。容闳曾经乘船去茶区调查,通过途中对于长江水道的观察,他提出了希望通过开发长江水道来促进交通发展的设想:“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 得完全行使其主权, 则扬子江开浚后, 其利益实未可限量, 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3]1868年,容阂还积极倡导组织—合资汽船公司,公司完全由中国人和本国资本举办。建议虽未获清政府许可,但4年后李鸿章按此思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不仅如此, 容闳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等。1896年, 容阂提出应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的设想。他为此草拟计划,制定章程,列出政府为建设银行所预筹资本的数额以及用项。计划内容详备,有可操作性。为更好地实施计划,他还将美国1875年有关银行的各种法律译成中文, 以备参考。1898年,容阂又向清政府提出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计划,光绪帝也给以支持。但由于清政府腐败,利益集团相互倾轧,最后这些计划都付之东流。
(二)殚精竭虑,践行教育救国之志。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是他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和步骤。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痛下决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32由此,容闳回国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教育救国思想。
在广州,容闳亲眼目睹了清政府草菅人命、屠杀无辜,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反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1860年11月, 容闳与曾兰生及两位美国教士一道秘访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在天京,他向接见他的干王洪仁玕进献了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七条建议”。[4]在这些建议中,他在第二、三、六、七条专门论及创办军事学校和各类技术学校的重要性, 体现了鲜明的教育救国思想。但此时的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正濒临于覆灭之际, 容闳的“七条建议”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幼童留美“教育计划”,是容闳教育救国活动最为出彩的一笔。早在他留美时,他心中就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 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5]容闳为实现“教育计划”愿望,前后奔走呼唤16年之久。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斡旋和游说下,曾国藩最终答应领衔上奏容闳提出的4条计划。1871年8月, 清廷采纳容闳派遣留美学生的建议。不仅如此, 容闳还在家乡积极倡导办学思想, 并于1873 年正式建成“容氏甄贤学校”。
“留学计划”的实施也是不平坦的,幼童留学时间原定以15年为期,但不久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以批评幼童“抛荒中学”、“腹少儒书, 德性未坚”[6]为借口, 决定从1881年8月21日起全部撤回官派留学生。此次留学计划最终破产,但这些早期幼童留学生,日后也在不同的行业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幼童留学计划”开创了近代中国留学的先河,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举。
三、革故鼎新,探寻社会发展新途径
容闳回国后,积极推行他的引进“制器之器”、“师夷长技”计划。但这些计划,无论是建银行、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等,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无情现实的刺痛下,容闳只得另辟蹊径,探寻新的救国之路。
(一)与时俱进,维新改良。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人开始图谋变法自强。早在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容闳就曾通过多种方式与洋务大臣张之洞取得联系,发表救国之策。1895年夏他抵达上海,先后提出“聘用外人”、“设立银行”、“修筑铁路”等建议,但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政府当局的应有重视。无奈之下,他摒弃借助“洋务”的“救助中国之心”[7], 改变“求知当道, 游说公卿”的救国途径。既然清政府无可挽救,只有另谋出路, 他认为“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才是中国强国富民的应有之策。容闳的新政策内容带有明显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色彩,得到了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高度认同。对于容闳的新思路,不仅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详细介绍其内容,同时,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容闳也积极支持康、梁, 在他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第一天, 容闳亲自到场支持。容闳赞扬光绪帝,称其为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明士, 同时还与维新派成员频繁往来, 支持和参加维新运动, 他的寓所几乎成了康、梁会议活动的场所。由于维新变法触动了统治阶级顽固派的利益,康、梁主持的变法运动仅坚持了103天便被慈禧发动的政变扼杀了。危急关头,容闳通过疏通多种关系,保护变法的同志,如他曾致函英人李提摩太,请求营救康有为、梁启超。
(二)大势所趋,走向革命。《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昭然若揭,这促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高涨。在族弟容星桥的介绍下,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开始关注和理解革命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维新派唐才常在上海邀集社会名流,召开“ 张园国会”,组织新政府,成立自立军,拥戴光绪皇帝执政。在会上容闳被推举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容闳为此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表达了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愿望。但不久,容闳等参与建立的自立军在武汉起义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被杀害,容闳遭通缉逃至香港。这次起义成为容闳走向革命的开始。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在逃往日本的“神户丸”船上,与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首次相遇,容闳对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极为钦佩。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继举行的起义,1909 年二三月间,容闳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中国红龙计划”,计划筹款500 万美元、购买10 万支枪和1 亿发子弹。1910年2月容闳致书孙中山,正式提出“红龙计划”的具体步骤:(1)向银行借贷150万到200万元作活动基金;(2)成立一个临时政府, 任用有能力之人,以管理占领之城市;(3) 任用一个有能力之人以统率军队;(4) 组训海军。[8]容闳还多次安排孙中山与他的美国朋友荷马李和布思见面、商谈,并写信督促落实计划内容。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和借款没有成功。
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在病中的容闳得到消息,接连写下多封信寄给国内朋友,庆祝革命党推翻封建帝制。在信中,他对新政府的施政提出了由衷关切,如告诫革命者“互相之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 紧紧团结起来”,“不应该互相纠纷, 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谴责袁世凯“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 指出“掠夺成性的列强”并未放弃“干涉”和“瓜分”中国的政策[9]。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致信容闳, 称赞他对国家的贡献,并邀其回国共商国是。但容闳已昏迷不醒,于1912年4月病逝。他临终前还嘱咐两个儿子放弃美国的事业, 回国参与建设。
容闳自留美归国后,在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为践行“强国梦”做了多种尝试和努力。纵观容闳的人生历程,充满着颠沛流离,坎坷崎岖。他本可拥有和谐、幸福、安稳生活和工作机遇,但为实现人生梦想,他宁愿舍弃。容闳回国后,因参与洋务活动不辞劳苦地来回穿梭于中美之间,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在上海、香港等租借地商讨维新、革命大计;他还成功解救了大批惨遭迫害的海外无辜华工,维护了华人尊严。这些都凝结着容闳的“祖国情”、“强国梦”。在屡遭挫折时,他的祖国至上爱国理念和行动是坚定不移的,也是不可西化和被撼动的。欲知大道,必先治史。容闳西学东渐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主要归因于清政府的封闭、腐败,但与他不能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思考问题也有一定关系。容闳的爱国精神为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容闳.容闳自传[M].恽铁樵,徐凤石,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2]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沈潜.试论容闳的现代化思想品格——以《西学东渐记》为中心[J]. 历史教学问题,2009(04):24.
[4]何雅伦. 坐失良机——从洪仁玕与容闳在南京的会晤谈起[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02):6.
[5]王忠萍. 容闳作为边缘人介入晚清主流社会的学理考察[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3(06):4.
[6]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出使美日密国大臣陈兰彬折[G]//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165.
[7]刘学照.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略议[J].鄂州大学学报, 2006,13(04):32.
[8]陈申如.容闳与孙中山[J].学术研究,1991(06): 42.
[9]罗福惠.边际人的报国心——容闳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新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38(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