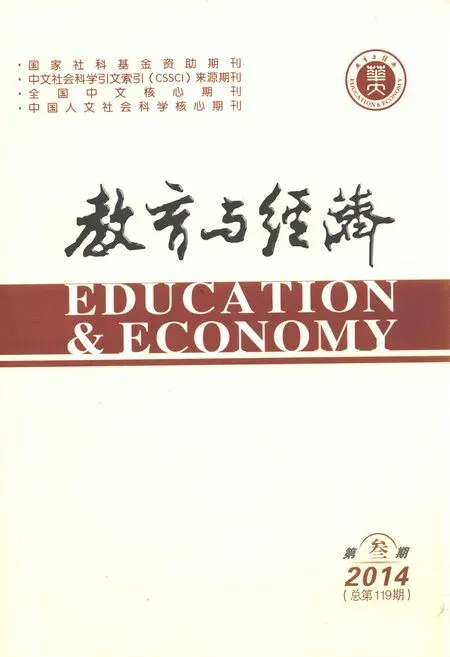农民工子女学校“转制”的产权分析:以上海为例
宁本涛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农民工子女学校“转制”的产权分析:以上海为例
宁本涛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200062)
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公平接受教育问题是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上海市政府2008年策动的162所农民工子女小学“民办公助制”试验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致命的教育产权问题隐患,需要积极应对。首先“转制”学校一刀切式的“民办非企业”法人架构,既不是纯公益组织,也不是纯营利性企业组织,导致学校实际办学性质定位模糊,“回民”还是“转公”,进退两难;其次“转制”前后各种学校资产产权归属的界定与划分还不够清晰,容易滋生国有资产流失及各种产权纠纷风险;再者“转制”学校的权力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未来发展方向也充满变数,不免引发人们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不稳定预期和各种办学短期行为,师生正当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农民工子女学校;“民办公助”制;产权明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外来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规模不断扩大,如上海现有2301.9万人常住人口中897.7万为来自外省市的常住流动人口,其中进城务工随迁子女达到近50.17万的超大规模[1],因此,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公平接受教育问题便成为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上海市政府2008年策动的162所农民工子女小学“民办公助制”试验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既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但也存在着致命的教育产权问题隐患,需要积极应对。
上海农民工子女小学的大规模“民办公助”式转制改革肇始于上海市教委2008年启动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三年(2008—2010)行动计划。该计划侧重在公共教育资源确实不能满足随迁子女教育需求的城郊结合地区,将符合条件的“简易学校”经过办学设施改造后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政府委托其招收随迁子女。计划共审批设立162所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同时关闭存在安全隐患、办学条件不合格的农民工子女学校100所。对新审批的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民办小学,上海市政府给予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政府还委托这些民办小学招收随迁子女免费就读,并根据学生招生人数给予基本办学成本补贴。2008-2010年,上海市、区财政共投入10余亿元,用于这些民办小学的办学设施改造和基本成本补贴。截止到2010年,上海各区县共投入资金2375万元,为全市162所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配备了标准图书室,增配了体育运动器材。
从80年代末的“备案制”简易办学、到2003年的“审批制”办学、再到2008年至今的“民办公助制”办学,上海这种由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转制模式”无疑
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在全国率先基本建立了规范的管理结构,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致命的教育产权制度隐患。首先“转制”学校的性质定位非常模糊;其次“转制”前后学校各类资产产权归属需要进一步明晰;再者“转制”学校的自主管理及师生权益保护还不够完善,学校未来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也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这些基本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不断危及“转制”农民工子女学校自主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带来农民工子女教育利益相关者对政策预期的不稳定和短期行为并诱发各种办学纠纷与风险。
一、“转制”学校的“民办非企业”法人定位模糊
上海“民办公助”式“转制”变革使当地农民工子女学校统一划归为“民办学校”,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农民工子女学校从“私人办学”到“法人办学”的华丽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转型而非实质意义的转型。
根据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我国的法人机构一般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1999年民政部发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办法》,民办学校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法律明确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但是,民办学校在民政部门注册时,根据政府有关法规被硬性界定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超越《民法通则》提出的新概念。从该规定来看,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组织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具有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其盈利只能用于其组织本身的发展和自身服务系统;提供社会服务活动,可提供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即对不特定的人和群体提供公益性服务;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出资人为非政府系统。根据上述特征的描述,在我国的现行制度框架中,民办学校被划归民办非企业单位中。这主要是来自对民办学校的一刀切的非营利性规定。尽管有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概念,但在实际运行中就民办学校税收、教师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重要问题并未制定与之相应的政策,相反只按企业的标准执行,而并未按“非企业”对待。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将我国的民办学校统一划归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这使得民办学校既不属于事业单位也不属于企业,而且《民法通则》中并没有此种性质对应的法人类型,这就使得民办学校不伦不类,地位十分尴尬。这直接造成了民办学校性质上的“非营利性”与实际运行中大多数学校“投资经营办学”的矛盾。如今,无论是政府决策者和教育行政部门还是民办学校都对这一矛盾持回避态度,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希望用非营利性的政策框架来进行统一管理,但实际上包括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内的大多数民办学校则将自己的非营利性避而不谈而在实际运行中满足自己的营利诉求。
此种法人制度安排直接影响了“转制”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未来自主发展。首先是不利于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多元化筹资办学的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出资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这对投资办学是有吸引力的,但这一规定却对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教育经营(主要是校长和教师的人力资本经营)非营利学校十分不利。由于民办学校的统一“民办非企业”法人性质,类型及分类并不明晰,这使得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和机构陷入“灵与肉”的纷繁纠结之中,让他们会对自己的投融资行为和教育经营行为有所顾虑,担心最后自己的投融资资产和心血付出会被从中抽取回报或直接纳入或外溢到他人腰包。此种担心合情合理,从这方面来讲,民工民办学校的法人不合理定位已经影响到了学校未来发展的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加盟和积聚。
其次,是不利于政府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由于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定位模棱两可,也使得政府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政府想要加大对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扶持力度,比如加大资金投入、基本设施改造与建设并给予其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或者给予教师民办教师同等的待遇。但另一方面,政府又同时担心最后这些投入都会落入到非政府出资人、举办者及管理者的私人口袋中。
笔者建议,取消当前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民办非企业”这一似是而非的法人性质硬性界定,重新进行分类治理。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温州地区的可贵探索,将“非营利性的全日制民办学校按照民办事业单位法人进行登记,管理营利性的全日制民办学校按照企业法人进行登记管理”,并明确“民办事业单位法人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企业法人由工商部门登记管理”[2]。
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应重点做好对非营利性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扶持与监管。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事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措施是建立有效的学校董事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中,董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全面负责学校的经营管理活动,出资人将自己投入的办学资产交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则拥有学校资产的支配权,并决定校长的聘用、奖惩及解雇。校长受聘于董事会,接受董事会的领导,作为董事会决议的执行者,在其授权范围内负责学校的具体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保证学校工作有序进行。同时,设立独立于董事会
的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的决策操作和校长执行行为的监督,以防止民办学校的失范行为。最终实现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和平衡。同时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发挥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区、毕业生、社会贤达等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形成学校内部权力纵向下移和横向分配平衡相结合的制衡体制。[3]
二、“转制”学校前后的产权归属有待进一步明晰
如何明晰“转制”学校的各种教育产权归属,是关系到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利益博弈的重大问题。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我国农民工子女学校是教育被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尽管农民工子女学校提供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服务,但是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是教育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混合物,是教育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它的生成不可避免地带有生产服务性、经营性和商业性。
首先,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私人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在转制过程中必须明晰。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私人举办的农民工子女小学,由于在转制过程中选择继续办学,因此原有资产未被评估和补偿,而转制之后举办者无法获得任何回报现象大有人在。比如,上海S区S小学学校由安徽籍人士创办于2001年,转制之前有小学生700名,中学生1500名。2009年转制为民办农民工小学,举办者聘任的校长继续留任。现有学生2600人,分为51个班。教师103名,本地人很少,每年到手收入为3万元,可评中高级职称。转制前创办者投入2300万改善办学条件,建设教学楼、运动场等,转制时政府投入50万元,由于举办者继续办学,政府未对原有资产完全赎买。给予的年生均经费中,规定70%得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其余部分得拿发票到教育部门支取,没有考虑到校舍租金的问题。这为今后学校终止时的教育产权纠纷埋下伏笔。根据《促进法》当地政府应根据民工子弟学校举办者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状况和学校声誉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和精神鼓励。
其次,政府、社会公益组织或公司为农民工子女校转制前后投入或捐赠资产的归属及处置也需要明晰。在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续存过程中,这些资产的归属应该属于学校法人所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遇到学校拆迁、关闭或转卖,政府或公司投入的资产应该归政府或公司所有。捐赠资产的处理可参照美国的做法。美国的长期实践中,捐赠是按契约形式处理,无论是现金还是物品(服务例外,因为无法收回)如果捐赠者无要求,则受捐者自主处理。如果捐赠者有要求,则按约定办理。常见的有:指定使用用途或指定时间限制;如未按所指定的要求,要退还捐赠者或向捐赠者申请更改要求。为此,政府、社会有责任监督“民办公助”类型的民办民工子弟学校建立全覆盖的学校资产管理制度,并建立相应的学校资产增值评估制度,以防止各种资产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与滥用。
最后,是对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中的个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合理回报及奖励问题,这是理顺政府与当前农民工子女学校关系的一个最为敏感问题。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虽然是民办非企业法人,但它客观上提供了部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纯公共服务,但并不能指望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举办者和经营者都是活雷锋和慈善家。没有稳定的合理回报预期,是让投资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举办者不能有长期打算,进而办学不希望加大投入的根本原因之一。为提高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多元化融资水平和校长及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笔者建议应当参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给予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私人投资者和举办者正当的合理回报。合理回报的具体额度由举办者和学校法人根据学校发展现状自主选择,但必须公开并接受政府与社会的监督。同时,政府应给予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校长和教师给予必要的实质性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
三、“转制”学校内部治理与师生权益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完善“转制”学校的内部治理与师生权益保障机制,首先要理顺“转制”学校与政府的政校不分关系。由于政校不分,学校责任主体实际依旧是政府。学校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承包或租赁的关系。学校赢了,皆大欢喜。若是亏了,还得由政府托盘,学校本身并不承担责任。转制学校并没有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人格化法人实体。如此,“转制”学校的组织结构依然按照公办学校的管理办法,校长并不是由董事会投票选出,而是政府选聘任命,因而校长不是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实际上还是直接对政府负责。校长缺乏微观监督评价机制,在有限任期内,校长的办学行为就极容易短期化。因此,“转制”学校应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最终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办学主体。
其次,要理顺“转制”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不断强化教师权利及发展保障体系建设。现行的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管理实施的是一般教师聘任劳动合同制,教师的人事关系不同于同行的公办学校教师的“事业人事档案制”而施行“人事代理制”,无法解决老师们的户口落户及住房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在学校存续之间与公办学校教师的福利待遇似乎差异不大,但在学校
终止或解散后却面临非常棘手的教师安置与补偿问题。根据劳动保护法,教师们非正常离职要接受所在学校的法定补偿(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为每满一个年度支付一个月,最多不超过12个月。)学校自身也因此面临很大的未来巨额资金应对风险,为此,转制民办学校应平时预留出一定的教育发展基金以备不时之需。
再者,要理顺“转制”农民工子女学校学生与国家而非政府的关系。流动人口子女公平受教育权保护问题是制约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一个掣肘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社会难题。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实施“关注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小学教育的计划”(PRONIM)和“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跨文化教育模式”,为小学一年级专门制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小学教育课程总体设置与教学指南。农业季节,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在法国,16岁以下的孩子,无论国籍是否在法国,都能在法国享受到与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法国人认为,赋予每个孩子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对国家来说是最有效率的事情,否则,将导致犯罪率和失业率提高等社会不利因素,付出更大的代价。
上述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少数弱势群体大都采用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模式,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义务教育公共产品性质的一种尊重和承认,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够通过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切实保证一国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需要的均衡发展,并为每个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说到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是“权利”公平的问题。在当前基础教育“户籍管学籍”体制下,由于农民工子女流动频繁和随意,很难为其建立一套持续和常规的学籍档案,致使学校和有关部门难以清楚地掌握农民工子女的流动去向,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就学监控,进而导致其学籍管理的混乱和无序,不利于从整体上确保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实现。为此,建议尽快建立专门的全国性农民工子女电子学籍联网档案。
此外,随着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时限的延长,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教育问题如公平考试权问题开始凸显,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相关政策的不健全,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初级中学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后,他们需要作出两种选择:要么中断学业留在城市中自谋出路,要么回原籍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对于在城市“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子女来说,再返回原籍已经不太现实,他们既是城市的“边缘人”,又是家乡的“异乡人”;既难以进入城市的优质学校,又无法融入家乡的教育和升学系统,只能成为身份模糊的“夹缝中人”,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格特点。
面对社会压力和民主呼声,尽管我国政府也不断推出相关政策文件,以期“保障农民工子弟的权益”。但是,这种保障在实际中却成为一种变相卸责,将本来由国家保障的农民工子弟的公民权,变成了地方保障的“市民权”问题。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主要是将国家层面上的“公民权”问题转换成了城市层面上的“市民权”问题,将”国民待遇”问题转换成了“市民待遇”问题。
当然解决农民工子女身上的包括“异地高考权”在内的受教育权不公平问题的关键是“绿色高考制度”的建立。加快招生指标分配办法改革,综合考虑各省受教育人口基数、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让各地的高考录取率特别是重点大学录取率大体一样,从而从根本上消解异地高考的内在动力。此外,加快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及其户籍结构的制度变革。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存在,而且今后较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将户口一分为二,公民被分成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大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的利益群体,城乡被隔离开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不得自由迁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民进城打工,获得了一种新的“农民工”身份,但这是一种未受制度认可的“半合法”的身份。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民工”身份,国家都跳过了公民身份的平等性要求,人为地构造出一种新的身份来实际地分享教育资源。笔者认为,未来体制保障方面,国家应适时启动改革现有的城市和农村隔离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保障方面,权利机关应从法律上确立农民工平等的公民身份,从而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各项教育权利。国家要制定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指导纲要,并切实指导地方、学校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文件和行动指南;行政保障方面,纵向上应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加强流入地教育主管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横向上应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1]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8898/no de28924/node28925/u8ai28563.html
[2]董圣足.温州新政:区域民办教育制度创新的典范[J].教育发展研究,2011,(22):1-6.
[3]胡卫.促进民办教育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J].上海教育, 2010(,9):60.
责任编辑 范先佐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job match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survey data from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We find that job mat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alary and job s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Definitively speaking,over-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starting salary of college students,while major match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tarting salary but promotes to raise present salary of college students.The students with matchable ability have higher starting salary than those with low ability,but ability match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resent salary of college students.The job of students with over-education has poorer stability,and their job-hopping probability is higher.College students,whose jobs strictly match to their majors,have higher job-hopping rate than those that don't match.And the job-hopping rate of students who have stronger ability than the job need i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who have lower ability than the job need.Therefore,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aising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promo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government,employer,colleges,and etc.participation,eventually employment match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raised.
Key words:job match;quality of employment;salary;job stability
责任编辑 叶庆娜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of the"Transformation"of Schools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NING Bent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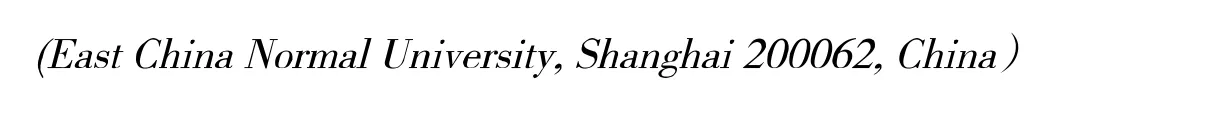
How to ensure that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receive education fairl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2008 takes 162 migrant children schools as pilot schools implementing"government funding for private school"system,and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However,at the same time,there exists a vital hidden trouble on education property.Firstly,"private non-enterprise organization"kind of legal person framework should be converted,because these schools are neither pure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 nor for-profit business organizations so that it leads to fuzzy positioning on the character of running these schools.To be private schools or public schools,it's really in a dilemma.Secondly,the definition and division of property ownership before and after transformation is not distinct which easily leads to the loss of state-owned assets and risk of property disputes.Lastly,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ransformed schools is unsound,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s also uncertain,which may causes instable expectations of educational policy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all kinds of short-term behavior, eventually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also be difficult to get effective protection.
schools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government funding for private school"system;distinct property rights
F08;G40-054
A
1003-4870(2014)03-0053-06
2014-05-15
上海市哲社及教科重点课题“教育产权的市场运行与法律保护”(课题编号:A1115)。
宁本涛,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教育政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