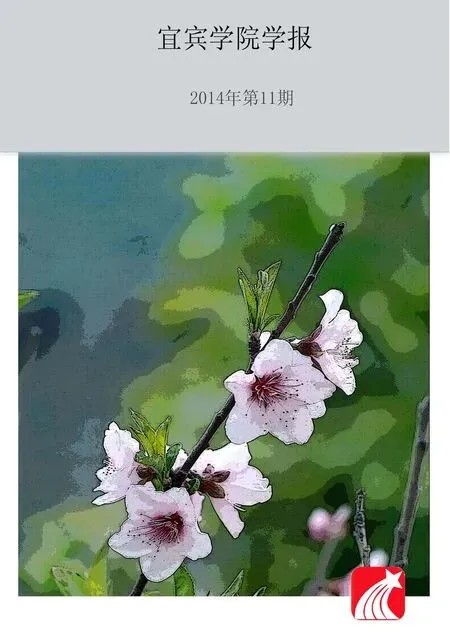梅山文化区域民间信仰的社会学分类与思考
陈 彬
(湖南师范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b.统战部党外人物工作研究(湖南)基地,湖南长沙410081)
梅山文化区域民间信仰的社会学分类与思考
陈 彬a,b
(湖南师范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b.统战部党外人物工作研究(湖南)基地,湖南长沙410081)
星火村至今仍存在着如“庆菩萨”仪式、树神崇拜、“寄子石”现象、“打箭碑”、丧礼中的唱挽歌与做道场习俗、祭祖风俗等民间信仰现象。这些现象若借用韦伯的“理念型”方法可梳理并归纳成风俗习惯型、集体压力型、个体自愿型三种类型,这些理念型方法都是对现实的信仰实践所作的一种抽象提炼,活态的信仰实践与这里界定的“理念型”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各种“理念型”之间的差异也被不同程度地凸显出来。这种社会学类型的划分可以告诉我们,虽然都可以被称作“民间信仰”的文化事实,但它们实际上具备不同的信仰特征,具有各异的信仰结构,并包含不同的社会学意涵,因而我们的研究必须要仔细区分,谨慎分析,慎下结论。
梅山文化;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型;集体压力型;个体自愿型
湖南中部地区属于史载的古梅山文化区域,这里的居民据考证是上古蚩尤部族的嫡裔,古梅山峒区域是上古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1]。在北宋开梅山之前,这里世代居住的苗、瑶两族已经离世隔居、不服王化几千年。据《宋史·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今湘潭)、南接邵(今邵阳)、其西则辰(辰溪)、其北则鼎、澧(今常德、澧县),而梅山居其中[2]。若按照这个四抵界址,翻中国地图就一清二楚,就是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沅水、湘水之间成西南——东北走向的资水流域——雪峰山区,土地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古称为梅山地。“蛮”——作为中国正统的北方汉民族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因此世居此地的苗、瑶两族在历史上被统称为梅山蛮。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宋王朝收复梅山,并设置新化、安化二县,对梅山地区进行了推行教化、发展生产等有效的开发。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大部分苗、瑶两族向西、向南的迁徙,梅山地区成为了多个民族杂居的区域。但因古梅山地区山高林密,交通阻隔,远离中原文明几千年,这里早已生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别具一格的梅山文化①。本次调查的村落地点就位于梅山文化中心地域的新化县,这里至今仍然遗留着众多神秘、独特的民间信仰现象②。本研究基于对处于梅山文化中心地域一个村落的田野调查,梳理并归纳出若干民间信仰的社会学“理念型”,最后就“民间信仰”的定义、民间信仰与现代性及民间信仰发展中多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关系等方面提出若干研究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 村庄情况③与研究方法
星火村隶属于新化县最南端的维山乡。维山乡位于新化县最南端,距县城15公里,东邻石冲口,西交洋溪镇,南接新邵县,北抵科头乡,全境横向12.5公里,纵向17.1公里,境内地势起伏大,属中、低山地貌,常年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全乡辖维山、四都两管区,辖28个行政村,466个村民小组,9 115户农户,共39 000人。④
星火村目前有500余户居民,共2 000余人口,目前,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以耕种稻田为主要收入来源,年人均纯收入只有450元,属于特困地区。整个村庄就分布在一座座绵延结连的崇山之中,在环山而成的盆地里房子较为密集,而从山腰到山顶依山而建的房子较为稀松分散,经常是两户人家之间相隔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山腰上密密麻麻缠绕着线条清晰、层次分明的梯田,成为了村落的一大景观。
笔者从2010年1月11日至1月20日期间,寄居在星火村村民胡海成家中,在他的大力协助下开展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因此,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即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作为其中的一员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通过参与观察和询问,去感受、感悟研究对象的行为方式及其在这些行为方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容,以逐步达到对研究对象及其社会生活的理解[3]。期间,笔者采取参与观察法对庆菩萨、做道场、打箭碑等信仰现象作了详细的记录,并实地查看了几处神灵庙宇、寄子石、树神等信仰场所,同时采用非结构式访谈法对20位村民作了较为深入的访谈,并收集了《新化县志》《湖湘民俗研究》《维山文化》等相关文字资料。
二 村落中存在着的民间信仰现象
(一) “庆菩萨”仪式
“庆菩萨”是所有当地村民都熟知的一种宗教仪式,目前这种仪式活动在星火村仍然较普遍存在。至于“庆菩萨”仪式肇始何时,又如何起源,当地人已经无法道明。《新化县志·民俗》对此有记载:“其神为本姓者称之为‘庆太公’,为异姓者则称之为‘庆法官’。为求家兴财旺,过年杀猪庆‘家主菩萨’,为求五谷丰登,在六月六日土地神生日庆庆‘土地菩萨’。师公无本经,只有诰咒。作法事时,师公戴发冠,插法牌,穿红色法衣,阀鼓鸣金,吹奏号角,拜舞演唱,语多俚俗,意为主家祈祷人口清吉,六畜生旺。吉凶祸福多取决于‘打卦’。法事晨起夕散。”根据笔者此次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庆菩萨”已与县志记载的情况有所差异。
“庆菩萨”仪式是由每户户主聘请师公⑤到家里举行。师公是一种民间宗教仪式的专业从业人员,至今还较广泛地存在于新化、冷水江、双峰等古梅山区域。师公的祖师爷据说是张五郎,因此我们在师公家所供奉的神龛下坛一般会看到一尊木刻张五郎雕像,其神像为双脚朝天,双手撑地,此即为“翻天倒立张五郎”⑥。以前师公所承担的主要法事很多,大致可分为替死人与替活人所作的阴阳两类法事⑦。师公的阳教法事一般皆因老百姓家中遭难、身体疾病或家畜不安等不幸之时祈求神灵显威,保佑其能逢凶化吉、渡过难关而“许愿”,然后请来师公作些法事来代行“还愿”。“庆菩萨”就是师公们在当前星火村施行最多的一种“还愿”法事,据当地人的解释,其目的是为了感谢本户家庭在这一年中的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而向各位神灵菩萨予以祭拜和告慰,并希望通过这个仪式除邪荡秽、驱魔捉妖以求保佑家庭来年的一切顺利和繁荣昌盛。
“庆菩萨”仪式的时间可以选在一年中任何一个时间,但实际上这种仪式活动的举行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年前的农历11月和12月这段期间,因为这期间时值农闲,师公们都能抽出时间来挨家串户主持仪式,且又逢新旧年交替之际,正符合户主为去年还愿,为新年许愿的心意。
笔者此次调查正好赶上“庆菩萨”仪式最为频繁的时间。据笔者调查的一位师公说,他在此后的一个月里都排满了档期,每天都要前往不同的家庭去举行“庆菩萨”仪式。一般户主会提前一两个月跟某个师公定好“庆菩萨”,也有在年头开春时际就早早与师公定好年底的某个吉日。“庆菩萨”举行的日期决不是随性而定的,而是师公根据户主和师公自己的生辰八字进行计算后,只能选定双方生辰八字不相冲突的日期作为仪式举行日。“庆菩萨”仪式一般举行一整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也有的将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左右。
2010年1月16日上午9点,笔者来到星火村2组的村民吴应强家中实地观看了一整天的“庆菩萨”仪式,整个仪式由三人完成,一位穿法衣的师公手拿法器,在摆满供品和神像的香案之前主持法事,两旁坐着两位助手,一个打鼓、一个敲锣。师公是整个仪式过程的中心人物,他站在堂屋神龛前面的正中间,时而低声念咒,时而挥舞法器,时而高声吟唱,时而翩翩起舞⑧。一旁的男户主毕恭毕敬地站在师公一侧,随着师公一起鞠躬拜神,女户主在听到号角奏响之时,便马上燃放一串鞭炮。在有节律的敲锣打鼓声中,他们通过变换香案位置、摆置不同神像、舞弄各式法器、同时颂唱不同内容来演绎一系列内容复杂、含义丰富的故事。全部仪式过程包括:1.布置香火堂;2.请神、开坛荡秽、召四值功曹发送文书上天;3.下马传杯;4.造桥;5.点兵安营立寨,杀鸡祭赏猖兵;6.鉴牲祭祀、勾愿请神领受;7.辞神圣,下火场烧箱,化钱财,高功回坛。实际上,这些复杂仪式所包含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迎神” “娱神”和“送神”。
据村民介绍,自解放到文革开始之前这段时期,星火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年底接师公作“庆菩萨”法事。但文革期间,“庆菩萨”被定为“封建迷信”而被予以禁止,当然仍有极少数人会悄悄地举行这种仪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放宽了对这些民间信仰活动的管制,“庆菩萨”活动又如火如荼地在村落里开展起来。对于一个农户而言,一般“庆菩萨”为三年一届,即连续三年都请师公到家里来“庆菩萨”,一届过后可以暂停几年再庆一届。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何时举行仪式实际上并无严格规定,主要随各户主的经济状况和信仰情况而定。因此,当前该村并没有如某些师公所描绘的“家家户户庆菩萨”之盛况,而实际情况是,该村每年恭请师公来家“庆菩萨”的家庭约只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实地调查还发现,另有一部分家庭已经不再相信神灵菩萨了,也不需要这种仪式来为家庭保平安了。
(二)树神崇拜现象
梅山文化区域由于地处崇山峻岭,高山峡谷,到处都有古木参天,满山遍野为郁郁葱葱。这些树木自然就成为梅山人生活生产的重要资源。但梅山人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很注意树木的再生和繁衍。也许正是由于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靠山吃山”的交换心理,使得梅山人自古就养成了爱树敬树以致崇拜树木的奇特信仰。据传以前当地人把大型的砍伐树木活动叫做“开山”,“开山”之际是需要举行简单的仪式,祈祷山神土地保佑砍伐树木的山民不出现意外伤害;砍完树木之后再举行“收山”仪式,祈祷山神土地保佑树木再生,达到“砍到哪里就长到哪里”的目的。这是原始山民们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念[4]。但笔者的田野调查证实,现在这种“开山”仪式已经销声匿迹,而人们崇拜树木的信仰心理依然存在。
笔者分别实地考察了位于星火村邻村的两棵神树,一棵是大梂树,位于龙寨村,枝叶茂盛,苍老遒劲。树干上挂有一块方形木板,上面用墨汁书写的字早已因年深月久而难以清晰辨认。依稀可见“新化县政府”和“古树名木”的字样,可以看出,这是一棵由当地政府命令加以保护的古老树木。至于树龄到底有多长,当地人谁也说不准了,几个村民说这棵树至少已经上千年了。他们还告知,这是一棵神树,十分奇特和神秘。这棵树的枝叶不能随便折断,更不能将其砍伐,否则会招惹神灵发怒而给人带来严重的惩罚。在这棵大梂树前面房子居住的一位中年男性村民讲了一个几年前发生的故事。
那年他的兄弟盖新房子,当卡车拉着一车货物经过大梂树时,他兄弟嫌垂掉到下面的树枝碍事,就顺手折断了一根树枝。没想马上便腹痛难忍,倒地呻吟。家人立刻意识到这是让树神生气而遭受的惩罚,赶紧在树神下点香烧纸,杀鸡祭祀,向树神求情,结果他兄弟便转危为安了。
关于这样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旁边的村民讲述了几个类似的故事。这棵神树显灵的故事早已为维山乡的村民所熟知,因此,大家都不敢随便“招惹”这棵树。
这里的村民还有将小孩“寄名”给神树、以求平安的祭祀活动。据村民讲,当家中有小孩“不好带”⑨时,便将小孩“寄养”给神树,求神树能禳灾避祸,保小孩健康平安。“寄名”时,需要由家长带着小孩来到神树前举行一个简短的祭祀仪式:将一些斋粑、鱼、肉、水果等供品摆放于神树下,并插上三炷香、烧上几张纸钱、燃放一串鞭炮,在树神面前将心愿吐露,希望能让树神作小孩的“寄养父母”,保佑小孩一切平安。村民认为通过这种对树神的信仰和崇拜,可以缓冲父子生辰命运之间的相冲相克,使新的生命得到古树的神力,撞过童关煞,消除百病,好养好带地顺利成人。在当地甚至也有一些家庭小孩刚出生,父母就把他们“寄名”给神树,祛灾避难,以保平安成长。以致当地被取名为“树生”“松保”“柏生”等与树名相关的人,村村寨寨到处都是[4]。
笔者在石门寨村的一个山坡见到了另一棵经常被当地村民“寄名”的神树,这是一棵足有15米高、树干需要三人合抱的大杉树。据说这棵树是由这方的“土地神”化身而成,因此当地人多称这棵杉树为“土地公公”,因为其十分灵验,这棵大杉树经常吸引各个村庄的人前来举行“寄名”祭祀。笔者到这棵树前,还看到树周围的草地上还残留着鞭炮燃放之后的鲜红纸屑,树下用几块石头堆垒围成的一块泥地上还插着几根未燃尽的香烛,旁边堆积了厚厚一层烧纸留下的灰烬。这些表明,大杉树的香火比较旺盛。这棵树临地的树枝上,到处都系有红布条,大概有十多条。有些布条历经风吹雨淋后已经变得破旧不堪。笔者翻开一块保存较为完整的红布,上面有按照古书格式,从上至下、由右向左用毛笔写就的几排繁体字赫然可见:
信人曾某某,室人李氏为长曾芳明,本命生于丙寅年三月二十日卯时,与父母不相生,发心寄与石门寨吴盛涛土地公公杉树上带养,自寄以后一切关煞消除,树大根深易养成人,财源广进,万事如意⑩。
(三)“寄子石”现象
与“寄名”给神树十分类似,星火村的村民有时会选择将“不好带”的小孩“寄养”于具有灵气的石头上,这块石头非一般的石头,一般被认为是神灵的化身,或至少是沾染了神仙灵气的石头,当地称之为“神仙石”,也可叫做“寄子石”。笔者在星火村的一块田地里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神仙石”,这块巨石可谓是奇形怪状,凹凸不平,极不规则,无法用长宽高数据来描绘。粗略估计其重量,至少应该在2吨以上。在这块巨石旁边,到处散落着鞭炮纸屑,香烛燃尽后剩下的几支长柄和一些纸钱灰烬表明前不久还有人在这里进行祭祀。随行的村民胡海成指着巨石表面上那些凸起的有如拳头般大小的石球说,每一个石球就表示一个被寄养在此的小孩,有多少个石球就说明寄养了多少个小孩。随便清点了一下,这些隆起的石球有将近20个,笔者满腹疑惑地反问道:难道这里已经寄养了20个小孩?胡海成十分肯定地点头,他还说,若你不相信,就把这块石头拍下来等几个月之后再来看,比较后会发现这些石球会有所增加。随后笔者再向附近几位村民的求证,他们也都肯定了这个说法。
(四)打箭碑
星火村当地的民俗认为,小孩在16 岁之前,要经过16 种关煞的磨练,才能长大成人。这16 种关煞是:“短命煞”“鸡飞煞”“雷公煞”“百日关”“将军箭”“水火煞”“四柱煞”“断桥关”“五鬼厌”“撞命煞”“落水煞”“四季关”“铁蛇煞”“断肠煞”“无情煞”“系脚煞”。在每一个关煞,即关卡上,都会有邪神鬼怪故意招灾惹祸,因此,就要请师公或算命先生给小孩推算这些关煞会在他生命中的什么时候出现,算出后就要请巫师来施法除煞,以过关煞。
其中,小孩若被算出带有“将军箭煞”,则需要在某个十字路口立一块“将军箭碑”,让它来代替犯该煞的小孩挡住鬼怪射来的暗箭。“将军箭牌”是用一块高约二尺、宽约一尺余的青石板,正面上端刻一道“紫徽符讳”,符下画有一张开弓搭射的弓,弓箭左右两边各写上“弓开弦断,箭来碑挡”的咒语,在碑的正中间刻上“左走何地,右走何地”的道路方向提示。这块“将军箭碑”是否灵验,据说关键在于师公道士的“紫徽符”和咒语是否有法术。师公道士在立碑时,常常烧纸祭神,念咒画符,巫步舞蹈,充满着巫术活动的神秘诡异。这种“将军箭碑”在今天的梅山地区内的山区岔路口,仍很常见。在星火村的很多小道上、小河边经常能够发现这种“将军箭碑”,从上面的落款日期可以看出,很多是近年置于此地,但也有些“将军箭碑”的年代稍久远,有的甚至是一二十年之前就立于此地,还有些箭碑已经残缺不全。当被问到“这种断裂的箭碑是不是有人故意所为”时,当地村民告之,这一般不会是人为的故意破坏,因为当地民众都知道这是被巫师用来除煞的法器,若对其随意挪动或故意损毁可能会引致煞气上身,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
(五)在丧礼中的唱挽歌与做道场习俗
当亲人去世时,丧家需要为其举办比较隆重的丧礼,这一点与湖南其他地方类似。但在新化县为核心的梅山文化区域中,丧礼仪式有两个比较特别的仪式活动,即唱挽歌与做道场。笔者在星火村调查期间参加了三次丧礼仪式,其中有两次就在星火村,还有一次是在距离星火村有三十公里之遥的另外一个乡村。亲历这三次丧礼仪式的全过程,笔者大概了解了丧礼中的唱挽歌与做道场习俗。在新化当地,若有亲人去世,主人则马上就要通知当地的歌师前来唱挽歌,不然就会显得很冷清,村民也会颇有微词。当地有俗语“三天的道场,不如一晚挽歌”。由于这种唱挽歌习俗的延续流传,歌师这种特殊的职业一直在当地乡村有所保留。他们平日就是与一般村民无异的种地农民,但有丧礼时,就成为拥有特殊技能的歌师。歌师一般是由中老年男性所担当,歌师职业可以由家庭内传承,也有收纳外人做徒弟传承技艺的情况。丧家邀请的歌师一般大概为三至五人。在接到通知抵达丧家后,开始唱挽歌之前,歌师们首先要点纸焚香跪拜亡者,然后念咒:“伏以伏以,天开黄道,紫微高照,有请五方童子,转告本庄土地正神,亡者初赴蟠桃,击鼓超度逍遥……”念咒完毕后,开始绘符,备香帛酒体之仪致敬于亡者灵前,众孝子均跪拜、叩首,祭奠完毕,歌师们击鼓开唱。挽歌主要是唱给亡灵听的,而亡者“三魂飘飘归地府,七魄幽幽上九天”,于是歌师们首要进行的是把亡者的灵魂招回,此乃“招亡魂”仪式。招亡魂时,歌师执幡走在最前面,敲锣打鼓的师傅跟在歌师后面,再后面是全家孝眷列队,歌师手执幡子,口唱挽歌,围着厅堂转圈,每走一圈,朝门外烧化冥纸一扎,孝子们叩首一次,这叫做“执幡招魂”。挽歌曲调简单,但是歌词丰富。有唱描述阴间状况的《游地府》,有劝慰亡者一路走好的《八洞神仙》,有表达孝道的《二十四孝》,有叙述妇女生儿育女的辛苦《投胎记》,有表达离情别意《十二月思亲》,有哭述失去亲人悲痛心情的《孟姜女寻夫》,有对亡者深切怀念《十月怀胎》,有慰导后人振作精神的《十劝孝门莫伤心》,有歌颂死者功德的,还有叙唱历史故事和世俗生活知识等。在整个挽歌过程中,最动人的是长歌“烧香奠酒”,此歌内容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歌师一般跪地歌唱,且在此期间歌师会多次走到灵前烧香、奠酒,孝男孝女们也会陪跪灵前。动人的歌词,动情的韵叹调,真正唤起对亡者的怀念,唱得众人动情擦泪,孝子放声哀哭。按当地习俗,当晚的招待费用全部由出嫁的女儿承担,并且还要送一笔不小的酬劳给歌师。唱挽歌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倒鼓安神。从民俗心理上来讲,死人毕竟是不吉祥的事,灵堂中的一切事物,有一种煞气和邪气,必须把它除去,决不能沾染家中。倒鼓本身除了结束讴歌的演唱外,还有一层除煞的含义在内。所以倒鼓有严格的程序和固定的唱词。主歌师手执一鼓槌,以雄鼓伴和,倒鼓要按固定的唱法和顺序从东方倒起,依次是西、南、北、中央等五方全都倒到,所以叫“倒五鼓”,其词曰:“自古辞丧辞不尽,欲将歌鼓倒何方?此鼓莫向东(南西北中)方倒,东(南西北中)方不是倒鼓场。要将歌鼓倒何方?此鼓丢向西眉山上去,鼓棍丢向九霄云外空,九霄云外虚空正是倒鼓场。此鼓倒进虚空里,歌者孝家各安康。”最后以赞语结束全场活动:人丁迪吉,老少安康,万事如意,永保太平,子孙发达,代代荣昌。
星火村任何村民家若有人去世,都必须做道场。哪怕是最穷的人家,若遇亲人去世,也一定会请道士来做道场,这在当地几乎成了一条定规。当然,丧家根据自身的财力大小选择做道场的天数,当地有“两旦一夕”“三旦两夕”“四旦三夕”等做法,天数越长,做道场的花费就越大。据当地村民说,一般若选择“两旦一夕”,做道场的开支大概在两万元左右,但若选择“四旦三夕”则需要大概要花五万元以上的开支。做道场时,一般是由一个五六人组成的道士班子操办,其中有几位是可以主持仪式的高功,其余则是辅助仪式的道士。道公们开始布置道场,扬幡挂榜,并将各种神像挂上,各种祭品摆上以及海螺、朝板、摇铃、水、令牌、经书等各种法器准备好。当仪式开始时,由高功吹响海螺,召集呼唤各方神灵,降临坛场,在锣鼓声中的伴奏下,开始各种仪式。以一个“两旦一夕”的道场为例,总共要举行十多场仪式,每个仪式都有一个名称,例如“开坛荡秽”“诵三官经”“请水、扎灶、扎香火”“青玄忏”“发功曹”“度亡魂经忏”等,每场仪式从二十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等。每场仪式完了,道士们就得休息一会,等体力恢复后再接着举办下一场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的为深夜操办的《绕棺》仪式,这个仪式所有的道士们在高功的带领下,伴随着高亢、铿锵的打击乐声响围绕在棺材或在棺材前面的平地上不停地摇摆身体、舞动脚步,道士们还不停地作出各种穿插绕花的高难度动作,道士们的表演欲望在此刻发挥到极致,也把整个道场仪式的氛围推向高潮。
(六)祭祖风俗
星火村祭祖的风俗十分浓厚,最明显地体现在村民家中普遍所设的神龛。民间设置神龛,表现正本清源、追念故祖、崇尚儒家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民间神龛文化。民间自古历来就有立造神龛习俗,在神龛中放置“天地國親師位”牌子和祖宗牌子。有的还在其中放置财神像、观音像、祖师像或祖师牌位。据笔者对星火村一部分村民家中神龛文化的考察,神龛一般立于厅屋正面正中,朝向大门,因为在当地民间有大门对神龛的说法。随着民居建筑式样变化和高层建筑套间居住,可能厅屋不适宜或无厅屋,有人就在客厅设立神龛;但忌面对镜子、音箱、房门(睡房)。神龛所在房屋间应干净,明亮。大多数神龛直接设在墙壁上,与墙壁处于同一平面,或贴紧墙面,神龛所在墙的后面不应该有卫生间及不干净杂屋。神龛设置的高度,其下沿与主人心脏的高度基本一致,寓意祖宗在心上。在当地,神龛风格各异,规格并无统一标准,比较常见的木制神龛还是有个基本尺度,总高度为1.6米,由横眉0.35米和正身1.25米组成;总宽是1.2米,正中0.66米加两边对联0.27米×2=0.54米;神龛对联尺度长0.95米,宽0.155米;中间统一为“天地国亲师位”的牌子。神龛上常用对联有“世代源流远 宗枝奕叶长”“神恩浩荡千年旺 祖德昭重万载兴”“祖宗功德源流远 子孙读书姓字香”“家无孔孟谁为首 我有祖宗即是神”“神圣一堂常赐福 祖宗百代永流芳”“祖功宗德流芳远 子孝孙贤世泽长”“宗功伟大兴民族 祖德丰隆护国家”。横眉多为“祖德流芳”“神之最灵”“受天之佑”“勤俭持家”“耕读传家”之类。若新婚时多用“金炉香篆青烟起 玉盏灯辉紫气腾”“九龙灯结连枝彩 双凤烛呈并蒂花”“烛摇红彩仪金凤 香喷青烟舞玉龙”。神龛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分檐角飞翘、多层叠建,每层浮镂空雕,雕刻飞凤、苍鹰、梅鹿等图案,雕刻工艺精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顶端高翘的檐角上,刻有“福”“禄”“寿”“祖德流芳”等字。中部为支撑上部,立圆形四柱,柱间设计有简单的排窗和木台,木台上摆放着质地为青花瓷的香钵和香筒。下部为神柜,侧面单向打开,用于存放祭祀物品。
祖宗牌上的“考妣” 祖宗牌上的抬头是“显考” 或“显妣”,“考”指男性,“妣”指女性。其意思是区分男女,但宗祖不能有别,都要尊敬。当地村民一般在逢年过节,尤其是中元节农历七月半祭祖也称接祖,过世直系长辈生辰日或忌日,都会在神龛前举办祭祀活动,如点燃香烛、燃放编炮(或敲神鼓)、焚烧钱纸、宰杀家禽、摆放餐具、食物祭品。
一年之内最隆重的户外祭祖活动,当属清明节。每当清明节来临,星火村几乎所有村户倾家出动,参加扫墓者也不限男女和人数。这样清明前后的扫墓活动常成为全体村民亲身参与的事,数日内郊野间人群往来不绝,规模极盛。按照习俗,祭扫的顺序是首先要先扫墓,即将墓园打扫干净。其次祭祀,人们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修整坟墓,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见,知道此坟尚有后人。然后叩头行礼祭拜。妇女和小孩们还要就近折些杨柳枝,将撤下的蒸食供品用柳条穿起来。有的则把柳条编成箩圈状,戴在头上,谓“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最后就是放炮送别。
三 当地民间信仰现象的社会学分类:三种“理念型”
深受梅山文化影响的星火村,当前活跃存在着各类民间信仰现象。尽管我们采用“民间信仰”这一个学术概念来指代这些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信仰现象,但实际上此类现象内部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各种信仰现象之间有着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借用韦伯的“理念型”(ideal-type)方法尝试着将当地民间信仰现象进行一种社会学分类。在韦伯看来社会学是一门面向实际的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绝不教导人们应当怎么样”[5]。所以从本质上来讲理念型使人们理性建构出来以分析实际事实的产物,决不是一种规律性的一般概念指导人们的行动,否则便与韦伯建立理念型的初衷相违背。“理念型是因为我们从单方面强调一个或好几个观点而产生的——它是许多分散的、个别的、多少是存在的(但是偶尔不存在的)‘个别的具体现象’的错纵体;这些具体的个别现象围绕着那个从单方面所强调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分析’建构。它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我们在可经验的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符合这种心智的边构物,它是一个乌托邦。”[6]也就是说理念型并不直接来源于现实事物,而是由研究者从主观出发择取感兴趣的、代表性的事物方面,然后经过理性加工构建出理想类型。
基于对星火村当前各类民间信仰现象的调查,再运用研究者的理性设计,按照韦伯的方法论我们可以建构出三种民间信仰的“理念型”。
第一种是风俗习惯型,这类民间信仰是基于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而形成的一种信仰遗留物,并没有经过理性算计或文化反思,群体长期以来持守某种信仰仪式活动。其主要的特点是群体性与习惯性,也就是说这种信仰实践普遍存在于群体之中,且群体内的个体大多是习惯性地参与信仰实践,故称之为“风俗习惯型”。这种风俗习惯成为村落群体的一种文化属性,也是一种迪尔凯姆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强制性。在星火村,庆菩萨与祭祖习俗属于风俗习惯型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信仰意识,但其背后真正的推动并非信仰意识,而是沉淀于每个个体内部的文化习惯使然。村民们一到年底,便自然地要请师公到家里来庆菩萨;每逢清明节,村民们就不由自主地会来到祖先坟头实践各种祭拜仪式。有时尽管他们并不具有清楚的神灵观念与祭拜目的,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长期养成的一种风俗习惯而已。这种信仰类型也十分符合保罗·康纳顿提出的“习惯记忆”:在于我们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回忆的内容指向过去,但我们并不经常去回忆我们何时何地掌握了正在讨论的这种知识,我们常常仅通过现场操演,就能够认可并向其他人演示,我们确实记得。它留下了一种习惯的所有痕迹,我们越是记得这类记忆,我们就越是较少有可能回忆在此涉及的我们的过去所作所为的某种场合;只有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才可能求助于我们作为指南的回忆[7]。按照康纳顿的理论,社会习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特定社会中,符合社会规范的、并被这一社会中的成员不断重复的体化实践(社会操演)。社会习惯记忆则加入了记忆的成分。作为一项长期被人们重复实践并形成习惯的社会行为,人们不可能做到将记忆从这项行为中排除出去。因为,本质上作为一种体化实践的社会习惯,也会拥有如体化实践般的特别的记忆效果:在体化实践中,个体不仅强化了对这一行为本身的习惯记忆,同时也强化了关于这一社会习惯的社会记忆。换句话说,“社会习惯记忆”是一体的,我们无法将“社会习惯”与“记忆”拆开而分别进行讨论。社会习惯记忆的作用机制是,只要社会环境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人们便会习惯性地不断重复这样的体化实践,并不会理性地考量这一体化实践的利与弊。长期以来,星火村村民在不断重复着“庆菩萨”或“祭祖”这一体化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庆菩萨或祭祖的社会习惯记忆。
第二种是集体压力型,这类民间信仰是指处于一定社会文化场域内的所有个体迫于社会群体压力之下而践行的信仰仪式活动,其主要的特点是群体性与非自愿性,也就是说这种信仰实践普遍存在于群体之中,且群体内的个体大多是非自愿性地参与信仰实践,故称之为“集体压力型”。因为行动者基本是在一种外在压力的推动下进行的信仰实践,故行动者的信仰意识程度很低。这种信仰实践或是在受到现代性冲击之后难以为村民从内心真正信奉,或是因为外在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村民不愿意遵守,个体并不真正信奉某种神灵,也并不愿意实践这种仪式,但由于在村落群体中形成了一种维护该信仰实践的道德舆论,像是一道无形的网络将村民们悉数网罗,无人能逃。在星火村,丧礼中的唱挽歌与做道场仪式就属于集体压力型民间信仰。据笔者的观察与访谈,发现尽管丧礼中要供奉很多神灵,很多仪式也有明显的神灵祭祀含义,但参与仪式活动的村民们其实并不具有明显的信仰意识,他们在参与诸多繁琐的仪式时,常常是非常盲目、被动地跟随道士们的引导或要求,他们对于所参与某种仪式的含义或者所祭拜神灵的名称基本不清楚。在访谈中,一位村民说道:“其实死人之后请道士做道场的花费很大,有的人家没有什么钱,从内心中是不想做很大的道场,但是出于压力,也是为了好面子,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借着钱也要把丧礼搞得热热闹闹的,做道场也尽量天数要长一些,免得村里人说闲话”。这就是“道德舆论”的魔力,它虽是经由很多个体的话语而产生,但一经产生之后便像“社会事实”那样具有独立的生命力,便能对其中的个体施展出控制力,不管个体内在的意愿。因此,导致尽管每个个体从心理层面并不愿意遵循某种行为模式,但却仍被“社会事实”包裹其中并受之约束,从而产生出与“社会事实”一致的行动。当地的神龛文化同样如此,每家每户都必须要在堂屋中设立祭祖拜神的神龛,这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也自然成就了当地住房建筑的一种内饰风格。哪家盖房子时若没设立这种神龛,则必然会遭致村里邻人的笑话或指责,这种集体舆论的压力是不容小觑的,谁也不会冒风险随便地成为集体舆论下的议论对象。
第三种是个体自愿型,这类民间信仰是所有个体在面对一定社会文化场域内的各种信仰产品时,可以基于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既可以选择实践其中一种信仰仪式,也可以选择放弃实践任何一种信仰仪式,同时这种选择并不会受到任何来自于社会群体的压力。其主要的特点是个体性与自愿性,也就是说这种信仰实践并不是普遍存在于群体之中,而只是被群体内部分个体选择而行之的,且个体均是自愿地参与信仰实践,故称之为“个体自愿型”。相比风俗习惯型与集体压力型,此类的信仰意识是民间信仰中程度最高的,行动者一般对于所选择信奉的神灵有较清楚的认识,对于实践的仪式活动内涵也能有较高程度的理解。他们往往都是在生活当中出现了某种危机或困境时,主动寻求一种信仰仪式进行解决。在星火村,寄子石、拜树神、打箭碑等都可归入此类信仰。当一户人家的小孩生病了,父母完全可以选择看医生,按照现代医学科学的方法解决小孩的病情,这样的选择既不会带来任何非议,也不会受到任何群体压力,这种选择完全基于个人的自由意愿。当然,一部分父母因着他们信仰的“惯习”,也可能选择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方式来应对小孩的疾病,他们或者将小孩寄名给当地的一块神奇石头,也可能到某颗神树前进行叩拜,还可能去请巫师来施法除煞并采取打箭碑的方式为小孩解除厄运。
四 余论
(一)民间信仰研究中的概念界定问题。近三十多年来,民间信仰现象已经成为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历史学、民间文学、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相继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已经积累了有关民间信仰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但我们看到,很多明确标榜以“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实际所论及的信仰事实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众多研究成果的观点纷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经常出现相反论点。还有一部分研究将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一个整体囊括在“民间信仰”下进行的阐述与分析。总之,以往有关民间信仰的各学科研究有很多并未刻意处理民间信仰现象的异质性,不假思索地将民间信仰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总体来进行论述,导致很多研究结论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很多研究结论也很难与民间信仰的实际相吻合。事实上,“民间信仰”是一个与五大宗教相对应的“大”概念,而不是与某一个宗教相平行的“小”概念。换言之,民间信仰并非是一种单一型宗教体系——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一样——而是包含了多种不同信仰和仪式的复合型宗教体系,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梅山文化区域的一个村庄内所实践的民间信仰就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即风俗习惯型、集体压力型与个体自愿型。这三种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念型”,它们都是对现实的信仰实践所作的一种抽象提炼,活态的信仰实践与这里所界定的“理念型”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各种“理念型”之间的差异也被不同程度地凸显出来。尽管如此,这种社会学类型的划分可以告诉我们,虽然都可以被称作“民间信仰”的文化事实,但它们实际上具备不同的信仰特征,具有各异的信仰结构,并包含不同的社会学意涵,因而我们的研究必须要仔细区分、谨慎分析、慎下结论。以探讨民间信仰与地方社区的关系为例,我们不能把村落社区内的所有民间信仰实践作为一个总体来阐述、分析并得出一个笼统的结论,而是要仔细区分风俗习惯型、集体压力型与个体自愿型三种信仰类型,并分别分析其与地方社区的关系,这样就可能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二)现代性与民间信仰。尽管社会在快速发展着,但宗教信仰并未随之衰败,更未消亡,这是一个为很多实证研究所证明的事实,“世俗化”理论早已被很多学者所抛弃。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低级形式的宗教信仰,仍然经受住了现代化的冲击与洗礼而得以传承,这更加说明了现代性与民间信仰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恩格斯说过:“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抽象的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8]这里表明两点: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曲折而间接的,宗教与社会运动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形式,其复兴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变迁有着一定的关联,并间接地发挥着作用。民间信仰是融合了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涵义等于一体的复杂系统,不会因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它只会调适自己的功能以便适应新的社会形态。个人自由是现代性的基础,它在宗教领域表现为信仰,被定义为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私人事务,宗教身份由群体归属形式变为志愿参与形式。传统时代民间信仰已有一定的个人自由。一些特定的象征可以表达多样的内容,个人可以赋予其符合自己愿望的意义、用以满足自己的个性化需求。一些个人仪式也有可以自由诠释与变通之处,或繁或简均随己意。民间信仰在城市出现了个体化、自由化趋向,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神灵作为自己的守护者和幸运神。在农村,虽然许多村落社区仍有民间信仰组织,但此组织正在失去传统时代的义务性质和自治职能,变成居民自愿结合、联系松散的精神生活团体。这类组织的首领由推举产生,信众与之关系平等。祠庙由信众推举若干人组成理事会或管委会实行民主管理,集体活动由其精英分子担任临时领导或由众人轮流负责主持,个人在加入和退出信仰组织、选择和参加信仰活动上也已有了较大自由[9]。我们在青树村的调查也可以发现,风俗习惯型与集体压力型民间信仰开始式微,村民们更多地趋向于个体自愿型民间信仰。以“庆菩萨”为例,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青树村由山顶至山脚的家庭举行“庆菩萨”仪式的频次逐渐减少,山下的一小部分家庭已经不再举行“庆菩萨”仪式,甚至也有个别家庭从未举行过“庆菩萨”仪式。即使是山上的举行仪式的家庭也有很多是应年老父母的要求。笔者在访问了村里7位17-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看不懂“庆菩萨”仪式,他们也都表示自己成家后可能不会再延续这种传统。不是在一种集体强制力下而得以自由地选择信仰实践,这也正好契合现代社会的自由精神。现代性背景下的民间信仰变迁,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
(三)民间、官方与学界三种力量互动下的民间信仰。最近十多年来,民间、官方和学界对梅山文化的挖掘与研究,成为了一股推动当地民俗旅游的强大力量。学者们对梅山文化的研究与当地政府发展民俗旅游经济形成了一股合力,在当地村民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很多村民都开始认为多年来大家的“搞迷信”并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一种当地的传统文化。他们往往还煞有其事地将日益消减的民间信仰故意隐瞒,肆意扩大,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遍地是崇拜、人人皆信仰的错觉。尤其是民间信仰的主要从业人员包括师公、道士和歌师更是从中看到了谋取经济利益的希望,他们自命为传承与发扬梅山文化的光荣使者,更加卖力地为研究梅山文化的学者提供资料,希望这些民间信仰仪式活动能够被加以宣传、给予重视,并赋予其一种优秀民间文化的地位;地方政府部门也在中央所提倡的“文化强国”“发展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口号的掩映下大力提倡要恢复与保留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梅山文化,同时带动民俗旅游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都能实现效益。围绕民间信仰文化、民间、官方与学界三方力量各自的立场,他们怎样保障各自的利益,他们如何互动,这种互动对于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变迁有何种影响,如何评价这种影响……这些都是十分有趣而又深具社会学意涵的研究问题,有待我们以后的深入调查与探索。
注释:
①近几十年,湖南省不少民间人士和学界人士致力于考察、挖掘和研究梅山区域独有的习俗、信仰、仪式、服饰、饮食、建筑、音乐等,这些从各个方面、多个角度出发的研究都积聚在了梅山文化这个大概念之下,这些涓涓细流也汇聚成了梅山文化研究的大潮。以1995年湖南省第一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新邵县召开为标志,关于梅山文化的制度化、正规化的交流平台开始搭建。自此至今,相继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
②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与法国远东学院联合主持的“湘中宗教与乡土社会”为调查报告课题的法中合作项目,集中联合本土学界、教界、政界及民间文化爱好者,对古梅山峒区域的宗教现状如师公教、梅山教、娘娘教、傩戏、雕匠、纸马、医俗、武功、风水学、鲁班术及富有地方特色的祖先神、祖师神、行业神、地方神和儒教的科仪等作了详细考察和细致考据,这些调查报告主要侧重于仪式描述与史料收集,为抢救梅山文化传统可谓功不可没。参见陈子艾主编的《湘中宗教与乡土社会调查报告集(上,下)》,2006年内部发行。
③根据学术研究惯例,本文中所出现的地名、人名一律采用化名。
④此处数据来自于笔者与该村村支书邓某的访谈。
⑤当地方言中一般称“师公”为“老师”(发第二声)。
⑥张五郎在古梅山地区被尊奉为“坛主祖师”“梅山教主”“梅山爷爷”“梅山神”等,至今在星火村一些老年人处仍能听到关于张五郎的神话故事,大概都是围绕张五郎向太上老君学法,被拒后却得到太上老君女儿即即的暗中相助,直至张五郎向太上老君斗法,却中计使其脑袋接反。这便是倒立张五郎的由来。参见谢本谟、谢五八、胡海成编著《维山文化(第三集)》(未公开发行),第103-105页。湖湘民俗文化研究院主办《湖湘民俗文化》2009年第10期,第62-63页。
⑦师公的阳教法事包括跄家主太公、和娘娘、和梅山、和坛、冲傩、唱菩萨、和良劝善和禳关度煞等,阴教法事叫做送度天曹的度亡法事,简称为送曹。参见田艳的《古梅山峒区域梅山教探究——以师公的信仰为中心》,载湖湘民俗文化研究院主办《湖湘民俗文化》2009年第11期,第152页。
⑧据说是因为师公在仪式过程中的舞蹈动作多为左右摇晃,前后摆动,有些类似于“踉踉跄跄”,故当地方言把“庆菩萨”的“庆”字念作qiang,同“跄”音,称之为“跄菩萨”。
⑨“不好带”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听得比较多的一个当地方言,意思是家里的小孩受惊啼哭、体弱多病或久病不愈。
⑩原文并无标点符号,此处标点为笔者所标注。
[1]陈子艾,李新吾.古梅山峒区域是蚩尤部族的世居地之一[C]//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2-233.
[2]转录自二十五史·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8.
[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7.
[4]马铁鹰.梅山文化区域自古就有树木崇拜风俗[J].湖湘民俗文化,2009(1):48-49.
[5]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2.
[6]陆绯云.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断想:价值中立原则与理想类型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1(6):119.
[7]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49.
[9]王守恩.民间信仰与现代性[J].宗教学研究,2011(4).
〔责任编辑:王 露〕
TheSociologicalClassificationandReflectionsonFolkBeliefsinMeishanCulturalDistrict
CHEN Bina,b
(a.DepartmentofSociology;b.TheStudyBaseofNon-partyPeopleoftheUnitedFront(HunanBranch),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Hunan,China)
In Xinghuo village, some folk customs such as “bodhisattva” ceremony, the worship to tree god, the phenomenon of “child adopted by stone”, “setting up the arrows tablet”, singing dirges and practicing Buddhist service in funerals, and ancestor worship customs are still rife.These folk beliefs can be combed and summarized into three kinds of ideological types borrowed from Max Weber: by customs and habits, by collective pressure, by individual accord.This soc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being an abstraction from folk belief activites, is not directly equivalent to the activities themselves.And this classification also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ideological types.Although many cultural facts can be referred to as “folk belief ”, they actually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belief structure, and contain different sociological meanings.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and do cautious analysis before coming to conclusions.
Meishan culture; folk beliefs; customs and habits type; collective pressure type; individual accord type
2014-09-18
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9CZJ011)
陈彬(1975-),男,湖南沅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研究。
D676.456.9
:A
:1671-5365(2014)11-0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