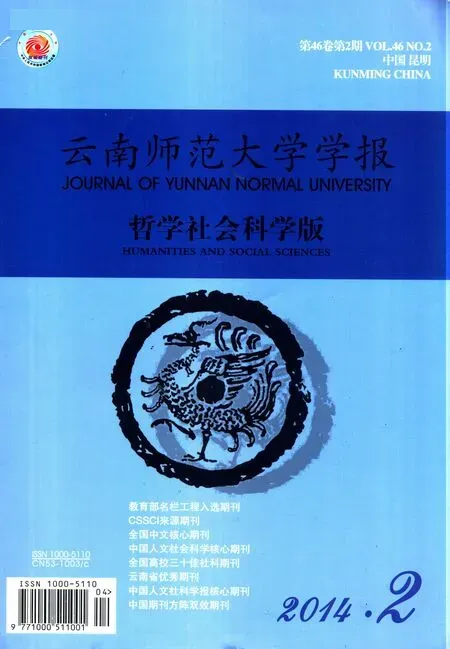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欧美传播论析
——以张爱玲、鲁迅、老舍及其作品为中心*1
布小继, 李全华
(1. 红河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2.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欧美传播论析
——以张爱玲、鲁迅、老舍及其作品为中心*1
布小继1, 李全华2
(1. 红河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2. 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20世纪50-70年代,包括张爱玲自译名作《金锁记》在内的作品在欧美传播受阻,同时期他译的鲁迅、老舍等为西方受众所欢迎的名家作品也出现传播低谷现象。究其原因,除了和自译与他译的生产目的、意识形态阻隔、社会形势变迁等因素有关外,还与传播渠道、传播方式的政治性操作和受众文化心理的干扰、国家对外传播策略的受制等相关。研究旨在探求欧美国家对华文化的态度、目的及消费需求,并希望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优化当今中国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欧美传播;张爱玲;鲁迅;老舍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欧美文学影响之下诞生的,又在欧美文学影响之下一步步发展和成熟起来。发轫期,欧美文学的输入不仅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达方式,塑造了作家们的表达习惯,拓宽了思维视野,也为现代文学“走出去”准备着条件,隐含了对话的可能。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现代文学就开始了欧美传播,鲁迅等人的作品在西方国家获得了读者的认同。然而,50—70年代,这一欧美传播过程出现了波折和起伏,传播陷入低谷状态。本文特以张爱玲、鲁迅、老舍等名家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欧美传播为中心,对该特殊情形进行分析探究。
一、张爱玲以自译《金锁记》为代表的作品之欧美传播
1968年,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被列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材内容。她在1966年7月8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到:“你编的小说集,我想还是译《金锁记》,因为这故事搞来搞去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先后参看或有猎奇的兴趣。”[1][p.50]在1966年10月13日信中又言,“《金锁记》一定在明年二月内译完,勿念。”[1][p.68]1967年2月16日张爱玲在回复夏志清的信中说:“《金锁记》已经译完。”[1][p.82]“《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19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1][p.90]按照刘绍铭的说法,张爱玲对自己作品的翻译,如果她管得着,她是绝对不轻易假手于人的。[2][p.218]也就是说,张爱玲对《金锁记》的自译是应夏志清、刘绍铭等人要编辑一本中国现当代小说读本之邀而进行的,从计划到完成耗时半年多。刘绍铭在仔细比对(部分译文也请了欧阳桢加以比对)后认为张爱玲的译文至少具有bookish English(秀才英文)的部分特征,对白有点不自然,“消化”的功夫没做好。[2][p.230]该文后来收入了1981年出版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Edited by Joseph S.M.Lau,C.T.Hsia,and Leoou-Fan Le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实际上,张爱玲在自译《金锁记》之前,就为自己作品的欧美传播做出过艰辛的努力。1955年,和《秧歌》同一题材的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由美国纽约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出版后,在美国评论界引起了不小反响,重燃起张爱玲英文创作的激情。1956年前后,她把《金锁记》由中篇拉为长篇,即Pink Tears(《粉泪》),次年5月,被美国Charles Scribner’s Sons退稿。作家对该小说又加以精心修改,1959年12月,再次被退稿,不得不再次改写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1967年,“这本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少数评论,都是反面的居多。有一个书评人抱怨张女士塑造的银娣简直令人‘作呕’(revolting)!这大概种因于洋人所接触的现代中国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可怜虫居多;否则,便是十恶不赦的地主、官僚之类,很少‘居间’的,像银娣这种‘眼睛瞄法瞄法,小奸小坏’的人物,所以不习惯。”[3][p.278]之后,直至去世,张爱玲的英文著作就没有再由欧美的出版社推出过。
那么,张爱玲英文作品难以在欧美读者群中打开市场,原因何在呢?不难发现,其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几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一,接受语境的阻隔。张爱玲以中文语境为背景所描述的故事对欧美接受者而言,不具有吸引力。以《金锁记》为底本的故事是以暴露旧家庭、旧家族的种种积习和劣根性为旨归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年代,欧美读者更倾向于欣赏和接纳那些描写激烈的革命斗争、阶级冲突和情爱纠葛的故事,譬如韩素音《瑰宝》(A Many-Splendoured Thing)或是陈纪滢《荻村传》一类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前者亲共,其英国出版商乔纳森在信中对韩素音说,“现在,(英国)在公共汽车上的所有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4][p.416]正因为其是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才把它搬上银幕(国内通译为《生死恋》或《爱情至上》),并获得两项奥斯卡奖;后者反共,陈的《荻村传》“长达12万字,是台湾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从义和团写到国民党兵败大陆,重点写60年来的时代变迁、乡民生离死别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共产党人的愤怒和仇恨……”[5]在美国,这类作品也很有市场。以《金锁记》为底本所衍生的系列小说既非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内幕”(铁幕)以迎合西方反共势力,又非歌颂新政权以迎合西方左派激进主义份子,在出版代理人那里无法获得青睐,而且还陷入了传播上的怪圈:作家创作出的作品无法得到有效而广泛的传播,譬如The Golden Cangue只能在少数大学文学系里被有限的读者阅读,无法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内去;读者所需要的作家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况且张爱玲也不认同前述两位作家。她曾说,“我自己的故事,有点像韩素英(今译韩素音——论者注)的书——不过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她是个second-rate writer(二流作家),别的主场等却没有关系。我从来不觉得jealous of her(妒忌她),虽然她这本书运气很好,我可以写得比她好,因为她写得坏,所以不可能是威胁……”[6][p.48-49]同样,翻译、改编《荻村传》(1959),改译徐速的《浪淘沙》三部曲(1967),也是她本人不情愿干的事。The Rice Sprout Song的成功显然是由于作品中含有不少的西方受众感兴趣的、在他们看来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暴露性描写,是作品无意间切合了受众心理的结果,而之后的作品却没有这样的阅读兴趣点了。实际上,1965年12月31日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张爱玲就意识到了其作品在美国的传播困境:“有本参考书20th Century Authors,同一家公司要出本Mid-Century Authors,写信来叫我写个自传,我借此讲有两部小说卖不出,几乎通篇都讲语言障碍外的障碍。他们不会用的——一共只出过薄薄一本书。等退回来我寄给你看。”[1][p.36]
第二,生活环境上的阻隔。张爱玲置身美国的时代,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因冷战而相互隔绝与对立的时代。1955年10月,张爱玲以“少数学有专长的人士”[7][p.214]的身份赴美,在其个人是寻求免受国内政治运动的波及和伤害,以获得一种自由写作和发表的空间。但张爱玲性格所致的自我隔离、自我闭锁使她选择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族,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3][p.318]除此,还有美国大的文化气候方面的原因,“她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希望不再受到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干扰。但是她来得不是时候,那时不像九十年代一样,对于亚洲经历方面的文学作品没有市场……因此,在美国的前二十年中,她收入的主要来源仍是为香港做翻译工作和写电影剧本,就不足为奇了”。[8][p.202]之后更是疲于应付身体疾病而不断搬家,耗费了她极多的精力。这样,尽管她与美国作家赖雅结婚共同生活了几年,但自始至终与美国主流社会隔膜,这使她有着不能观察、描写、揭示美国社会人群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巨大局限。她不断回溯香港、上海记忆的创作行为和创作思路,从根源上说是“患”了一种文化上的焦虑症和新文化环境中的“失语症”。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写作,丧失了与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的意愿和能力,成了异邦都市里的孤独者和流浪汉。终其一生没有写过以美国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作家本人的一个巨大的失误和遗憾。这种阻隔使张爱玲的英文作品找不到更大、更多的受众群体,从而使其丧失了中西文化交融、碰撞和汇流的空间与平台。她难以融入美国社会,限制了她的中文文本转化为适应英语世界读者口味的文本的可能。
第三,传播渠道的困厄。张爱玲包括自译《金锁记》在内的文学文本的传播渠道都是不够通畅的。传播就其本质来看是信息的扩散和流布,信息要获得广泛的认知,就要有相应的扩散平台和必要的流布通道。张爱玲前期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时间内红遍上海滩就得力于传播渠道的相对通畅,有着夹缝里求得生存的诸多可能。在欧美的环境里,尽管也有人如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马宽德( P.Marquand)等帮忙,但出版商不买账,Stale Mates(《老搭子》)、A Return to the Frontier(《重到前方》)二文分别于1956年9月、1963年3月在The Reporter(《记者》)杂志上发表,影响力有限,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张爱玲作品在欧美传播的艰难。
二、鲁迅、老舍等现代名家他译作品之欧美传播
其实,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欧美传播过程中,张爱玲作品的遭遇并非偶然。以鲁迅为例,他毫无疑问是把西洋文学技巧与中国文学经典之技巧融合得极其到位的作家,西方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在1926年已经开始,以法国为最早。50—70年代,鲁迅作品的译介除了法国本土翻译家、文学家和汉学家的不懈努力外,还多了中国政府外宣机关——外文出版社和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这一渠道,这也使得鲁迅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于70年代出现了高潮。这固然有着“文革”对法国左派和极左派颇具吸引力而使鲁迅像在中国大陆一样被“工具化”方面的原因,但统观欧美,在“繁盛期”(1946——1965)的 20 年间,平均每年出版14 种鲁迅译品;在1966——1973年的8年间,全世界却只出版了26 种鲁迅译品:日本出版10 种( 26 本) ,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出版2 种,苏联、法国、英国、西德、罗马尼亚、葡萄牙、朝鲜、越南、尼泊尔、缅甸各出版1 种。[9]有评论指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鲁迅外,老舍、萧红的作品最受英语译者的关注。[10]老舍作品译本众多。先看《骆驼祥子》,该小说1945年被美国翻译家伊文·金(Even king)选中翻译后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New York, Regnal and Hitchcock) 推出, 1946年被纽约桑代尔和伦敦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New York, Sun Dial Press, London Michael Joseph)再版,以此为基础,1947年,让·布马拉译其为法文,即《北京苦力欢乐的心》,由巴黎的阿尔多出版社出版。再看《离婚》,1948年伊文·金翻译后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出版发行,1955年又有翻译家据中文原作重译后出版了法文本。其他的还有:1951年英国登特父子阿尔定有限出版公司( J. M. Dent and Sons LTD Aldine House)出版了《 天狗》(Heavens-ent),纽约的出版社推出《惶惑》(The Yellow Storm)。1952年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又出版了《鼓书艺人》( The Drum Singers),1964年詹姆斯E·杜( James E.Dew)翻译的《猫城记》(The City of Cats)由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W. J. F. 詹纳和戴乃迭(W. J. F. Jenner and Gladys Yang)合译的《现代中国小说集》(Modern Chinese Stories, 1970 ) 中收有老舍的小说, 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翻译的《猫城记》(Cat Country: A Satirical Novel of China in the 1930’s)也于1970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又,据曹禺回忆,“老舍的长篇名著《骆驼祥子》曾在美国成为畅销书, 发行很广, 因而老舍出名,受到美国读者的崇拜。”[11]但1953——1963年期间老舍却没有一部作品在欧美出版。1958年外文出版社推出了曹禺名剧《雷雨》的英文版和法文版,1960年该社又推出了《日出》、《明朗的天》的英文版,[12][p.106-113]但其作品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的欧美传播同样遇冷。1958以前,张天翼的《仇恨》、《二十一个》、《华威先生》、《大林和小林》等十五篇作品也被英译在欧美国家印行过。另有儿童文学作品《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蓉生在家里》和《大灰狼》被译介印行。[13]
但是,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张爱玲的自译较诸前述作家的他译似乎是更不成功的,这从作品出版、印行情况可以看出。缘由何在呢?
先从翻译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张爱玲的自译(包括改译)是作家的一种典型的再创作行为,它可以忠实于作家艺术创作的良心和水准,确保跨文化语境中的读者也能够读到几乎和母语读者一样的、原汁原味的文本,但它的市场指向往往是模糊的,对传播和市场运行规则缺少深刻的理解,对接受者心理的揣测也会显得隔膜。他译是由目的语国的专家对出版商感兴趣的外国文学作品加以选择和甄别后翻译的结果,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定位清晰。有时候为了能够真正做到投其(出版商、读者)所好,甚至不惜对原著加以增删改写,譬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被伊万·金初译时,就“把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14]即是一例。欧美接受者认可某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不完全是原著好,更可能是译笔好而容易被接受。即如葛浩文翻译了莫言作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终致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明证。可见,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与鲁迅、老舍、曹禺、张天翼等人的他译作品之间还是不能等量齐观,张爱玲也确实无法替代与出版商有紧密联系并密切关注出版界、读书界动态和谙熟母语国读者心态、文化背景的翻译家。
再从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来看。按照罗兰德·萨雷(Lorand Szalay)的理解,和文化内传播的情景相比,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相对论和多元论必须取代影响文化内传播的虚幻的同质性。在跨文化情景中,有效的传播需要系统地弥合分歧,需要文化自觉性以及对另一种文化的了解。参与者必须形成更系统地适应那种可供选择的文化的框架而不是自发地去适应它,他要能了解或欣赏另一种文化的代码,比如语言代码和非语言代码。[15][p.58-59]显然,在母语国倍受欢迎的作品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无法推论出其一定也会受到欢迎,因为他国参与传播者的文化自觉性、主动适应接纳程度和理解能力都必然会对该作品的传播构成制约。故此,一部文学文本在跨文化语境中能否被有效地、广泛地传播,绝不仅仅取决于翻译者的主观意愿,更取决于传播链终端的参与者/接受者的意愿。唯有通晓二者之间的复杂而丰富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使其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得到传播。显然,张爱玲以己度人式的翻译和传播意愿也无法与他译者/翻译家等同,更无法与欧美语境中的大多数读者进行“对话”。
三、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之欧美传播
在前述基础上,我们再来论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的欧美传播问题。
一是有学者曾指出,40年代老舍、曹禺等人的作品之所以在欧美能够得到传播,是和其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当时,美国、苏联竞相拉拢中国,老舍、曹禺之访问美国也是美国针对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二人所采取的行动。为配合此举动,才有各种翻译传播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政府行为。而当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亲华变为排华、反共,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等系列事件中,中美完全处在了对立面,文化传播逐渐宣告终止,张爱玲的作品即便能够被夏志清等学者高度认可,但依然无法走近众多的普通读者。
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与现代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密切相关。应该说,在对欧美文学的吸收和内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套路,一方面是对中国现实境况的写实主义式描叙,尤其是对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鞭挞,对国民劣根性的不遗余力的暴露,都很能够吸引欧美人的眼球,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烂熟”的国度里所发生的各类稀奇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构建出欧美读者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学技法与欧美文学技法的融合与交汇,产生了新的文学质素,如小说中写意式的心理描写,意象与人物心境的暗合,细腻传神的白描,结构上横截面与纵剖面的有机结合,反“大团圆”的结局,对故事之点、线、面的立体交叉叙述与宏大叙事的追求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欧美文学,构成对话,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互生互补,各取所长。法国著名作家、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就对老舍很敬重,称其为“师者,老舍”,并以此为题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老舍《四世同堂》法译本作序,在法国《解放报》撰文评论老舍。[16]这些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欧美传播的基础和可能,但回到本文所限定的年代,实际情况却难如人意甚至是异常艰难。
三是受制于欧美市场的传播途径。并非所有的优秀作品都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有效传播。尽管“优秀”的内涵在不同国度理解不一,但文学对生命、人生和人性的表达和探索是共通的、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能够传达出这种共通性和永恒性,对人类的精神家园进行不懈追问、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独特而持久的探索、对人类世界的前途与命运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验而在艺术上堪称精湛的作品都可以进入这一行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在欧美的跨文化传播一方面是出于艺术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出于传播者(翻译者、出版商、出版代理商和编辑)对接受者口味、兴趣的评估。50-70年代之前或之后进入欧美市场又能得到广泛传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显然是合乎欧美传播需要的。但在该时期,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却与政治宣传紧密挂钩,以迎合时势和政治需要为第一要务,文学性因之悖离。
四是极易受到接受群体文化心理的干扰。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近代文化是“近亲”,这不仅表现在诸多的现代文学名家留学日本或有到过日本的经历相关,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学的起源、发展中的“日本因素”所占分量极大,是西方文学影响中国的中介和桥梁。在文化心理上也有更多的趋同性。日本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封建家庭不竭余力的鞭挞之作品更易认同,对专制制度之腐朽、黑暗面之揭露也更能够接受。相较而言,在女权主义高涨、社会革命剧烈的50—70年代,西方读者对这些作品缺少共鸣,那些实验性的、先锋和前卫的个性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如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更有吸引力。也就是说,西方读者群的文化心理在时势的影响下,在文化优越感的支配下,在文化多样性和审美泛化的前提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干扰。
五是受制于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策略。国家的外宣部门有意识地推出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作为对外宣传的一部分,这些作家作品必定是要获得官方认可的。在获得相当的传播基础后,方可能自我扩散。那些依靠自己力量进行自我推销的作家如张爱玲,其作品无论是自译还是改译,都被摒弃在这一体制之外,况且当时她也离开了中国大陆。有学者考察后发现,在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对外宣传中作品译介资格的获取要围绕着体现爱国爱民情怀、揭露批判旧社会的黑暗、反映民主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配合内政外交这几个方面,译者本人也必须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品质,国家对外宣书刊有着严格的选择规范。[17][p.62]这些限制和要求无疑背离了文学性和审美需要,也就使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欧美传播变得不同寻常地艰难起来。
最后想强调一点的是文化软实力与跨文化传播关系究竟如何?毋庸置疑,二者关系紧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命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格局,其中文化治理排在第三位,比例之大,位置之重,彰显了文化强国的战略。显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水平和有效性构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如何加强和改进跨文化传播的水平,不断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优化出良好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则关系到当前国家形象的建构、国家利益的维护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长远方针,不断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善用之,才可能为当下的发展赢得有利的舆论环境,通过不懈的努力以塑造出良好的国际形象。本文以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欧美传播论析为题,其选题动机正是关注当今中国文化如何有效向外传播的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希望研究结果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如何优化当今中国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有所裨益。
[1]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M].台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
[2] 陈子善.重读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 金宏达.昨夜月色——生平·家世·交往[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4] (英)韩素音.瑰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古远清.亦官亦民陈纪滢[J].武汉文史资料,2004,(12).
[6]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M].台北:台北皇冠出版社,2010.
[7] 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8] 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M].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
[9] 宋绍香.世界鲁迅研究与译介六十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5).
[10] 马会娟.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现状与问题[J].中国翻译,2013,(1).
[11] 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J].新文学史料,1985,(2).
[12] 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13] 杜元明.张天翼作品在国外[J].新文学史料,1982,(3).
[14] 黄苗子.老舍之歌——老舍的生平和创作[J].新文学史料,1979,(3).
[15] (美)迈克尔·H·普罗瑟.何道宽译.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6] 宋绍香.走向现实的中国新文学——欧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介管窥[J].国外社会科学,2012,(3).
[17] 骆忠武.中国外宣书刊翻译及传播史料研究(1949——1976)[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3.
[责任编辑: 肖国荣]
Publicit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A Study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Eileen Chang, Lu Xun and Lao She
BU Xiao-ji1& LI Quan-hua2
(1.CollegeofHumanities,HongheUniversity,Mengzi661199,China;2.ChuxiongNormalUniversity,Chuxiong675000,China)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quite a few translated works like The Golden Cangue translated by Eileen Chang herself and others by such famous writers as Lu Xun and Lao She became less popular than before. The causes were related to the translators' purposes, different ideologies, social changes, as well as transmission channels,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Western countries' cultural demand and consumption attitude towards China, which should have much significance to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ross-cultural publicity of China's cultural product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publicity in Europe and America Eileen Chang; Lu Xun; Lao She
2013-12-16
布小继(1972—),男,云南大姚人,红河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和现代文化。
I2
A
1000-5110(2014)02-01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