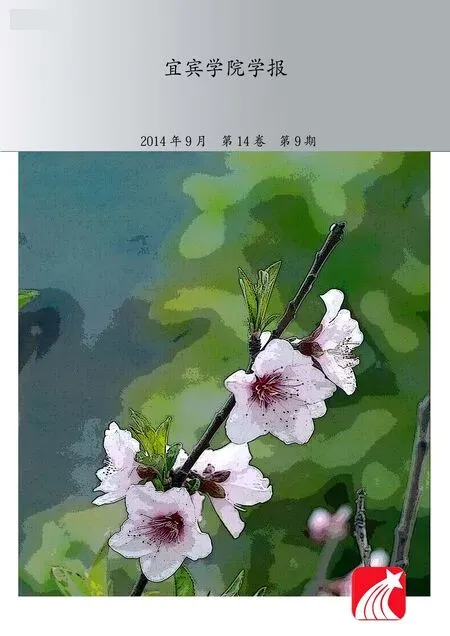从心、性、理三者的关系看朱陆心性思想的异同
王 洁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吕思勉先生在《理学纲要》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朱陆二儒的思想分歧:“朱陆之异,象山谓‘心即理’,朱子谓‘性即理’而已。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而所谓心者,则已不能离乎气质之累,而不免杂有人欲之私。惟其所谓心即理也,故万事具于吾心;吾心之外,更无所谓理;理之外,更无所谓事。一切工夫,只在一心之上。二家异同,后来虽枝叶繁多,而溯厥根源,则惟此一语而已。”[1]100吕思勉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积累与敏锐的哲学思考,一语点破朱陆思想分歧的切要之处。而朱子与象山同属宋明新儒学系统,在主张心性与天理的贯通层面上,二儒的立场又是一致的。通过心性对天理的上达,儒家的“仁学”获得了形上学支撑,而通过天理对心性的下贯,儒家的“仁学”又显示出了强烈的内在主体性格。
一 朱陆心性之学的不同架构
(一)心之义涵:知觉之心与德性之心
在朱子与象山的心性形上学建构中,二者对于“心”这一概念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朱熹看来,“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2]3180所谓知觉,“知是知此一事,觉是忽然自理会得”。[3]1363依朱子之意,心之义涵主要落在知觉之能上,心作为人的知觉之灵,是人身的主宰,是应接事物的主体。而心之所以有知觉之能,是因为心有“虚灵知觉之性”。对于心的这个特性,朱子常以镜鉴作喻:“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象,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若先有一个影象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4]347“虚”指的是心本无形象,“灵”指的是心能随感而应。也就是说,心之所以能够洞照万物之本然,显现其神明知觉的作用,是因为心体本身湛然虚明、无尘垢之蔽。可见,朱子所讲的心,侧重于其作为认知主体的意义,虽然在实际的认知过程中,朱子认为此认知之能不能只在一草一木、器用之间下工夫,而应当认识事物“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则”,但此心之自体,仍然落在知觉处,这与象山直接以德性言心有很大不同。
陆九渊之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于心”的[5]471,所以他对心体的理解,是直接顺着孟子的“良知良能”和“四端之心”展开的。在与曾宅之的书信中,象山指出:“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6]5在这里,象山把孟子提出的“良知良能”称之为“本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表征的是“本心”的先验性,“万物皆备于我”所表征的则是“本心”的自足性,这个先验自足的“本心”即德性显发的主体。对于“本心”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说明,是陆九渊回答弟子杨简“如何是本心”的追问时所作的阐释:“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5]487杨简对此始终不得其解,及至其在断扇讼时,象山指出“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即其本心”[5]488,杨简才言下大悟。在孟子那里,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普遍根性已然地具足“四端之心”,而“四端之心”自然能够显发为仁义礼智四德,所以孟子讲“性善”。象山这里直接以“四端之心”解释本心,是把人之本心视为人人所同具的道德心灵,即,本心就是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可见,象山思想体系中的“心”,并非从知觉处下手,而是从心作为德性主体的“本心”意义上立论,从而开启了与朱子理学完全不同的心学进路。
(二)心体与体性的关系:心统性情与心性为一
己丑之悟后,朱熹的心性思想渐趋成熟,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未发之中为性,性安然不动,是心之体;已发为情,情感物而动,是心之用;心统性情,贯通于已发未发、动静之间。在《元亨利贞说》一文中,朱熹讲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2]3254从这个观点来看,朱子是以内在的道德本质指称性,以此作为现实意识及现实情感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而把具体的情感念虑看作情,以此作为内在道德本质的外在体现,实质上是析心之本体与发用为二。而且,性体作为安然不动的心之本体,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讲法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心体的活动层面是通过感物而动的情表现出来的,所以,心体的存有与活动也是两面隔开的。这样一来,在朱子心性形上学的建构中,性体是理之下落在人心处的着落,与“虚灵知觉”的心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心体与性体是两分的。
那么,这个两分的心体与性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朱子看来,最确当的表述应当是“心统性情”,所谓“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7]93是也。作为兼统性情之心,不仅是“兼性情而言者”,而且能够主宰性情。在《答胡广仲》中,朱熹这样解释“心主性情”:“心主性情,但以吾心观之,未发而知觉不昧者,岂非心之主乎性?已发而品节不差,岂非心之主乎情?”[8]1902就对情而言,“心主性情”是指心对情的主宰作用,即道德主体和道德意识对外显之情感念虑的引导和控制,这是心对情的省察。就对性而言,未发之时心须有主宰,“所谓静中有个觉处,只是常惺惺在这里,静不是睡著了”[7]1503,即在无所思虑和情感未发生时,仍努力保持一种收敛和警觉状态,这是心对性的涵养。所谓“心主性情”,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朱熹既以“仁义礼智”指称性,即是假定人性是纯善无恶的,然而现实的人却表现出不同的善恶倾向。朱子对此这样解释:“性只是仁义礼智。所谓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9]164也就是说,朱子不仅承认纯善无恶的天命之性,亦承认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而且此天命之性在人出生以后就是顿放在气质之性之中的,两者不离不杂。朱子曾说:“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也。然其本体,亦未尝杂。”[10] 2430这个全是理的“天命之性”,只能从形而上的角度说;而人出生以后的现实人性,是兼性之本体与气质之禀两面而言的。由此可见,朱子的心性思想是与他的宇宙本体观联系在一起的。在朱熹的思想系统里,理、气是宇宙生化的两个核心概念。“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2755在朱子看来,天地间有理有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此天地之理作为一“洁净空阔的世界”,“只是善,无有不善者”[11]83,人与万物禀此天道天理以生,故人之本然之性净洁纯一,此之谓“继之者善也”。天地之理虽为人所同受,然而,现实的人之气禀却有不同。人的气质之禀有清明、浑浊,正通、偏塞,纯粹、驳杂之别,当气禀的浑浊、偏塞、驳杂与天命之性浑成一体时,就会造成对本然之性的隔蔽,因此,现实的人性会呈现出恶的一面,此之谓“成之者性也”。
而象山以“本心”指称心,这个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体,实质上与天命所赋的性体是同一的。象山弟子曾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对此,象山是这样回答的:“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又问:“莫是同出而异名否?”象山说:“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是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12]444关于心与性的关系问题,象山认为这是建立在自家体察基础上的“一般物事”,如果一定要说,那么,从天命所赋的层面上讲,可称之为“性”;从得之在我的层面上说,则应称之为“心”,其实二者就是同一的。自二程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后,以性体与天理为一的讲法就得到了宋明儒者的普遍认可,而至陆九渊以“心即理”立论,这个在朱子理学体系里被隔断的心体与性体又合而为一了。
(三)心体与理体的关系:性即理与心即理
在《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11]85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在朱子的心性思想中,心、性、情是明确的三分结构,性是天地之理之所赋,情是感于物之所发,而心作为性情之主宰,只是个知觉的灵明,三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朱子在回答弟子的问题时,以强调性的语气指出“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由此,在朱子的心性建构中,理体与心体也是二分的,言“性即理”可,并且只能言“性即理”,而言“心即理”则不可。
不过,在朱子的论述中又会发现“心与理一”的说法。据《朱子语录》记载:“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如何与理贯通为一?’曰:‘不须去著贯通,本来贯通。’‘如何本来贯通?’曰:‘理无心,则无着处。’”[11]85可见,朱子所谓“心与理一”并非是说“心”与“理”无所分别,而只是在“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的“本来”意义上,即此理此天命之性落着在人心处才说“心与理一”的,这是“心与理一”的形上学意义。 “心与理一”亦可以从工夫上显现。牟宗三先生对这一层意思曾专门作说明:“心明之知本有认知事物之理之作用,认知之而依理发为存在之然,此即是性理之显现。”[13]337在心能认知性理并通过修养工夫彰明性理的基础上,“心与理一”的说法在修养论意义同样得以成立。
在“本心”观念的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他说:“‘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4]149从本原上看,本心是天之所赋,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根源,因此,本心与宇宙之理是同一的。从实践上看,此心若能通过修养工夫去除私欲,做到“尽我之心”,也就自然能够与理合一了。所谓“义理之在人心,实天之所与,而不可泯灭焉者也,彼其受蔽于物而至于悖理违义,盖亦弗思焉耳。诚能反而思之,则是非取舍盖有隐然而动,判然而明,决然而无疑者矣”[14]376是也。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本原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心与理一”的命题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都是成立的。所以,陆九渊这样概括“心”与“理”的关系:“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6]4-5按照象山的理解,既然此心此理无有不同,只要识得本心,也就自然体认到了天地之理。故其言:“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15]423所以,在象山的心性之学架构中,心体与理体二者是同一的。
二 朱陆心性之学的契合
(一)心性对天理的上达
在朱熹的心性建构中,他虽然并不主张心体与理体的直接同一,但仍然认为“理便在心之中”“本来贯通”的意义上“心与理一”。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朱熹在性情二分基础上的“性即理”说,还是陆九渊在本心概念基础上的“心即理”说,在强调人心即仁心仁性与天理天道通而为一的立场上,二者是一致的。这样一来,“人之仁心仁性具有了超越个人的生死与天道、天理同在的绝对性、普遍性、恒常性和本体宇宙论的意义”。[16]
在先秦儒家那里,孟子讲“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都蕴含了心性与天命相贯通的思想传统,但先秦儒者并未在理论上对于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的论述。朱熹与象山延续这一思想传统,以《中庸》《易传》《孟子》等经典为依据建构其心性形上学体系,对天理、性命与人心的贯通给予了系统的说明与阐述。在宋明儒者看来,人与万物同为大化流行中之物,皆禀天道天理以生,此天道天理落在人心即是“仁德”,故人之“仁德”与天之“生理”贯通不二,从这个层面上说,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即是贯通天人之终极所以然。正是由于仁心仁性秉承了天道天理,仁心仁性的发显才被赋予了天地之理自然流行的本体宇宙论意义,至此,孔子所创立的“仁学”体系才得到了系统的形上学支撑,这不得不说是宋明理学家对传统儒学的巨大贡献。
(二)天理对心性的下贯
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佛老二教的心性形上学理论已经相当系统和完备了,北宋儒者意识到:“如果只局限于既有的礼法传统或仅停留于世俗性的社会道德层面来探寻与说明儒家价值的根源和道德实践的根据,那么,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将根本无法抵挡佛老思想的攻击和否定,故必须在心性形上学领域有所建树,才能真正肯定和维护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文世界。”[16]也就是说,无论是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还是陆九渊所领军的心学,他们致力于心性本体的开显和道德本性的涵养,都是要求挺立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以对抗佛道二教。在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建构中,一个以“无”为本,一个“一切皆空”,反应到社会人生层面就是主张“出世”或“避世”,这与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积极入世态度显然是相悖的。因此,无论是朱子的“性即理”思想,还是象山的“心即理”主张,“理”都是以“仁义礼智”为其具体内容的“实理”,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实理”就具体体现为亲亲长长尊贤之道、父子君臣朋友兄弟夫妇之伦。
如果说在宋明儒者将仁心仁性与天道天理相贯通的努力中,儒家具体的价值原则与人伦规范的实践,获得了天道天理意义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那么,在宋明儒者直接将天道天理下贯于每个个体的“仁心仁性”时,儒家具体的价值原则与人伦规范的实践,又因本出于每个人所本具的仁心仁性而成为每个现实个体的当然责任。在朱子与象山这里,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依据,都不在外部,而在每个现实个体本来具足的“本性”或“本心”。故道德践履的任务,以开显个体本心本性本体的方式落实于每个愚夫愚妇的头上,至此,儒家的践仁之学不仅具有了坚实的形上地基,而且显现了强烈的内在主体性格。
结语
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与陆九渊所领军的“心学”,其心性之学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朱子主张“性即理”而象山强调“心即理”。究其原因,盖出于朱子析心与理为二,而象山合心与理为一。然而朱子与象山同属宋明新儒学系统,二儒都试图“通过向内在的人格世界的不断开拓,吾人自我就可以在成就德性生命的同时,在个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与天地宇宙纯亦不已的创造生命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贯通”[17],在致力于仁心仁性与天道天理的贯通、挺立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吕思勉.理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4]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文碧方.宋明理学中理学与心学的同异及其互动[J].武汉大学学报,2005,58(4):415-418.
[17]郭齐勇.现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论纲[J].周易研究,2004(4):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