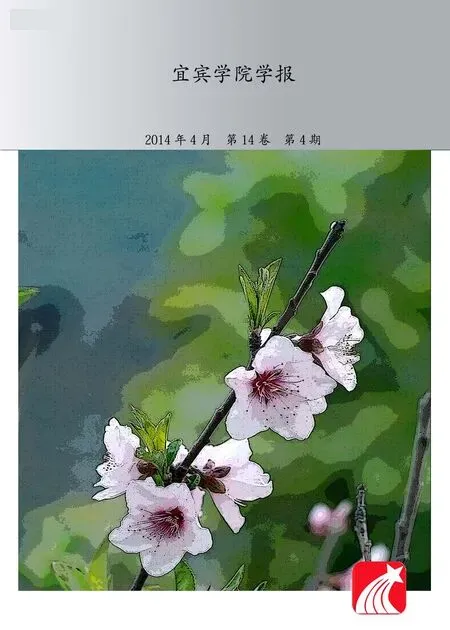崇拜与反抗
——《追风筝的人》主人公对男性权威的态度流变
郭 飞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自出版后,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该书,讲述阿富汗少年阿米尔的成长故事。他背叛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却又走上救赎之路。据CNKI统计显示,目前国内有80余篇关于此部作品的研究,它们以身份认同、民族关系、成长小说、生态批评、意象解读等视角解读该小说。余刚对阿米尔的身份认同轨迹进行阐释,他认为,主人公由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从而导致在找寻过程中的焦虑[1];曾万泉通过分析作品的人物关系来探讨阿富汗的民族关系,他指出,小说以人物关系折射出阿富汗民族间的冲突以及不平等的社会阶级观念[2];蒋小庆在其硕士论文中用成长主题探讨阿米尔的思想和心理如何在外力的推动下一步步摒弃自私和唯我的道德观,从幼稚走向人性善良和在邪恶面前不畏强暴而秉持正义的高贵品德。[3]王建荣从民族精神与道德传承、社会文化变迁与伦理关怀等角度解读风筝意象,他认为风筝意象具有重要叙事功能,是多元隐喻的载体[4]。但目前国内关于《追风筝的人》的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在救赎主题,不少学者从认知诗学、会话分析、亲情关系、人性原罪等方面阐述该主题。他们认为,胡赛尼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反映阿富汗社会中因阶级、宗教信仰不同造成的友谊与背叛之间的矛盾,为追求人性真谛,个体冲破宗教戒律和社会习俗的束缚,获得救赎。然而,在成长与救赎中,小说中的“我”与“男性权力”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国内研究还未涉及到。主人公阿米尔的背叛、反省与救赎同“我”对男权意识的崇拜、摈弃、反抗一一对应。救赎之路,是对男性权威的态度流变之路。
一 父权崇拜与人性背叛
《追风筝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一个男权世界,母性缺失是这个世界的典型特征。小说给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有四位。阿米尔的母亲因生产时出血过多而谢世。“我”从照片上看到“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5]5。寥寥数字,母亲的和善、纯洁、高贵,令人心生向往。“我”的母亲在小说中只作为思念的对象出现过几次;哈桑的母亲漂亮但身份卑微,年轻时放荡不羁,对自己的丈夫冷嘲热讽,与当地军人厮混,最后抛下刚出生的儿子自顾寻欢;“我”的岳母雅米拉,心地善良,喜欢歌唱。丈夫塔赫里同她结婚时,签署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5]171。第四位女性是“我”的妻子索拉雅,虽出身高贵却曾跟人私奔,成为难以嫁出去的女子。可以看出,小说中的女性或红颜薄命,或烟花风尘,或丢失自我,或无法生育,她们都以弱势的形象出现在阿富汗男人眼中。
相反,塔赫里、阿辛汗等人则扮演着主宰或先知角色,塔赫里传统、自尊,身上带有典型阿富汗男人的秉性,他对妻女苛责,不准自己太太随意唱歌,不准女儿选择自己喜爱的教师职业;阿辛汗在小说里起着引线作用,出现次数不多,但他已化身为先知式人物。起居室的橱柜里,有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我还是婴儿,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惫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拉着拉辛汗的小指头[5]5。小说开始就通过这一细节隐喻了拉辛汗在“我”生命中的重要作用,这似乎暗示,他是我心灵救赎路上的指引人。多年后,拉辛汗打电话给在美国的阿米尔,“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5]186。小说虽未对拉辛汗着过多笔墨,但他却以男性世界的智者和先知的姿态出现,围绕“我”发生的一切,他似乎都心知肚明。
小说描写了阿米尔父亲的外形、爱好、性格及关于他的神奇传说。父亲的话题永远只是政治、生意、足球;父亲的绰号叫“飓风先生”,“身材高大……双手强壮,能将柳树连根拔起”,“眼珠子一瞪,能让魔鬼跪地求饶。他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5]13这些言辞,无不折射出“我”对父亲的仰视及崇拜。甚至,我的梦里都少不了关于父亲的传说。据说父亲跟黑熊搏斗过,“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性。”“我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象着爸爸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都梦见,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熊。”[5]12政治、足球、黑熊,这些充斥着男人阳刚之气的符号将父亲打造得威武、高大、神气。此外,父亲慷慨仗义,修建孤儿院,每隔一周宴请三十多人来家用餐。在阿米尔眼里,“我对父亲敬若神明”[5]31。然而,阿米尔生性懦弱敏感,并不讨父亲的欢心。父亲带他去湖边度假,他跟父亲说话,父亲只简单“哼”两下;父亲带阿米尔看比武大赛,“我”看到选手死亡而大哭,父亲开车时“沉默不语,厌恶溢于言表”[5]21;父亲跟阿辛汗聊天,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他的儿子。父子间的情感失衡,让阿米尔陷入无边的挫折感与焦虑中。父亲对阿桑的喜爱加深了阿米尔的挫败感,“我”不明白为何父亲会对一个哈扎拉仆人那么友爱而温和。阿米尔为了让爸爸只属于他一人,对父亲撒谎说,阿桑有事情不能一起去湖边。他还恨孤儿院的孩子,希望他们随父母一起死掉。阿米尔对父亲的爱渴望至极,他睡前臆想:“我想起爸爸,他宽广的胸膛……他身上甜甜的酒味,他用胡子扎我的脸蛋”[5]32。在崇拜父亲和得不到父亲宠爱的矛盾里,阿米尔设法寻求父亲的认同。弗洛伊德认为:“当人失去或不能拥有某一爱恋对象时,为了重新得到甚至长期拥有它,他或许会努力使自己与该对象相似。这便是损失认同。”[6]74母爱的缺失、父权崇拜的冷漠回应,促使阿米尔努力跟父亲相似,变得勇敢、坚强。父亲在闲谈中认为阿米尔能赢回风筝巡回赛,阿米尔立志“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不同凡响”[5]55。弗洛伊德指出:“损失认同常见于遭到父母冷遇的儿童身上,为重获父母的爱,他们卖力地按父母的意志来表现。父亲对孩子怎么要求,孩子就怎样与之认同。”[6]75然而,正是阿米尔在父权崇拜与认同找寻的纠缠中,他背叛了哈桑。
阿米尔与阿桑将其他放风筝的人斗败。捡拾被打败的风筝时,阿桑遭到阿塞夫鸡奸。阿米尔站在巷口目睹一切,却一言不发,他想的是“为了赢回爸爸,这也许是阿桑必须付出的代价”[5]77。阿桑返回时,阿米尔首先关心的是风筝并检查其是否有裂痕。为得到父亲的爱,阿米尔对阿塞夫的罪恶行为只字未提,虽然他知道那是犯罪。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阿米尔“忘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5]78。由此可见,阿米尔对阿桑的背叛皆因他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崇拜而起。父权下的爱与认同激发出阿米尔内心的民族歧视、自私唯我,从而为他日后的内心煎熬与痛苦埋下苦涩种子。阿米尔在日后生活里,他无法忍受阿桑真诚而绝望的目光,无法跟阿桑分享父亲的关爱,他制造偷盗假象诬陷阿桑。阿桑父子决意离开,阿米尔并未如释重负,相反,罪恶感却加重了。
二 男权崇拜的消隐与自我反省
阿米尔与父亲流亡到美国后,他们作为阿富汗人的异域身份凸显出来。阿米尔和父亲住在破旧的民房里,父亲在加油站干活,他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后来,他们收购旧货到二手市场去卖。父亲曾经的风采与神性不复存在,他身负的男权色彩也一点点消退。“对爸爸来说,美国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5]125父亲对阿富汗曾发生的一切耿耿于怀,作为曾是阿富汗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为失去的感到痛心,独自哀叹:“美国,甚至世界需要一个强硬的汉子。”[5]122言外之意,阿富汗政府当时需要捍卫自己的国家,捍卫以“父亲”为代表的一群人的过去。父亲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拒绝参加英语培训班,拒绝接受移民局赠送的食物券,在美国商店,他为对方要查看身份证而大为光火。由此,父亲变成一个弱者形象,作为男权象征的他出现垮掉的迹象。美国对阿米尔来说“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5]125。他将心灵上的愧疚淡忘,阿桑不在了,无人跟他争夺分享父亲的呵护与关爱。在处理父亲与美国文化冲突时,阿米尔以成人的姿态去解释、道歉,提议替父亲报英语补习班。逃亡美国后,阿米尔全然摈弃曾经对父亲盲目的迷恋与崇拜。相反,他开始同情父亲。吃饭时,“我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5]126。在得知父亲患癌症后,阿米尔找来《古兰经》,跪在地上乞求自己不曾相信的真主。父子相依为命,彼此认同。在阿米尔高中毕业时,父亲对他说:“我很骄傲,阿米尔”[5]127。父亲在阿米尔上大学前为他买了旧汽车。父子深情将阿米尔从父权崇拜中拉出来并让他体会到人间温情的宝贵与珍惜。
阿米尔对美国这一异域文化心存热爱。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城市之外有城市……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还有更多城市,更多的人群”[5]132。他认为美国没有鬼魂、没有遍地的地雷、没有阿桑那样的兔唇儿童、没有被草草掩埋的儿童,没有罪恶。“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5]132阿米尔对的美国欣然接受似乎也暗示着美国的某些诸如独立、自由等标签会对其产生影响。小说里,阿米尔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确实表现出独立意识,他告诉父亲将写作当做未来事业。父亲反对,希望他去学医、学法律。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5]130。这俨然说明,阿米尔已放弃对父权及男权的崇拜,走向独立。虽然他爱父亲,同情父亲,但他已跨出摈弃父权的一大步。
阿米尔摈弃父权崇拜的最为明显例证,就是他爱上阿富汗失足少女且要娶她。索拉雅,塔赫里将军的女儿,正宗普什图人。她曾跟人私奔,被将军拿枪逼回来。在阿富汗,失足少女为人不齿,“自那以后媒人再也不敲将军家的门了。”[5]137“阿富汗男人,尤其那些出生名门望族的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几句闲话,数声诋毁,都让他们落荒而逃”[5]143。尊严与名誉对阿富汗男性多么重要,这也体现出阿富汗社会的典型男权特色。阿米尔是阿富汗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的唯一儿子,母亲也是被公认为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祖上是皇亲贵胄,他的祖父是一个万众景仰的法官。阿米尔也是出生名门。但他摈弃男权意识并为“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5]144。父亲病逝前,阿米尔恳求他前去将军家求婚。新婚之夜,阿米尔与妻子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5]166。对阿米尔来说,女性或者母性的回归,无疑了遣散他内心存留的那一丝男权崇拜,他的世界开始平衡。
正是父子间的深情与扶持、美国异域文化的影响及生命中母性的回归让阿米尔找到性别情感上的平衡,帮他发现内心的自责与内疚,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他曾有过的民族及性别偏见,他对过去的背叛开始自省。父亲送车给他的那个夜晚,阿米尔激动而开心,父亲提起阿桑,“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堆铁手掐住了”[5]129。阿米尔开车去海边,他想起自己曾跟阿桑看海的约定;索拉雅教女仆读书认字的事,让阿米尔想起他曾愚弄不识字的阿桑及用晦涩字眼取笑他;索拉雅向阿米尔说起自己的过去,阿米尔“怀疑,在很多方面,她都比我好很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5]160;新婚之夜,阿米尔寻思阿桑是不是也结婚了;面对索拉雅的过去,阿米尔不在意,他认为他也有过去,且对过去悔恨莫及;出版第一本书后,阿米尔想起阿桑曾说过全世界都会读你的书之类的话;索拉雅不能生育,阿米尔认为:“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5]183……男权崇拜的消隐及生命里的母性补偿在阿米尔的自我反省中起到关键作用,阿米尔在自我回归及周遭温情的浸润后发现心灵及人性漏洞,他开始自省,这是他心灵救赎的铺垫。
三 对男权的反抗与心灵救赎
阿米尔对男性权威的崇拜导致他对哈桑的背叛,那么,自我救赎就意味着回头寻找这一引发罪恶的源头,这样,救赎才具有对精神背叛的等值补偿意义。阿塞夫对哈桑的性侵犯行为,这一行为在阿富汗可谓重罪,但当时阿米尔视而不见,也未举报,父权崇拜是阿米尔冷漠的根本原因。多年后,哈桑的儿子落到阿塞夫手中,成了他的小男宠。如果说阿米尔的父亲体现出男权的父性权威,那么阿塞夫则是阿富汗社会中的男性霸权代表。
青少年时期的阿塞夫已暴露出极端分子的端倪。当他提议性侵犯哈桑时,同行的伙伴面带迟疑,他呵斥他们为懦夫并声称哈桑只不过是一个哈扎拉人。在阿米尔的生日会上,阿塞夫能说会道、拍马阿谀,他送给阿米尔一本《希特勒自传》,这一细节无疑是阿塞夫未来人生的某种隐喻。阿塞夫还侵犯过他的儿时伙伴——卡莫,卡莫在流亡路上因精神崩溃而死。阿塞夫对法律、教法的藐视可见一斑。
在小说中,阿塞夫是塔利班政府的小头目,他的所作所为尤为极端。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思想,还是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发展到了不正常的状态,而塔利班政权却继续把它们视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并有意识地加以推动,于是塔利班政权开始向极端主义的方向迅速滑落。”[7]34塔利班在20世纪末“把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赋予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把自己打扮成复兴古老的‘民族’文化和传播普遍性的宗教价值的角色”[8]143。作为塔利班的一份子,阿塞夫极为残暴毒辣。他监督部下将犯有“通奸”罪的一对男女活活砸死,而这一切都是在“遵照”真主的旨意。一个为传播伊斯兰“宗教价值”的极端主义者,绝对奉行伊斯兰教法之源——《古兰经》。该经书在男女两性问题上,“要求男女平等,这只是伊斯兰教法妇女观的终极认识目标,但它降示在封建的阿拉伯社会,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社会,在这种时代,人们的妇女观深深烙上‘男尊女卑’的印记”[9]。此外,塔利班在1997年夺取坎布尔后颁行了一系列妇女、文化问题的法令,法令在女性教育、婚姻、就医甚至衣着方式上提出极为苛责的规定。[7]147这是塔利班政府对阿富汗社会男权至上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强化。因此,作为塔利班成员,阿塞夫的男权至上观念也有迹可循。更让人痛心的是,哈桑死后,他的儿子——索拉博——被阿塞夫从福利院带走并将其收为自己的“男宠”,甚至玩弄“男宠”是权贵尤其是民兵领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
至此,阿塞夫身上体现的男权至上思想已毋庸置疑。可以说,他是阿富汗社会的男性权威代言人。颠覆打倒阿塞夫这一具有符号意义的代言者及心灵之罪的直接肇事者,将成为阿米尔涤清内心罪恶感、获得内心救赎的唯一途径。面对阿塞夫,
阿米尔不再如幼时那样顺从忍耐,他选择对峙与反抗。他跟阿塞夫搏斗,那是他第一次跟人打架。内心充满恐怖,说话也语无伦次,被对方的不锈钢圈套击倒在地,几近死去,阿米尔躺在地上大笑,内心想着:“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5]279。此时,他获得内心的宽慰与救赎。在阿米尔男权意识的流变里,他逐渐认清父与子的关系,理解亲情与善意,摈弃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最为主要的是——阿米尔因崇拜男权而留下的心灵罪恶,在与阿富汗社会典型男权代表的搏斗中得到清洗与救赎。
结语
《追风筝的人》在救赎主题中还存在一条引线,这就是小说中的“我”与“男性权力”存在关系的流变。“心灵犯罪——反省——救赎”与“男权崇拜——摈弃男权崇拜—反抗男权”这两条线路彼此交织,互相影响。甚至可以说,阿米尔的救赎就是其自身对男性权威的认识过程。
参考文献:
[1] 余钢.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及其寻找的焦虑[J].电影评介,2009(5):47-48.
[2] 曾万泉.《追风筝的人》人物关系隐含的阿富汗民族关系[J].社会纵横,2013,28(3):259-261.
[3] 蒋小庆.救赎中的成长——从成长小说的角度解读《追风筝的人》[D].扬州:扬州大学,2010.
[4] 王建荣.《追风筝的人》风筝意象解读[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2):91-94.
[5] 卡勒德·胡塞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 卡尔文·斯·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包华富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7] 何明.塔利班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8] 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9] 马东平.论伊斯兰教法之妇女观[J].甘肃社会科学,2001(5):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