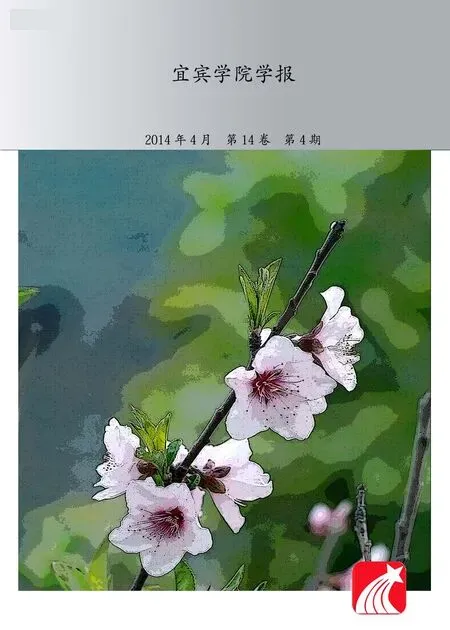对唐君毅谈朱陆异同源流之反思①
杜保瑞
(台湾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北)
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领域的浸润,实为当代中国哲学最深最广也最能引领入学的大家,值得作为所有学人学习的教材。但是,唐先生之文辞亦十分艰深,深遂入理而超越前人,既是将前人之说明白托出,更是要建立新旨深化其说,之所以有如此现象,关键即在唐先生自己的思辨能力过于强盛,又尽量以疏解会通为讨论的目标,而不在求其对立以畅遂己说,故其每每为先哲排难解纷而通贯各家,此举,未必能为其所论学派之门人所认同,但亦正显示唐先生的哲学立场与深厚学养。本文之作,将针对唐先生儒学诠释朱陆之争的问题,主要就唐先生于《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之《附编:原德性工夫,朱陆异同探源上、中、下三章》中之材料,进行讨论。限于篇幅,先进行上部,中、下两部,另待它文。 唐先生对此一主题之处理,实因缘于牟宗三先生的宋儒讨论,唐先生认为其意与牟意亦相同[1],但有意更为疏解,于是为朱熹建立了朱熹工夫论的三义,极有深意,值得讨论。以此为基础,便能汇通朱熹与两位当世敌论:胡五峰的察识说和陆象山的“先立吾心之大者”说。唐先生必是有所不同意于牟先生严分朱陆的立场,故有以感发。从全文三章之写作上来看,基本上,唐先生是采会通朱陆的立场的,而这种会通的立场本来就是唐先生中国哲学著述的一贯立场。但是,在唐先生的处理中,却亦有类似牟先生处理进路的立场,此即唐先生对朱熹谈工夫而基于宇宙论进路的反对立场,但宇宙论实不能分立于心性论、工夫论之外。唐先生其实就是不同意牟先生的做法,故为此文,但在他发挥贯通朱陆的思辨长才之后,却仍然保持与牟先生贬抑朱熹的某一特殊立场,这就使得他的汇通有了漏洞。 唐先生对朱陆之争的问题,从他以《朱陆异同探源》的标题讨论此一问题就可看出。唐先生是主张朱陆有异有同的。朱陆有争,即是朱陆有异,学界顺其所争言其所异者多矣,有些立论更创发新说以为朱陆之异建立截然对立的哲学体系,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学”系统中以陆、王为孟子嫡传,以朱熹为别子之说即是显例。劳思光“心性论中心”中说象山是心性论,朱熹是形上学的天道论、本性论亦是显例。但是,唐先生却在说其异中留下空间而更说其同,只是,虽说其同而仍保持其异。则此异便只是表面上的言义之别而已。就其能同而言,则是唐先生首先建立朱陆各自的源流,是皆在二程哲学中。然后就工夫论的路径而疏理朱陆之类型,类型中有交错,交错中能会通,更重要的是,都因不善解他人之意,故有对辩之冲突,若皆能善解,则朱陆互为之非议皆可不必,则便皆可会通了。所以,唐先生一方面盛说朱陆之真实思路,以求会通之路径,另一方面便重说朱陆之何以误解他说而致生嫌隙,以求嫌隙之解消。这才是唐先生发为此文之真正用意所在。
一 朱陆之异之根本在工夫论
世谓朱陆之别在尊德性与道问学,唐先生以为不然,关键不在此两路之别,而在尊德性的工夫论的不同,其言:
自二賢一生之學而觀之,其早年鵝湖之會中,于尊德性道問學之間,畧有輕重先後之別,不能即說為根本之不同甚明。而朱子與象山在世時講學終未能相契,其書札往還與告門人之語,或致相斥如異端者,乃在二家之所以言尊德性之工夫之異,隨處可證。[1]532
唐先生明讲朱陆两家之差异就是尊德性工夫的不同,而不是一做工夫一讲道理之不同。但说工夫论的不同即可,不必再加上尊德性工夫论的不同之说法,让工夫论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保持开放性定义,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处理问题,因为说是尊德性的工夫论时,其实已经为工夫论设下了框架。朱熹在作为学风格的差异定位,象山在作人格修养的批判。然而,无论是朱熹之比较,或象山之批判,皆不能等同于理论上朱熹主张道问学而反对尊德性,而象山主尊德性而贬抑道问学,此事皆无关工夫理论的主张,只是朱陆双方在为学风格及修养程度上的一次无谓的冲突而已。对于朱陆之别异是一种工夫论问题上的不同型态之事,唐先生认为朱陆都是尊德性工夫,但有路数不同,且非形上学立场的不同,上说诸义笔者皆完全同意,而且唐先生这样的定位真是正本清源,一扫牟、劳两先生从形上学进路说朱陆之别的失误。从形上学进路说朱陆之争的理论意义,来自阳明说朱熹析心与理为二的批评上,然阳明之意亦只能从工夫论上说,而不能从形上学处说,关键即在,朱熹讲格物穷理,谈理气关系,对此,阳明以求于心外之理批判之,故批评其为析心与理为二,此说即是阳明将朱熹说形上学、存有论的命题当作工夫论的命题,从而批评朱熹的工夫论不能心理合一,此说自然是错解。所以,这还是工夫论的问题,亦即阳明的批判本身亦未能说为是形上学的问题。从形上学处说朱熹析心理为二而象山、阳明是心理为一的则是牟宗三先生的创造性诠释,唐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不走牟宗三先生建立形上学体系之别异以处理朱陆之争的问题的路子,而是锁定只是工夫论意见的差异。朱陆工夫论绝对有可会通处,之所以两人意见对立,根本上是意气之争,就是两人都对对方人格修养的不信任的意气之争所致②。此义,唐先生于中、下部之文中亦提出:若善会解之,则两造皆可通可解,若不善会解,则势必引生种种怀疑、批评、误解与争辩。
对于阳明批评朱熹之为心与理为二之说,唐先生也为朱熹澄清。唐先生从工夫论进路说象山之工夫论主心理为一,但对朱熹是否有心理为二的主张,并不置可否,而是对朱熹被指称为心理为二的思路予以解释,这一解释就是说明朱熹是为了解决人有为恶之事实,因而对心理关系提出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诉诸于理气论形上学的问题,是在这个问题意识的脉络下而有的说心说理的二分。然而,理气论形上学问题的提出及意旨的界定,提供了朱熹讲工夫论的存有论架构,即是要先去其气禀物欲之杂,才能达致心理为一之境。然而要澄清的是,讲形上学而作的心、性、情、理、气的概念区分,并不是在主张工夫论上不能心理合一,更不是在主张主体不可能达致心理为一的境界。
确定功夫论是朱陆差异关键之后,唐先生要做的就是,首先将朱熹的去杂成纯的工夫设为三型,以收摄朱熹和五峰的对立,以及处理朱熹对二程的汰择。其次是在这样三型的基础上,建立与象山工夫论会通的路径。讨论至此,已清楚说明唐先生将从工夫论进路说朱陆之别异,而这个别异,却有共同的源流,即皆是源自二程哲学中。唯象山源于明道,而朱熹源于伊川。
二 二程为朱陆之源流
唐先生对朱陆同源于二程之说,有主要主张大程、小程分别对象山、朱熹的传承,这是继承意义的源流,但是也有反对的源流,亦即朱陆亦皆有对二程的反对意见。唐先生首先从朱熹的源流说起,对于朱熹与象山的差异甚至对立,认为这种差异对立,亦已源流于其对二程的反对意见之承续在。其言:
而朱子之不契于象山一型之教,亦不由對象山而始。實則朱子早對明道伊川以及上蔡龜山五峰之言之類似者,皆先已有所致疑。[1]535
这个置疑,就在朱熹对于工夫理论的关切,更为谨慎,并不是找到一套说法就畅为言说,而是不断地自我置疑,以找出最为完善统备的系统性做法,而这样的做法,正是在唐君毅先生的朱熹工夫论涵养、致知、察识三义中获得最佳的彰显。然而,唐先生特为平和朱陆,故又说朱熹之此三义工夫亦不能无弊。其弊之发生,正在主体必能自信本心一节,有此一节,发为三义,则里外备然矣。这样的说法已经是唐先生太为和会朱陆、平等两家而提出的说法。依唐先生后文详细的讨论来看,只要善会其义,象山之言亦无弊,朱熹之言亦无弊,有弊无弊一在善会意否,二在语言的本身有限制而已。不过,唐先生欲会通朱陆之用心无可非议,而此一作法亦等于提出一套新说以统编朱陆二说,然这又正唐先生明言谦辞之旨,亦即唐先生不会承认他自己又提出一套新说以统编二家,而只会承认他在沟通诸家之说③。
上文中,对朱陆会通的问题,有一伏笔,即唐先生对于朱熹本于伊川之涵养工夫中,对于心体的解释,唐先生谓伊川论中只一性体,不能为工夫。但朱熹之论中论心体,却是主敬工夫之本根,故又同于象山之旨。这又是唐先生自己限缩伊川之义而只以文字表面意思说之所致。伊川未说到并不表示伊川之意只是此义,伊川、朱熹意旨一贯,亦皆同于象山,伊川、朱熹、象山皆各有其所论之要点及所重之问题,故而有言语上之种种差别,且语言功能有限,一说既出似即遗漏众说,不特意限缩其义,即不必有许多的差异对立。唐先生为拉近朱熹与象山的距离④,不意竟推开了朱熹与伊川的距离。
总之,唐先生在二程源流中主张既有程朱之传,也有程陆之传。而就在这个分疏中,展现了唐先生理论绵细的深厚功力。他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深入讨论,便正是因牟宗三先生的研究结果所引发的。唐先生对牟先生之处理结果,有一些是同意的,即谓象山乃孟学之传,及对五峰之言受到朱熹之攻击之处,为五峰评议。笔者不同意牟先生处理的,端在对朱熹的整个系统的定位。而唐先生则说在牟先生尚未处理之处再为深入,其实就是不同意牟先生的立场了,只是用词宽和,不作冲撞而已。这就包括:朱熹之所以反对五峰、象山之说法,唐先生深入为朱熹作说明,以明其宗旨及说其合理之处。又为朱熹所论亦有如象山之高明之处,而甚至就说朱陆相近矣,此正如阳明言《朱子晚年定论》的做法是一样的,关键就在见到朱陆之间必有相同的本体工夫论旨。唯一让读者可以感叹的是,唐先生自己承认他的讨论实在翻折太多、太过援引推说,但这也不是学术的缺点,故都须接受。总之,唐先生为朱熹批评五峰、象山之说评议其理,就是不同意牟宗三先生的立场,牟先生只为象山、五峰评议,也只有五峰、象山直承孟子之旨,而朱熹为别子,此一立场,即非唐君毅先生的立场。至于朱陆之通邮,那就更非牟先生能接受的了。无论如何,唐先生欲解开牟先生过于严分朱陆之紧张局面,值得肯定。
三 陆象山为二程之传之分辨
历来程朱并称,则指程颐与朱熹,但唐先生首先认定,象山亦需上溯二程,其言:“二家之思想之渊原,皆当同溯至二程,唯所承之方面则有别。”[1]538,那么,象山之传乃在程颢。其言:
吾今所以證象山之學導原于二程者,首擬指出象山之言「心即理,以己之心接千百世之上之下之聖賢之心」,據黃梨州宋元學案、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劉蕺山人譜雜記,皆載明道對神宗有同類語。曰:「先賢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又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此即與象山言「心即理」「四端萬善皆備」之語,幾全無異。然朱子所編二程遺書,未嘗載此語。[1]538-539⑤
依唐先生为明道、象山接合之处理,并不是很清楚,唐先生多引明道文,又接引象山文,以为两者有共同的立场意旨,此时,才清楚定位出明道、象山宗旨:
此皆是謂在此第一義之工夫上,只須正面的直接承担此心此理,更無其他曲折,或與人欲私欲雜念相對而有之工夫可說;亦皆與盂子即就人之四端之發,而加以存養擴充之工夫,同為一直感直達之明善誠身之工夫也。[1]540
唐先生说明道、象山之别异之论点,才真正是有学术讨论的要点。唐先生为此发明一套说法而以明道之工夫为一横面型,而象山的工夫为一纵面型。因其横面中涵摄天、道、理、气等概念,知天道不离气禀,且气禀对天道有一限制,虽求其一贯之旨,但初仍未在此诸概念上加以更多的讨论,而是之后才由伊川为之析理分解,故而明道之说首先开出伊川之重去气禀之恶之系统,继而由朱熹继承之。若依此说,则明道开伊川、伊川开朱熹,明道竟非象山之端续矣!唐先生强调,因明道之横面说法,故而不能离物与气以言工夫,故而下开伊川重气禀之说,重谈气禀对人之限制诸义。此正是伊川面对的重要的哲学问题,但这就展开了伊川与象山之工夫论的不同传统的讨论。唐先生言以伊川天资不如明道,故须重谈去此气质之昏蔽之事。天资高低必有标准,但绝非就哲学家所主张的工夫理论的类型决定高低,只有工夫论的不同类型而已。唐先生又谓伊川之涵养进学工夫,较明道之以诚敬存之的工夫更为落实,此说亦得成立,但明道就是在讲成境界后之功力展现,伊川正是对所有的人的正常工夫之开展,给予明确的进路程序,故而才能落实。
唐先生说象山是明道之传,但明道亦开伊川继而朱熹之理路,那么,象山、伊川之分别在何处?唐先生自己又进行了不少的讨论,最后仍主张两边可通。唐先生说到伊川之思路,此一思路基于存有论的主体实践架构,要谈做工夫时的主体实践架构的转折变化,就是这样的命题语句,至于直接谈主体的实做,就是象山讲的本心之自明,但本心之能够自明,实赖形上学问题中的性理之本善为基础,而所要自明的本心亦是藉此自明去其已存之昏蔽,可以说,伊川讲得完整明白,就主体之先天后天状态而说及去恶向善的结构及历程;象山讲得简易直截,直接谈主体活动在主宰之心之一边中事,伊川、象山两路本就有可通之处,而不必以为互相否定。两套理论功能不同,没有反对的必要。象山对伊川,谓其“若伤我者!”是因为象山直接处理心之发动,故不须了解这许多复杂结构,觉得反若伤我。但是若要为此一心之能发动而得与理合一之事,求其理论上的可能性时,此时即是形上学地谈的问题,此时即是需要提出气禀说、性理说之形上学之理论矣!以及去蔽求真、去人欲存天理之工夫论的命题矣。伊川说理论结构,象山说做工夫,因此,性究竟能发不能发?这是语意约定的问题。依伊川,谈发就在心上谈,心统性情,性为心之理,则心之发时即有如理之可能。唐先生后文亦是如此说伊川之意旨。唯中间一段唐先生替象山提出反对伊川的说法,根本上是象山不必反对之理论,也是唐先生不必为象山说明的理论。这是唐先生刻意委屈伊川意旨,而又努力会合朱陆意旨而作的界定。
明道而后有五锋,相对而言亦为朱熹之敌论,依牟先生之理解,五峰、象山自是一圆圈的两往来,故亦已会通。依唐先生,五峰亦为象山之一源流,唯本文着重朱熹及朱陆之间,此一讨论就暂时不进行,后文在处理朱熹时仍及于五峰。
四 朱熹为二程之传之分辨
唐先生认为,无论象山是否自觉,象山确实是承自明道、伊川、龟山、上蔡以至五峰,此处诸家皆是圣人直往会得此心与理一之旨。唐先生以心理关系说朱熹与陆象山对二程之不同源流,以“心以性理为内容,而主心与理一”,说陆象山的源流;而以“心性理之关联于气禀,故心与性理不一”,说朱熹的源流。其实,象山对伊川之言有疑,站在象山自己的立场,当然不是像唐先生所说的“心以性理为内容故心与理一”之思路,这是经唐先生会通的结果。然就此一路而言,也必须是陆象山的工夫论进路之“心即理”命题的形上学预设,更当然是朱熹“心性理关联于气”时的本体论进路的形上学之理论预设,至于“关联于气而说心与理不一”,则是就主体在凡夫位尚未做工夫时的状态说,故而有不克制气禀之私即有为恶之行为之可能,这是对主体存在架构的说明,是一理论上必须建立的系统,陆象山亦不能反对,甚至亦接受而有时用之[2]。当然,从主体结构处说之工夫,就是要去己私、去人欲,由于已预设了有“心以性理为内容”的形上学立场,故直下本心,自信得及,即是工夫,这就是象山的话可以成立的依据,也是象山与唐先生上述二路皆可会通之背景。
唐先生即依此心之是否关联于气,及所涉及之工夫论要点,以说有下学、上达两路之别异,力为朱熹求其思路之所经,及其理论之所以成立的种种转折。其言:
其悔後之所悟,則在識得吾人之原有一「未發而知覺不昧」之心體,而以在此處之涵養主敬為根本工夫,以存此心體,而免于氣稟物欲之雜,使「吾心湛然,而天理粲然」;更濟之以格物窮理致知之功,而以此所知之理,為一切省察正心誠意之工夫之準則;乃還契合于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者,為「體用本末,無不該備」之說。(王懋竤、朱子年譜卷一下)此涵養主敬,在朱子又初為致知之本,應屬第一義,致知以窮理屬第二義,而其前諸儒所謂察識之功,在朱子,乃應位居第三矣。觀朱子所言之涵養主敬與窮理致知之工夫,其精切之義之所存,亦初純在對治此氣稟物欲之雜。[1]553
本段文字,就是唐先生为朱熹量身打造的工夫论之三义,亦即,朱熹言于工夫时,为对二程所言之工夫,补其不足而重新结构的系统。依明道,即为察识一型,由五峰承之,立为朱熹之第三义(即最末义)。伊川之涵养、致知两型,则改良第一型,接纳第二型,而为三型中的第一及第二义。此中改良涵养一型最有特殊意旨,此即唐先生又为朱熹找到会通陆象山的工夫论路子。朱熹谈已发未发工夫迭经数变,究竟转折后之最终要点何在?唐先生此说可谓已将其解析至一最高级的型态矣!重点即在一方面收纳察识说于第三义,一方面将涵养义上升为一积极的本体工夫,而为象山本心直显工夫之一类。此即极大差别于牟宗三先生将朱熹之言主敬只合于穷理,而穷理只合于抽象思辨的理气论,故主敬变成为哲学思辨的活动,干干扁扁,毫无本体工夫的意义了。
至于说朱熹的工夫论初在对治气禀物欲,唐先生即是以对治此一反面者之工夫为朱熹型,而以跳过此节直接呈现的正面工夫为象山、阳明型。就对治而言,须先叙明其非就圣人境界位之言说,而是就一般人的做工夫的讨论,就此而言,唐先生借朱熹谈已发未发问题而论,关键在,如何于意念未发前有一工夫,使得发皆中节。唐先生认为,朱熹之主敬工夫所思考的,是一纯粹无偏的本心工夫,是要直达圣境的本体工夫,在此保住,则能发皆中节,这就是工夫论所追求的目标,人能为此,已是圣人。朱熹要谈的是一般人在做工夫的问题,朱熹要思索的是一般人如何能如圣人一样地有一纯粹无杂的心的活动,那么,这就是做在意念、行为尚未发生时的功课。为处理此节,周、张、二程之思索,即是于念虑之初发生时,于几微隐动之际,用一工夫。而五峰之思索,则是在行为已产生,念虑已发作之后的察识。但唐先生认为,这样做都是念虑已经发出之后所做的工夫,故皆不纯,因而不能保证有圣境,故而朱熹对此有所疑虑,因此要有此种主敬工夫为工夫的第一义。此种工夫,就比前此周、张、二程及五峰的种种工夫更先、更隐微了。因此,唐先生的诠释,为朱熹的主敬涵养工夫建立一套比周敦颐的诚、神、几更先一步的工夫,更比程明道、胡五峰的察识于念虑之后更先两步的工夫。此一工夫,直逼圣人境之纯粹至善、从容中道、不思不勉、直心而发的路子。此一说明,可谓即是唐先生为朱熹建立的最深刻的工夫论的系统。
唐先生后面的讨论,要顺成朱熹的遥契圣人意境之依性理而发之工夫,即要建立直接如圣人境界者之直发而中节之工夫。唐先生仍认为伊川之说仍为已发之后的工夫,有所不足,言之不明,其仍为消极的不违或依于心外以反求之的工夫而已。而唐先生要为朱熹建立的,就是要在一真正尚未应事接物、情欲私意完全未动之前,能有一使主体得如圣境般纯粹至善的工夫法门。这一法门,真正是一种新工夫,伊川未及言之,虽与伊川之未发涵养同型,但义理更为精深一层,而为由杨龟山、罗豫章,至李延平所触及之者,即是其所发展出之“观未发气象”之说者。唐先生之后的论述进入了其特殊定义下的“观未发气象”之本体工夫、圣境工夫、直依性理而发之工夫之说。唐先生以朱熹老师李延平的“观未发气象”之说表之,指朱熹以其为自龟山之传而非伊川[1]562,此一工夫,确实是在事件未至之时,主体自己收敛心神,无有观念、事件之对象,纯粹一心之照见自己,这真是平日的工夫,而非事上磨炼之事。但它有一积极的意义,即是凝念于此一纯粹之意境中,使性理之呈现,得有一出口,在未临事应物之先,能有一主体的自修活动,此即不同于伊川之言未发涵养之只茫茫然无所应、无所主的涵养形式,更有一收敛贞定的实义,此一“观未发气象”就是要直逼出心以性理为内容的性理直发之圣人气象,使发而皆中节矣!但此一工夫在延平只停留在“观未发气象”,然在朱熹,却是以此为基础,配合伊川“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架构,则展开格物、致知、穷理的客观原理之追求之工夫,则内有主,而外应事,再加上五峰型之应事接物时之念虑已发后之时时察识之工夫,则朱熹工夫之三义圆成。故而唐先生自信此确为一新工夫论矣!此一新工夫,唐先生明白认为确与伊川简易之言未发涵养及五峰畅意之言心皆已发两说不同。唐先生认为,五峰察识说只能成功于在圣人分上之已发察识上说,以寂然不动是状心非状性,是说圣境是五峰所追求,但所提出之工夫是发后察识,因圣境是在行动中的纯粹至善,而不是停留于一未发之虚理中,故而是心之已发之后的呈现,故是“善观者就已发而观之”之意,而非在未发处静观虚理之路径。此五峰之路。此路当然就凡人而言确有可疑,故不能是一全备之工夫论,故又另有一路以为修正,即龟山、延平之“观未发之中”之路,唐先生即提出由五峰型而对照出之延平型。唐先生为朱熹为对治气禀物欲之思路而创作之工夫论旨,可谓已为一全然是本体工夫的型态矣,而这仍是于第一义之涵养工夫所诠释而出的型态。形上学上预设有一浑然不偏之性体,心存此体以为心体,即可免于气禀之昏。为何?因其为未发涵养之工夫,此一未发之状态,是一未有事件临在、未有情欲思虑之出现之前之平日敬持之状态,故必得有敬持之功效,亦能保有一但临事得依性理而发的机制。此种涵养,方真有涵养之功效。
至于此一未发涵养性体寂然的动作与象山之别为何?就其发动而言皆是性体之发,唐先生为朱熹所持之论说较偏重于未有临事之前的平日工夫,不过象山之说则未分已发未发、临事平日,只要一动心念即是本心而起,此正是日常做工夫的共同状态。对于朱熹的新工夫论,唐先生之下文又有阐述,其说有两项重要意涵,其一为涵养之后辅之以穷理之说,其二为此一涵养工夫之本身即是一心呈性理、发而中节之工夫。唐先生说朱熹认识到性理本身无工夫,对心本身亦无工夫。此说有待疏解,说心上不能做工夫的话是不宜的,做工夫就是心在做的,且是对治于气禀之私而做的,至于如何谈此心上之工夫,则无定说,端视面对什么问题而说。
至于对此未发涵养之工夫是一心呈性理之工夫而言,这就是一般的本体工夫的理论模式,心内具性具理,但不一定呈显,因气禀牵扰,故于未有外物外事临在之前,即直接对向性理,使性理粲然于中,再加上格物穷理以知世间诸事及是非道理,而能处事应事,则内外一贯矣。此处,直逼象山之说,已难辨雌雄矣!
结语
本文之讨论,以疏解唐先生《原德性工夫(上)朱陆异同探源(上)》一节为主,唐先生意旨细腻,重在为朱陆与二程之关系重新张本,盛开象山、伊川之源,与明道、朱熹之统,真扫学界一般所说之窠臼。其言有理乎,关键即在善会意之时,种种哲学问题条理清晰之后即得说此。然在《原德性工夫(中、下)朱陆异同探源(中、下)》两节,唐先生又重新为五峰辩义,亦仍指出朱熹之所言亦非无弊,唐先生翻转之绵密,令人惊叹。然仍是有其合理之旨,重点还是善会意之还是限缩屈解而已。
注释:
①本文第一次发表于2013年11月16~18日在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举办的“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②参见拙著《南宋儒学》之《第十二章:鹅湖之会与朱陆之争》。
③参见其言:“吾即缘此以更进而详评朱子对象山之言不免有误解,与朱子所言之工夫论亦不能无弊。再继以言欲去一切圣贤工夫之弊,正有赖于人之自信得及如象山所言之本心。最后则就朱子所言本心之体之别于伊川,转近于象山之处,以言循朱子之学再进一步,即同于象山之教,而见二贤之论,正有一自然会通之途。故于此二家之言,不待于吾人之谓其无异,亦不待吾人之强求其同,更不待吾人之自外立说,将二家之言,各取一端,截长补短,为之综合。此则吾人之此文所欲次第申论者也。”载于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36页。
④参见其言:“然吾又确信殊涂自有同归,百虑终当一致,方见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则朱陆二贤之言,自应有通处。”载于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37页。
⑤参见“然今即据上所引明道告神宗之言,纔以立志定志为先,又谓必先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能充其道,择四海之同心一德之臣为辅;则亦未尝不隐涵通古今四海之贤圣之心之旨。”
参考文献:
[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台北:新亚书院研究所出版,1974.
[2] 杜保瑞.南宋儒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