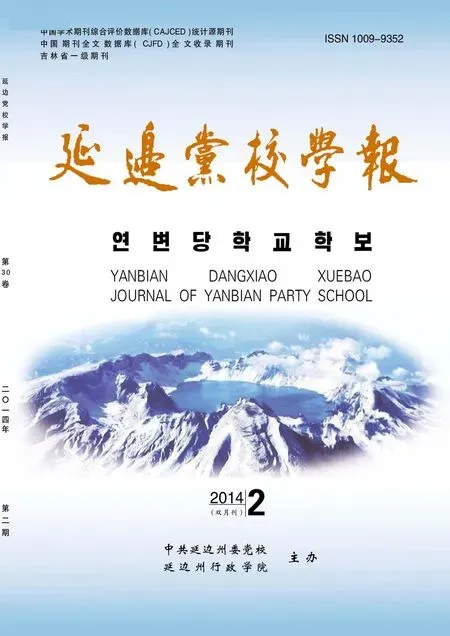关于“已满75周岁不适用死刑”条款的再思考
刘保丽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刑法上都享受到特殊的“关爱”,而对于同是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保护却只字未提。让人可喜的是,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将老年人的刑事责任与其年龄挂钩,弥补了刑事立法关于老年人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空白。对老年人从宽处罚与慎用死刑都是合理的,贯彻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的规定,符合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但笔者对现有的刑法条款仔细斟酌后遗憾地发现,从规范刑法学角度出发,刑法第49条第2款的规定脱离了我国老年人犯罪、司法实践以及社会保障等实际。
1 学说争议及评价
学界及实务界就我国刑法典第49第2款的争议可以追溯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审议阶段,最初关于老年人免死的规定表述为“犯罪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该内容当时立即引起了观点对立的两方观点,①笔者且将其分为支持与反对两派:支持派认为这样的规定是:(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2)刑法谦意性要求;(3)刑罚人道主义要求;(4)矜老恤幼传统伦理的体现。反对派理论根据在于:(1)该规定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刑罪一致”的司法精神不符;(2)对那些罪行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罪行,还是应当依法办理,年龄不能成为少数人享有“治外法权”的理由;(3)75周岁不适用死刑,可能会在司法实践中导致老年人犯罪数量上升。最终立法者采取中立立场,将75周岁老年人绝对不适用死刑规定了一个例外,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从两方辩论的理由依据可以得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该规定能否实现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效果?第二,当前我国规定75周岁不适用死刑是否存在巨大风险?在反方的呼声人数远多于支持方的情况下,虽然立法者补入“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进行调和,但是实际上立法者是站在支持派的立场,坚持原来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规定。然而,在笔者看来,该条款的意义仅在于对老年人刑罚轻缓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持肯定态度的一种表征,实际上却给司法实践和社会保障套上枷锁,固步自封,引发种种诟病。本文开头已经表明对老年人刑罚轻缓化持赞成的立场,诚然,赞成派的初衷也是从该立场出发,但是,支持派对于该条款一味地在宏观的立场上寻找理由,却鲜有把目光聚焦在该条款的仔细分析上,相比之下,反对派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刑法条文进行利弊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反对派不赞成该条款并不意味着对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反对。
2 关于“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年龄界限问题
多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是否有必要确定刑事责任年龄上限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学者撰文指出:“我国刑法中应当明文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理由主要是,人的年龄与其认识、辨别、控制能力存在自然的联系。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辨别、控制能力经历发展-成熟-衰退的自然过程。②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的生理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必定呈现出发展-成熟-衰退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生理机能的衰退与年龄的老化划上等号。但是,“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并非客观存在,刑事责任年龄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推定,将生理机能的衰退作为辨别和控制能力单一考量因素极不严密,忽略了老年人丰富的社会阅历、所知甚多的犯罪案件和犯罪方法、有犯罪前科的还有犯罪经验。有些法院办理的老年人犯罪案件中近一半犯罪老年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且涉及的罪名大多都为智力犯罪③。另外,由于老年人生理机能出现明显衰退,很多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等,“攻击”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老年人在选择犯罪对象时往往“专挑软的捏”,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例如,在巴南区检察院办理的20件70岁以上老年人犯罪案件中,有8件涉嫌罪名均为猥亵儿童、强奸罪。④由此得出,老年人对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实施犯罪较易得逞以及如何逃避刑事制裁都有明确的认识,可谓老谋神算而非意识上的衰退。因此,如果说老年人该主体身份与刑事责任能力有联系的话,也仅是在生理机能衰弱方面对《刑法》所规定的各种刑罚的承担能力有所影响,绝不意味着作为犯罪构成所要求的主观方面上的欠缺。
可见,以规范刑法学的角度看来,规定75周岁不适用死刑似乎很难从最能表征老年人犯罪主体身份特征的“刑事责任年龄”这一概念中得到解释,但是这样的规定似乎也没有实现支持派一贯主张的刑法人道主义和歉抑性的念想。理由如下:第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2.38岁,女性平均寿命为77.37岁,均在75周岁以下;第二,老年人犯罪年龄段集中在60周岁到70周岁之间,70周岁以上的的犯罪群体在老年人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第三,在老年人犯罪群体中绝大多数为男性,而男性的寿命一般比女性短4、5年;第四,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每年就几起案件,75周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触犯死刑的案例。因此,立法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作为免死界限,形式上看是在响应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但在司法上能够符合“已满七十五周岁”主体条件极少,使该规定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意义。另外,该立法在违背了“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之事”这一法律格言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新隐患。
3 关于“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风险考量
关于“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而“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有必要回答或者解决如下两个问题:
3.1 “75周岁不适用死刑”规定是否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
有学者认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仅仅指的是在刑法制定之后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定罪量刑。至于刑法制定时能否体现‘人人平等原则’,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也不能这样‘平等’地制定刑法,因为采用‘人人平等原则’来制定刑法,那将会使刑法条款千篇一律,不会有任何差异。对‘已满75周岁的人’规定免死条款,这属于刑法立法问题,无所谓是否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⑤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已满七十五周岁老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不符合这个法制原则,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之规定,岂不是也违反了这一原则?”⑥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值得商榷。在提倡实质法治的当代,笔者很难苟同在立法阶段不以“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作为立法宗旨,立法不平等更何谈司法上的平等。而我国刑法规定“未满 18周岁的未成年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均不适用死刑”,其立法依据在于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主观上对许多问题无法做出独立且正确的判断,欠缺刑事责任能力所要求的辨别和控制能力。刑法对认识因素欠缺的行为人给予照顾,是为了避免客观归罪。刑法对孕妇的宽宥,是基于其腹中的孩子,避免殃及无辜的生命。而已满 75 周岁的老人对社会的认知较为成熟,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因为其高龄而受影响,其刑事责任能力并未因高龄而有所欠缺,在主客观犯罪构成要件范围内老年人犯罪与其他人犯罪完全没有差别,如果仅考虑高龄这一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量刑情节而不顾其罪行极其恶劣一律不适用死刑,难免有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现行的刑法体系下也没有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在法律上承认实质的不平等,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才能真正符合平等的要求,这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实质平等。⑦高龄老年人毫无疑问是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一员,但是老年人在犯下极其恶劣的罪行时就不止老年人一个弱势群体,还有受害者,保护人权首先应当保护受害方的人权,这才符合正义原则,更何况老年人往往专挑弱势群体作为犯罪对象。因此,对于穷凶恶极、人身危险性极大的老年犯罪分子,很难再将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看待,人民群众的情感也无法接受。
3.2 “75周岁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是否会导致老年人犯罪大幅上升?
有学者认为,这种担心或者质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到了七十五周岁以后,其身体条件逐渐衰退,有的行动都不方便,哪有条件再去犯罪呢? 至于“身强力壮”还想去实施犯罪的老年人则是为数极少,而其中对老年人判死刑的案件更是寥寥无几。⑧在笔者看来上述理由:一方面,暴露了该立法在实践中恩惠到的老年人少之又少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却是在用这一华而不实的法律条款冒险。
从司法实践看,我国老年人犯罪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可以说,现行的刑罚制度对年老者适用的机率是相当少的。在罪行轻重与刑事责任大小成正比的情况下,人们在实施重罪时往往会更加审慎地衡量利弊。刑法关于75周岁免死的明文规定意味着给高龄犯罪者极其严重罪行的处罚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在意图实施严重暴力性犯罪的准备阶段,就会少了许多顾忌,导致老年人犯罪的增多,甚至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审判的时候”的时间界限也可能造成犯罪分子事后积极潜逃到75周岁,此时,刑罚不但达不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反会刺激人们去犯罪,体现出一种负效益。这些风险不是不可能出现的。面对当今未成年犯罪人员组织化、手段成人化、结果严重化等特征的出现以及利用怀孕妇女贩毒等问题,不能否认立法上给予未成年犯和怀孕妇女的优待与此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⑨所以,在对待老年人犯罪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重视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
4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调和效果考量
或许立法者也意识到老年人绝对不适用死刑过于绝对存在巨大的风险才补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除外”作为例外以应对实践中各种复杂的情况,即便如此,很多学者仍然批评该条款的规定表述的范围过于狭窄,如果除外情形只局限在致人死亡这个后果,其他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就被排除在适用死刑范围之外,比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等。另外,“特别残忍的手段”这一表述过于主观。适用死刑的标准还是应该以被告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后果、社会危害性为尺度。⑩
虽然在致人死亡法益之外还存在着危害程度相当的法益侵犯罪行,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罪,从事贩毒活动等严重罪行,但是作为刑法总则意义上的“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未对罪名适用范围作进一步限定。 因此,“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可能存在于刑法分则所有涉及“致人死亡”的故意犯罪中,例如放火、爆炸、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绑架、抢劫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暴力性犯罪。因此,这样的表述不存在太大问题,基本上能够囊括实践中常见的数量微少的老年人所犯的严重罪行,这样的规定体现出刑法对老年人的谦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又做到社会保障之实际。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所担心的范围失之过窄的真正原因在于“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这一限定条件。理由如下:第一,“特别残忍的手段”这一表述过于主观。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得到的结论也会不同,如果是死者的家属,他肯定会认为是残忍的手段。对于手段特别残忍的具体含义,当前立法、司法机关并未作出明确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法官自由裁量,很容易导致量刑偏差和司法混乱。第二,立法如是规定意在对存在“罪行极其恶劣”的死刑适用情节时加上“以特别残忍手段”作为限定条件以实现对老年人刑罚宽宥的目的。因此,“以特别残忍手段”这一情节的危害后果应当比适用死刑的通常条件即“罪行极其恶劣”更加恶劣,但是新刑法在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下,适用死刑的罪行必定是达到了非杀不可的程度,很难说有比“罪行极其恶劣”更加严重的罪行了,因此“以特别残忍的手段”与“罪行极其严重”之间很难说存在层次之分。第三,立法加上“以特别残忍手段”这个限定条件意在给原本应该判处死刑的老年人另外一条活路,但是这样的规定反而本末倒置颠倒了刑法一般逻辑,使得实施危害社会的手段却成为适用刑罚核心关键情节,而犯罪的本质——社会危害性却及不上行为的重要程度。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利用下毒的方法造成数百人死亡所判处的刑罚反而比与碎尸一人判处的刑罚来的轻。第四,该条款如是规定也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条“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中要求考虑的多种情节一概拒之门外,这样的规定难免过于僵硬。
5 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高龄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思考


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高龄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如何实现一般预防及公平正义似乎陷入更大的困局:一方面,部分老人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刑罚对其已经没有多大的震慑力了;另一方面,对罪行极其恶劣的高龄老年犯罪分子虽判处重刑往往有很多刑期没有执行,等于没有刑罚(犯罪分子多为男性,寿命更短)。因此,在我国尚未具备废除死刑条件的背景下,基于一般预防和公平正义的考虑,对于罪行极其恶劣的老年人处以生命刑及相应的名誉的剥夺看来是有一定必要的。
结语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仅两年时间,但是不能为了法的安定性就停止追求真理的步伐,特别是在该条款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的情况下。“75周岁免死”条款看似传达了刑法对老年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废除死刑论趋势的靠拢,但是不管是对老年人刑罚轻缓化的落实还是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都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我们应该看到距离老年人刑罚宽宥化实质轻缓之路仍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为笔者惊讶地发现对老年犯人从轻、减轻处罚以及缓刑宽宥的年龄界限均在75周岁高龄!
【注释】
①郑赫南:《刑法拟“75岁免死”引争议 委员称或导致老年人犯罪上升》,http://news.jcrb.com/jxsw/201008/t20100826_407496.html ,2010-08-26.
②马柳颖:《对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探讨》,载《政法学刊》第26卷第2期,2009年4月,第30页.
③李松,黄洁:《近半老人所涉罪名属智力犯罪》,载《法制日报》2010年10月15日第005版.
④徐伟,黎小锋:《60岁以上老年人犯罪案逐年上升》,载《法制日报》2011年11月28日第005版.
⑤孟庆华:《“已满七十五周岁不适用死刑”条款的理解适用》,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1 年 12 月第 23 卷第 6 期第10页.
⑥方一凡:《顺应现代刑法发展潮流之举》金华日报2010年09月13日第005版.
⑦马留颖:《对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探讨》,载《政法学刊》第26卷第2期,2009年4月,第34页.
⑧孟庆华:《“已满七十五周岁不适用死刑”条款的理解适用》,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1 年 12 月第 23 卷第 6 期第10页.
⑨参照郑鸿鹄,张莉:《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 年 2 月第 22 卷第 1 期第108页:“香港大律师公会曾提出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由7岁改为10岁,但港府保安司及律政署有关负责人等却反对修改法例,拒绝提高年龄,理由是:第一,若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将被有组织犯罪有机可乘;第二,不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可避免传递错误讯息给青少年;故此认为维护现有刑事责任年龄不变,是必要的。 第三,如果改变责任年龄可能令父母难以在儿童幼年时向他们灌输尊重法律的观念。”
⑩陈丽平:《老年人“免死”是否应有限制条件》,载《法制日报》,2011年1月4日第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