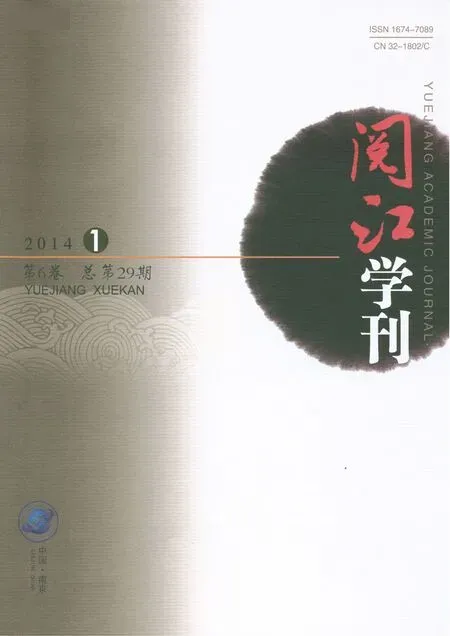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研究在中国考察
丁国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研究在中国考察
丁国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一直存在,然而,新时期以前,学术界更多的只是译介他的著作,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而且这些研究基本还带有政治的眼光,不能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新时期之后,由于摆脱了过去认识上的政治思维模式,人们对他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有规模地展开。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异常丰富复杂,从“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总体研究”、“关于艺术起源问题探讨”、“对功利和审美问题的探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几个方面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始终围绕并且从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指导,他对艺术问题具有独特性的认识与主张。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思想做庸俗化、机械化的理解是错误的。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中国研究
鲁迅先生曾在《艺术论》“译者序”中说,普列汉诺夫“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打下了基础。……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1],称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2]苏联当代美学家M·卡冈在《美学史讲义》中则指出:普列汉诺夫的“大量著作对几乎所有美学基本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3]。而苏联时期作为师范学院“俄语和文学”专业学生用教科书《十八世纪——二十世纪初俄国批评史》则认为,“正是因为普列汉诺夫,俄国的文艺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哲学方法论,在经过民粹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幼稚的学理主义领域的30年徘徊之后,重新走上了19世纪世界革命和理论思维的道路。”[4]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个人贡献上几乎无可挑剔的理论家。
一、普列汉诺夫译介、研究简况
普列汉诺夫著作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是1923年11月19日至1924年2月27日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的译名是《社会改造中之两大思潮》,翻译者署名“一鸿”。1924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三期刊登了普列汉诺夫著、郑超麟译的《辩证法与逻辑》,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明介绍。普列汉诺夫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有两个版本来源:一是日文本;二是俄文本。鲁迅、瞿秋白、冯雪峰、杜国庠、张仲实、博古等人都曾经翻译介绍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普列汉诺夫著作的各种中译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入门书、参考书,帮助和培养了那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
据初步统计,解放前,从1929至1949年这20年间,中国各个出版社共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4部。[5]建国以后,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的三十年间,我国在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文艺论著方面不仅更新了不少原有的译文,而且新译了许多重要的论著。其中,陈冰夷、吕荧、程代熙、曹葆华四位同志译文的数量较多,贡献较大。曹葆华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数量最多,贡献最大。[6]解放后,我国普列汉诺夫文艺论著的翻译出版和文艺思想的研究论述,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至1973年这一阶段,有大量的普列汉诺夫文艺论著的翻译出版,《论艺术 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艺术与社会生活》(陈冰夷译)、《论西欧文学》(吕荧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等先后重译或新译。1979年以来这一阶段,除曹葆华译的两卷集《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①(1983)外,主要译著还有程代熙的《普列汉诺失美学论文选》(1983)等。可以这样说,普列汉诺夫论著的译介在我国出现过三个高潮,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其文艺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从译介之初到今天一直没有停止过。
1982年,有学者撰文统计,“一九二四年到现在的五十七年间,我国共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著作不下三十种,约五百六十余万字。按字数算,在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外的所有外国哲学家著作汉译中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解放后三十二年,国内没有出过一本反映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专著。”[7]进入新世纪之后,有文章统计建国后的普列汉诺夫研究认为,从1949年到2005年,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著有10本,主要涉及哲学的有4本,美学的有3本,1本是评传,有关著作相关章节涉及到普列汉诺夫的有10本左右。[8]实际上,这些被提到的著作基本又都是在新时期以后出版的。
1987年,王秀芳《美学·艺术·社会——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专著。作者论述了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评述了普列汉诺夫关于审美与艺术的起源、审美的特征、艺术的木质和社会作用、艺术与阶级斗争、艺术与社会心理、艺术的相对独立性、文艺批评、现代派艺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等方面的理论。该书还设专章介绍了普列汉诺夫本人,他的美学活动及主要美学著作,国内外对他美学思想的研究与评价,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地位。[9]除王秀芳这一著外,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研究还有全国马列文论编委会编《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论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马奇《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楼昔勇《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这些文集或著作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比较全面地对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各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其中,楼昔勇的著作按“审美的一般理论”、“艺术的一般理论”、“艺术批评的理论”三编十二章展开,把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体系基本勾画了出来,同时,本书善于从历史联系中来考察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并能对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冯契认为,该著“是一本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对于提高美学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能起到良好作用的。”[10]
二、普列汉诺夫社会学文艺观的基本内容
普列汉诺夫一生经历了多个思想阶段,自20年代始至今,国内外对普列汉诺夫政治、理论活动阶段划分有多种意见,比较详细地划分可分五个阶段,分别是民粹主义时期(1875—1883)、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08)、反对取消主义时期(1908—191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818)。这一见解是我国学者高放和高敬增提出的。[11]由于普列汉诺夫思想一生中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1903年以后,其思想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影响到苏联学术界对他的思想价值评介的不同说法。不过从总体上说,普列汉诺夫主要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他蜕变为孟什维克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和孟什维克派同流合污,而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与思路研究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还说过:“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12]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有许多独特的理解与贡献,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到列宁主义出现以前,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高水平。”[13]新时期以前,对普列汉诺夫思想更多的只是译介,研究的比较少,而且很多研究还都带着政治的眼光,不能客观认识他的真正价值。新时期之后,人们对他的研究才真正有规模地开始。
(一)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总体研究
新时期之后,吴元迈较早通过论述普列汉诺夫有关无产阶级文艺的基本思想,在科学认识普列汉诺夫方面给学界带了个好头。吴元迈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应当以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全部指示为准绳,来评价他的文艺遗产。正是列宁无情地揭露了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和对革命的背叛,同时又高度地评价了他在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上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所起的作用。”[14]这一主张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遵守的。在另一篇文章《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中,吴元迈对普列汉诺夫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及其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批判“四人帮”一伙在“纪要”中借口“批判”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实则全盘否定现实主义的奇谈怪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问题,无疑都是一份宝贵和重要的材料。[15]印锡华1980年的研究文章,同样认识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遗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及其总体上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文章指出,普列汉诺夫在精辟地指出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的同时,还研究了这种依赖关系在实践中的复杂表现,他十分重视在“劳动和艺术之间形成了一些中间性的东西”[16],这些构成了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遗产中具有特殊价值的部分。普列汉诺夫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种种艺术的创作和理论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篇章。[17]吕德申则在文章中十分看重普列汉诺夫对文艺上现实主义理论所做出的诸多有益的探索,在艺术发展的规律及意识形态研究方面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对艺术影响的“中间环节”中“社会心理”、阶级斗争因素的重视,以及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的探讨,等等。[18]樊大为也在文章中结合普列汉诺夫的具体著作,探讨了普列汉诺夫在诸如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文艺的特征和创作原则、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上所作过的精辟阐述。[19]这些论述都表明,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是始终围绕而从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指导的。
赵宪章探讨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社会学思想,他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继丹纳创立文艺社会学体系之后,第一位给文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的解释的巨匠”,普列汉诺夫对文艺社会学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三方面的突出贡献:第一,“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普列汉诺夫文艺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第二,注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文艺现象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社会学的重要特点;第三,在对文艺现象进行解释和研究中,普列汉诺夫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创立了以“五层楼”公式为主要内容的文艺社会学方法论系统。[20]王秀芳也认为,“这个‘五项因素公式’是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概括的一个公式,也是他研究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总纲。”作者从关于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关于美感的特征、关于艺术的本质与社会作用、关于艺术与社会心理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21]陶东风研究了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史观,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史观的主要来源是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泰纳的文学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普列汉诺夫文艺史模式的特点有两个:确立了经济关系决定论,提出了社会心理中介论。“从泰纳、勃兰兑斯到普列汉诺夫,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就在于将文学史的基础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而社会心理学说的运用和阐发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22]卢那察尔斯基在他晚年完成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中认为,“正是普列汉诺夫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基础”[23],对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家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心峰的文章就集中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巨大贡献,作者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学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主要在于他明确地宣告:艺术理论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探讨了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因素,尤其是提出“社会心理”这一中介环节或中介因素;对艺术的本质即“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富有个性特点的、有价值的理论追寻,把它作为建构自己的艺术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对于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作了深入系统的探讨。除此之外,普列汉诺夫还广泛讨论了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作用,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的复杂关系,美感的直觉性特点与理性内容的对立统一,等等。[24]以上各家在探讨普列汉诺夫艺术思想的社会学面貌时,都十分重视普列汉诺夫对艺术独特性的认识与论述,避免了对普列汉诺夫社会学文艺思想的庸俗化、机械化理解。
在研究中,有学者们注意到,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观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陈复兴认为,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的观点——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一个时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关系揭示出艺术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从而认定“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任何艺术所具有的功利主义性质,这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一大贡献。他还从普列汉诺夫重视艺术的思想性,捍卫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等方面对这种功利性进行论证。[25]刘文斌也认为,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地存在的,他通过分析普列汉诺夫对“纯艺术”论的批判来证明这一点。文章认为,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地剖析了“纯艺术”论的荒谬性、产生原因及其对文艺发展的影响。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普列汉诺夫以大量事实说明:“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地存在着的,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26]艺术的功利目的主要靠作品的思想内容去实现。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是由阶级斗争的形式所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深入考察了“纯艺术”论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对“纯艺术”论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批判。[27]与以上两位学者的探讨略有不同,王又如在对普列汉诺夫功利主义艺术观的探讨中,则更多地反映出自己对于功利主义艺术观的批判性反思。作者认为,对艺术的功利要求与功利主义艺术观是两个内涵与外延都不相等的不同概念,不能相互混淆,对艺术的功利要求不应当归结为功利主义。“人们衡量艺术,不仅有功利标准,而且有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前者必须融合于后者。如果把功利要求变成不顾艺术规律的唯一的、简单的和直接的要求,就成了功利主义。”由于没有将两者区别清楚,普列汉诺夫就不能在肯定对艺术的功利要求的同时,彻底地否定功利主义艺术观。事实上,功利主义艺术观给整个文艺的发展都带来损害。“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主要通过审美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它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也必须通过审美的方式才能实现。离开审美特质,便不能科学地说明艺术。”“普列汉诺夫只看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片面性,却没有看到功利主义艺术观的片面性,这恰恰说明,普列汉诺夫关于功利主义艺术观的论述,并没有以他对审美活动和功利活动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它反映出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复杂矛盾。”[28]文章在艺术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中探讨艺术功利主义的利弊得失,有理有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与思考。
(二)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
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下就国内学者探讨比较多的艺术起源问题、审美与功利的关系,以及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再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对于艺术起源问题,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艺术起源于劳动”,并认为这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一些文学理论教材也基本持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发生学的重要思想。新时期以后,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人的主体情感,或者起源于原始人爱美的天性和他们的社会实践,“劳动说”忽视了艺术的自然根源以及原始人从事艺术创作的生理基础,等等。这些质疑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也发动了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张育新认为,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公式说成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不对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并没有提出这个公式,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远比“劳动说”全面、深刻。“普列汉诺夫在对艺术起源问题的论述上,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从艺术与其社会根源的关系上,他认为原始艺术产生于原始人维持生存的物质活动之中,而不仅仅是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从原始艺术的创作本身看,他认为原始艺术产生于原始人在物质活动中引起的特定感情思想的形象表现,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出来的。”[29]《文摘报》1983年第81期以《艺术起源于劳动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为题摘登了张育新的文章。针对张育新的观点,何梓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尽管普列汉诺夫没有简单地作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结论,但他强调艺术对生产劳动的依赖关系。‘艺术起源于劳动’不是普列汉普诺夫关于艺术起源问题的全部观点,但却是他的主要观点;生产劳动不是艺术起源的唯一因素,却是主要因素,因此,不能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不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文摘报》在摘登张育新同志的文章时所加的标题是不确切的。应该说,艺术起源于劳动,又不仅起源于劳动。艺术起源于劳动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并且是他的基本观点。”文章还针对张文论述艺术起源提出的“原始人在物质活动中引起的特定感情思想的形象表现”、“艺术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出来的”等观点,进行了批评性分析,认为“在探讨艺术起源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强调艺术对生产劳动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自然条件和其他社会因素在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对艺术的起源作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分析。”[30]显然,在何梓焜看来,在探讨艺术起源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的思想要丰富得多。
对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起源说,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多的解读,有些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解读呢?周平远从普列汉诺夫研究问题的方法入手,对此进行了分析讨论。针对各种观点,作者认为,普列汉诺夫理论自身的矛盾乃是这些分歧发生之根源。作者从普列汉诺夫的研究方法、与达尔文的影响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与探讨。[31]
(三)对功利和审美问题的探讨
“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26]这是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中的话。作为俄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美学问题的人,这句话引发了人们关于审美与功利关系的持续探讨。在我国,早在60年代,耿恭让就对普列汉诺夫相关的审美与功利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普列汉诺夫继承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传统,把艺术看作生活的教科书,强调艺术不是无益的娱乐,应该为重大的社会利益服务。在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中,普列汉诺夫雄辩地论证了审美与功利的密切联系——审美是以功利为基础的,正确地论述了审美与功利、美与善、艺术与政治的关系。[32]新时期之后,针对这一问题,朱梁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普列汉诺夫不仅看到了生产力的状况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且己进一步看到了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文明民族的艺术起影响作用这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33]
普列汉诺夫关于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的研究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所谓美感的矛盾二重性,是指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个人主观的非功利性与社会客观功利性的辩证统一,是人们审美过程中直接性与间接性的辩证统一。早在50年代李泽厚就认为,“美感的这两种特性是互相对立矛盾着的,但它们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形成为美感的统一体”,并认为普列汉诺夫对此“曾作出了光辉的独特的科学贡献”。[34]然而,80年代以后,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计永佑就在《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一文中认为:这种所谓“美感矛盾的二重性”是根本不存在的。[35]计永佑的看法引发了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何梓焜对此进行了批驳与辨析,他认为,普列汉诺夫向来十分强调审美的功利性,认为功利是审美享受的基础。他用艺术史上的大量资料来论征审美与功利的关系。然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审美的功利性是对社会、一定的阶级、阶层而言,对于个人的审美感受则是非功利的。[36]都本伟也认为,计永佑并没有全面地正确地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整个观点,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始终把他的观点和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作了严格的区分,非但没有把人的美感等同于动物,而且一开始就指出人的美感与动物的快感不同。在美感的起源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坚持了一元论的唯物史观。他是把自己的研究放在“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领域终结的地方”,即从社会学角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究美感问题。而不像计永佑同志所说的那样,普列汉诺夫混淆了动物的快感和人的美感,因而“把自然界的历史搬回到了社会的历史”[37]。柳正昌也在文章中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人类美感发生论和审美认识中的直觉与理性、审美与功利的关系两个问题的理解、评价与计永佑进行商榷。[38]
与审美与功利相伴生的还有美感的起源问题。由于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普列汉诺夫是借助达尔文的学说及其人类学研究方法展开对艺术与美的探讨的,“美感的矛盾二重性”本身也遭受到人们的各种质疑,因而,关于美感的“人性论”问题也就成为讨论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又一重要命题。黄药眠在讨论中就认为,“普列汉诺夫常常自命为阶级论者。但不完全对。他曾经是阶级论者,但后来他已变成阶级论和人性论的调和论者,最后则索性变成为生物学的人性论者。”事实上,普列汉诺夫也正是沿着“生物学”的斜板,扑通一声溜到生物学的人性论底水潭里去了。[39]作者对普列汉诺夫所谓的从“人的天性”上解读美学大加鞭挞。黄药眠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学术问题,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问题的。本伟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他考察了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时期(1903年以前)和在孟什维克时期(1903年以后)所写的主要的美学著作,认为,“给普列汉诺夫美感论定性,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而不应只凭一两篇文章中的一些个别论述就轻易下断言。”实际上,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大致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始终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美学问题,不曾“滑向人性论的泥潭”,“成为人性论的吹鼓手”;他非但没有把人的本性看成是天生的、抽象的,相反,而是看成历史的、具体的。[40]1985年被文艺理论界称为“方法年”,黄海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角度,对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中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美和美感的生物性层次和社会性层次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有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习惯于把达尔文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历史唯物论同进化论对立起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对普列汉诺夫进行无理指责的哲学基础。不破除这种思维方法,就无法理解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精髓。”对于历史的产物采取简单的、平面的、仅仅抽出它的单一层次而不顾及其他层次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就是机械论的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用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认识复杂的事物。这也是某些人对普列汉诺夫上述美学思想长期横加指责的认识论根源。[41]
(四)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批评
普列汉诺夫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对许多文艺理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主张。他在文艺批评方面的贡献,也是中国学者关注比较多的内容之一。王秀芳从五个方面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思想:普列汉诺夫历来十分强调文艺批评在评价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职能;普列汉诺夫在强调对艺术作品的思想评价的同时,也很重视对作品的美学评价;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倾向性是一致的;普列汉诺夫承认文艺批评标准的相对性与客观性;重视文艺批评家的修养。[42]印锡华则认为,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批评的任务可以用“了解它的观念评价它的形式”[43]来概括。在《“二十年间”论文集序》中普列汉诺夫说过,文艺批评首先应该“把某一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译成社会学的语言,从而找出那可以称为某一文学现象的社会学的等价物的东西”[44]。关于形式方面,普列汉诺夫说:“艺术品通过它的美的形式供给人们认识伟大心灵的热情。”[45]当然,普列汉诺夫对于形式的看重“最终不过归结为一点:形式必须和内容相适应”[46]。普列汉诺夫的批评观念与他的文学观念是一样的,那就是强调文艺批评标准的社会性、时代性,这是他的艺术社会学的核心内涵。[47]张春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艺术史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因此,分析文学艺术作品,就须把文学艺术作品放到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去考察,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倡导的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基本特点所在。作者对在“方法热”思潮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被视为僵化、过时的模式,并遭到众多的非难这一现象,从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批评实践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这一非难是言过其实的批评。[48]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批评观还表现在他对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研究与评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研究文章主要有:1907年的《预兆性的错误》,1908年的《托尔斯泰和大自然》,1910年的《尼·加·车尔尼雪夫的文学观》、《政治家的短评·从这里到这里》、《概念的混乱(托尔斯泰的学说)》、《如此而已》,1911年的《再论托尔斯泰》、《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等。即使在1903年以后,在政治和策略上滑到了孟什维克主义的泥潭,而在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方面普列汉诺夫却基本上仍然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在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中,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陈复兴认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托尔斯泰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贵族阶级的儿子’,‘他是描写上层阶级生活的艺术家’。这是普列汉诺夫关于托尔斯泰的一组论文的一个基本的具有特征性的观点,也是他评论托尔斯泰一系列著名作品的出发点。”[49]几乎在普列汉诺夫评价托尔斯泰的同时,列宁也发表了一组评介托尔斯泰的文章,尤其是1908年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910年的《列·尼·托尔斯泰》和1911年的《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这三篇评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评价托尔斯泰方面都有很好的建树,也引来了学者们对两者进行的比较研究。李珺平在文章中分别对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评论托尔斯泰的“闪光”的地方进行了论述,同时也在论述中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作者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评论虽然有些地方不如列宁站得高,可是他的文章中确有个人的独特的‘研究心得’和‘精辟见解’,有的方面正好填补了列宁没有论述的空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50]
与李珺平不同,张弼主要研究了由于方法论的不同而导致普列汉诺夫在评托尔斯泰中与列宁观点的分歧问题,作者分析了列宁批评的正确性和系统性,指出了普列汉诺夫所表现出的更多的局限与不足。[51]这是新时期以后采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层次论等一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尝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邱运华关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论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到了他们批评背后的东西,作者认为,二人的差异与分歧不能仅仅用政治观点的差异、学识和趣味的差异来解释,而是“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体运用到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实践性问题”。文章认为,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内容:有关托尔斯泰全部学说的本质问题,如何历史地具体地在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中运用反映论的美学原则,意识形态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文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托尔斯泰学说的社会历史土壤的重视等。[52]在这种分析论述之下,邱运华基本得出了与张弼相近或相似的观点。
在普列汉诺夫所建立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中,除了艺术起源问题、美感问题、社会学文艺批评理论之外,普列汉诺夫还在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理论、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理论界对这些问题探讨的文章也是数量巨大。另外,在他对鲁迅、瞿秋白等中国作家文艺观的影响等方面,学界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异常丰富复杂,要真正理解普列汉诺夫的美学,不去整体上阅读他的著作是很难达到的。新时期以后,理论界对于普列汉诺夫相关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论争,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他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或许这些探讨基本都处于理论层面,但事实求是地讲,普列汉诺夫在我国所受关注的冷热程度始终是与中国文艺的基本实践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直接相关的。
[1]鲁迅.鲁迅文集:卷4[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224.
[2]鲁迅.鲁迅译文集:卷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10.
[3][苏]卡冈.马克思主义美学史[M].汤侠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7.
[4][苏]库列绍夫.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批评思想[J].潘泽宏,译.湘潭大学学报,1992,(4).
[5]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著作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传播[J].教学与研究,1982,(4).
[6]刘庆福.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在中国之回顾[J].学术月刊,1985,(9).
[7]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的命运[J].读书,1982,(6).
[8]郭鹏.普列汉诺夫研究综述[J].科教文汇,2009,(2).
[9]贺水贤,孙志娟.一本研究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专著——评《美学艺术社会》一书[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
[10]冯契.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待于发展——楼昔勇著《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序[J].文艺理论研究,1990,(6).
[11]李占一,李澄.关于普列汉诺夫政治、理论活动阶段划分的问题[J].河北学刊,1992,(1).
[12]列宁.列宁全集: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292.
[13]陈辽.论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J].齐鲁学刊,1986,(2).
[14]吴元迈.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J].外国文学研究,1979,(3).
[15]吴元迈.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J].文学评论,1980,(5).
[16][俄]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J].译文,1956,(12).
[17]印锡华.谈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文艺观[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
[18]吕德申.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5).
[19]樊大为.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5,(4).
[20]赵宪章.浅谈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社会学理论[J].社会学研究,1986,(2).
[21]王秀芳.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艺术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22]陶东风.论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史观[J].晋阳学刊,1991,(5).
[23][苏]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艺术的对话[M].吴谷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00.
[24]李心峰.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家的普列汉诺夫[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5.
[25]陈复兴.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功利主义艺术观[J].东北师大学报,1980,(4).
[26][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C].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95.
[27]刘文斌.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地存在的——普列汉诺夫对“纯艺术”论的批判[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28]王又如.试评普列汉诺夫关于功利主义艺术观的论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4).
[29]张育新.普列汉诺夫怎样论述艺术的起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1).
[30]何梓焜.对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起源的理解——兼与张育新同志商榷[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
[31]周平远.关于普列汉诺夫研究方法的思考——《没有地址的信》札记[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1990,(1).
[32]耿恭让.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审美与功利关系的美学思想[J].江汉论坛,1963,(9).
[33]朱梁.普列汉诺夫论原始民族的艺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3).
[34]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A].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206.
[35]计永佑.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A].美学论丛:第一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3.
[36]何梓焜.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美感矛盾二重性”[J].学术研究,1987,(3).
[37]都本伟.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与计永佑同志商榷[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5).
[38]柳正昌.普列汉诺夫美感理论的再评价——兼与计永佑同志商榷[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39]黄药眠.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中的生物学的人性论底批判之一[J].文艺理论研究,1980,(2).
[40]本伟.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是人性论吗?[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6).
[41]黄海澄.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看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之一得[J].学术论坛,1986,(4).
[42]王秀芳.普列汉诺夫论文艺批评[J].江汉论坛,1984,(5).
[43][俄]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J].吕荧,译.文艺理论译丛,1958,(1).
[44][俄]普列汉诺夫.俄国批评的命运[J].世界文学,1961,(11).
[45][俄]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46][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M].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79.
[47]印锡华.“了解它的观念评价它的形式”——普列汉诺夫论文艺批评的任务[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
[48]张春吉.试谈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批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
[49]陈复兴.普列汉诺夫的托尔斯泰论[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2).
[50]李珺平.简评列宁、普列汉诺夫对托尔斯泰的评价[J].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
[51]张弼.从方法论上看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评托尔斯泰中的观点分歧[J].学术交流,1986,(3).
[52]邱运华.在批评的背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论托尔斯泰比较研究[J].俄罗斯文艺,1999,(3).
〔责任编辑:渠红岩〕
Research on Plekhanov's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DING Guo-q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Plekhanov's literary thought has a 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academics.However,the academic world mostl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his works but seldom did related research before the new period. And these research are in political vision which cannot offer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appraisal.Since the new period,people has start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him because they were free from political thinkingmodel.You may find that Plekhanov's thoughts are unusually complex.His literary thought always focused on and never depart from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method instruction of Marxism if you research on his literary thought from those perspectives such as“general study on Plekhanov's literary thoughts”,“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art”,“discussion on utility and aesthetic problem”,and“Plekhanov's soci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e has his own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proposition.It is wrong to vulgarly and mechanically understand Plekhanov's sociological literary thoughts.
Plekhanov;Literature and art thoughts;China research
I01
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1-0081-10
2013-08-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
丁国旗,男,河南荥阳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和文学基础理论研究。
① 即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这一卷全部是美学论文。这本书除作为中文版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出版外,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10月,以《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为题名,出版了两册书。该集共收入普列汉诺夫1888—1913年间的美学论文19篇,可以说,他的重要美学论文大多数都收入了。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收入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最多的一部书,是我国近年来翻译出版普列汉诺夫文艺和美学论著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参见刘庆福《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在中国之回顾》,《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