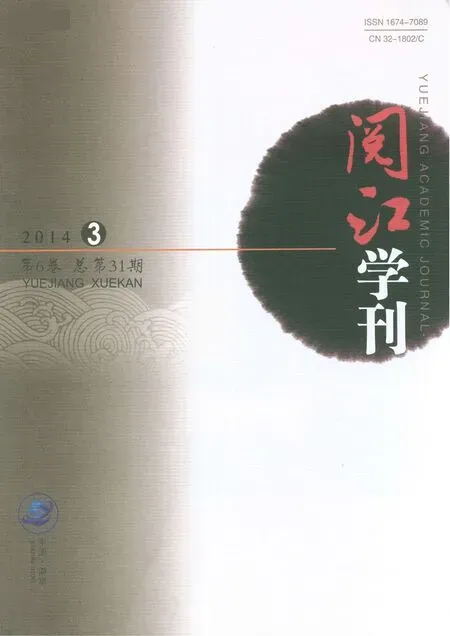姚元之诗论
温世亮
(南昌师范学院,南昌 330038)
在嘉、道时期的诗人中,姚鼐的族孙姚元之是值得一提的一位,他文翰从容,雅负时望,曾为陕甘、顺天、江西乡试主考官和会试同考官,广揽天下文才,“识奇士于风簷寸晷中”,[1]诗歌不仅具有时代特色,也不乏自我性灵,在当时的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他广泛地参与“宣南诗社”等京师雅集,与良斌、张问陶、吴嵩梁等被称为“锜中风雅眉目”。[2]而李慈铭《白华绛柎阁诗集》卷癸《潘星斋丈以新刻小鸥波馆诗补集见眎率题二首》其二一首云:“老辈吴(玉松太守)程(春海侍郎)接迹难,桐城(姚伯昂总宪)娄县(张诗舲尚书)迭登坛。误他落第罗昭谏,也作贞元朝士看。”[3]更是将他与吴云、程恩泽、张祥河等当时著名诗人并置同列,一样昭示出其重要的诗坛地位。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廌青,一作豸青,晚号“五不翁”、竹叶亭主。嘉庆十年(1805)进士,历官河南学政、咸安宫总裁、工部、刑部、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内阁学士。早从游于族祖姚鼐,后又问学于著名诗人张问陶,诗书画兼善,称“三绝”。又熟稔于经史,“习于掌故,馆阁推为祭酒”(《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五)。喜交道,待人“有晏子之风”,[4]在京师与斌良、程恩泽、陈用光、吴嵩梁、陶澍、吕佺孙、陈启迈、史致谔、张亮基等名士过从甚密,以诗文相倡导,集中亦多见唱和之什。所著《使沈草》三卷、《廌青集》二卷,录诗近千首,虽非其作品的全部,但足以借此一窥元之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面貌。今即以《使沈草》《廌青集》两集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文献,从民俗学价值、现实意义和艺术风神等方面对姚元之的诗歌创作逐一展开论析。
一、姚元之诗的民俗学价值
姚元之深受传统的功德思想影响,少即胸怀天下之大志,为官后更是悉心关注国是,重视边疆史地的考察和研讨,每到之处,必深入民间,采其地之民俗风情于笔端以供考索。在他的《竹叶亭杂记》中,便有许多相关民俗、民情的记录,例如卷三“记载各地的风光物产、人情习俗、奇闻趣事及同国外的交通往来”,[5]地域色彩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特点也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此,我们可以其《使沈草》为例予以分析。
元之曾于道光元年(1821)奉命出使辽东地区,考察边地民情,以供治边之用,其《使沈草》三卷即是此间所作。在他的诗笔描画之下,许多东北边地的民习和风土得到了展示,这也使他的诗歌创作显现出浓重的民俗风情。例如《使沈草》卷一《宁远竹枝词》:“车中女儿髻盘龙,猩毡半覆牛车蓬。后有蹇驴前有鼓,轻绡一幅作蒙红。”以清新通俗的语言描绘了辽西一带新娘出嫁时的现实场景,宛如一幅古朴的民俗画。实际上,诗作正是根据“乡中嫁娶多用牛车,被以红毡,前导鼓乐,送者或策蹇,手握红绡一幅,问之,云:‘用备蒙红’”[6]的习俗衍化而来。卷二《辽阳杂诗》其八一首,书写辽阳“安其人”“只今不识人间世,犹问秦皇几叶孙”,几乎与外界隔绝,依然沿袭汉制、穿汉时衣、戴汉时帽、说汉时话的生活状况,纯然是一种原生态的笔墨点染。这种关乎“安其人”生活常态的描述,从文字表述上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但又并非像陶渊明那样纯然出于美好理想而进行的人间世的想象和虚构,而完全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真。以此而论,其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提供了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实际上也为上层统治阶层观“风俗之凉薄”、察“政治之得失”提供了最为原始的资料。卷三《食山蛤》一诗,则详细地描述了俗名为“哈什蟇”这种深受沈阳人所喜爱的小动物的外形、功用,以及做法、吃法、味道等,同样是一种地方民俗的真实反映。类似这样的作品在《使沈草》中还有很多。
总的看来,《使沈草》中的诗歌作品并不乏一定的艺术兴味,带有情感的渗透和诗性的点染,是艺术凝练的结果,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论及。但更为重要的是,《使沈草》又是诗人实地考察辽东之后所作出的现实描摹,无疑可视之为东北地区社会风情的诗性记录,显然具有了极高的民俗学价值,既为统治者观政提供了材料,也可供史家摭拾。
二、姚元之诗歌的现实意义
元之少小即从学于族祖姚鼐。作为一代文宗,姚鼐为诗行文讲究“义理、考据、文章”并重,而又以“义理”为中心。但是,姚鼐同时也是一个注重性情浸渍的诗人,能够将义理、情感熔于一炉,秦朝釪《消寒诗话》即称其诗“沉郁有体裁,才思纵横,无不入律,比兴往复,得风人之遗”。[7]而元之的另一位受业师张问陶,更是有清一代“性灵派”的后劲,钱钟书先生即称:“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问陶)代之。”[8]实际上,元之对船山的为人和为诗也是钦慕有加,曾不止一次地赞叹他以诗寄写心声的作风,如《呈张船山夫子》云:“一部乖崖集,千年心声同。风云写怀抱,笔砚老英雄。”[9]《寄蓬莱太守张船山夫子》则云:“蓬莱仙吏出尘姿,管领神山鬓未丝。堂上琴悬无长物,郡中乌集已多时。仙人楼阁春长住,水国烟波秋到迟。出海云霞天五色,不知何似使君诗。”[10]师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对师者的向慕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元之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会将自己的经历心声以及世情时事果敢地融入其中,或“触兴为章”,或“言诗纪事”[11],透过这些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所具有的现实认识价值。
作为封建士人,元之亦不缺强烈的科举仕进的功名之念。然而,在实际的统治中,清王朝却深怀“华夷大防”的隐衷,始终控制着汉人执政的权力,相反给予了满人更多的升迁的机会。因此,多数的汉人官吏即便是大权在握,胸怀济世利民的宏伟志向,却往往是官位不显,俸禄不厚,甚至时常受到打压,难有升迁之机,在附庸风雅中寻求自适自慰便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就官阶而言,元之虽说也曾位至一品,但屡遭贬谪、诬陷、打压之苦,[12]在发挥政治功用上显然是难有作为的,这与其满腹的经史文才并不相称,跟他“上释天子忧,下使农人喜。壮实志四方,良图在万里”[13]的志向更是背道而驰。正因如此,他时常在诗歌中感叹时序的变迁和人生的苦短,借此抒发自己功名难遂之愤。如《览镜》一首:“四牡騑騑未解装,忽嗟白发镜中生。如何半月辽阳客,却带临渝塞上霜。”[14]诗作于作者道光元年(1821)服阕出使沈阳时,此时诗人已届知非之年,且正遭受了钻营之诬、降职罚俸、丁父之忧等人生困厄,[15]如果结合这一实际来进行解读,就不难发现诗歌的意旨所在了。
《使沈草》卷二题名为《与松君芳安苏纪亭两舍人夜话》一首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作品,诗云:“更阑烧尽广南香,人海浮沉夜话长。两鬓不堪灯下照,芙蓉镜里有微霜。”对镜览容,两鬓已微霜,把人事升沉漂浮的凄楚感慨寄寓文辞之中,同样是意味深长。而《廌青集》卷二《始兴江口奉蒋御史秋吟》,则将其颓唐不安、凄苦无告、难有作为的宦途心理深刻地表现出来:“始兴江口柳如丝,仗雨阑风客艇迟。同是愁人在江水,相逢未敢问归期。”元之为人正直,为官也清廉,而在朝廷俸禄甚微的情况下,生活穷苦潦倒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这样的情形,诗人并未予以掩饰,而是毫无顾忌地进行描画和陈述。例如《使沈草》卷三《岁暮沈阳行》,先描绘沈阳冬日“万里关山纵所指”的优美景色和沈阳满人府邸“高大宇宏绝尘滓”的富丽堂皇,叙述出使沈阳所受到的“居然上客坐虎皮”高规格的礼遇,然后就自己京师生活的实际展开叙写、议论:“嗟我廿载溷清班,破帽羸车东郭屣。长安大是不易居,更逢岁暮清如洗。……,既刻画出自己赤贫的官宦苦相,也透露出自己对京师中下层官员的艰辛生活的不满。
元之虽仅仅着眼于自己的经历而展开客观的描述,但诗歌所展示的官吏生活图景以及此前言及的功名念想,在当时应该都是有普泛意义的。其《金春甫就暮偏关书来极言山路险恶时已七十九岁矣感而有作》“八十无家命已穷,依人又隔太行东。……书生饿死寻常事,语不吾欺是放翁”[16]云云,对陆游《秋思》诗意的肯定,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在仕途上算不上顺风顺水,但经世致用毕竟是元之的人生目的。对“代宗儒门,世膺朝黻”[17]的家世,元之是感戴于心的。他少即负兼善天下之志,入仕后亦努力地去做一个尽职的官吏,而且始终怀抱着一颗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集其一生心血所著的《竹叶亭杂记》一书,“记述当朝掌故、礼仪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科举考试的场面、宦海仕途的风云。不少地方触及到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问题,如盐政混乱,弊端百出;兵制松弛,军队腐朽;民生凋零,反抗四起,等等。尤其对于吏治的败坏,更有所披露”[18],这便是其心系天下的重要佐证。而其致仕之由,说到底是因为鸦片战争期间与当时的主和派政见不一。对此,他的同邑后学马其昶讲得很清楚:“道光末,海氛初起,(姚元之)即疏陈:‘广东形势,可力战,请速弭巨患!’与总督林公则徐意合,柄用大臣或不便,遂吿归。”[11]惟其如此,面对渐趋凋敝腐朽的社会现实,诗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廌青集》卷一《龙伐木歌》是一首名作,借顺天府隶属平谷、三河等县民间流传的“为龙造宫取木”的故事来反映民生,批判长久以来统治阶层不顾民疾而穷奢极欲、大兴土木的腐朽荒唐,而结末所云“吁嗟长江滚滚流,巨筏纵横断复续。千里万里息可致,取用未闻或不足。龙宫纵须山木材,顺流亦可供其欲。东澥之龙何不仁,蹂践人命等牲畜。何当六丁为扑之,三河不波吾民福”,又足以昭示诗人实政为民的真切心声。此诗广为流传,甚至被张际亮称为元之诗集中“最佳”[20],其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它具有深刻的现实针砭意义,符合张氏所谓“志士之诗”、“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观万物之理,备四时之气,其心未尝一日忘天下”[21]的标准。同卷《正一真人》同样是言关民瘼,诗云:“宽衣大袖来青冥,手持一纸书黄灵。云是正一真人之法曹,绿章封事奏帝庭。邓马元帅开九阍,下情一一天为听。真人之权吁如是,千妖万怪不敢肆。昨者东邻村,有妖乱捉人,昼伏不出夜恣行。攫取帛与财,鱼肉老与婴。土神无如何,愁苦不得明。真人尔为天帝之耳目,何不直陈帝所,使得寝皮而食肉,群丑闻风皆窜伏。岂惟东村,普天之福。”写“正一真人”借朝廷赐封之权位以妖孽之法蛊惑人心,愚弄百姓,既不能真正地平息世间的盘剥,又不能给人民带来安宁祥和的生活,反而制造出种种的人间不平事,实际也是一首深具现实批判力度的作品。对此,郭则澐《十朝诗乘》便作出如此评价:“其诗疑有所讽。承平日久,法窳吏弛,上下相蒙,心乎民瘼者,宜有是作。”[22]
《送前金匮令齐梅麓起复之原官》、《虎门行》等则是直面现实,指责时弊。前者云:“记曾投笔去瀛洲,辛苦梁溪又几秋。每笑塞翁悲失马,却虞黔首叹无鸠(自注:梅麓料理荒政最劳)。谁能能识周厂伯(自注:梅麓颇具卓识,著有《海运》诸议,大吏殊不喜之),吾子依然郭细侯。落木不应成别恨,春明花发好春游。”齐彦槐(梅麓),婺源(今属江西)人,嘉庆十三年(1809)进士,官至苏州知府。为江苏金匮县令期间,其“毁淫祠,断疑狱,振荒歉”,富具政声,在苏州府知府任上,却因“陈运海策”而遭江苏巡抚非难落职。[23]诗即以此为背景进行营构。英雄难有用武之地,在殷殷的劝慰中寄寓深深的愤激之情,其实正是晚清时期朝廷党派纷争、官场黑白颠倒的反映。后一首《虎门行》,则是围绕东南海患而展开,既描绘了“攒峰列嶂隐青翠,芙蓉乱插沧波中”的鸦片贸易状况,也抒发了“瞪目不敢偏师攻,赫赫重臣总元戎”那样遭人欺凌却无力反抗的感慨,甚至还提出了了解夷情的政治见解——“黑齿国人歌来同,方壶员峤遥相通”,同样富有现实针对性。
嘉、道之世,世风日下,时局昏沉,加上传统文化的浸染和自身仕历困顿的历练,成就了诗人的现实情怀,促使他用诗笔隐曲地记录下种种忧愤和悲悯,其诗作也因此展露出应有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元之诗歌创作的精义所在。
三、简淡写意的诗画意境
元之的诗歌创造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而且创造出简淡写意的诗画意境。
一方面,元之既是嘉道时期的优秀诗人,也是当时造诣颇深的著名画家,甚得画坛之推誉。例如法式善便将他列入清代“十六画人”,[24]秦祖永则称其“虽不能与南田、新罗争胜,亦近时士大夫中之翘楚也”。[25]而“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作为姊妹艺术,诗画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共通点,诗人加画家的双重身份也决定了元之在诗画创作中会进行必要的双向互动。另一方面,元之为画追摹接迹于南宗,并不刻意于形模而趋尚沈周、华岩一类的平淡简练,重在于传神写照,也就是钱泳所谓的“工于花果、翎毛,落笔苍秀,如石田翁;亦画山水,近华秋岳,寥寥数笔,精妙入神”。[26]事实上,他自己也是非常乐意将简淡写意的画法融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尝明确地指出:“作诗如作画,澹处见精神。气纵疑无法,情多不累真。”[27]因此,在诗法取向上他虽然与其族祖姚鼐一样唐宋兼宗,主张“醯醢唐宋非一种”[28],也留下了一些浸渍理趣的作品,但是就诗歌总体风格而言则更趋向于唐诗一路,若用姚莹《廌青诗集序》中的话来概括就是:“全集雅托唐音,绵邈其思,俊逸其气,清辞丽句不绝于篇”,[29]而其诗也确实很容易将读者引入到那种清新的诗画境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语言洗练洁净,有一种精纯自然之美。对于诗歌的语言,元之并不苛于字斟句琢,而更钟情于用那种自然、质朴的常语来描摹各种景致风光和物质形态,言情说事亦见恬静,善用清新之笔作淡语,也就是张澍《姚伯昂中允五十寿序代潘石生考功》所谓:“赋诗得句,皓月当天,字织龙梭,珠探骊颔,自然冲妙,无事推敲,岂非人境结庐致外飞颖者乎?”[30]这在其五七言小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使沈草》卷一《宿望海店望海》:“不见珠宫十二楼,却看明镜半天浮。夕阳红处归云外,一点清帆似白鸥。”诗人满怀兴致登楼眺望那传说中的海上“珠宫十二楼”,远远看见的却是闪烁悬浮于半空犹若明镜的海面。更为精彩的是,一叶轻快的白帆恰似一只翱翔的海鸥,慢慢地消逝在那夕阳将落、暮云浮动的水天之际,似一幅明净的图画。同卷《千山》:“明霞为饰玉为容,山到辽阳峦嶂重。欲问青天花数朵,九百九十九芙蓉。”前两句重在景物的客观描绘,后两句着意于主观情感的抒发。虽是对景突发奇想,运实而入虚,却不见雕琢之痕迹,用语甚为省净、通俗。
二是意象清澈透明,有一种空灵寂静之美。元之为诗善于借景渲染,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他具有诸如孟浩然、王维、严羽、王士祯等诗人的特质。因此,像澹烟、落日、明月、白云、梅花、芙蓉、刍兰、秋葵、杨柳这些具有清远或者清圆特点的自然物象也便成为其诗中最为常见的,例如“澹烟浓树久前屯”、“白日下西山”、“月华依旧挂林梢”、“荞麦山西起白云”、“始兴江口柳如丝”等便是。而依靠这些或清澈素淡或空廓寂静的意象,也使他的诗歌获得了别样的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恰当使用意象的同时,元之也善于将它们进行有机的组合,在意象的叠加中创造出一种天然不可凑泊的艺术境界。如《早行》:“早行阴雾重,微日断云遮。郭外两三里,野桥南北斜。山含新雨重,路隔乱流赊。幸有秋光好,风吹荞麦花。”[31]诗写早行之景,同样是多种自然意象的叠加组合,而情在笔墨之外,一样具有空逸邈远的诗画境界,诗人的心声或诗歌的内涵完全隐藏在山形水色中。
三是淡而有味,富有真挚沉郁之致。前面讲到,元之为诗总是以事真、情真为基础,所以,作品具有精纯自然和空灵寂静之美。对此,张问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其《题姚伯昂诗》云:“一月不相见,新诗陡胜人。奇篇能磊落,淡语亦丰神。志定原生慧,才高恐更贫。聪明君自足,珍重葆天真。”[32]称元之诗淡而有味、淡中见真,蕴含着深厚浓烈的个人情思,而无单薄浅露之弊。梅植之也赞其诗或“旨远词微”,或“浑厚茂美”,或“清新自得。”[33]
一如张、梅所言,元之满腹经纶,一生却屡经宦海升沉、人事消磨,所以,从其简淡空灵而富有画境的笔墨中,我们时常能捕捉到他那凄凉的心境。如作于道光元年出使沈阳时的《忆旧游三十五首》组诗,实乃通过对曾经风光无限的乐事的追忆来折射当下境况的萧瑟惨淡,其二十九云:“鄱阳湖上蓼花洲,酾酒烹鱼八月秋。欸乃一声湖水绿,慢船明月上饶州。”诗由柳宗元的《渔翁》诗而来,写旷朗自娱于鄱阳湖上的情景,而以碧水渔舟、中秋明月这些清新素淡的背景作为陪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这实际与诗人当时的孤苦寥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乐景写愁思。苏东坡评柳宗元《渔翁》诗有言:“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34]相形之下,元之此诗自不乏苏轼所谓的“反常合道”,甚见“奇趣”。
四、结 论
姚元之主要生活于由盛转衰的嘉道时期,能以自身经历为基础,贴近现实进行诗歌创作,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认知价值,这主要从民俗学价值和现实针砭意义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同时,姚元之的诗歌能将诗情与画意熔铸于一炉,显示出简淡写意的艺术境界。就某种意义而言,他的诗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传统诗教精神与诗人情怀的结合,显示了时代特色,彰显出较高的艺术价值,正因如此,其诗名亦屡屡得到时人的扬誉。
遗憾的是,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姚元之的诗歌创作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各种诗史专著难觅其踪影。实际上,元之一生光环累累:系出文化望族(桐城麻溪姚氏)之后,具备了深厚的家学渊源;曾受知于姚鼐、张问陶等大家,深得名流之陶染;为官京城,交游既广泛,亦倾心于民瘼;为乡试主考、会试同考和地方学政,则力揽培育英敏之才于草野;为馆阁祭酒,主持风雅更是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各种诗文化活动,诗学影响非凡。可以这样说,这一切都决定了对元之其人、其诗展开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围绕这些对元之其人、其诗作更进一步地探究,既有利于认识元之的诗坛地位,也有利于对其诗歌成就作出更为恰当的评估,实际也为嘉、道时期诗歌的客观、全面、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个案。
[1] 钱仲联.广清碑传集[Z].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696.
[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Z].退耕堂1929年刻本:卷一百一十二.
[3] 李慈铭.白华绛柎阁诗集[M].清光绪十六年刻越缦堂集本.
[4] 刘瑗.国朝画征补录[M].清道光刻本:卷上.
[5][18]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11][14][28] 姚元之.使沈草[M].清道光二年刻本:卷一,卷首,卷一,卷三.
[7] 何文焕,丁福保.历代诗话统编(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587.
[8]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7.
[9][10][13][16][17][27][31][33] 姚元之.廌青集[M].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一,卷二,卷一,卷二,卷一,卷一,卷二,卷首.
[12][15][2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3275 -3277,3275 -3276,6014.
[19]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合肥:黄山书社,1990:383.
[20]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M].清同治间刻本:卷十.
[21]张际亮.张亨甫文集[M].孙庆衢,李云诰,编.清同治六年(1867)增刻:卷三.
[22]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四册)[Z].上海:上海书店,2002:442.
[24]陈康祺.郎潜纪闻[M].清光绪刻本:卷十一.
[25]秦祖永.桐阴论画三编[M].清光绪八年刻朱墨套印本:下卷.
[26]钱泳.履园丛话[M].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卷十一.
[29]姚莹.东溟文后集[M].清中复堂全集本:卷九.
[30]张澍.养素堂文集[M].清道光刻本:卷六.
[32]张问陶.船山诗草[M].清嘉庆二十年刻、道光二十九年增修本.
[34]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