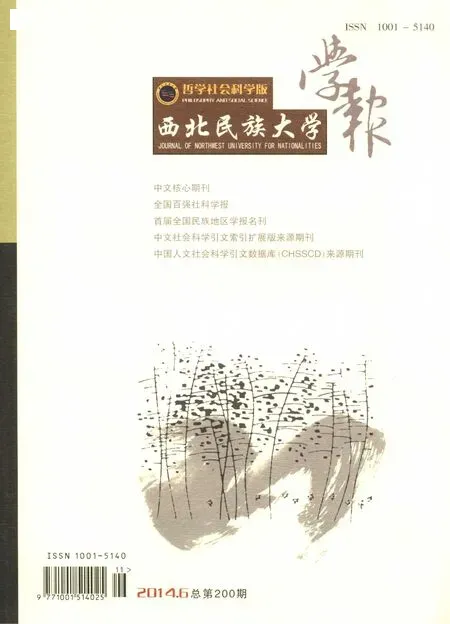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许晓冬
(大连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对中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的有三类人:美驻华官员、美商及传教士。三者相互依存、共同合作,贯穿于美国对华贸易与外交关系的各个阶段,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诠释者。美国传教士与其他西方国家派出的传教士有着不同的起点。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法国在与非基督教国家交往时,传教士与商人通常是同行的,荷兰与英国的情况也几乎如此。基督教会不是和通商、征服或探险同时开始就是被指派到已由通商、征服或探险指明道路的国家去,如在美洲、印度、菲律宾群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可是美国在最初数十年间却找不到这样的关系。在鸦片战争前后,通商与传教构成了美国对华关系的主要特征。但美国的传教与美国的商业完全是两回事。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但直到1830年美国才有第一批传教士来华,这期间整整46年的时间。传教士不仅在西方文化、教育、出版等领域对华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中美贸易协定、鸦片走私、美国对华政策等领域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没有哪个国家的传教士参与贸易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美国传教士一样的深度。从产生的效果来说,美国传教士比早期其他国家来华的传教士更具影响力。
一、传教士与商业扩张
(一)传教的商业基础
关于基督徒与西方商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有两种声音,其一是传教士与英美商人坐在一条船上,传教士是贸易与商业的先锋。“传教士从没有公开谴责过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相反地,他们乘着鸦片船到中国,还从贩运鸦片的商人手中获得资金支持。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1]基督徒还鼓吹通过战争来让中国人屈服,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另一种观点是传教士与商人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猜忌与敌视,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出商人与传教士关系的两面性,彼此独立却互相依赖。
基督徒来华之始并非带有商业目的,这是因为基督教义对唯利是图不屑一顾。《新约全书》中曾记载耶稣对弟子的训诫,“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他们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富,钱的化身)。”[2]耶稣的训诫并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的扩张,对商人来说也没有约束力,但对于传播福音的教徒来说却是金科玉律,他们视玛门为罪恶之源。除个别传教士因生活所迫弃教从商外,很少有传教士涉足商业。然而,传教士对商业的不屑并没有影响他们借助商人的力量来扩展传教业务,传教事业一开始即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及海外的商业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及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纽约商人、广州同孚商行经理奥利芬的资助,他慷慨解囊,帮助来华的传教士解决交通、住宿、办报印刷等方面的费用。奥利芬因其在传教事业上的贡献,在美国被誉为“对华传教之父”。商人这种支持不仅在国外,很多商业组织团体还向国内的母会捐款,甚至在教会中担当一定的职位。商人参与传教活动不仅使传教事业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有号召力的商人的加入,使美国在海外的传教活动更具声威,其影响与规模都超过其他西方国家。
虽然基督徒与商人来华的目的大相径庭,但却在迂回的斗争中保持了一致性的目标与相辅相成的作用。美国在华的商业活动以西方的价值观为主导,它改变了中国的消费观念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这对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环境。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外贸易主要聚集在沿海通商口岸,通商口岸是外国商业活动发达的地方,同时也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地方,而这里也是基督教徒最早登陆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商人与百姓对外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认可度极高,这对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铺垫的作用,事实上所谓的西方文明正是通过商务活动发达的通商口岸传播到中国的沿海及内陆,一般来说,商业兴盛的地区往往也是传教事业兴旺之区。
商人及商业活动为传教者带来的支持同时也换来了传教士的回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它的传播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刺激了中国人对西方商品的消费与对西方生活的向往,这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基督徒们本身作为西方人,在中国吃穿住用等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无一例外地影响着当地居民对西方人的看法。有些中国人崇尚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跟学基督徒的穿衣、饮食、居所等习惯,自然而然地在这方面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相对于遥不可及的官员与商人,基督徒游走在普通人中间,这种亲和力与感染力更容易让有先进思想的人所接受。从生活上的简单模仿到精神上的忠诚依附,基督徒们完成了基督教国家推销员的工作,也为他前方的商人开辟了通向东方的通途。
(二)海外扩张
1830年至1905年,美国基督教来华的差会共计35个,其中主要的差会组织有美部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浸礼会、美国长老会等。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1810年建立的美部会,1830年派裨治文来华,1833和1834年分别派卫三畏和巴驾来华传教。美国早期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正面临着行商制度的废除与多口岸的开放,这对传教士们是极大的鼓舞。但鸦片战争前,受清政府禁教限令影响来华传教的人数仍寥若晨星,但随着1844年《望厦条约》的签署,在华传教士的人数在增加,1845年有两个美国人,1848年有44个美国人,1855年有46个美国人[3],1877年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人数为212人。美国传教士无疑是最大的阵营,几乎占中国所有教职人员的2/3以上。
海外扩张往往与基督教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美国的触角伸向哪里,十字架也同样就挂在哪里。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开发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为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推动国家经济利益与传教利益相统一,传教组织也借此掀起了海外传教的新高潮。1886年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大学生暑期圣经学校”,鼓动大学生积极投身海外传教事业,很快国内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圣经学校要求学生将海外传教事业作为“征服世界的战争”[4]。1894年在海外传教的学生志愿组织提出“用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这一口号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穆德发起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最早提出来的,而此时美国正准备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又提出“用基督教去刷新异教徒的所有生活观念,将异教徒变成耶稣基督的新人。”[5]19世纪末至一战前,美国海外传教事业达到高潮,在海外传教的人数达到近万人,在华传教人数也近2500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20世纪最初20年美国基督教在华迅速膨胀的原因。
二、传教士的鸦片观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的学者一直认为美国传教士是不反对鸦片贸易的,有些甚至为鸦片商为伍,充当鸦片商的帮凶。这一观点最早出于美国学者S·E·莫里森。事实上,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在中美商业关系之后开始的,传教工作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与财政支持,早期的传教士多数乘着鸦片商的船来到中国,也从鸦片商手中得到资助在华传教。在鸦片战争的看法上,个别极端的传教士不断鼓吹通过武力让中国屈服。《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曾肯定英国通过战争手段强迫中国走上了一条与各国利益更为一致的道路。美国第一位女传教士夏克夫人说,“中英之间的纠纷曾使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相信英国人会被激怒,这样上帝就会以其力量打破阻止基督福音进入中国的障碍。”[6]对于这些事实与看法也仅是一个方面,更多传教士的言论是反对鸦片贸易的,因为鸦片贸易不利于传教士最终目标的实现——基督教征服中国。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通过传播基督教和用美国的文化观、价值观征服中国,他们不是军人与政客,也不是商人,他们关心的是美国的整体利益,而不是鸦片商人的利益,当商人的利益与传教士们所追求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当然要选择后者。至于通过什么方式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是没有统一说法的,只要在中国突破传统,让西方思想有生根发芽的平台,即便使用武力也是必要的。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麦都思曾这样描述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那些没见过鸦片对中国产生影响的人,很难理解鸦片的吸食对人健康的影响,它是对精神与生命的双重摧残。经过几年的吸食后,身体羸弱,寿命缩短。鸦片商们很少知道在他做这种败坏道德和具有破坏性的交易中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害处……在鸦片输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口的增加率为每年3%,在鸦片输入以后则为1%。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鸦片商们最好想一想,人口增加率的降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由鸦片烟造成的,而其罪过则应加在作为输入鸦片烟的媒介的那些人身上。”[7]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同时引起中国人民对西方社会的普遍反感与痛恨,这样的敌对情绪是不利于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很多传教士对这种敌视情绪也深有感触,鸦片战争让中国人对传教士更加厌恶,战争的破坏作用抵消了基督教对中国所做的所有贡献,这种贸易已造成中国人对传教士和福音的一种强烈偏见,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群人一边带给我们救世的福音,一边又把毒药放在眼前,身着伪道士服的我们还是否有资格向他们传播西方文明与美好,他们会相信吗,虽然身为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有谁能分辨出传教士与其他西方商人有何不同,他们必然会质疑鸦片贸易不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吗?这种担忧是普遍存在的,鸦片战争后这种尴尬的关系也困扰着许多传教士。
此外,鸦片贸易也违反了基督教道德观念。我们固然不能仅从道德角度分析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但是吸食鸦片导致吸食者精神萎靡、身心俱损,毕竟与基督教道德和传教士宣传时所说教的内容是不相符的,传教组织是不允许吸食鸦片的人加入教会的。一些稍具良知的传教士都将鸦片走私看做是西方文明的耻辱,传教士杨格历数鸦片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说它破坏了中国的法律,摧毁了健康与家庭,并逐渐使整个民族的道德沦陷。传教士谢卫楼也承认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的接触大大加剧了无节制的罪恶,社会上不道德行为更加普遍,鸦片充斥中国大地带来了悲惨与痛苦,这种不幸是基督教国家的人造成的。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反对尽管是苍白的,而且在批评英国鸦片贩子的言论中受到嘲讽,但这并不影响传教士对正义的表达。
鸦片贸易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对美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也是不利的。在鸦片战争前的广州,美国商人在市场所占的份额仅次于英国,而鸦片走私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损害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和消费力。美商奥利芬与金查理也反对鸦片贸易,称这种短期的眼前利益只会破坏市场的稳定,减少美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望厦条约》签署之前,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途径主要是通过在华商人与家人的书信、官员的报告及传教士的声音。由于传教士在民间传教,又深谙汉语,对中国的了解比前者更深入与具体。传教士将中国吸食鸦片的情况反馈到美国国内,这形成了美国政府不支持鸦片贸易的主要依据,在1834年至1860年间,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美国人多于英国,比例约为2∶1,他们向国内各团体提出的报告在美国人民的深厚宗教意识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旅居中国的美国商人中,有些是尽其所能大肆贩卖鸦片,而大部分美国商人及传教士却纯粹凭着良心不赞成参加鸦片贸易,传教士一遇到机会就对鸦片贸易的罪恶进行谴责。在《望厦条约》中美国明确禁止携带鸦片及违禁品到中国,但由于1854年之前历届美国领事都是在积极从事鸦片贸易的旗昌洋行中选派,而美国领事又不具有行政权力,不能发布官方声明,对鸦片的管理自然也就听之任之。但从条款的内容可以反映出美国统治集体已经认识到鸦片贸易不符合美国的长远目标与利益,传教士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
传教士与美国政府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之初并未派传教士来华达到政治目的,传教士也未受政府派遣为政府效力与服务,但从传教士来华后的传教活动看,这一活动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与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一致。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目标是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层目标是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发展;第三层目标是寻求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相统一的利益。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对美国而言就是把美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在华传教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层次上,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秩序。海外传教运动不仅传播了基督教教义,而重要的是推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占有基督徒较大比重的美国传教士通过建教堂、学校、医院、出版机构去影响与感染中国的“教民”,他们像是一种特殊的媒体,连接中国与美国,通过这股力量西方的意志与思想可以通过他们准确地到达中国,虽然这些组织与行为并非由美国政府领导,但潜移默化地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中国的这些作为彰显着美国的影响力。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传教士已经成为一种媒体,一股势力,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与思想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8]
传教士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与中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上。自1830年裨治文来华传教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签署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美国的传教士规模在所有国家中位列第一,传教士在华的主要任务不仅体现在争取传教的合法性及普及教义,更重要的是在与商人和外交官一起充当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践行者。早期来华的裨治文、巴驾、卫三畏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望厦条约》与《天津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工作。条约的内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反映,而传教士的参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巴驾感到这是将传教事业推向高潮的最好时机,便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的情况汇报给差会及美国政府,以利于美国采取必要的措施。1840年他离开广州到达纽约,在向美部会汇报完工作后就赶赴华盛顿,他要当面向政府汇报中国的形势。他会见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和其他政要,并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为了改善目前我国政府与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应毫不犹豫地派一位全权公使前往中国。”除了提交政府报告外,他还到国会发表演说,除大谈在中国的经历及中国的形势外,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吹美国应派特使到中国。巴驾的游说并没有徒劳,美国决定派顾盛作为全权公使赴华谈判。巴驾被任命为使团的中文秘书。巴驾获得这一殊荣不仅仅是他懂得汉语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更重要的是巴驾在中国开设医馆产生的影响力很广,很多政府的官员乃至林则徐都成为了他的病人,他个人的声望及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将对使团完成订约任务产生重要的推动力。在巴驾的日记中他曾这样写道:“我对中国语言和清政府官员的熟悉使我获得了作为使团秘书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谈判中,只有一个中方官员我不认识,是翰林院的赵长龄,耆英是我的病人,广东布政使黄恩彤是我的朋友,潘仕成的父母曾是我的病人……他们对我的品格和我对中国人乐善好施的精神都很熟悉,因此对我表示明确的信任。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猜忌心理,这种情况对谈判是非常有利的。”[9]而这样的判断很快在《望厦条约》中得到了验证。在巴驾参加的中美谈判中,由于他与中方代表的特殊关系使他轻而易举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获得建立教堂的权利,而这些涉及传教士的部分条款也均出自巴驾之手。除了聘请巴驾作为使团秘书外,顾盛还增聘裨治文为官方牧师,后来卫三畏也帮忙做一些中文函札事宜。
1844年订约后,不论新教或是天主教,不论美国或是英国等其他国家的传教士都可以援引《望厦条约》中允许到中国开放口岸传教,很多传教士不顾明文规定到处游历,甚至引起当地官员、民众、绅士的愤慨而生产激烈对抗。不论活动是否违反法律,他们都以领事裁判权为由拒绝受中国政府的管理。而这一切皆源于传教士在条约中对自身权利的扩张。
《望厦条约》并未让传教士在整个中国自由传教的心愿达成,他们不断地抱怨着清政府将传教的权利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他们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冷漠和拒绝归咎于政府的限制,在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前,他们赤裸裸叫嚣着将跟随联军通过武力让中国做出让步。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谈判中,传教士卫三畏担任美国代表团的翻译兼秘书,在初步谈判中他拟定的条款是,“一切人等有信仰基督教的完全自由,允许美国传教士游历全国各地、租赁或购买房屋土地和携家眷居住。”[10]这一条款很快被拒绝了,理由是新教的传教士携有家眷必须限定在通商口岸,很明显,允许怪模怪样的外国妇女在中国各地旅游会让中国人感到不安。但卫三畏却通过欺骗的手段,在措辞上进行了调整,实际内容与之前的一样,第二天送到钦差面前时没有进一步讨论就顺利通过了。之后卫三畏还庆幸自己用巧妙的手段获得的成功并为自己解释,“既然基督教是所有国家获得上帝最伟大恩赐的惟一来源,那么为了使福音让更多人听到并免遭一切质疑与阻止,有义务使用任何手段。”[11]《天津条约》中的传教宽容条款获得通过后,卫三畏还将四国《天津条约》中有关宗教宽容条款的内容向传教士们宣读,并号召他们尽量对条款作宽泛的解释。两年后的中法《北京条约》中规定,“准许人民传习天主教,给滥行拘捕基督教徒的那些人应给予处分,将之前没收基督教的不动产,一体赔偿,允许教徒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房屋。”[12]经过这两个条约,传教士终于获得了在中国全境自由传教的特权。
美国传教士之所以处心积虑一步步获取在华的传教权利是因为在华传教士所受的限制远比商人多,传教士更希望在美国政府庇护下沿着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维护在华商业利益下获得自己的那份利益。在政教分离的美国,政府是不允许传教士参与政事的,但在中国外交工作的最高领域,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扮演了政府左膀右臂的角色。正如1858年担任公使的列卫廉对传教士所作的评价,“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的人们的学识,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任翻译人员,公事就无法办理。有了他们,一切困难与障碍都没有了。”[13]而传教士们也对得起政府对他们的重任,在很多重要的谈判中他们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容阐述得淋漓尽致,并利用天赐良机将传教条款塞进中美条约中。
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与美国的商业扩张是紧密相连的,无论其起到的积极作用或是消极作用,都烙上了美国侵略的印记。他们的一切服务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关。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无疑是对基督教义的亵渎,引起了早期来华基督教徒的反感。商业与福音本身是不相容的个体,但为了福音在中国大范围推广,部分传教士站在了鸦片走私商的阵营中,因为前者在进行鸦片走私及对华武装威慑的同时,传教士搭了便车。传教士是所有美国人中最深入中国社会的群体,他们懂中文,能准确表达华人对美国人的看法,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信息传递给美国,这些言论得到国内传教组织及美国民众的关注,甚至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最终对美国政府对华鸦片政策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1][4][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8,257,258.
[2]William Tyndale.New Testament.[M].Wordsworth Editions Ltd,2002.228.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637.
[6][9][11]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63-69.
[7]R.M.Martin:China,Polical,Commercial and Social,Vol.I,[M].British Library,1847.177-178.
[8]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141.
[10][13]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72-476.
[12]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一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472-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