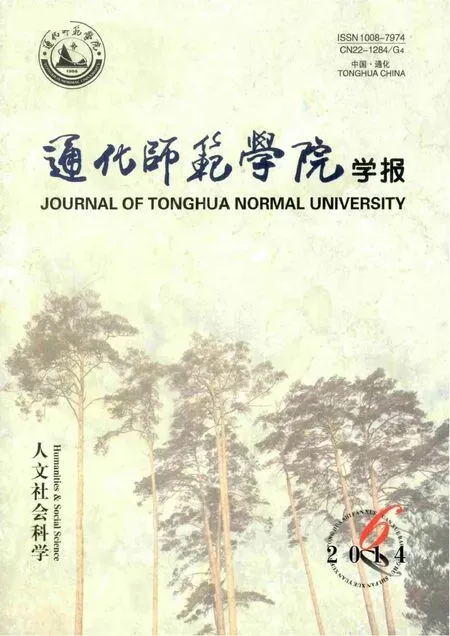“底层文学”的创作误区
王学胜,袁 华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底层文学”的创作误区
王学胜,袁 华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底层文学”的作品在学术界的质疑声中大量涌现,仔细解读这些作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底层文学”的作家们在创作中走入了误区。诸如作品中底层生存环境与现实的偏离、情节的“失真”和人物的“空壳化”等。
底层文学;误区;偏离;失真;空壳化
如何最大化地接近底层,应该是作家在创作中努力实现的目标。学者安敏成就非常推崇鲁迅关于写实主义的观点,对于鲁迅所提出的:“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的观点,安敏成认为,鲁迅的观点是朴素的和意义深远的。通过它,鲁迅完成了社会关系与“写实主义”的结合,他暗示,文学经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我”“你”和“他”或“她”分别构成了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人物,决定了选择哪种文学模式。如果我们还未洞悉底层的面貌,那个“本真”的底层离我们仍然遥不可及时,我们不得不在“社会关系”中来面对“底层文学”的问题。惟其如此,底层才有意义,底层才能去除空虚的、缺乏厚重的假想与阐释。我们才会重视底层的复杂性。而现在我们关于底层的表述有简单化的倾向,这显然有把底层作“本质主义”定义的原因。细读“底层文学”的作品,我们发现较为成功的底层生活的书写来自于精英阶层对“底层”的描述:精英与底层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书写在想象中顺利前行。比较而言,精英作家笔下的作品虽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底层的自我书写则问题重重。
无产阶级、平民、劳苦大众这些在过去阶级时代频繁被使用的阶级术语,很多时候被替换成 “底层”的“等价物”。今日中国,虽然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阶层却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学者的视野中,作家就被划分为精英与草根两个阶层,精英作家和草根作家都离不开文学创作的倾向性的问题。虽说精英作家身上摆脱不了阶层差别的利益性制约,甚至作家笔下的底层生活根本无法摆脱某种意识形态的附着。可叫人欣慰的是,即便作家的世界观不那么靠谱,也并不必然带来其创作中的倾向性,就一定会偏离对底层的悲悯和尊重。马克思曾就此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作家的创作有可能突破自身世界观的局限,这在现实主义作家当中尤为明显。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某种现象或事件的看法,很可能有别于他所一直坚持的观点或倾向,即世界观与作品效果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恩格斯在该问题上的见解与马克思达成了共识,他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现实主义可以突破作者思想的局限而展露出来,巴尔扎克就其打破了自身的政治偏见和阶级情感,从而走向了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马恩的论述从理论上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之外仍然存在着书写真实“底层”的可能。而 “文革”时代的“工农兵创作”则从创作实践中给我们的“底层文学”创作提供了负面的教材。
一、作品中底层生存环境与现实的偏离
像大家熟悉的那样,近期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了“底层文学”热衷的书写对象。数量庞大的书写农民进城打工的作品中,充分地关注了这些农民的权益保护、社会福利保障以及子女受教育权力等问题。研读一下这些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关于城市边缘人群的书写大多都夹杂着对城市的道德审判,这种渗入其中的道德主义意识,让这些“底层文学”作品失去了客观与公允。大部分的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人公的小说常常夸大城市居民的自私、冷漠和虚情假意,美化进城务工人员的忠厚、热心和勤劳俭朴。即便有部分进城农民做出违法之事,也是由于城市道德败坏对他们的污染同化导致其精神的扭曲。
《太平狗》是2005年陈应松推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程大种带着他的赶山狗太平去武汉打工,最后惨死在黑工厂,而土狗太平虽然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丢了半条尾巴,最后还是奇迹般地回到了神农架的家中。在这个悲惨的故事中,城市像地狱一样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即便是程大种的姑妈亦是人情冷漠,骂起程大种来如同泼妇,即便是年节也不让儿女前来探望。如果说作为个体,这倒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因为每个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对待亲人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城市当中肯定存在激烈的竞争,然而并未达到像小说表述的那样可怕,到处是弱肉强食,能置人于死地的黑工厂毕竟是很少的。但是小说由于把黑工厂作为主人公程大种生存的环境,城市似乎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魔窟,似乎进城的农民工只有被骗进高墙内如奴隶般工作,得病之后,由于无人照顾,只能在床上任由老鼠啃噬,直到病死。小说为了情节发展的必要,同时也是要反映出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黑砖窑事件,但是就目前披露的新闻事件而言,那些黑工厂所用的工人大多是智障人群或聋哑等残疾人。因此小说在进行艺术加工时,虽然突出了程大种所遭受的苦难,但是却制造了城市随处是危机的假象。因此整篇小说中,陈应松有把城市妖魔化之嫌。这种妖魔化在其他“底层文学”作品中也比较常见,一般把乡村看作是净土,把城市描绘为罪恶之源。
我们必须承认程大种的经历或许存在真实的可能,但它不具备代表性。为了程大种在小说中恐怖经历能够自然地发展,陈应松把城市和乡村描绘成了恶与善完全对立的两极。城里人,有钱人永远都是无情的、卑鄙的、残忍的。在限定的历史空间内,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对某些事物抱有的特殊情感等因素往往会左右他在撰写作品时的心态,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在此得到展现。陈应松曾直接表达过自己讨厌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他说他厌恶城市和富人,在电影和小说中,他们经常居住在华丽的住所当中,电影中演员的表演都是不真实的,感情是不真挚的,城市和富人的心态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变态的。而农民和小人物的情感才是真实的,痛苦与幸福都是催人泪下和优美无比的。
意识中乡村道德与城市道德水火难容,导致大部分作家选择用极端的形式来进行道德描写。其中尤凤伟、孙惠芬和荆永鸣可谓其中代表。他们的作品往往在歌颂乡村道德淳朴的同时,抨击了城市道德的失序。这三名作家在表现进城务工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尤凤伟所创作的《泥鳅》堪称丑化城市道德的代表。小说没有从进城务工者自身去寻找道德沦丧的原因,而是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城市。《泥鳅》中的蔡毅江,原本只是搬家公司中一名靠力气吃饭的搬运工,但是一次货车司机紧急刹车事件让他的睾丸被撞碎,被工友送到医院后,因未被及时救治而丧失性功能。于是他带领一伙人强奸了当事的女医生,并逼迫女友寇兰去做小姐,自己则当上了替工商局收税的盖县帮老大。王手的中篇小说《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主人公农村女孩李美凤为了能够使用老板家的浴室洗澡,不惜沦为老板泄欲的工具。更可悲的是,李美凤并不把这种侮辱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反而认为身体白天打工赚钱,晚上闲着也是闲着。最后因为老板儿子在车祸中丧生,老板一家把丧子之痛都发泄到她的身上,诬陷她偷了儿子的钱,让她进了警察局。类似的境遇,在尤凤伟的《泥鳅》中也能读到:纯洁、质朴的陶凤和寇兰,都计划着进城后用双手赚钱养活自己,没想到最后前者被逼疯,而后者沦为了出卖肉体的妓女。
综上所述,对城市进行“丑化”在很多“底层文学”中流行。数量之多,已经不能让我们相信这仅仅是个别的例外。诚然,城市当中肯定存在卑劣的坏人,而且部分城市居民往往对进城的农民抱有一种天生的歧视,但这绝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然而,由于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泛化处理,透过这些“底层文学”就会构建一种假象:是城市道德的沉沦造成了进城务工人员的苦难和不幸。可是我们又如何解释同样发生在乡村的罪恶呢?把蔡毅江放在农村,我们很难相信报复心如此之强的性格会忍气吞声地迎接外界的戕害。由此可见,无论是小说还是小说外,受了伤害便不顾一切去打击报复的行为,都只能是非典型性的个案。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很多一时无法解决的矛盾,矛盾的激化会把一系列的磨难推给底层民众的生活,“对底层苦难的表现同时伴随着仇恨与暴力,”[1]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接受对于城市进行歪曲化的书写以及为实现此目的不符合情况的“胡思乱想”。或许大多数作者对城市作出偏离现实的“妖魔化”的处理是为了提高文本的阅读快感,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如此毫无顾忌地刻画极端,何况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削弱作品的批评力量,而且还以对城市的“恶意中伤”为代价。“包容或正视那些来自边缘的异议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怂恿、鼓励某种极端社会情绪和‘革命’的滋生。 ”[2]
二、情节的“失真”
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同时,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城市与乡村、精英阶层与底层百姓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严重。农村无保人群、城市失业、半失业以及城市边缘人等社会底层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忍受着、挣扎着、盼望着,尤其是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社会矛盾也相当尖锐。同时,我们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农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用工荒的难题,于是每年正月一过,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这些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劳动或服务性行业,他们只能处于城市的底层。无论是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群,还是这些农民工,他们生活中的苦难和悲剧都成为众多作家书写底层的热点。苦难的极端化书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产生并大行其道。
农民工从人情味浓厚的庄稼院来到钢筋混凝土铸造的“城市牢笼”,“他们虽然工作、生活于城市,可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却保留着在家中式的印记。”[3]这必然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冲突的设计要水到渠成方可,如果人为痕迹过于明显,必然会降低作品的批判力度,沦落为猎奇媚俗之作。如刘庆邦的《守不住的爹》中的一段情节显然就不合情理,叫人无法接受。爹一心想找个女人,让小青和小龙有个娘,有个完整的家,这倒是符合逻辑:无论从照顾孩子的角度,女人更细心些;还是从性生活和情感的角度都能让人信服。可是爹把一个暗娼领回家,把小青和小龙都撵到二婶家去睡,然后整宿地嫖,最后由于付不够嫖资,被那个叫乔阿姨的女人坐在堂屋里一顿臭骂,这和小说的前后情节及人物形象不太匹配。
事情很明显,小说中过分渲染了底层生活的细节并做了“性趣化”处理。当然刘庆邦的作品不是情色文学,对性爱细节的刻画只是点到为止。这种情节虚假的情况也出现在胡学文等其他作家身上。
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中就采用了情节突变的叙事技巧。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字叫吴响的乡村地痞,他是一个喜好女色的光棍,因为有把力气,一股匪气,而且六亲不认,副乡长毛文明任命他为护林/坡员,并享受村干部待遇。而吴响也利用他的这种小权利,为自己占女人的便宜创造各种条件。小说在开篇就描写了吴响试图勾引尹小梅的场景。为了得到尹小梅,他故意装作没看见,等尹小梅牵牛越过围栏进草场吃草,才去当场抓住把柄。可是倔强的尹小梅并没有让他得偿所愿,恼羞成怒的吴响为逼其就范把她押到乡政府副乡长毛文明处关了起来,没想到尹小梅却再也没能活着走出乡政府。到此,小说的第一次突转出现。但是此处情节便有故意夸张之嫌:首先小说中我们未发现尹小梅的身体有疾患的伏笔;其次开篇也并未表现出来尹小梅长的多么漂亮。这就让我们对尹小梅的死因充满疑问:既不是突发疾病而死,也排除了乡政府工作人员强暴未遂杀人灭口的可能,如果单单就想教训教训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尹小梅的死对毛文明都没有好处,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尹小梅服软。随后的吴响从一个可以说是“狗仗人势”的流氓,转变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形象,开始奋不顾身地去调查尹小梅死亡的真相。如果不是胡学文故意用来对比基层权力机构对待底层百姓还不如地痞流氓的话,读者无法接受吴响反差如此巨大的举动,我们也很难相信是为了塑造丰满人物的需要。胡学文指出:“我对乡村情感上的距离很近,可现实中距离又很遥远。为了这种感情,我努力寻找着并非记忆中的温暖。”[4]可是胡学文展现“温暖”的方式却很特别,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良心泯灭的光棍无产者“吴响”来描写这种远离的情感,着实叫人生疑。令人遗憾的是至此情节的虚假依然在继续:小说的结尾黄宝因为后悔没给妻子尹小梅伸冤,先撒钱后跳河自杀了,这显然有悖常理。如果黄宝既不贪财也不怕死,为什么不去调查妻子的死因呢?有什么还有比选择死亡更苦更难的吗?作家这么处理更多的只是故意加重悲剧的惨烈程度罢了。
上面我们提及的作品中,大都描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可是我们不能忘了,生活中还有温暖和亮色的一面。比如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舍身救学生,最美警察李博亚为救乘客被火车轧断双腿等等,可谓不胜枚举。然而,“底层文学”的这些作品中回避了阳光的一面,除了要博取读者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同情之外,还隐含着另一层含义:写不出优秀的,就写怪异的。为了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为了读者能够买账,好多作者不惜去搜罗一些怪异的、离奇的、罕见的内容写入作品。批评常常从实际利益出发促生了城市妖魔化书写的流行。一句话,如此样态的创作与批评是不折不扣的小众文学圈子的合谋。一些“底层文学”只是把阴暗公开呈示一番而不加褒贬,会贻误众生。因为我们无法体会到有尊严的生命和纯净的心灵,无法读出带有正义追求的真理及人类的共同价值。
三、人物的“空壳化”
脱离原型,把人物完全变成作者的影子,情况会如何呢?贾平凹在2007年出版的《高兴》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客观地说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最具实力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一曲《秦腔》让我们看到了他勾勒农村底层的生存百态的能力。《高兴》原本可以成为贾平凹得心应手之作,但是由于他刻意地追求创新,虽然逃离了“底层文学”目前热衷的苦难叙事,但是由于笔下的刘高兴,已经不是那个发小“刘书祯”,完全变成了是捡破烂的“贾平凹”,让这部《高兴》失去成为“经典”的机会。小说中刘高兴是一个颇有些书生气的拾荒者。他穿戴干净、齐整,见城里人不卑不亢,他拾破烂用的板车上还时常放着一只萧。即使是见到让很多司机都发憷的交警,他也未表现出任何慌乱,他甚至还和交警搭讪,几句不失身份的恭维之后,交警笑着拍着他的肩膀让他走。在这部整整62章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刘高兴有什么突出的缺点,几乎尽是美德。相反,五富、石热闹和黄八等人身上,却有很多底层人民的缺点。吝啬的五富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舍不得错花哪怕是一毛钱。好逸恶劳的石热闹,一直装瘸利用行人的同情心来乞讨为生,即使是刘高兴给他钱去买烧饼,他也没花那三元钱,而是要来了一张饼。在刘高兴需要他向警察说明自己不是杀五富的凶手时,他却悄悄地躲了起来。
小说中对刘高兴性欲望的书写,也显得比一般的底层民众要“清高”得多,因为他不会去找妓女来解决身体里膨胀的欲望。即便是他心仪的妓女孟夷纯也是如此的“脱俗”——卖身救兄的行为可以称得上是当世的“锁骨菩萨”。刘高兴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欲望,似乎超越了人物自身的可能,毕竟是孟夷纯当街亲了他之后,他也没有想去马上去占有她的想法和行动,读者会相信如此虚假的强大和纯洁吗?我想大家都不会怀疑这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道德感使然。当一位作家试图塑造某种传声筒式的人物,而无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欲望和需求时,抛开人物的自身的行为逻辑时,只能是对书写对象的漠视和扭曲。
刘高兴的人格高尚,他把一只肾脏献给了城里人,他遵守交通规则,他随时随处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以获取所有人的尊重。他恪守着道德的底限,不收脏物,不挣来路不明的钱,在五富死后得知黄八替自己和五富垫付了一百元的房租,非要把一百块钱硬塞给黄八。为了表明刘高兴的不同,贾平凹还让他的主人公嘴里不时出现些哲理名言,以表明刘高兴是有修养和高雅的人,尽量去适应城市。刘高兴还经常劝五富不要对城市充满仇恨,要学爱这个城市,只有这样西安城才能接纳你。如此的人物特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中提倡的高大全英雄形象是多么类似啊。可惜,他们都太没有“人情”味了,太过虚假。为什么底层人民一定要漠视金钱和抑制身体的欲望才会被认为美好;为什么底层人民只能忍让和奉献?他们应该有愤怒、不满及正常人所应该普遍具有的一切情感。遗憾的是,在刘高兴的艺术形象里,早早就设定了基调:知足常乐的“好人”与“有素质的人”,表面上似乎保持了人物的特点,但实质上却没有留给人物能获得生长和发展的自由,相反,他从始至终都是为作者的既定意图服务的工具。刘高兴实际上是贾平凹指导底层人民应该如何生活的一个符号。通过小说,贾平凹在向底层渗透一种生活哲学——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读小说《高兴》时,我想到了陈应松在2002年写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由于《松鸦为什么鸣叫》很大一部分是写伯纬的“背尸”和“救人”的场景,没有像陈应松另外的几篇作品小说那样经常被提起。小说《高兴》中也有一段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回家乡的描写,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松鸦为什么鸣叫》写得更为出色。伯纬遵守了对一起去修路的王皋的承诺——如果王皋死了,就要背他回家。就是这样一个半开玩笑的话,成了伯纬历尽千辛万苦把王皋的尸首背回村里的精神支柱,当然这里面还有共患难的友情和同乡之情。伯纬在深山老林中背着王皋的尸体往家里赶,一路上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啃生苞谷和洋芋,在经历了失足差点跌入悬崖、黑熊的对视、松鸦的追赶等一系列磨难之后,终于把王皋的尸首运回了家。虽然王皋的尸体已经不是完整的了,但这不能怪伯纬,因为缺失的半个脑袋本来就是在工地被炸药崩没的。陈应松对伯纬背尸回家一路上的描写可谓句句到位,无论是伯纬一边走一边跟王皋的尸体说话,求王皋不要在他背上作怪,还是对王皋尸体在夏天的高温下产生的尸胀进行的细腻刻画,都显示出陈应松不俗的写实功底。然而反观《高兴》我觉得就要稍微逊色一些。从医院中谎称去拍片把五富的尸体偷出来,接着骗出租车司机说五富喝醉了,一直到火车站被警察发现,过程都比较简单,我想这肯定不是贾平凹的想象的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预先设定的基调决定的:他不想表现过多的苦难和悲伤,那样就和把主人公叫“刘高兴”的巧妙设计相违背了。贾平凹不是忽略苦难,而是更多地想展现底层在面对苦难时的乐观,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刘高兴”的形象中有太多的在城市谋生的农裔作家的影子,这就压制了在苦难时刻应有的表达。如果在偷运尸体的叙述中再多些笔墨,可能更会彰显底层生活的苦涩,还能和“高兴”的标题更强烈地构成一种“欲哭无泪”的张力效果。
因而,当一位作家仅仅描写底层人民的眼泪,或者只是赞颂底层人民的某种美德,都是不尊重他人生存状态与情感方式的行为。我们需要谨记这样的事实:一个人,无论他的知识、地位、财富如何,他身上都参杂着善与恶、简单与复杂、阳光与灰暗、高贵与卑贱。正如前面所说,底层人民的生活有质朴、节俭、重情义的一面,也有自私、贪婪、胆小等小农意识严重的一面。他们有着对世界的复杂感受和认知,他们都是俗人,并不像官方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没有缺点。因而,我们需要关注底层人民,但不需要毫无节制地赞美,更不能掏空了底层人物,而把作家自己的灵魂附体在其身上。如何理解并尊重底层人民的生活,而不是想当然地“改写”,这恐怕是作家面对底层生活时的最大挑战。
读了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描写底层社会生活的“底层文学”既不是文学的一种现实性突破或现实性转向,也并不比其他范式的文学做出了更多的诗性突破,因此它根本就不是新的文学曙光。相反,由于它正在走向一种玩味和展览,正在发展成一种新兴的公共写作 (局限于小众群体)。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文学范式,“底层文学”凭借介入现实的穿透力量,依然是很多评论者和作家热衷的对象,尽管如此它直到现在还没有显示出某种诗性的优越和主题倾向。
“底层文学”将底层民众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人物形象的主观臆造,虽然或许会吸引一些读者的猎奇心理,却缺乏对底层民众一种负责任的书写与尊重。对于这样过度夸张地呈现的底层生活状态,对底层生活缺乏了解的“底层文学”读者就会以为,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如果缺少了对这种生活的追问和批判,必将误导人们去接受甚至模仿生活中的丑陋和卑劣,于是,乡间陋习、城市丑恶、变态人格、阴暗心理都会在生活中自由自在地生长。
[1]陈晓明.“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J].文学评论,2005(2).
[2]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J].天涯,2005(5):29.
[3]张谦芬.90年代以来乡村书写中的城市背影[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4):67-69.
[4]胡学文.《命案高悬》创作谈:高悬的镜子[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8):121-123.
(责任编辑:章永林)
Creation Misunderstanding of"Underlying Literature"
WANG Xue-sheng,YUAN Hua
(College of Literature,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Tonghua,Jilin 134002,China)
The"underlying literature"works caused large numbers academic questions,after careful reading these works,we found that the"underlying literature"writers had gone into the creation misunderstanding,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underlying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ality,the"distortion"of plot and"emptyshell"character in the works.
underlying literature;misunderstanding;deviation;distortion;empty-shell
I021
A
1008—7974(2014)06—0059—05
2014-06-30
王学胜(1978-)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底层文书”批判。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385号;通化师范学院博士扶持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