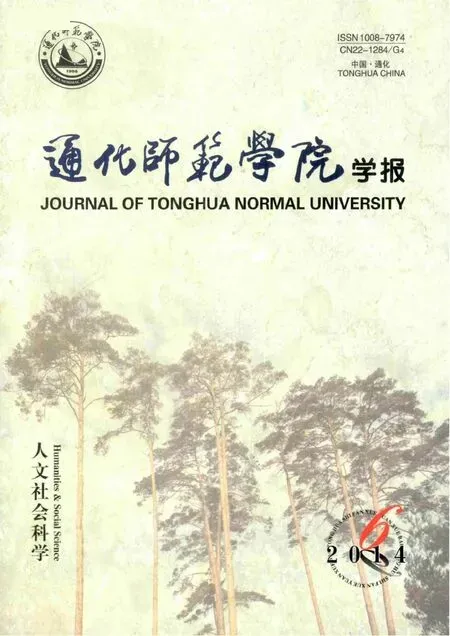巴利和薛施蔼整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与贡献
许卫东
(河南大学 文学院 语言所,河南 开封 475001)
语言理论研究
巴利和薛施蔼整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与贡献
许卫东
(河南大学 文学院 语言所,河南 开封 475001)
该文重点梳理了巴利和薛施蔼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整理工作,分析其带来的影响与贡献,总结了二人的整理工作对当下索绪尔思想研究的指导意义。
巴利;薛施蔼;普通语言学教程;整理工作;影响与贡献;指导意义
【主持人的话】本栏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言理论和教学专业委员会协办
■河南大学许卫东副教授,通过分析巴利和薛施蔼整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与贡献,使我们再次听到索绪尔“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也看到索绪尔的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学术创新动力,对研究语言学历史具有启发意义。
■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曾传禄等,认为现代汉语副词“果真”和“真的”的明显差别是:“真的”表示使人相信的主观愿望;“果真”表示跟客观事实相符的预先相信的结果。这启发我们:挖掘词义的区别特点,需要有音位学的对立意识。
■山东工商学院周树江教授,列举语言生活中的交际现象,探索语言使用者怎样根据语境不断变换交际策略达到交际和谐有效,对语言的动态使用具有理论意义。
(彭泽润,关彦庆)
德·索绪尔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被称为结构主义创始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因《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我们简称 《教程》,中译本《教程》我们下称高本①)影响很大。但《教程》并非他本人所写,而是经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当时听课同学所作的笔记并参考他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手稿编辑整理而成的。《教程》使索绪尔获得了世界声誉,但似乎也掩盖了巴利和薛施蔼的贡献。本文试图对巴利和薛施蔼整理工作予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他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②及对我们当下进行索绪尔思想研究的指导意义。
一、巴利和薛施蔼的整理工作
(一)整理工作的背景
1.对索绪尔思想的敬仰与了解
沙·巴利和阿·薛施蔼在《教程》第一版序言里用“天才”“顽强”“独到见解”“不断革新”“大师”“敬爱的老师”等来称谓和描述自己的老师,[1]11-15足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人格魅力的敬仰、赞美与维护之情,这是巴利和薛施蔼整理工作的一个很直接的动力。巴利在1895~1905年听过索绪尔的课程,薛施蔼在1891~1893年听过索绪尔的课并根据听课于1908年发表《理论语言学的方法和纲要》,巴利为此撰文予以评论,而索绪尔也于同年曾写过一则短札予以褒奖。[2]298由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了解老师的思想动态,时常听到索绪尔“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不足为奇,追随索绪尔的学术思想并加以整理也在情理之中。
2.弥补遗憾
遗憾有两个方面:
一是索绪尔本人的遗憾。索绪尔在1908年为薛施蔼撰写的短札里说过,19世纪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发表过许多论文,为建造语言学大厦备足了有用的材料,可惜没有哪个人致力于探讨这座大厦的基础,就连他最欣赏的美国人惠特尼,也不觉得有必要构筑一种全新而系统的语言学理论。[2]、[3]226-227索绪尔只能孤独而顽强地“探索在这一片混沌状态中能够指引他的思想的法则”。他曾在1911年对戈蒂耶(Gautier)坦言,他曾为之而努力过,并对戈蒂耶谈了对语言科学的设想,但他记的笔记却遗失了。[3]5-6不难看出,索绪尔有过著书愿望,但因诸多痛苦尤其病痛折磨而无法完成这个愿望。
二是索绪尔学生们的遗憾。索绪尔的法国学生梅耶就称颂他是一位“有自己的学说和方法,能够以个人的特色来陈述一门科学”的优秀老师。[2]297索绪尔授课内容充实,方法独到,但最终没有出版过普通语言学方面的一本书,凡特别有幸听过这门课的人都深以为憾就在情理之中了。探究深层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有两点:一是老师的人格魅力,一是老师的思想,这两方面在学生的心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作为学生,巴利和薛施蔼觉得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弥补这两种遗憾。
3.超前的预想
如果对索绪尔思想的敬仰和为弥补遗憾是巴利和薛施蔼整理索绪尔遗稿的头等精神动力的话,对索绪尔思想将能产生的影响,他们不可能是盲目的,换句话说,他们对此有一种超前的预想,尽管是模糊的,这应该是他们整理工作的另一种动力。
德·索绪尔夫人把索绪尔的手稿交给巴利和薛施蔼后,他们第一反应是“指望在这些手稿中找到这些天才的讲课的忠实的或至少是足够的反映”,“并且预想到有可能根据他本人的札记配合同学们的笔记加以整理,付梓出版。”[1]11很明显,在对索绪尔思想有了一定程度了解的基础上,他们希望能比较直接地在这些遗稿里找到印证材料,加以整理就可以出版。但事实上,问题远比这复杂和困难得多。诸多困难没有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整理工作,本质上就是源于他们对索绪尔思想影响的超前预想:这却正像很早以前《论元音》一书问世时那样,标志着索绪尔一生事业中一个光辉的阶段。[1]12
(二)整理工作的难度
1.巴利和薛施蔼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但因为职务缠身等原因,他们为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去亲自聆听索绪尔最后的讲课而深感遗憾。因此,他们在理解索绪尔思想的深度上必然有所折扣,这是造成他们整理工作的第一个难度。
2.因德·索绪尔是一个不断革新的人,因他思想的发散性以及自由论述中的重复、交错和变幻不定的表述方式所致,他每天赶写讲授提纲的草稿,已经随写随毁掉了;从索绪尔夫人那里得到的部分手稿里面几乎找不到一点儿跟学生笔记对得上号的东西;他的书桌的抽屉里的一些相当陈旧的草稿,虽然不无价值,但要同三度讲课的材料配合起来,却有难度。所以索绪尔的相关资料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框架,这是巴利和薛施蔼整理工作的第二个难度。
3.第三个难度与学生的笔记有关。上述两个难度使得巴利和薛施蔼只好求助于听过三度讲课的同学们的笔记。尽管这些同学的笔记都很完备,提供了很好的证实材料,但学生的笔记肯定会因主人各方面素质不同而呈现出杂乱不一的情况。他们说过有一个特殊的要点还是从路易·布律茨(Louis Brütsch)的笔记中得到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4.第四个难度是口讲形式和书面形式发生的矛盾。巴利和薛施蔼认为这个矛盾给他们留下了最大的困难,这和第二个难度其实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简言之,索绪尔的表述和学生的笔记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偏差。
上述四个方面是巴利与薛施蔼整理工作中必须要面对的客观难度。
(三)整理的合理途径
面对诸多困难,他们为把工作做好,在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他们选择了以下两个重要途经。
1.考订
因在索绪尔手稿里面几乎找不到跟学生笔记对得上号的东西,考订工作就主要集中在学生的听课笔记上。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对每一度课,通过把所有的本子加以比较,来捋清讲课中的每个细节,尽管它们往往互不合拍,以此深入到索绪尔思想的端倪。
2.类化与重新组织
巴利和薛施蔼的整理工作拒绝把一切都照原样发表,也否定了只发表其中一度课的作法,更不是按照别人的建议把一些见解特别新颖的片断照原样刊印出来,所以考订工作并不意味着整理工作的结束。他们为解决口讲形式和书面形式之间发生的矛盾,最终采取的办法是:以第三度课为基础,重新进行组织和综合全部材料,按整个系统的指引,试图找到每一个要点的确定形式,然后镶嵌入它的自然间架中去;所有各部分都按照符合作者意图的顺序表达出来,哪怕他的意图并不显而易见,而是处于我们的猜想。不难看出,巴利和薛施蔼的材料梳理与归位无异是一种重新创作,而且越是要做到完全客观,越是困难。很显然,这种整理是在“类化工作和重新组织”的基础上的二次创作,其合理之处在于抓住了一个基本点——第三度教程,由此辐射到包括德·索绪尔个人札记在内的其他全部材料。这种作法由点及面,便于对索绪尔的思想形成整体的把握,从而“使人窥见德·索绪尔理论和方法的全豹”,而不至于损伤索绪尔思想,尽管其中也有对索绪尔意图的猜想成分,但总体来看,它是大胆的、自信的,也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
(四)对整理成果的解释
巴利和薛施蔼的整理成果面世时,他们在自省自己工作的基础上预见到了会遭遇到批评。这种预见本质上是对他们工作的深层解释。
1.他们首先阐明了整理工作的主旨:要建立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忽略任何有助于形成完整印象的东西。但这个整体并不是要涉及语言学的一切方面,把一切问题都讲得一样清楚明了,因为他们认为索绪尔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打算这样做过。这个整体是以索绪尔个人几条基本原则为基础构建的系统,所以在巴利和薛施蔼看来,有人会批评这个“整体”的不完备也在情理之中。他们“现在只能把这个初具规模的大纲中的一些闪闪烁烁的指示搜集起来,安排在它们的自然的地位;超过这一点就无能为力了。 ”[1]14
由上述可知,巴利和薛施蔼的整理工作是提纲挈领的,他们只想通过索绪尔提出的基本原则来贯穿索绪尔思想中的闪光点,而要涉及到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他们自感无能为力。所以,对于《教程》里缺失“语义学”,巴利和薛施蔼“并不感到这些欠缺对整个建筑物会有什么损害”。[1]14这不难理解,在他们看来,按照索绪尔的几条基本原则构建的系统没必要专门设置“语义学”的章节,况且即使不设“语义学”,也不代表索绪尔不关注语义方面的问题。
而对“言语的语言学”的缺失,他们解释为因索绪尔身体状况乃至离世,尽管索绪尔曾向听第三度讲课的学生许过愿会在以后的讲课中讲授这方面的内容,但最终这个诺言无法实现。
2.对于转录的一些要点,巴利和薛施蔼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是,他们认为“要一切都很新鲜是办不到的”。索绪尔的思想是在继承他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教程》里出现“一些人家说过的东西”是不难理解的。二是,他们认为某些转录的要点“对于了解整体是不可少的”,即转录的要点是整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他们还举语音变化的一章为例来说明他们的观点。[1]14-15
由上述可以看出,巴利和薛施蔼的整理工作很注重索绪尔思想的系统性建构、主体性的凸显和继承性的把握。
(五)面对批评的态度
巴利和薛施蔼面对批评,他们的态度是很坦诚的:他们说如果把予头指向他们,他们将乐意接受;他们的态度更是负责任的:他们深深感到 “对于批评,对于作者本人所负的责任”,他们“完全接受这个责任,而且愿意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不过,对于批评他们也提出了比较委婉的看法:“批评者是否知道要把一位大师和他的解释者区别开来呢?”言外之意,批评者不能盲目批评,对于他们整理工作的缺失不能归咎于他们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攻击到我们所敬爱的老师,那是不公正的[1]15。”他们对老师思想的维护可见一斑。
(六)《教程》的后续工作
《教程》出版后,索绪尔的学生们最早开始研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思想并形成了日内瓦学派,这个学派的第一代成员是巴利、薛施蔼、卡舍夫斯基(S. Karcevskij)等。他们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例如巴利的《语言和言语》(1926)、《共时和历时》(1937),薛施蔼的《在一种新的理论启示下的语言问题》(1917)、《三种索绪尔语言学》(1940)等。[4]日内瓦学派还从1941年起创办 《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de Saussure),刊登研究索绪尔的文章、索绪尔的遗稿和有关他的传记作品等。[5]51《教程》出版后,巴利和薛施蔼还在为整理、传播索绪尔的思想不停地奔波。
二、整理工作的影响与贡献
(一)带来赞誉
巴利、薛施蔼的努力使得索绪尔富有哲理和创建的精辟思想“充分焕发出它的光辉”。[5]53、[6]特伦斯·戈尔登称巴利和薛施蔼的这一举措是 “思想史上最令人吃惊的一种措施”。[7]1许国璋(1983)认为这些创见以一本书的形式传诸后人,则应归功于两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兼编订者。总的来讲,他们的工作是令人敬佩的。[8]15《教程》出版后,世界各国陆续用本国文字翻译出版这本书。例如上世纪20年代的日译本,30年代的德译本、俄译本,40年代的西班牙译本,50年代的英译本,60年代的波兰译本、意大利译本、匈牙利译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译本,70年代的瑞典译本、葡萄牙译本、越南译本、朝鲜译本、阿尔巴尼亚译本、土耳其译本,80年代的中译本。[5]52这本书真正拉开了现代语言学的新时代,也真正使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逐步走向世界,赢得了语言学的“哥白尼革命”这种声誉,《教程》因之成了表述索绪尔思想的《圣经》。时至今日,《教程》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从事索绪尔思想研究的学者,大都对《教程》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莫罗指出,在巴利和薛施蔼编写的《教程》中,“索绪尔的思想片断(很少的几处误解除外),一般说都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和忠实的传达,因此这本《教程》是索绪尔理论最完整的总汇,今后很可能还会流传下去。所以,我们对巴利和薛施蔼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是很诚恳、很明显的。”《教程》的编写,需要对学生的笔记等资料进行梳理、剪裁和整合,但巴利和薛施蔼对索绪尔思想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对索绪尔授课内容的转述,基本是可以信赖的。比如,《教程》中的“语言学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对象是语言,从语言本身去研究,为了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和“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1]323、169这两句名言经考证是编者所加,虽不能说是索绪尔语言哲学的完整概括,但它确实也概括表现了索绪尔的部分思想。
(二)遭遇批评
《教程》出版后的三年中,反响平平,相关的文章为数不多,只有十几篇,而且大都是质疑和批评之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质疑《教程》的忠实性,批评《教程》中存在的误解和歪曲。据莫罗的考证,严重误解、歪曲索绪尔的原意的地方就有二十多处。因材料的繁杂性和索绪尔思想的发散性,编写者或杂糅资料,或以自己的理解组织讲义而将自己观点强加于《教程》之中,这使得《教程》所反映的思想有了一定偏差,《教程》是否真实完整地体现了索绪尔思想也打上了折扣,人们据此无法判断书中一些有争议的细节 “究竟是属于作者还是导源于两位编辑者”。梅耶和索绪尔的学生勒嘉尔都提出过质疑,尤其是梅耶,作为最受索绪尔器重的学生,他至死也不了解《教程》的观念。[10]23
其次,质疑和批评《教程》的编排体系。质疑者认为索绪尔思想还不成熟,《教程》所建立理论体系,完全是编写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制造出来的;另外,许国璋认为《教程》编辑者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把索绪尔的最主要论点 (即语言符号和并时研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放在全书的绪论部分,作为索绪尔语言学的纲领,《教程》的这种编排次序并不符合索绪尔的语言学体系。[6]
抛开质疑与批评,我们应该承认,《教程》的确为索绪尔思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足也在所难免。如果不指出《教程》中的编写疏误,莫罗认为“我们对巴利和薛施蔼为传播语言学大师的理论所做的工作就不够负责。 ”[9]
质疑与批评提醒我们,要真正了解索绪尔的思想,《教程》是基础,但还要依靠其他不断发现的索绪尔资料。
(三)促成语言研究的新发展
《教程》促成了语言研究的新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1.提出了语言新思想
许国璋指出,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静态与动态、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符号和符号系统等一系列概念都是索绪尔的创见,并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和线条性原则是贯穿于索绪尔思想中的基本原则。《教程》提出了新语言思想,这恰如布龙菲尔德所言:索绪尔那本书为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11]
《教程》里索绪尔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从后来发表的1891年至1894年期间的手稿来看,他已经在思索“实质”“同一性”“惯例”“静态”和“动态”等一系列新范畴,并把语言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从索绪尔的三次授课中,更是容易看到上述新理念。索绪尔敏锐地指出:五十年来,在德国诞生和发展,并为许许多多语言学家推崇的语言科学,一次也未试图上升到抽象的程度……直到今天语言学的特点仍然是完全没有基本原则。[12]这些创见是索绪尔反叛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理性思维结晶,也正是因为他多年从事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多年在大学里讲过这一门类的课程,深知其中的底细,于是在晚年创立新理论,以图革新语言的研究。[6]
2.开辟了语言新时代
J·卡勒(1989)指出:费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重新组织起对语言和语言本质的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新方向,从而使语言学在20世纪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现代思想家,一位使一门学科面貌一新的思想家。纵观20世纪语言学诸流派,无一不在《教程》中吸取营养,几乎一切语言学研究都沿着他指出的方向走向深入。
结构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都以索绪尔的系统和价值理论为依据: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接受了对立和区别的学说,哥本哈根学派的语符学理论则借鉴了价值学说和“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的命题,而美国描写语言学则从索绪尔的系统理论出发,提出了分布理论。[13]除此之外,梅耶和索墨菲尔特(Sommerfelt)的社会语言学,英国的伦敦学派和系统功能语法,巴利的日内瓦派风格学,薛施蔼的心理语言学,乌尔曼(Ullmann)、帕里埃多(Prieto)、特里尔(Trier)和莱昂斯(Lyons)的语义学,勃莱松(Bresson)和奥斯古德(Osgood)的心理语言学,乃至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都与索绪尔的语言思想有着割裂不开的联系。[5]、[9]、[14]其中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韩礼德的“语言潜能”与“实际语言行为”,都打上了索绪尔思想的烙印。乔姆斯基特别指出他提到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差别和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差别是有关系的。[15]110
索绪尔在许多方面标志着当代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开端,他最早阐明了今天几乎被公认为语言学要素的许多特征的课题[16]465,所以,索绪尔对20世纪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17]248,称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实不为过。
3.促成了索绪尔思想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范围内索绪尔思想研究具有可持续性,这主要体现在三波研究高潮上。
第一波高潮。我们在前面的第一部分的(六)里谈到过《教程》出版后日内瓦学派第一代成员是巴利、薛施蔼、卡舍夫斯基(S.Karcevskij)等的工作。最早研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思想的主要是索绪尔的学生们。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因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Benveniste)1939年在《语言学学刊》第一期发表《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语言符号施指和受指的关系是必然的而非任意的观点,引发了语言符号性质的“任意性与非任意性”争论。以薛施蔼、巴利为代表的日内瓦语言学派的观点是支持符号任意性。
第二波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70年代。期间,索绪尔思想考证成为重点,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日内瓦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戈德尔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1957)、该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恩格勒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1967~1974)、意大利莫罗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1967)。
第三波高潮开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1990年,俄国语言学家斯留萨列娃出版俄文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在恩格勒校勘的基础上,汇总全部已发现的索绪尔研究资料。[5]561993年,英国出版了索绪尔第三期课程的听课学生埃米尔·孔斯唐丹(Emile Constantin)的听课笔记《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本书由Eisuke Komatsu(小松·英辅)和Roy Harris编辑和翻译,是一个法英对照本。这为在《教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索绪尔的思想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参考。1996年,因翻修索绪尔旧宅发现了大量的索绪尔手稿。我们认为这三方面促成了第三波索绪尔思想研究高潮。
索绪尔思想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体现了索绪尔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强大的生命力,而这一切都起因于《教程》的出版面世。
(四)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我们知道,不只是当代的语言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等其它学科,受益于索绪尔的地方也是很多的,《教程》中的很多概念已为其他不同的研究领域所采用。
许国璋指出索绪尔的《教程》在欧美被认为是符号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符号学理论被运用到文艺批评领域,被称为“结构主义诗学”;其组合、聚合关系学说被应用到社会文化、社会习俗的研究领域,被称为“结构主义社会学”或“结构主义人类学”。典型代表如:
法国人Levi-Strauss最先也是最完整地把索绪尔的符号学说应用到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他把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学说叫做结构主义,于1945年发表了“在语言学中和人类学中进行结构主义分析”,以“结构主义”的称号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理论贯穿下的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人文学科统为一体。1960年,Levi-Strauss在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教授就职讲演时指出,索绪尔关于人类学的定义最为接近现代人类学家的定义。
1964年,法国文艺学家罗兰·巴特出版了《符号学要略》一书,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系统地运用于食品、时装、玩具、摄影等日常消费文化领域,对消费文化进行了符号学的解说。
徐志民指出,尽管目前对符号学的内容和功用,尚有争议,但索绪尔在这方面确实提出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13]
除了符号学的思想被运用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并把“语言”置于首要地位的思想对哲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话语”逐渐取代了“语言”的核心位置,人类思维焦点从“语言”转移到了“话语”,人类的研究由结构主义进入了后结构主义。这一转向与索绪尔不无关系,设想如果没有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划分,那么这个转换也许不会发生。 [7]186
此外,其他领域如:意大利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nalistes),如德伏托 (Devoto)和南奇奥尼(Nencioni)、芒德尔勃罗(Mandelbrot)和赫尔丹(Herdan)的数学语言学;历史主义者如巴格里亚罗(Pagliaro)和科赛里乌(Coseriu)等也都借鉴了《教程》的思想。[9]
三、指导意义
索绪尔的学生在索绪尔的思想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利与薛施蔼是其中的代表。从这些优秀的学生身上,人们看到了索绪尔学术生命的延续。莫罗说他们是索绪尔“教导学生从事研究的深刻责任感所结出的丰硕果实,一种通过学生使研究工作连续不断的意志以及利用这种方法来战胜自己的孤独感的标志”。[9]巴利和薛施蔼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敬仰的,他们的做法对我们当下的研究有独到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巴利、薛施蔼的师道尊严风范
本维尼斯特评论索绪尔回归日内瓦的科研沉默是 “思想的悲剧”,[10]16他最终也没有能够为普通语言学写出一部完整的著作。幸运的是,以巴利和薛施蔼为代表的索绪尔的学生和同事们意识到,应该把他口头传授的普通语言学思想保留下来。编辑出版这部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还是竭尽所能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使索绪尔成为一位有创见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8]14巴利和薛施蔼成就了索绪尔,他们不欺世盗名,不为自己谋名利,而惟一的动力就是要保留、传播老师的学术思想,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热爱真理的布道者,他们执着于此,明心见性。他们用自己的切身行动,不仅解释了老师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师道尊严”的内涵。巴利和薛施蔼的学术素养和做人的品格与胸怀堪称是学术界的典范,值得我们去敬仰。
(二)巴利和薛施蔼的朴学治学态度
巴利和薛施蔼在整理和传播老师的学术思想这个过程中,多方面搜集材料,从材料入手,以材料为依据;他们承认整理工作困难重重,但他们严谨、大胆而自信,努力做到客观,对自己工作能力也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谦虚的认识;他们敬仰、尊重自己的老师,在忠实于老师的思想同时,他们也实事求是地评价,有很多问题也不是老师所能解决的。很显然,他们的学术态度是朴学的治学态度。也正是他们的这种治学态度才使我们看到了索绪尔思想的基本面貌,他们为同时代和后世研究者提供了索绪尔思想框架,索绪尔思想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在这个框架中将得以丰满和发展。
(三)巴利和薛施蔼的同道合作和创造精神
《教程》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面世,离不开巴利和薛施蔼的同道合作(当然也有与阿·里德林格的合作),而且这种精诚合作必定抛开了其中的个人名利得失,至少我们没有看到过二人为名序排列而有的纷争。除此,巴利和薛施蔼整理工作还富于创造精神,这表现在他们在整理过程中对索绪尔思想的整体把握和恰到好处地整合,比如《教程》中的“语言学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对象是语言,从语言本身去研究,为了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和“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这两句名言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结语
索绪尔思想的伟大与丰富通过 《教程》得以体现,巴利和薛施蔼功不可没,但索绪尔的光芒似乎掩盖了巴利和薛施蔼的贡献。如果把巴利和薛施蔼比作索绪尔思想传播的桥梁应该是再恰当不过的,我们不该忘却他们。也许我们对索绪尔思想的把握和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他不仅是索绪尔个人的,也是巴利和薛施蔼乃至全世界的,索绪尔思想是以索绪尔为核心的集体结晶。它是在语言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领域中的一种认知成果,它已经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一种方法论,并将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 我们参考的中译本《教程》由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9。
②这里谈的影响和贡献主要是通过《教程》体现出来的,但有时也是通过巴利和薛施蔼的工作体现出来的,这二者往往是很难区分清楚的。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序[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慧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3]索绪尔(瑞士).普通语言学手稿(中译本)[M].布凯(瑞士),恩格勒(瑞士)整理.于秀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申小龙.评20世界的索绪尔研究[J].汉字文化,2007(3).
[5]戚雨村.索绪尔在世界和中国[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国外语言学,1983(1).
[7]刘艳茹.语言的结构之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8]Jonathan CuIIer.Ferdinand de Saussure[M].London:Longman,1978;中译本,张景智译.刘润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9]莫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J].陈振尧,译.国外语言学,1983(4).
[10]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中译本)[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1]熊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再认识[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1).
[12]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J].国外语言学,1993(4).
[13]徐志民.索绪尔的语言理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1).
[14]桂灿昆.索绪尔思想对美国结构学派的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1963(4).
[15]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6]罗宾斯.普语言学概论(中译本)[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7]罗宾斯.语言学简史(中译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8]作者索绪尔的生命历程与思想脉络[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责任编辑:章永林)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 on Sorting out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XU Wei-dong
(Literature College and Language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the work of sorting out 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At last summarize its direc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aussure thoughts.
Charles Bally;Albert Sechehay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work of sorting out;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directive significance
H146.3
A
1008—7974(2014)06—0001—07
2014-08-28
许卫东(1969-)山东招远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语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