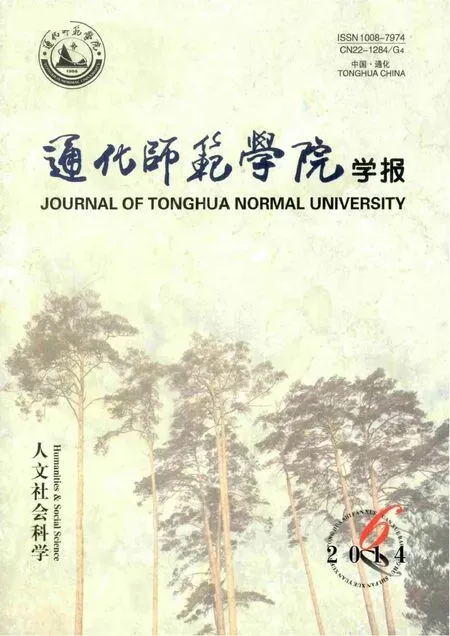“重新创作,另给新意”
——论许希哲小说《荔镜缘新传》对梨园戏《荔镜记》的改编
古大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文学·艺术研究
“重新创作,另给新意”
——论许希哲小说《荔镜缘新传》对梨园戏《荔镜记》的改编
古大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许希哲的小说《荔镜缘新传》对梨园戏《荔镜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创作”,从而产生了一些原作所没有的“新意”:在思想上,小说表现出崇儒与逆儒二元杂糅的特征,形成小说复杂多元的思想意蕴;在艺术技巧上,小说的心理活动描写、叙述方式和结构设计、文字风格、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别致之处。
《荔镜缘新传》;小说改编;思想和艺术;新意
“陈三五娘”故事是宋末以来广泛流传于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的民间爱情故事,以此故事为载体,出现了戏曲(梨园戏、潮剧和歌仔戏等)、传说、文人笔记、小说、歌册、民谣、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仅就梨园戏而言,就分别出现了明嘉靖本《荔镜记》、清顺治本《荔枝记》、清道光本《荔枝记》、清光绪本《荔枝记》,蔡尤本的口述本《陈三五娘》和华东会演本《陈三五娘》。许希哲在梨园戏《荔镜记》的基础上,将之改编成小说《荔镜缘新传》。张俊璂在小说的序言中说:“本书《荔镜缘新传》,系将流传在广东、福建一带家喻户晓的闽南才子陈三与五娘的故事重新创作,另给新意,可读性甚高。”[1]2-3张俊璂认为《荔镜缘新传》对《陈三五娘》进行了“重新创作”,那么,较之前版本,作者“重新”进行了哪些内容的“创作”?又“另给”了哪些“新意”?
一、崇儒与逆儒的二元杂糅思想倾向
《荔镜缘新传》“重新创作”的内容不少,其中两处内容比较重要,其一是虚构了一个“为主殉义”的丫鬟小香的形象,其二是改变了原《陈三五娘》各个不同版本都具有的喜剧性结局,把主人公命运改编成双双殉情的悲剧性结局。那么,这些“重新创作”的内容又赋予了小说哪些原版本所没有的“新意”呢?
小说中小香是个没有文化的哑巴,但却完成了一件义薄青天、荡气回肠的“大事”,即为挽救主人五娘一命,主动装扮成五娘,为主投井殉义。这个属于作者“重新创作”的情节用意何在?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观念?这个“重新创作”的内容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林玳带官兵来陈三家搜捕,陈三有事外出,五娘刚好在家,官兵破门而入,五娘危在旦夕,寻机藏身橱内,这时,益春“竟瞥见小香浑身上下,穿戴着五娘的服饰,站在五娘的卧房门口,怅然凝望,似乎有所等待。一见益春,即双手作势,比向她自己,又比后花园的方向,又作投井状,接着不待益春有什么反应,就转身向后花园跑。益春立刻明白她的意思了,心中一急,竟喊不出声来,只好跟在后面急追。但小香本来手脚比益春灵活,所以当益春追到后花园的时候,小香已经手按在古井栏上,纵身一跳,跳下那口数丈深的古井里了。”[1]74-75义仆小香穿戴五娘服饰,为主殉义,其目的是为了让官兵误认为五娘畏罪投井自杀,误认为小香的尸体就是五娘,从而能放过五娘,救五娘一命。后来林玳果然中计,五娘因此逃过一劫。
众所周知,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人的每一种社会行为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都受到其背后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内在制约。益春和小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小香还是个哑巴,但她们同样受到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52统治阶级通过各种途径把儒家文化的“世间法”灌输给老百姓,成为他们约定俗成的世俗行为规范和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化为他们血管中流淌的文化血液的一部分。这些“世间法”有三纲五常、忠孝观念、仁义礼智信、宗法统治、节烈观念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世俗规范。丫鬟哑巴小香也不例外,她对儒家“世间法”的接受主要来自于五娘的灌输。小说中写道:“五娘虽出身官宦门第,从小饱受教育,知道了不少古今忠臣义仆、义夫节妇的壮烈哀艳故事,所以每当小香缠着她请她讲故事时,她总讲这些给小香听,使小香被感动得泪水盈眶。”[1]71因此,小香后来的“殉主”壮烈行为自然也就不奇怪了,其中折射出深深的儒家文化思想烙印。具体而言,就是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奴仆对主人表现出的一种以“义”为主要内涵的行为,这种“义”不同于存在兄弟之间那种具有相对平等性质的“义”,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兄弟之“义”,而是存在于主奴之间、夹杂着变形的“孝”观念的“义”行为,十分类似《红楼梦》中鸳鸯的殉主行为,延伸开去,也有点类似于一些中国古代大臣的“殉国”行为。对于这些殉主和殉国行为,评价自然会有差异。但如果从现代立场来判断,至少它与个人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是以扼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代价的,所以,就有所谓“愚孝”“愚忠”之类的称谓。但作者许希哲却是站在正面的立场来评价小香的行为,在小说结尾,作者感叹道:“一个为主殉义、两个为爱殉情的少年男女,长埋地下,尸骨已腐,而其情义长存,令人凭吊感叹”。[1]82作者高度评价小香为主殉义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间 “情义”,显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和褒扬。
当然,作者不但浓墨渲染仆人小香的“殉义”行为,同时也强调了五娘作为一个主人对奴仆的 “仁爱”行为。小说中交代,五娘对于出身贫寒人家的哑巴小香,“特别疼爱,有一回,小香病了,五娘和益春都亲自煎药喂药”。[1]71
五娘不但对小香投以满腔仁爱,同时对名为仆人、实为情敌的益春也表现出少有的宽容、大度、善良和慈爱。陈三、五娘偕益春三人从潮州私奔回泉州后,虽然陈三、五娘两人尚未举行正式婚嫁仪式,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恩爱夫妻。陈三在五娘之前就已和益春有了鱼水之欢,并有纳她为妾的约定,但由于五娘日夜伴在身边,所以不免冷落了益春,益春因此日渐消瘦,而五娘对陈三、益春之间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私下猜想益春的消瘦是因为她也喜欢陈三。五娘遂主动与益春和陈三沟通,“苦口婆心”地劝说陈三纳益春为妾,玉成益春和陈三之间的好事,并要求“三个人一起交拜天地”。[1]60在新婚之夜,“五娘一定坚持要陈三睡到益春房里”。[1]68五娘所表现出的这种仁厚、无私、宽容、大度和雅量,真乃举世无双。所以,作者称之为“天下间至理至性的女人”。[1]60小说对于五娘这一特定心理和行为的详细描写文字是原“陈三五娘”诸版本中所没有的。
当然,五娘的这一行为也是对封建妻妾制度的认同,按照此制度,陈三可以拥有一妻一妾(多妾)。益春钟情陈三,而陈三亦慕益春姿色,想纳益春为小妾。妾在封建社会属于半个主人的角色,因此陈三纳益春为妾,是提高益春的地位,是令益春感激的有情行为,更符合封建社会的规范要求,五娘自然没有反对,最后形成了“二女共侍一夫”的圆满结局。
从五娘的行为来看,五娘对封建妻妾制度的归顺和尊从符合历史真实,但是,五娘在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心理却不一定符合艺术真实。按照常理,女人对爱情都有先天性的独占心理倾向,对于爱情的对手是嫉妒而排斥的,不愿意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爱人,这是女人的本性,无可厚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佐藤春夫改编自《荔镜记》的小说《星》中的五娘,后者是一个具有嫉妒性、想要独占陈三爱情的女子形象。她和益春比赛谁最美,“两人决定,花朝那天,大家各自到城里走一圈,看路上的人究竟讲谁美”,“胜了的人,可以随自己喜欢地择自己钟爱的人为自己的丈夫”,[3]12最后五娘胜出。可以看出,五娘在爱情心理上表现出独占和排他的心理。最后,当陈三“偏爱”益春时,五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嫉妒和怨恨心理:“千怪万怪,都怪自己不该遵守那开玩笑的约,而把益春荐为自己的丈夫为妾。……可恨的是有着轻薄的情的丈夫!不,丈夫仍旧是可爱的。可恨的是益春!不论怎样说总是益春!她毫不念及当日之恩,独占了丈夫的爱,却以为她多了不起似的,时时用怜悯般的眼光偷看自己,自己是知道很清楚呢。”[3]34-35从女性心理的角度来看,《星》中的五娘比《荔镜缘新传》中的五娘无疑更真实。《荔镜缘新传》为了把五娘塑造成一个体现儒家文化内涵、受儒家文化规范的代表人物,就不惜违背女性的心理真实,把五娘改扮成一个“高大全”的完美形象,一个“太伟大”[1]63的女性形象。五娘最后就成了某种“理念”的产物,成为儒家文化的“传声筒”和符码,而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具有独特个性的“这一个”五娘形象。
如果说丫鬟小香为主殉义等情节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归顺和尊崇的立场,那么陈三和五娘之间生死不渝、感天动地的殉情故事则体现了对儒家礼教的蔑视和叛逆。在本文序言中所提及的梨园戏《陈三五娘》的六个版本中,都有一个不变的核心情节,就是五娘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挑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大胆反对其父母给她订下的与富家子弟林大(林玳)的婚姻,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与自己倾心的陈三勇敢相爱,并机智逃离黄府的魔窟,通过“私奔”的方式,争取自己的个人幸福,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个性解放之歌。这些版本的《陈三五娘》主人公的命运都是喜剧性的,即陈三与五娘虽历经磨难,但最终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收获了幸福的爱情,取得了“大团圆”的结局。而许希哲的《荔镜缘新传》主人公命运结局却与上述迥然不同。作者对此进行了“重新创作”:林玳带官兵来陈三家搜捕五娘,陈三外出,五娘在家,丫鬟小香代替五娘跳井自杀,林玳误认为井中小香尸体就是五娘,遂将益春带走,留下兵队在陈宅把守,以追捕陈三。仆人陈忠进目睹小香投井,由于眼花,误认为就是五娘投井。陈三在邻居胡三炳的帮助下,来到家里,听仆人陈忠进说五娘已经投井自杀,哀伤之余,不忍独活,遂而投井殉情,岂料就在他投井的一霎那,五娘在仆人陈年元的陪同下回到后花园,却发现陈三正欲跳井,但已经来不及阻拦,陈三纵身跳下去了,五娘悲痛至极,随后也投井殉情。小说以主人公双双殉情而结束,作者感叹道:“两个为爱殉情的少年男女,长埋地下,尸骨已腐,而其情义长存,令人凭吊感叹。”[1]82《荔镜缘新传》悲剧性的结局把《陈三五娘》的“个性解放”的主题推向巅峰,接近了《牡丹亭》“情至”之精神。《牡丹亭》表现的是杜丽娘、柳梦梅跨越生死的人间“至情”,特别是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古今的生死至情,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笔者认为,《荔镜缘新传》中陈三五娘以死殉情、生死不渝的悲剧爱情和《牡丹亭》中的人间“至情”何其类似!这种穿越生死的人间“至情”正是对儒家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纲常名教的高度蔑视和无畏反叛,是对个人价值的自觉追问和大胆追求,是一曲“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庄严宣言!
总之,《荔镜缘新传》一方面认同妻妾制等儒家文化的典章制度,大力宣扬以“仁义”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世间法”,另一方面,也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等儒家文化“世间法”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崇儒与逆儒两种思想杂糅地存在于《荔镜缘新传》中,造成了小说复杂多元的思想倾向。
二、比较成熟的小说技巧
《荔镜缘新传》是运用小说的体裁对传统的戏曲文学作品进行改写,由于作者在此之前已经创作了多部小说,对小说艺术技巧的把握已经了然于心,所以在创作《荔镜缘新传》时,能比较自如地运用小说的艺术技巧,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1.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
《荔镜缘新传》运用了不少深入内心、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人物复杂丰富的人性内涵因此而得以逼真呈现。如写益春受五娘所托,替五娘向陈三传递题诗绢帕,不料被陈三拉进“小木屋”,瘫倒在陈三的怀里,这时的益春,一方面,“一些错综杂乱的情绪与心理,迫使着益春想要挣扎推拒”,另一方面,“三郎的身上好像有一股强大不可思议的力量吸住她,她顿感迷茫若失,竟乖如绵羊地任由三郎轻薄。”[1]30益春这种心理正是她受封建纲常名教束缚的“超我”与青春期欲望本能自然流露的“本我”之间的矛盾斗争,并且最终是“本我”战胜了“超我”。
五娘突然向陈三提出要陈三纳益春为妾,这正是陈三心中所愿,但由于是五娘提出,陈三不知五娘是试探还是出自真心,接下来有一段很丰富独特的心理活动:“这倒是出乎陈三的意料!心理突然有如十五双吊桶,七上八下的,感觉到一阵无法按捺的慌乱与迷惑,直到现在他还弄不懂五娘的意思,究竟是真还是假的?是出于真情发乎至诚呢?还是想藉此对自己有所试探?难道五娘已经知道了自己与益春在小木屋中的暧昧?想想又好像不可能,相信益春大概不至于会把那天晚上的事,不加隐讳地全部告诉五娘吧!陈三脑筋电转之后,觉得五娘这样说还是真诚的成分多。按照常理,多数的女人都是善妒的,尤其对于爱情,每个女人都有着先天性强烈的独占心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情愿把爱情分一点点给另外一个女人;而现在五娘却愿意慷慨的把自己获得的分一半给益春,这好像已经超出常理了。……(这)确确实实是纯真情感的自然流露,陈三放下了心中的不安和狐疑……这根本就是自己心里所希望的,如今这样轻易地获得了,不禁兴起一层茫然的感觉!是对自己的收获感到庆幸;也由于五娘的仁厚而对自己暧昧的行为感到惭愧,内疚。”[1]61-64此处陈三的心理变化过程千回百转,跌宕起伏:其中有对五娘行为初衷的猜测,有对五娘知晓自己与益春暧昧之事的担心,有从五娘的言行表现猜测五娘此举发自内心,也有从女人的心理推测五娘的行为不合常理而实为试探之举,有明白五娘真意之后的如释重负,有如愿以偿获得益春之后心中的窃喜和庆幸,有因为五娘的胸怀宽厚善良而引发的内心愧疚……种种心理如跳动的河水流淌在陈三的意识中,把陈三那种犹疑、担心、慌乱、矛盾、复杂而变化多端的心理状态逼真展现出来。
2.颇具匠心的叙述方式和结构设计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在《陈三五娘》的各个戏曲版本中,都是先从陈三写起。陈三的兄长陈必贤官任广南运使,陈三奉母之命,从泉州护送家嫂到其兄官邸,路过潮州城,彼时正值正月十五赏花灯,陈三在赏灯的时候无意邂逅黄五娘,由此拉开了一曲传奇爱情故事的序幕……如明嘉靖本《荔镜记》的剧目前面各出分别是:辞亲赴任、花园游赏、运使登途、邀朋赏灯、五娘赏灯、灯下答歌、士女同游、林郎托媒……。[5]2-3戏剧体裁的《陈三五娘》基本是按照顺叙的方式来交代剧情。《荔镜缘新传》一改这种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在小说的开始就运用了倒叙的手法。小说的开头就展现了一副“闺思图”,描写五娘在闺房里思念陈三:“五娘竟痴痴地倚在窗口,哀声叹气的,将近两个时辰了,却仍然没有要睡的意思。”[1]11-12此时的陈三已经乔装改扮成长工来到黄府做苦力,无奈黄府防范严密,等级森严,陈三和五娘虽近在咫尺,却犹如远隔天涯,始终不得相见。而这些情节在戏剧体裁的《陈三五娘》中却要到剧情的中间部分才能得到交代。倒叙手法的运用能将小说的矛盾冲突提前展现,诱发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探究的欲望,使读者能在最短时间里进入剧本内容的核心,达到文学欣赏的最佳状态,有利于准确把握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小说整体上以五娘、陈三和益春的故事及其视角来组织情节,弱化林玳这条情节线索,这样使情节和矛盾更加集中。
小说的结尾设计扣人心弦,出乎意料,有着欧亨利小说出奇制胜的效果。上文已经提到,丫鬟小香的“为主殉义”已经属于作者创造性的“无中生有”,给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表现手法上,小说屡屡采用类似于相声“抖包袱”的“误会法”,制造矛盾或巧合,推动情节发展。“误会法”在小说结尾共运用了三次,丫鬟小香穿戴五娘衣服投井自杀,引起林玳“误会”,从而暂令五娘逃过追捕。仆人陈忠进目睹小香投井,由于眼睛看不清,“误会”五娘真的投井,并将此消息告知陈三,引发陈三的“误会”,并殉情投井,陈三投井,又推进情节发展,矛盾激化,最后五娘投井,矛盾才最终得以缓解。
3.“深入浅出”“清新可喜”的文字风格
张俊璂在序言中说,“文字方面仍一贯其深入浅出之风格、清新可喜”。[1]3通读整篇小说,发现此评价大体准确。小说的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清新雅致,富有诗意。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常在紧张而绵密的情节冲突中,穿插三两情景交融、充满诗意的景物描写的文字,这些景物描写文字,或衬托人物心情,或暗示人物命运,或预示情节发展趋向,或奠定整体情感基调。如:“残夏将尽,溽暑全消,秋已悄悄来临了。深夜里,月黑,露冷,大地一片死寂”,[1]11此段文字描写的是五娘在漏尽更残的深夜对陈三的思念,两人近在咫尺、却如远隔天涯,景物描写衬托出此刻五娘忧郁、黯淡的心情。“时已经晚,黑暗笼罩着大地,远处虫声唧唧,入耳凄凉”,[1]27此句同样暗示的是五娘思念陈三而不得的苦闷心情。“外面,无星无月,一片漆黑”,[1]28写的是益春决定冒犯家规礼教,替五娘传送绢帕给陈三时的情景状态,景物描写也许象征益春心中对于此举前途未卜的担忧。“举目栏杆外,漫天繁星”,[1]37或许暗示益春回忆其和陈三之间初次鱼水之欢的幸福体验。“这是个平静的下午,天气晴和,秋风送爽。黄府里面显得异常宁静”,[1]40此段以静写动,此静乃火山爆发前的静,平静中实蕴含着不平静,因为随后黄府使女秋菊向黄诗吉报告“小姐不见了”,掀起轩然大波,直接导致后面矛盾的爆发并达到高潮。
4.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塑造
《荔镜缘新传》部分人物的形象塑造颇具个性化的特色,其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是陈三和益春的形象。在以往的包括戏曲、小说和电影等体裁在内的《陈三五娘》诸版本中,陈三的形象内涵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陈三是一个敢于大胆追求个人爱情自由、冲破封建礼教制度束缚的“反封建”人物形象,这是陈三形象内涵的核心。但是,不少版本的《陈三五娘》在塑造陈三形象时,仅仅集中于表现此点内涵,凸现陈三“反封建”光辉形象,甚至把陈三当成一个“完人”来塑造,造成陈三性格内涵的单一化,成为一个扁平人物形象。《荔镜缘新传》则力戒这个缺点,把陈三塑造成一个性格较为多元、有凡人缺点的“反封建”人物形象。陈三的“反封建”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变化,但是陈三性格的其它侧面有了充分地表现:陈三既有在“反封建”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同时也表现出些许自私、虚伪、富有心计、狡黠、不够坦诚的人性缺点。如益春为五娘传送题诗的绢帕,来到陈三居住的“小木屋”,第一次见面,陈三就将益春揽入怀中,强行占有,并在心中打起了自私的“小算盘”,“陈三暗自思量,益春与五娘,一个聪明伶俐,姿容秀丽,一个是端庄高贵,艳光照人,主婢二人,可谓各有千秋。自己与五娘两地相思,好事难谐,如果能够稍为运用手段,先把益春占有,答应将来收她为偏房,笼络住她的心,那么她一定会死心塌地,玉成自己和五娘的好事。”[1]29-30陈三不但先在五娘之前就占有了益春宝贵的处女之身,并且还算计着利用益春,再进一步得到五娘,可谓一箭双雕,占尽便宜。一个自私、富有心计的陈三形象跃然纸上。另外,在“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这一小节,提到陈三那段跌宕起伏的心理活动,从中显然可以看出陈三的虚伪、狡黠、富有心计、不够坦诚。当五娘向陈三提出要陈三纳益春为妾,这本是陈三心中所愿,但他不敢立刻答应,因为他不知五娘是试探还是出自真心,所以还在装糊涂,在心中盘算如何应答对付五娘。与五娘光明磊落的行为相比,陈三的虚伪和富有心计则原形毕露。但这些缺点并不妨碍陈三整体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总之,正是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陈三的性格内涵更加丰富,从而由一个扁平人物形象变为一个丰满人物形象。小说中益春的内涵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她为五娘和陈三牵线搭桥,全心全意,毫无怨言,堪比《西厢记》中的红娘;另一方面,她也有出于自己私心的考虑,渴望如愿以偿地成为陈三小妾,一则是自己喜欢陈三,二则也为自己后半生找到依靠和归宿。这样一个具有一点“私心”的红娘才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符合人性的人,因此,也是相对成功的人物形象。而小说中五娘,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反封建”人物形象,如果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未必是一个成功的角色,因为她的性格过于单一,且有些行为不太符合人性真实。这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有论述,五娘某种程度上成为儒家文化理念的“传声筒”,而并非一个有血有肉、性格多元、内涵丰富的真实人物形象。
[1]许希哲.荔镜缘新传(序言)[M].台北:台北照明出版社,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佐藤春夫.佐藤春夫集[M].高明,译.北平:现代书局,1933.
[4]汤显祖.牡丹亭题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第一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章永林)
I106.2
A
1008—7974(2014)06—0054—05
2014-05-19
古大勇,安徽无为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三五娘”故事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项目编号:11BZW107;“2013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NCET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