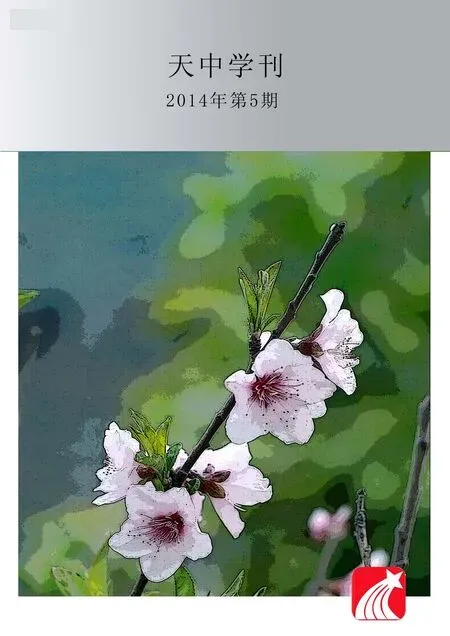试论《达洛维夫人》中二重身手法的运用
王锐
试论《达洛维夫人》中二重身手法的运用
王锐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运用二重身手法,将塞普蒂默斯塑造成克拉丽莎的另一个自我,在生与死的主题上达成平衡,引发读者有关生存方式及生存价值的思考。小说在中心刺激物联接、对海浪和树的冥想、同为相似机制的受害者以及对生死的感悟四方面,集中体现二重身手法的运用,进一步起到了塑造人物和烘托主题的效果。
维吉尼亚·伍尔夫;二重身;《达洛维夫人》
《达洛维夫人》是维吉尼亚·伍尔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描绘了克拉丽莎在夏季的一天之内所做的事,始于早上为聚会做准备,结于晚上聚会的散场,但呈现给读者的信息却相当丰富。克拉丽莎遇到的所有人,包括回忆里的人物都出现在了那天晚上的聚会上。小说有两条分别聚焦于塞普蒂默斯和克拉丽莎的叙事线索,他们的活动在过去和现实中来回转换。
二重身起源于德国民间传说,多用于神怪和恐怖小说,能反映个体内心深处压抑的情感。这种手法尤其为一些现代和后现代作家所青睐,如Slethaug所说:“作家们都非常青睐这种手法,看重一个自我对立两面分歧的解决,不管是男女之间还是特权阶层和被压迫阶层间。”[1]2伍尔夫也声称:“我要展开一项对疯狂和自杀的研究,一个神智正常和不正常的人眼中的世界,大概就这样。”[2]207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巧妙地设计了克拉丽莎和她的二重身塞普蒂默斯之间的联系。他们是互补的两个人物,前者向现实妥协,按社会规约行事,而后者拒绝向现实低头。他们分别代表生活中光明和黑暗的一面,但后者使前者的形象和性格更加饱满,使生与死的主题凸显。伍尔夫把这两个人物连接起来,丰富了情节,也深化了主题。
一、二重身人物: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
(一) 中心刺激物的连接
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的相遇看上去是在小说末尾,也就是当克拉丽莎听说了塞普蒂默斯的死讯而陷入沉思时,然而“克拉丽莎从来没有看到过伍尔夫称之为其‘二重身’的人物,但他却在她的一天中起到了核心作用”[3]。从小说一开始,他们就变得密不可分了。在一大早克拉丽莎去买花的路上,一辆豪华汽车发出爆炸声,“以它为中心串联物,作者自然地将叙述焦点从一个人物的意识屏幕切换到另一个人物的意识屏幕上”[4]。克拉丽莎好奇车里坐的是哪位大人物,并且猜测“很可能是王后”[5]13。与此同时,塞普蒂默斯则感觉“某种恐怖之物马上就要浮出表面,即将爆发出熊熊烈焰的景象”[5]14。因为他经历了战场的残酷,爆炸声激起了他痛苦的回忆。外部事件成为他们内心感情流动的催化剂,反映出不同的心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一心境的两个方面。
(二) 对海浪和树木的冥想
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都很容易在不同场景中陷入冥想,回到过去,体现最明显的是对海浪和树木的冥想。海浪的运动就像情感的波动,有时让人心潮澎湃。小说一开始,克拉丽莎打开窗户,感觉“那是清早的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宁静,当然比这里沉寂;像海浪的轻拍;像海浪的轻吻”[5]3,美好的天气使她想到和彼得·沃尔什年轻时度过的时光。海有潮起潮落,人的感情暗流也是忽涨忽落,例如克拉丽莎把人们召集到一块儿举办聚会时,她活力无穷就像奔腾的海浪,但在内心深处也有无尽的孤独感:“在她看着出租车的时候,总有一种自己是远远地独自在海上的感觉”[5]8。海浪有时也是危险的,克拉丽莎缝衣服时就体会到了这一点:“不要再害怕,那颗心说,把沉重的负担交付给大海,它为一切的忧伤叹息,然后复苏、开始、聚拢、跌散”[5]35。塞普蒂默斯也同样体会到了大海的力量:“但是他自己仍呆在高耸的岩石上,就像个淹死的水手躺在石头上。我把身子探到船外,掉进了海里,他想道。我沉入海底”[5]61。他看不到继续生存的意义,感觉自己已经被异化,被现实世界吞噬。海浪很好地体现了两者的人生状态,他们都渴望寻求生命的价值,却苦寻无果,倍感孤寂。
树木是自然、活力、希望的象征,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都喜欢树,敬爱自然。克拉丽莎曾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树木散发的勃勃生机与她自由无羁的性情吻合,她“坚信自己是家乡树木的一个部分”[5]8。塞普蒂默斯在去看医生的路上也产生了对树木的思考:“树叶通过千百万条纤维和他坐在座位上的身体相连,上下扇动着他的身体;当树枝伸展时,他也作出同样的表示”[5]20。他还把树木、爱和美联系起来:“首先,树木都活着;其次,没有犯罪;再有,爱,普遍的爱。”[5]60树叶树枝的交叉纵横正是人与人交际的象征,但医生在为他诊断病情时,完全基于和他妻子的谈话做出诊断,丝毫不理会他的感受与困惑,甚至否认战争对他心理造成的伤害。这是对人性、沟通和理解缺失的抨击,正如Karen所说:“士兵想表达他自身经历的残酷和强烈的情感,一个倾听者要想象并体会到他那种经历和情感,这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6]这条鸿沟的存在使塞普蒂默斯无法得到他人理解,因此往往陷入自己的超验经历和冥想中,在自然中寻找慰藉。自然是原始的,人类社会却被利益和冷漠污染,因此他们期许在自然中寻求安宁,却始终逃不出现实的束缚。
(三) 同为相似机制受害者的经历
在Littleton看来,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的“世界观已不能感知这个日益令人费解的世界,最终导致了精神不安”[3]。克拉丽莎是一个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塞普蒂默斯则经历过战争,因此他们对压抑的社会都感到绝望。克拉丽莎曾经和彼得相恋,但最终选择了身为国会议员的理查德做丈夫,她的身份也从克拉丽莎变成了达洛维夫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毕竟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在那个男权社会中是很难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不过是社会的附属品与受害者,她们需要仰赖男性才能得以生存。但克拉丽莎并没有从现在的婚姻中得到快乐,反而感觉活得无意义,她依然心系彼得,想象“如果当初我嫁给了他,这样的快乐就整天都属于我了!”[5]32她举办晚会不过是想借喧闹的人群掩盖自己内心的孤独和空虚,正如Karen所说:“虽然她为无序孤寂的现代社会,至少为上流社会,带去了美与和谐,她的集会活动只不过是掩盖了她所熟知的人性中的邪恶”[7]。
“塞普蒂默斯是首批自愿入伍的人之一。他去到法国,为了拯救一个几乎完全由莎士比亚的剧作和穿着绿色裙衣在一个广场上散步的伊莎贝尔·波尔构成的英国。”[5]76他带着守卫国家和心爱女人的信念参战,力图捍卫正义,担负起社会责任,而战争实际上却是权力游戏的产物,没有人性可言,这打破了他所有的设想。好朋友的去世加重了塞普蒂默斯的精神负担,他已对现实绝望,他的灵魂已经随着战争的结束消逝了。塞普蒂默斯甚至认为他们的婚姻完了,因为他的妻子和医生为伍,坚持把他送入精神病院,否认战争对他身心造成的伤害。很显然塞普蒂默斯受战争影响,已经对人性丧失了信心,就像Karen说的,“战争中,塞普蒂默斯看出了人性中邪恶的本质,战争结束回到英格兰后,他也见识了这种邪恶”[6]。当自我不能与外在世界达成一致,他选择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和世界交流,以自杀获得解脱,成全自我。他们都是相似机制的受害者,克拉丽莎受制于父权社会,塞普蒂默斯沦为利益和战争的受害者。前者的激情与浪漫情怀向世俗生活妥协,后者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宁可自杀不愿屈就,如Henke所说:“替罪羊塞普蒂默斯的死像一种仪式,他的牺牲既能帮助女主人公更好地应对自己的创伤,又不致使她陷入愤怒和抑郁。”[7]126
(四) 对生死的感悟
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各自都有对生死的感悟,这加深了二重身手法的叙事效果。大本钟的钟声和莎士比亚剧中的台词很好地反映了克拉丽莎的人生态度。在克拉丽莎去买花的路上,有对大本钟的详细描述:“深沉的钟声响了起来。先是预报,音调悦耳;然后是报时,势不可挡。一圈圈深沉的音波消失在空气之中。在穿过维多利亚街时她心里想,我们是多么愚蠢啊。”[5]4这时,克拉丽莎对大本钟的直接感受就是要好好利用时间,此时她充满着拥抱生活的激情。有时候克拉丽莎感觉很恐惧,“因为大本钟这时以其压倒一切的力量直截了当地、极端威严地敲了三下;她什么别的声音也没有听见”[5]105。回想年轻时候的美好时光,再对比现在自己的处境,她感到无助和脆弱,渴望找到自我身份和存在的价值。
时间在无形中也对塞普蒂默斯施加了压力,仅仅是“时间”这个词就使他敏感、暴躁:“‘时间’一词撕裂了荚壳;它将自己的珍宝倾泻在他的身上;确凿的、公正的、不朽的词语从他的唇边自动地滚出,像炮弹、像刨床上流泻的刨花,飞到时光颂中占有了一席之地。”[5]62战争的创伤挥之不去,他没能完成从战争时期到战后正常生活的平稳过渡,而是一直在困境中挣扎,他已不惧死亡,相反,死亡对他来说是摆脱压力的最好方法。小说末尾这两个人物被连接到一起:听到塞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克拉丽莎默默地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进行了检讨。
三、二重身手法的效果:刻画人物与烘托主题
一方面,伍尔夫把塞普蒂默斯设定为克拉丽莎的二重身,使女主人公形象更饱满。作为彼此的另一个自己,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分别代表了光明和黑暗的一面,而光明和黑暗是两种对立的形象,就像生和死。“克拉丽莎被前景化以后,伍尔夫把本来安排在她身上的死亡转移到塞普蒂默斯这个角色上”[2]xi。这一二重身的设计使作者能全面阐释她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即人死后就丧失了表达对死亡认识的能力,但活着的人可以自由展示对它的理解,因此克拉丽莎从塞普蒂默斯的死亡中受到启蒙并得以重生。另一方面,二重身手法使作者在烘托主题上达到一种平衡,John Hawley Roberts曾说:“我们读这部小说的乐趣在于认识到这种设计的正确性,即塞普蒂默斯与克拉丽莎是互补的,克拉丽莎对生活最初的热情恰恰是塞普蒂默斯所抵制的。”[8]63实际上,塞普蒂默斯也并非真正想自杀,因为“他要等到那最后一刻。他不想死。生活是美好的”[5]133,他只是选择了灵魂的自由。他的死对克拉丽莎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反观自己的人生,克拉丽莎感到无地自容,这位年轻人的勇气与生活态度是她所钦佩的,就像Guth对她的评价:“在这种时候,吸引她的不是生命的力量,而是拥抱死亡的决心和美。”[9]塞普蒂默斯跳出窗户拥抱自由,而克拉丽莎跳进了令她窒息的生活,也形同自杀。故事结尾,她又回到聚会上,镇定自若,但镇定不意味着生存战胜了死亡。Guth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道:“灵魂的私密允许她自由地转换自我形象,她可以同时过两种生活,又不会全然交付给任何一种。”[10]她骨子里有塞普蒂默斯的精神,但她还是继续生活,一如从前。
二重身手法在《达洛维夫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样的设定使读者阅读并体会小说主题变得更加容易。它丰富了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也达到了作者要表现理智与疯狂主题的目标,正如Sue Roe所说:“两个没有明显相似之处的人物实现了完美的融合。”[11]伍尔夫没有像传统观点主张的那样,把生与死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使这两方面有机结合,互为自我。对于塞普蒂默斯的自杀,克拉丽莎没有太过悲伤,因为她理解一个被异化了的自我无法容忍这个世界,但克拉丽莎没有因此变得不知所措,而是选择容忍,坚强地继续生存下去。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观,有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这也是伍尔夫想通过这个故事传达给读者的。
[1] Slethaug,Gordon E.The Play of the Double in 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
[2] Anne Olivier Bell.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M].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78.
[3] Littleton,Jacob.Mrs Dalloway: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Middle-Aged Woman[J].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995,41(1).
[4] 申富英.《达洛卫夫人》的叙事联接方式和时间序列[J].当代外国文学,2005(3).
[5] 维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M].王家湘,译.南京:译文出版社,2001.
[6] Karen,DeMeester.Trauma and recovery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J].Modern Fiction Studies,1998,44(3).
[7] Henke,Suzette A.New Feminist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 Ed. Jane Marcus[M].Lio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1.
[8] Roberts,John Hawley.Vision and Design in Virginia Woolf:Reading in Literary Criticism[M].London:Allenand Unwin,1970.
[9] Guth,Deborah.Rituals of Self-Deception:Clarissa Dalloway’s Final Moment of Vision[J].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990,36(1).
[10] Guth,Deborah.What a Lark! What a Plunge!:Fiction as Self-Evasion in Mrs Dalloway[J].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89,84(1).
[11] Sue Roe,Susan Sellar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责任编辑 杨宁〕
I106.4
A
1006−5261(2014)05−0061−03
2014-01-03
王锐(1990―),女,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