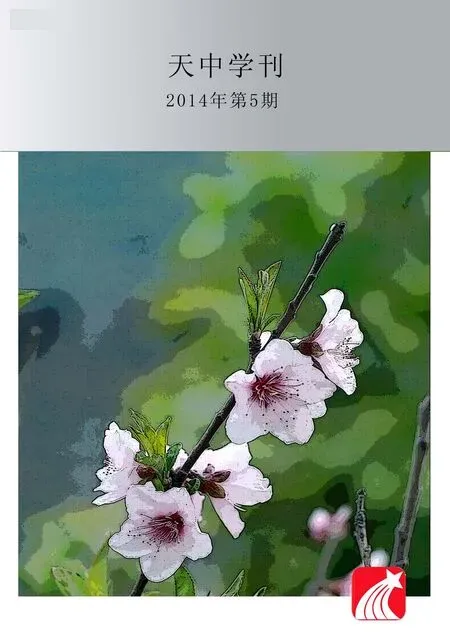社会现代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
张伟
社会现代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
张伟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的构建,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深层次上的不利因素。公共利益的建构,利益的满足和表达以及分歧的排解与控制,能减少甚至消除社会现代化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利影响,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选择
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推进其社会认同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关系到社会意识的整合、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现代化对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设计和选择的深层次因素。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路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一、社会现代化概述
现代化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社会维度,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展开,是现代化的一个维度,既与其他领域现代化有共同的表现,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于社会现代化涉及多个方面,国内外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斯宾塞基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认为社会现代化是社会“由一个结构单元同时承担多种功能到由若干个子单元分别承担单一功能的过程”[1]。帕森斯通过分析伦理、价值与社会规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认为社会现代化是“非感情性、个人取向、自致性、专一性和普遍性原则”逐渐主导社会的过程[1]。杜尔克姆着眼于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认为社会现代化是“由‘机械联系’的社会向‘有机联系’的社会转变的过程”[1]。李路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为,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念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过程”[2]。何传启认为,社会现代化有四层含义:是社会领域的一种革命性变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场国际竞赛,具有相对和绝对、国内与国外两种视角[3]。
从理论界的讨论可以看出,社会现代化在纵向上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并紧密联系;在横向上它影响着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组织管理、文化和人的现代化以及城市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深刻变革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社会领域的上述变化,势必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多伊奇指出,社会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4]。亨廷顿也认为,“从心理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5]25。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重构了社会成员新时期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设置了或利或弊的前提。以社会现代化为视角,探索现代化对社会成员价值信仰的影响,能够更加深刻、系统、全面地洞悉价值变迁的机理,为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建构新时期的价值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点。
社会现代化对价值层面的上述影响,只有通过家庭、学校、同辈团体和传媒等社会化渠道才得以产生,在纵向上我们可以将这些社会化渠道理解为一个由介质、动力构成的完整机制,此机制将社会的现代化延伸到价值的现代化。首先,风俗、习惯构成了社会现代化发挥作用的首要媒介,它们为社会成员的成长、生活提供了某种价值或者情感启示,塑造了其未成年时期的价值观念,并进一步影响其成年时期价值的革新与调适,它们通过对社会成员心理的奖惩形成了有效的价值诱导机制。其次,以家族、村落、同辈集团、工作场所等为具体内容的非政治性权威模式,构成了社会现代化影响价值调适的重要媒介,它塑造了社会成员的原始认同,规定着其后的价值变迁,“一个人所处的非政治权威模式,在他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上有重要影响,家庭的权威模式,是他第一次置身于权威之下。他最初关于政治体系的看法,似乎就是这些经历的概括。”[6]291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肢解了这些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建构了新的非政治性权威模式和新的价值及价值秩序。最后,利益构成了社会成员对某一价值给予特定偏好的最重要动力,“利益是个模糊的概念,它通常涉及政治生活中个人或集团的基本价值体系、基本目标、希望和追求。”[7]51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催生了价值多元化,既为现代性观念的生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消解了社会成员对某一价值的高度共识性。
二、社会现代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
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大众文化的发展,社会分歧的凸显,在深层次上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设计和选择。
社会现代化对政治参与的动员,能够增加政治功效感,增进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也为价值灌输提供了重要条件,参与意识“与政治行为密切相关,与对政治体系的肯定认同密切相关,还与接受民主的态度密切相关”[7]180。但制度化参与渠道的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中国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及其有效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强的参与渴望,这一方面催生了公众对公共生活的疏离,为社会主义政治系统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里昂·费斯廷格所定义的“认知失调”,该理论认为,“一旦一个人的信念与他自己的因外部限制和要求形成的行为不一致,他就可能试图改变自己的信念,使之符合其行为,以期缓解失调”[8]378。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如果缺乏制度安排和现实支撑,社会成员就会进行价值理想的调适,使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与其所理解的现实相一致,加之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就会弱化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对民主、法制、平等等社会价值的认同。
新葛兰西学派将大众文化界定为“特定时期的形式和活动”,认为它“以特定社会阶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体现在大众的传统和实践中”[9]47。社会现代化对大众文化的促进,有助于打破文化一元格局,让公众接受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调整价值系统和塑造新的行为方式,为价值的制度安排以及阿尔蒙德语义下的“公民性格”的形成创造条件,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也会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大众文化解构了旧的文化及其价值的权威和统一性,使个体得以相对自由地建构自身的价值秩序。这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往往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其次,大众文化滋长了消费主义,将大众性价值取向导向了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甚至个人主义。最后,大众文化的发展肢解了社会文化的同质性,产生了亚文化,“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被称为亚文化。”[10]78它不同程度地认同和依靠主导性价值观念,却又同时接受另一些与其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价值观念。
社会现代化对局部性社会的规范,对伦理道德普遍化的推动,冲淡了社会成员的地域性、阶层性和角色性等狭隘观念,使其开始形成或者强化共同体意识,这有益于社会共识的形成,但也催生了消解这一共识的社会分歧。社会现代化所引发或者激化的社会分歧,会减弱不同社会群体或者个体之间政治合作的意愿和能力。社会信任与合作意味着,在利益和价值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时候,一方与其对立方达成谅解,愿意与对方一起信守共同体层面上的规范,履行自身的义务,也乐意与对方分享共同的政治命运和政治价值。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是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必要的社会基础。
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本质是获得社会成员“多元完备性学说”的重叠性支持,获得这一支持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正义原则”的倡导和维护。公共利益是体现此种原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为共识性价值的有效条件。“即使可以证明‘公共利益’在任何客观的和实质的意义上肯定都是空洞的,但是,相信存在或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利益的信仰,将有助于在对立的观点中带来某些调和。它为寻找某些可能作为协议和妥协为基础的共享的原则创造了条件。”[11]378公共利益所激发的社会责任感、自我成就感,使不同社会系统的成员在信守某一价值信念不符合自身利益或者有损自身利益情况下,仍然在合理程度上保持着对该价值信念的忠诚,自觉约束危及共同体和谐的愿望和要求。这种公共意识培育了公众的共同体感,“一个共同体所凝聚的程度,就是共同体感。这种感觉显示了共同体成员支持现有政治劳动分工继续存在的程度”[11]214。共同体感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愿意在现有政治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分享共同体层面上被强化的价值规范。
相对于公共利益,利益的表达和满足,使得价值信仰与社会成员的动机结构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它在深层次上为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了内在动力。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通过不同渠道,聚合不同的利益诉求,以积极的政策输出或制度安排来满足公众需要,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利益需要得到满足外,他们的社会利益,比如声望、友谊、尊严等,也需要得到关注。党和政府还要通过制度安排,为不同群体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提供设施和机会,并以不同的方式向社会成员传递制度运转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其价值认同。“政治表达的目的不是存在于训练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的选民,对于过渡社会来说,政治表达更为基本的目的可能在于向大众灌输一种新的价值和新的观念。”[12]63
利益矛盾与文化差异所滋生的社会分歧,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公共利益的倡导与维护以及利益的表达和满足,虽然促进了这些分歧的弥合,但往往不能最终消除它们。此时,通过行政手段促进分歧的消减和价值取向的趋同,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只有靠压迫性的使用国家权力,人们对某一完备性宗教学说和道德学说的持续共享性才得以维持下去。如果我们把政治社会当作认同某一完备性学说而达到统一的共同体,那么压迫性的使用国家权力就是必须的。”[13]166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使矛盾非政治化,并控制分歧排解的过程,去除和减少分歧产生的不利因素,使分歧与矛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可控范围内,从而不阻碍价值共识的达成。这虽然不能使社会成员的分歧完全消除,但能减少他们之间的隔阂,为政治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展开,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具有全局性、深刻性,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的设计,也要具有整体性、系统性、长远性。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过程中,要积极利用有利影响,正视制约因素,以社会成员的价值和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循序渐进。同时,多样性也是宝贵的,社会要尊重不同群体和个人“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合理性、差异性。
[1]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内容刍议[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1).
[2] 李路路.“社会现代化”理论论纲[J].社会学研究,1983(3).
[3] 何传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思考[J].理论与现代化,2006(6).
[4] Karl W Deutsch.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1(3):494..
[5]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 [美]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7]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 [美]塞缪尔. P. 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周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9] [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G]//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0]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2] [美]鲁恂. W. 派尹.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3]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叶厚隽〕
D64
A
1006−5261(2014)05−0006−03
2014-02-24
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项目(Y1318017);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132400411221)
张伟(1986―),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