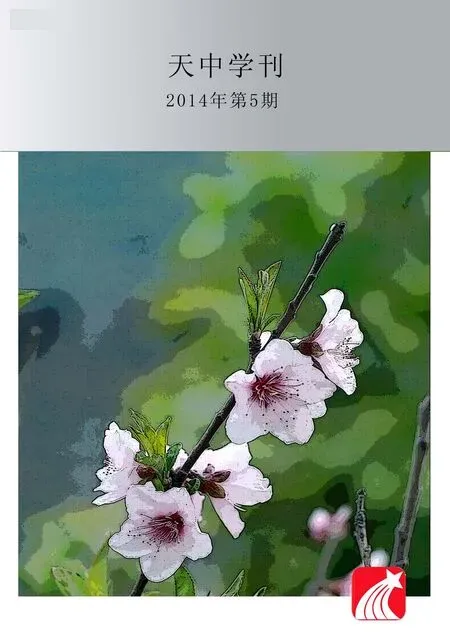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杨兰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杨兰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语境中,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它们都试图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然而,在对文化的属性、文化与社会以及文化工业的认知、评价方面,两派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转向;总体性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出现了三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和伯明翰学派。这三个流派都共同营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上的“文化转向”,都以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强调了“回到马克思”。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最为显著。法兰克福学派是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如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人,致力于对现代性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贯穿这些批判之中的是文化的焦虑,他们借此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文化持否定态度。相反,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如雷蒙德·威廉斯、伊格尔顿、霍尔、霍加特等人,继承了英国本土“甜美的文化”传统,肯定了文化的作用,揭示无产阶级在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中的巨大贡献。其中,雷蒙德·威廉斯把马克思的根本学说理解为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
一、怀旧的精英情怀与革命的大众文化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往往通过对各种现代主义高雅艺术的怀旧、依恋来审视大众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倾向意味着,他们轻视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及其阐释活动,在大众文化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文化悲观主义情绪。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精英情怀首先表现在对文化的片面理解上。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光谱”[1]29。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像利维斯民粹主义一样,将整个大众文化置于理想化的“真正的艺术”的对立面,认为只有高尚文化才具有批判、颠覆和解放的维度,而一切大众文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低劣的,具有欺骗消费者、大众的效应。这实际上表达了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和大众教育的批判态度:以尼采和利维斯为代表,他们既轻视大众及其文化,也对造成大众及大众文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和科技发展深恶痛绝。弗洛伊德依靠他的无意识理论来论证“大众”的“罪恶”以及少数人控制和管理大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32−33。正是以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为指导,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自身归约和单一化的文化批判路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30―50年代发展了文化产业的研究模型,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就再没有发展、更新自己的文化研究。
与法兰克福文化研究着眼于区分文化类型不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唯物主义的,它集中关注文化的物质起源、影响,以及文化交织于社会权力场的种种方式,它推翻了关于高雅文化和低俗大众文化之间的高低级别之分,把那些被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剔除在文化之外的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等重新确定为文化的类型和风格,使文化研究的社会学性质更加浓厚。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源于他们的“文化怀旧”和精英情结。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构成了对高雅文化和精致生活的涸泽之灾。大众文化潜在的庞大消费群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这是大众文化挤占高雅文化生存空间的基本原因,甚至构成对高雅文化的诱惑,导致高雅文化自甘堕落。像但丁这样没有迎合一般品味而修改自己作品,没有“受了诱使为《体育画报》写文章”或接受合同“为电影改写脚本”,是殊为难得的。大众文化将使生活失去个性,使人永无休止地追逐弗洛伊德的“替代性快乐”以及利维斯的“替代性生活”,它们取代了“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生活”。这无疑符合这些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怀旧者”的口吻,这些人用过去理想化的作品谴责现实。
相比之下,威廉斯更看重“真实的快乐”和“真实的生活”的多元维度。在威廉斯看来,总体性的生活样式不可分割,总体性的文化也不可分割,大规模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更新使大众文化成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现实的世界里,人们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分并不那么关心,有识之士甚至保持明确的反对态度,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流行艺术也反对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区别。当时的流行艺术反对把文化规定为特定类型的思想和艺术,而倾向于威廉斯的“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观点[3]185。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诸如法兰克福学派这样顽固区分文化的现象?按照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观点,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其中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衡量标准的错用,换用爱德华·希尔斯的说法:“现在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快乐不值得用美学、道德和理性的标准去考究,但与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前辈带来快乐的腐化堕落的东西相比,它们肯定毫不逊色。”[4]35而约翰·洛克维尔认为,艺术就是你认为是艺术的东西,“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如果他们想成为艺术家的话。”[5]120作为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威廉斯,不可能看不到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弊病,但基于一种多元文化视野和“斯文的中庸思想”[6]95以及对共同文化的向往,威廉斯想必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尽管文化选择和消费成了阶级属性和阶级差别的双重标志,但各个文化阶层只要互不干涉,就能生存下去。
大众文化理论是威廉斯文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与他的“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理论一脉相承,是其把文化理论与社会理论综合起来的结果。从理论来源上说,威廉斯的大众文化思想是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利维斯精英主义和高雅文化观念进行批判的结果。威廉斯继承了利维斯的“文化”武器,从个体经验和实践的角度探寻普通大众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启蒙和实现解放的可能性和途径,把大众文化纳入文化的序列,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较为客观合理的评价。威廉斯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大众文化的状态及其重要变化,在不断扩展的文化形态中探寻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大众文化表现出较为客观的理解。这与卢卜契、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对现实和一般大众表现出的不满和傲慢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二、大众视野与阶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倾向于疏离工人阶级政治,而威廉斯等人则继承和延续了英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致力于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论阐述被统治阶级和阶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目标,去解读束缚英国工人阶级的权力和知识话语。可以说,威廉斯这一代英国知识分子大都具有本土的、阶层的本位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总是假设大众文化充其量代表的不过是文化衰落和潜在的社会混乱,只不过是文化史的短暂现象,趋向大众文化的过程就是大众文化自我终结的过程。这与利维斯的“文化与文明”传统何其相近。贝内特指出,“文化与文明”传统不在深入分析大众文化作品和实践上下功夫,而是从高雅文化的高度向下俯视大众文化的商业荒原,目的是为了印证他们心目中认定了的某种时代的文化腐败、差别,从而找到调节和控制文化发展趋势的根据,他们跟大众文化及其阶级力量保持距离,也没有以他们的研究参与其中,他们一直把大众文化当作是文化的他者,是“其他人的文化”。马尔库塞把文化工业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称为“肯定性文化”,这种肯定性文化的特点是去阶级化:“肯定性……其决定性的特点是主张建立一个必须被无产阶级无条件地加以肯定的具有普遍强制性的、更好的、更有价值的永恒世界;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每日为生存而奋斗的现实世界、不需要对现状做任何变革,只需通过每个人‘自内而外’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世界。”[7]58在大众文化时代,社会的对抗、阶级的斗争都被文化工业清洗,“文化工业通过消灭更高层文化的对抗的、异己的和超验成分,从而碾平了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性”[7]61。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在文化工业控制范围边缘,是被边缘化的“被抛弃的人和局外人”[8]142,疏离的文化体验使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对抗力量。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与闲暇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关系:文化工业的结果是由工作的品质来保证的;工作过程确保文化工业的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工业的职能最终是要以工业化组织工作时间的方式去组织人们的闲暇时间,工作阻碍了人们各种感觉的正常发展,无以形成威廉斯所说的代表某种文化形态的情感结构,其中文化工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文化工业所承诺的对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辛苦工作的逃避……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乐趣促使人们听人摆布、与世无争,而这一点本来是它应该帮助人们去忘却的。”[9]377−378
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把资产阶级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区分开来,资产阶级文化是“基本的个人主义观点、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出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目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基本的集体主义观点、制度、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出于工人积极文化的目的”。威廉斯说:“工人阶级由于它的地位,从工业革命以来,就没有在狭义上创造出一种文化。工人阶级所创造并对识别他们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是在工会、合作运动或政党里产生的集体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文化从它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根本上是社会化的(从它创造了制度的意义上),而不是个性化的(从创造精神或虚构作品上看)。当从内容来看,就会发现它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性的成就。”[10]313−314威廉斯给大众文化找到了一个阶级的、日常的生成基础:文化是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阶级经历中创造的,文化是人们的“活生生的经历”。简言之,“文化是物质性的”,这是威廉斯打破利维斯“文化与文明”传统的地方,也是他在大众文化观点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不同之处。威廉斯乐观看待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而法兰克福学派担心大众文化是一种时代“毒药”。
总的来说,文化唯物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都有把文化理论与社会理论综合起来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有别于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文化唯物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文化自主性的理解。威廉斯认为,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源自文化的自我建构功能,文化是一种在整体社会结构中自在自为的实在,文化的流变遵守它自身的规律,情感结构的存在和变化是无意识的,只有借助文本才能发现它,找到文化流变的痕迹和趋势。而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的意识形态统治角度理解文化的自主性,认为文化的自主性其实是一个权力运作的操作过程,是外在力量赋予的,文化自身不过是传播意识、配合统治、愚人以器的工具而已,文化的背后,是理性的统治和权力的行使。在现代性条件下,文化研究重视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现代性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面临着解构的挑战。因此,只有切实把文化研究与社会理论相结合,才能正确理解文化自主性。
[1] [美]道格兰斯·凯尔那.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M].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善,郭发勇,周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Edward Shils.The Culture Taste, Culture and Common Interchange:vol 1[M].Cambridge:Chadwyck Healey Press,1978.
[5] Simon Phyllis.The Incoming from Artto General[M].London:Methuen Press,1987.
[6] Herbert Macuse.The Negative[M].Londun:AllenLane Press,1968.
[7] Herbert Macuse.One Dimensional Man[M].London:Sphere Press,1968.
[8] [德]西奥多·阿多诺,麦克斯·霍尔海默.启蒙辩证法[M].梁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9]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M].London:Chatto & Windus Ltd,1961.
[10]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叶厚隽〕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rankfurt School and Bermingham School’s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YANG Lan
(Dongguan Polytechnic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cultural turn”, Bermingham School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are two different cultural criticism paradigms. They both try to recover and establish the Marxist Totality. However,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fundamentally in the attribute to the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Birmingham school; the Cultural turn; totality
B089.1
A
1006−5261(2014)05−0023−03
2014-02-16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基金项目2013年课题(GD13HMK01)
杨兰(1982―),女,贵州凯里人,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