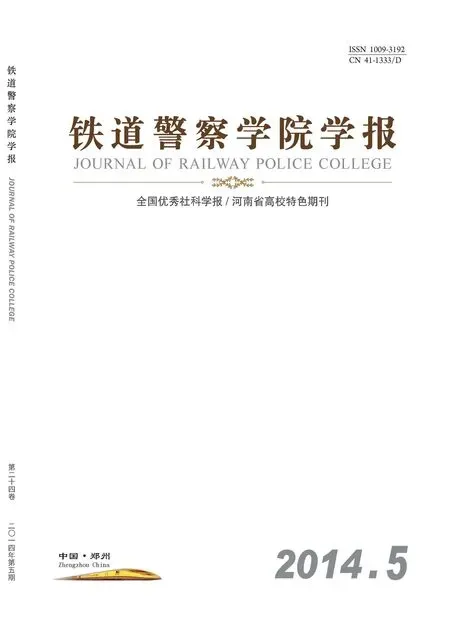内线侦查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应用
王彦学
(辽宁警察学院侦查系,辽宁大连 116036)
内线侦查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应用
王彦学
(辽宁警察学院侦查系,辽宁大连 116036)
集群事件属于主要由公安机关应对和处置的突发公共事件类型。此类事件一旦爆发乃至失控,往往会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隐匿身份侦查”制度,为公安机关处置集群事件提供了新策略。虽然一些集群事件存在合理诉求的成分和不宜简单评价的过激行为,但其间也可能存在着犯罪行为。由于集群事件的特殊性,一些犯罪的取证、定性和侦办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的种种障碍。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基于化被动为主动的考量,可派出秘密贴靠力量及早干涉介入,一方面可防止或遏制事件的膨胀、扩散或损害外溢,另一方面,也可为事后对一些人员涉嫌犯罪的法律评判提供线索和证据。
集群事件;隐匿身份侦查;内线侦查;即时型侦查;证据转化补强
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阐释了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并赋予公安机关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具有治安执法和刑事侦查的职责①《总体预案》规定: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总体预案》还规定:公安机关要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和设备的安全保护,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必要时,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控制事态,维护社会秩序。。集群事件是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形态之一,是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一些事件的起因具有正当诉求,不应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更不应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而应充分发挥法律在规范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始终坚持依法处置,有效引导,及时化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事件演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涉嫌杀人、伤害、放火、抢劫、抢夺、毁坏财物、寻衅斗殴等犯罪行为,由于集群事件的特殊性,一些犯罪的取证、定性和侦办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障碍②上海某基层法院法官归纳了群体性刑事案件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的难点:一是涉案人员众多,其中的一些单个刑事案件中往往仅有数名甚至一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二是证据不足和缺失,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工作难度大,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已获证据仍不能覆盖案件全貌和全过程;三是案情复杂,犯罪次数多,取证面广,不同的成员共同实施同一犯罪行为的情况较少,而不同成员实施多个犯罪行为,甚至同一犯罪成员实施不同犯罪行为的情况十分普遍。一些严重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未全部到案,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人直接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最终不得不以寻衅滋事罪草草结案,寻衅滋事罪成了某些案件法律适用的首选罪名和无奈之举。二是《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其内容宽泛,且使用了“随意”、“任意”、“严重混乱”等需要主观判断的表述,司法机关对本罪认定的标准难以统一,造成了法律适用的较大随意性。详见张锐《寻衅滋事罪在群体性暴力伤害案中的法律适用》,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加强对集群事件的临场取证工作是事件处置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往在事件处置中,公安机关多以公开力量进行封锁、围堵、抓捕和瓦解,辅以谈判分化和政策攻心等方法。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制度,提升了警察法律意义上的内外线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的法律位阶,为严密应急预案、规范处置方案、增强治理实效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我们在集群事件处置中应坚持“公开、秘密结合,处突、取证互补”的原则,加快推动信息和情报的快速反应、战略研判和应急决策的科学化、标准化和精确化,及时确认和妥善应对处置决策中的优先性问题,提高复杂情势下的应急决策能力。这对于深化以风险管理为方向的应急体制改革和以协同治理为走向的治安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探讨了内线侦查作为传统秘密侦查措施组成部分的新制度内涵,然后分析了内侦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实施要点,最后基于证据转化与补强的原则明确了内侦所获证据的诉讼应用。
一、内线侦查的制度演绎:内侦在新制度语域中的内涵简析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这次法律修改虽确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制度,但缺乏更为细化的相关配套制度设计,如隐匿身份侦查人员的选任、司法审查、执业保障、政治待遇、人身和家庭安全保障、专项资金、证据转化制度、职业卧底警探制度等。更为要紧的是,隐匿身份侦查与传统上的秘密侦查、卧底侦查之关系(混同、契合、包容等)也是一个尚待廓清的问题。立法者将隐匿身份侦查制度放在“技术侦查措施”之中,似有意指隐匿身份侦查是技术侦查措施的组成部分。从隐匿身份侦查的秘密性和技术侦查实施的秘密性上看,两者在行为样态和概念内涵上具有相合点,但也具有诸多不合点,对照实际情况则更揭示出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所谓秘密侦查,是指为了对付危害大且侦破难度高的某些特殊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侦查机关针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对象,暗中搜集其犯罪的证据和情报,以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种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的侦查措施[1]。秘密侦查措施一般包含如下三类:第一类是秘密拍照、秘密录像、监听、电子通信等技术性侦查活动;第二类是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策略性侦查活动;第三类是以秘密方式实施的一般侦查措施,例如隐瞒身份或目的的调查访问、隐蔽实施的辨认活动等[2]。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立法上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总括术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不能涵盖全部秘密侦查(隐匿身份侦查)行为,诸如卧底、线人、圈套等行为,古已有之,其中的技术含量并不明显地高于其中的谋略含量①艾明曾根据对侦查对象的合法权利造成的侵害程度,将秘密侦查手段按高低顺序进行了一定排序。第一类为:容易使国民降低对整个国家道德和伦理信用评价的秘密侦查手段,例如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卧底侦查等。第二类:容易侵犯当事人某些具体的合法权利,如隐私权、通信自由权、肖像权、住宅不受侵犯权,这类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电信截留、秘密拍照、秘密搜查等。第三类:属于机动灵活,且对当事人合法权利不具有明显侵害的秘密侦查手段,如跟踪盯梢、守候监视。艾明:《秘密侦查概念辨析》,载《贵州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5期。;二是技术一直处于发展中,其本身就是一个进化和流动的概念,支撑技术侦查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也不是静止的,同时也不容易被悉数囊括,每个探讨理论准确性的研究者都必须根据科学技术标准来判断其价值②我们对“技术侦查”中的技术应当从狭义上理解,技术侦查中的技术不同于一般的经验技术或者公知而普遍使用的技术,也不同于刑事技术部门采取的勘验、鉴定、测试技术。这些技术在一般侦查活动中是不允许使用的,也就是说,技术侦查的技术具有特殊专用性和国家垄断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高科技手段。。在此解释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之间的全部关系当然不易,但就传统侦查理论在新制度语域中的内涵提出粗略看法则是必要的。基于更大的制度变迁视域,技术侦查措施、隐匿身份侦查制度等新法律概念的提出,对于我国现行的侦查制度体系,特别是秘密侦查制度的体系整合和内涵拓展而言,无疑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引领性。
传统侦查理论将技术侦查、内外线侦查等视为特殊侦查手段,以区别于讯问、搜查、辨认、现场勘查、身体检查等一般侦查手段。《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5条第1款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指由设区的市一级以上的公安机关负责技术侦查的部门实施的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技术侦查的种类进行解释时,认为它“主要包括监听、技术追踪(如GPS定位)、音频视频监控、互联网监控等手段”[3]。从我国的立法技术层面来看,“隐匿身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被裹挟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侦查”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的项下,如果简单地进行逻辑推演,将“隐匿身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视为技术侦查不无道理。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并非在这种严格的逻辑下进行的,有些内容是在归纳困难或者条文较少,不宜专门列项规定下采取的“搭车式”规定,纯属权宜之计[4]。从实践层面来看,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7条和第262条之规定,技术侦查的实施主体具有独立性,由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行动技术部门)具体实施,而非隐匿身份侦查的“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指定的其他人员”。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互联网监控、记录监控等主要由网安部门负责,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具有情报收集的功能,属于监管部门的行政措施。鉴于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应从“大技术”的角度审视我国的相关制度,正视法律规定背后的意蕴,从而推进包括内线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制度的便宜适用。
在内线侦查中,贴靠、卧底、逆用和复线等均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内线侦查概念的确立源于一种二分式的架构:外线侦查与内线侦查。传统理论认为,外线侦查是指侦查人员以掌握侦查对象的外部活动情况和获取犯罪证据为目的,对侦查对象进行观察、监视、控制的一种侦查手段,主要是采用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秘密拍照和录像等以户外活动为主的方式,广泛应用于重大复杂案件嫌疑人的外部活动的秘密监控中。传统理论还认为,内线侦查是指在案件侦查中,对特别重大案件或有组织犯罪集团等案件采取内线打入的直线侦查模式[5]。从隐匿身份侦查制度的视角来看,外线侦查和内线侦查都需要身份的暂时性变更和隐藏,同时需要且不局限于外表、服饰等外在装束的改变、数据的支撑、资源的协同。由此可见,内外线侦查是隐匿身份侦查实施的不同形式,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秘密侦查行为的一种诠释性理论。总体而言,外线侦查往往要侧重于借助现代视听、监控等技术手段进行秘密侦查;内线侦查则侧重于借助特殊的侦查力量、装备投放来开展秘密侦查。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般多存在具体战术上的思考,使用外线侦查并不一定要使用内线侦查,而使用内线侦查则往往要考虑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互相协同,以清晰犯罪动向,弄清犯罪意图,且保护内线侦查人员。根据上述传统侦查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内线侦查是侦查机关针对侦查对象的目标需求、活动情势和犯罪动向,通过与其保持或建立起某种外部的亲密、形似的关系,并参与犯罪者所组织实施的有限活动,从而获取犯罪者情报和犯罪证据的一种即时型侦查措施。从行为的状态和效果来看,内线侦查往往是一种短期性、暂时性、应急性的短线秘侦行动。内线侦查的秘密性是分层次的,其稳态把控和良性运行,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单纯隐藏身份和侦查装备的单兵侦查行为;二是通过欺骗战术、制造假象来掩盖真实身份,迷惑侦查对象;三是在一定的场所、街面实施化装侦查,定点监控,单兵侦查与合成侦查协力接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全时空、广领域、大环境的信息空间格局之下,内线侦查措施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通信电磁空间等复杂环境中。
二、内线侦查的应用转圜:内侦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组织实施
一般理解,内线侦查作为传统刑侦工作的重要手段,主要应用于对刑事案件的“前置型侦查”(或曰“主动型侦查”positive/proactive investigation)或“回应型侦查”(reactive/responsive investigation)活动之中,而将内线侦查应用于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刑事案件侦查之中却是一个在目前侦查实践与理论上都有待商榷的问题,这一探讨将有助于本文意旨的归位和证立①我国理论界较早就有关于“回应型侦查”模式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的分类论断。区分两种侦查模式的标准之一是行为目标:回应型侦查以被动受案为行为特征,即以特定犯罪案件为目标,具有明确的破案目的;而主动型侦查则包含概括性的侦查破案的目的,其目标就实践而言较为复杂,主要是获取违法犯罪情报、打击某类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犯罪活动、阵地查控危险人员和物品、整治治安乱点和复杂地区等。。集群事件一般都有一个集聚、膨胀、扩散乃至危害外溢的分节点、分阶段、分时空的动态过程。将上述定位词分而释之可以发现:集聚是指人们在某一地点、处所范围内开始聚合;膨胀则是指集聚的人越来越多,突发事件征兆越加清晰;扩散是指聚集的人群开始以一定规模运动,并可能在移动中不断吸纳新的人群加入;危害外溢指的是上述行动中可能伴随着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滋事、扰序、毁物等,甚至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活动。如果把“犯罪发生时”作为我们观察犯罪既遂前后的轴线之中点,可以不周延、建设性地提出“即时型侦查”(synchronous investigation)的概念。如果单纯依据从“犯罪发生时”与“侦查开始时”之间相隔的“相对时间”这一单一要素进行一个纯粹的线性量值分析,则可发现即时型侦查的“相对时间”数值最小,甚至可能为零,因而在其之前的为“前置型侦查”,在其之后的为“回应型侦查”①按照物理学的原理,速度的快慢首先取决于动能的大小;按照相对论,两点之间的距离、时钟的快慢都与观测者的速度相关。侦查破案简单理解是猫鼠之间的博弈对抗和信息对撞,其动量大小和速度快慢,直接取决于侦查组织的动能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则是包含侦查要素在内的警务执行力的动能强弱。见王彦学:《论合成侦查》,载《公安研究》2014年7期。。回应型侦查的目标主要是指既遂的历史性刑事案件,而前置型侦查的目标通常是不特定的可能案件、可能犯罪者、可能侵害对象、可能活动时段、可能活动(如销赃或藏匿)场所等。这种可能性是一种预估性,如果以可预见的行为样态为评价基点,则这种可能性预判评估显示出前置型侦查应包含同步性的即时型侦查的含义,即“即时型侦查”应当是一种范围有所减小、目标更为清晰、手段有所限缩的“前置型侦查”模式②陈瑞华在探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影响时指出:从侦查的角度来说,最大的机遇是给检察机关历史性地赋予了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权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在取证方面,侦查过程与犯罪过程保持同步。在犯罪侦查学中,传统的侦查手段都是事后侦查,是滞后的。犯罪发生一段时间再去寻找证据,恢复犯罪现场,恢复原来的事实原貌。所以,原来的取证手段有一种极大的局限性。相反,技术侦查措施是新兴的一种侦查手段,它的最大特征是犯罪在进行,侦查在同步进行,犯罪完成时,证据基本搜集齐全,侦查也即结束。见陈瑞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主要制度创新及对检察机关工作的影响》,载《刑事司法指南》(2012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公安机关针对即将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案(事)件采取一定的即时型侦查措施既符合警察法、治安法的基本规定,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意义。《110接处警工作规则》规定,指挥中心对危及人身、财产、公共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紧急案(事)件,应当在派警处置的同时,立即向分管负责人报告,并向业务主管部门通报,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12条规定:“公安民警在现场处置过程中,应当依法及时收集、固定有关证据;有条件的,应当对现场处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③《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11条规定:“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和对正在发生的民警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处警民警接到110报警服务台处警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9条规定:“公安民警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根据现场警情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涉及人数、当事人身份及警情敏感性等综合因素,快速判断,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上述规定并未明确规定临场取证和录音录像是秘密还是公开进行,临场取证的方式如何操作,考虑到出警赶赴现场的时间长短、在场警力与对方力量的对比、各种集群突发事件的特殊性等情况也不宜做出“一刀切”的规定,而这就为内外线侦查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和操作程式。
当然实际情况远复杂于此。公安机关的早期预测和预警机制固然使一些集群事件在萌芽阶段就被有效化解,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近年来的一些实践则显示,早期预测预警机制有时也百密一疏,一些事件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公安部原任宣传局长武和平指出,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事实上导致民怨的燃点过低,“一个火星就可能燎原”。一些集群事件的参与人在法不责众、正当诉求等思维下可能出现各种无理性行为。群体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员集聚多基于一定个体目的的达成和不满情绪(不一而足,甚至可能千人百面)的宣泄。戴维森的“DBO理论”分析了社会行动结构与社会心理因素的直接关系。创立“集团动力学”的日本学者杉万俊夫指出:“集团是指具有某种不可继续分割的性质(整体性的性质)的一群人与他们环境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种整体性的性质称为集团性。我们可以把这种集团性比喻为‘蚊帐’。集团就是被包裹在具有集体性的‘蚊帐’之中。”法国历史哲学家勒庞深入分析了群体的冲动、多变、急躁与易受暗示、怂恿、轻信,以及群体意见的简单化及其道德感显著降低的事实④勒庞指出:“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群体挫折重组理论认为,遭遇挫折的人们集聚为群体并试图冲突滋事必须“动员必要的精英、人员、时间、金钱、物资、空间(场所)、第三方力量、传媒等各种资源,对组织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关键作用”[6]。上述引论虽然略显宽远、散博,但无疑都说明了集群案件从爆发、失序到危害外溢具有复杂的原因。为取得集群事件处置(含侦查)的良好效果,应结合事件起因、性质、规模、演化等因素,严密预警系统,精心筹谋施策,追求实现集群事件的严防、严查和严惩的统一。
(一)随附启动:内线侦查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启动原则
集群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需要一段时间,一旦发现问题征兆和集群现象,公安机关在投放公开警力的同时,还要伴随投放贴靠力量。从我国目前而言,集群事件的起因突出表现在经济纠纷、执法不公、民族问题、宗教矛盾等方面。实践中,城管商贩冲突、交通事件、土地房产纠纷、灾害事件、医疗卫生事件、环境事件、群体性上访、恐怖组织蛊惑煽动、国家矛盾(如中日岛屿争端)等都可能成为集群事件的爆发原因。集聚的人员一般为稳定小群体带领下的非稳定大群体,常常是非正式群体①非稳定群体是指,聚集人群的人员组成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多数属于只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联系的集合体;稳定性群体则是指聚集人群的一些成员的关系相对稳定和持久的集合体,包含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其中的非正式群体主要表现为同乡会、同学会、帮会、有组织犯罪团伙等等。非稳定群体由于难以建构起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其成员依特定的角色(如观众、旅客、围观者、行人等)而聚合在一起,整体行为常常是个人行为的松散混合,且角色需要和心理均比较简单,它难以把社会规范真正有效地转化为内部规范约束机制,一旦失控,这类群体行为的运行后果不堪设想。大量集群事件的发生,往往导源于这类群体行为的失序和失控。。集群事件的发生一般需要一个场所聚集、心理共振、交叉感染、情绪激愤、行为失控的发展过程,而对隐藏于其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苗头监控和线索发现,指挥中心、交警、巡警、便衣侦查、图侦、网侦、派出所等部门因为职责和任务设定都可能是第一发现者。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一旦发现问题征兆和集聚现象应迅速报告上级和主管部门,并迅速派出公开警力拦阻和紧急处置。同时,应完善预案体系,从信息和情报收集的视角,在制服警员公开执法的同时,在集群人员中部署一定的秘密力量,结合情报信息员的配合,持续贴靠观察取证。近年来,各地都在探索“警力下沉”的基层工作创新,如“网格化巡逻”、“治安警亭”、“交巡警一体化”等,提高了见警率和出警速度,阵地控制和要害保卫的效果也不断提升,但这种都市化警力部署对于一些发生在城郊接合部、乡镇等警力薄弱的街面、处所则显得鞭长莫及,力有未逮。因此,我们应推进勤务机制改革,在广泛撒网,积极投放能够覆盖到社会各行业、各角度、各层次的秘密探查力量的基础上,提高对集群事件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早期发现和同步取证,特别是获取深层次证据的能力,为事后责任分解、案件评鉴、集中收网奠定基础。
(二)择情受案:在集群事件处置中提高内线侦查的策略含量
集群事件中的犯罪活动,是群体性事件的伴生现象。犯罪嫌疑人(群)较为明确,一般就隐藏在集群闹事的人群中,故群体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到案机制比较特殊,即事中和事后就可强制到案(即可采取留置盘查、行政拘留或拘传、刑事拘留)。有些案件中存在幕后的犯罪嫌疑人,则侦查思路须按照传统上“由案到人”的侦查机制开展工作。集群事件中犯罪案件的受案机制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种情况中:一是事后即可受案。一些集群事件中发生打、砸、抢、烧行为,这些行为主要涉及故意伤害(杀人)、故意损坏财物、放火、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冲击国家机关等罪行,基于后果严重程度之预判,即可认定涉嫌上述罪行。二是行政受案转化为刑事受案。有些事件参与人员在事件中的行为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模糊,主要原因在于案件定性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如混乱中加害行为者不易判断、财物损失程度鉴别、伤情鉴定(是轻微伤,还是轻伤)、行为表现综合评价等。三是情报信息传受。在一些集群事件中,社会面与网络虚拟社会遥相呼应,且虚假谣言满天飞,并为集群事件的扩大推波助澜。因此,从网上和网下两个斗争层面上看,对这些实施煽动、造谣、污蔑等行为者的刑事受案需要信息系统后台的综合研判决定。鉴于集群事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到案和受案机制的上述特征,可以考虑秘密力量携带专业设备贴靠开展工作。实践中,贴靠警探可置身于人流中心附近,这样容易取得一些人犯罪的核心证据。从安全角度考虑,对主使者和骨干分子的过激行为是否采取制止行动需要权衡之后决定。一般而言,在关系特定人员生命或国家重大财产利益安危的关键时刻,无论秘密警力还是公开警力都应及时加以干涉和处置,防止事态损害扩大。
(三)主体禀赋:内线警探在集群事件处置中要有较高的融入度
由于集群事件起因各异,对于处置中投放的警力、装备、设备等资源要素的数量、类型、位置、构成、战术队形等均应充分考虑。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对贴靠警探的人数、工作方式、装备设施、团队协作等都要深入研究。内线侦查的本质在于“骗术”,“骗术”的高明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贴靠警探要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对事件中多发、易发的刑事案件侦查具有相当的实务经验;长相要群众化、大众化,不能靓丽帅气;扮相要自然,在人群中无显著特征,能隐匿于人群中;衣着不宜奇装异服、特立独行,避免引人注目和怀疑;要具有较好的抗压性、身体和心理适应性;年龄要与集群事件的主流人群年龄相近,要与预侦查犯罪的背景环境相当;行为举止要协调,要与涉事集群人员融为一体,可考虑携带一些标识虚假身份的道具,必要时可以一定的虚假身份公开介入事件之中,如化装成携带清扫工具的清洁工和摆摊的小贩;与公开力量联络渠道畅通,秘密取证设备要隐藏稳妥,防止暴露;一般不宜单兵作战,要组队而行,不能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只暗中观察事件发展,选准事件的问题焦点,拍摄、录制事件活动情况,秘密投放的警力、装备、设备等要素要根据处置需要决定。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林东茂指出,秘密侦查不仅有程序法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也容易出现实体法的问题,对秘密侦查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十分必要,防止警探的行为产生陷入刑法上“陷入教唆”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问题[7]。虽然集群事件处置中的内线侦查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组织等特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卧底侦查存在着明显差异,如存在时间长短、虚假角色公示等问题,但考虑到其程序性、敏感性和重要性,应参照技术侦查的审批机制,建立内线侦查的内部审批制度和检察机关备案审查制度,即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对集群事件中的犯罪采取内线贴靠,并由后台人员及时报同级检察机关负责人备案,使其具备“形式理性”,从而推动内线侦查的法治化塑形,最终化为秩序建构的正统化资源。
三、内线侦查的证明效度:内侦在集群事件处置中的证据适用
在集群事件处置中依靠内线侦查所获得的技术监控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过去曾经掀起关于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权衡争议。熊秋红指出:“技术侦查使警察可以获得有关犯罪的关键信息而没有被发现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该技术使警察可以‘知道全部、看见全部、控制全部’。”[8]《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死刑案件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核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在集群事件处置中通过内线侦查获得的各种材料可以直接当作证据使用,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内线侦查获得的材料的证据力(证据资格),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并不突出,关键是内线侦查证据在整个案件证据体系中的效度问题,其证明力问题才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在集群事件处置中,对采用内线侦查措施所获的证据材料应采取如下三条思路予以适用。
(一)对内线侦查所获证据予以补正解释
《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一技术侦查适用的审批门槛相对较高,而且要求是立案后才可审批适用,显然与集群事件处置和内线侦查工作不相适应。但《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此,考虑到集群事件处置的特殊需要,我们不应自缚手脚,过多关注内线侦查所获得的视频、音频资料、定位信息等各种材料的适法资格,而应关注这些材料的证明效果,关注集群事件中的犯罪证据多样化问题,树立应用多种证据指控犯罪的举证意识和执法思维。实践中,内线侦查获得的证据往往是集群事件现场的第一手材料,含有案件的重要信息和深层次证据,如从集群现场中收集的参与打、砸、抢、烧的主使者和骨干分子为谁,参与程度如何,事件中每起或每种案件的参与人为谁,具体某人的涉案情形如何,可以此引导事后对参与人不同责任的追究方式和侦查方向。对证据中记录的说话内容,现场出现的书证、物证,现场人员的结伙紧密情况、肢体活动情况、持有器物情况,被害人和事主情况,被损害财物对象等等,可以根据证据的信息量,或直接提交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也可以分别转化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后续物证、书证搜查,犯罪嫌疑人之间资讯的电子数据调查,对特定物证的鉴定意见等活动之中,当然亦可转化为实际指控犯罪的线索和证据。对内线侦查所获证据的补正解释应根据事件的突发性、危害性、紧迫性等实际情况,结合拍摄、记录资料所反映的具体内容予以合情、合理、合法解释,证据形态应完整、客观、真实地反映内线侦查所获得的证据事实,防止遗漏重要信息和线索,切勿捕风捉影、牵强附会。
(二)内线侦查所获证据与视频监控资料相结合
集群事件一般发生在街面、广场等相对空旷的区域。近年来,各地视频监控的清晰度、覆盖面和布局合理性显著加强,通过公共视频监控系统拍摄的画面来发现犯罪线索、开展视频侦查成为公安机关的重要手段。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哈尔滨会议”之后,视频图像侦查部门的体制改革进程大大加快,为广泛应用视频侦查手段的提供了组织保障。内线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一般具有临近现场、平面拍录、动态记录、取景窄小等突出特点;而公共视频监控摄像头一般集中于人流、物流、车流的主要通道和活动区,在区域边界的通行区域以及重要工作区、物质交割区、存放区等的外围周界,具有不同的部署要求,一般具有画面长时,景深、范围广等突出特点,同时也可能存在光轴远的画面不清等问题。我们可以将内线侦查所获的证据材料与视频监控资料组合使用,后者是对前者的证据补强,应采取出示动态画面、影像处理或者截屏标注等多种方式制作集群犯罪人员涉嫌的罪行佐证材料,与其他证据保持高度的统一和证明方向的稳定一致,而这对证据材料的制作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同时,公共视频资料有助于发现事件解散后的参与人逃匿路线、活动轨迹以及与现场作案工具、现场被盗抢赃物有关的调查等线索和证据,有助于打破“就现场论现场”的框架。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可借助视频图像所关涉的地理空间数据、通信数据、交通票卡数据、资质登记数据、商业贸易数据、金融数据、互联网数据和警务数据等信息展开数据侦查和体系取证,全方位地收集嫌疑人的各种事证,完善证据链条[9]。
(三)内线侦查人员以多种方式参与举证
内线侦查所获得的证据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死刑案件若干规定》第16条第2款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了对特定犯罪中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有关诉讼参与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保护性措施。其中第2项规定,诉讼参与人因在诉讼中作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不公开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鉴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对集群事件处置中内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出台保护措施,保障其本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亦可结合法律规定来创新内线侦查人员的作证规则。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对于因作证行为可能导致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内线侦查人员,可以经县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负责人批准,对其身份采取保密措施。对于内线侦查人员,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制作笔录或者文书时,应以代号代替其真实姓名,不得记录其住址、单位、身份证号及其他足以识别其身份的信息。此外,还可以书面答询,即内线侦查人员就其在现场上的所见所闻予以书面形式举证,对记载其真实姓名和身份信息的笔录或者文书,以及代号与真实姓名对照表单独立卷,交办案单位档案部门封存。法庭审理时不得公开内线侦查人员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信息。用于公开质证的内线侦查人员的声音、影像,应当采取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影像和声音或者使用音频、视频传送装置等技术处理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内线侦查措施在集群事件处置中对犯罪的控诉效果。
[1]唐磊,赵爱华.试论我国的秘密侦查制度[J].政法学刊,2003,(2).
[2]杨郁娟.侦查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40.
[3]孙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205.
[4]郭华.技术侦查的诉讼化控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87~88.
[5]艾明.秘密侦查概念辨析[J].贵州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3,(5).
[6]胡联合.冲突的社会功能与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制度化治理[J].探索,2011,(4).
[7]林东茂.卧底警探的法律问题[J].刑事法杂志,1994,(4).
[8]熊秋红.秘密侦查之法制化[J].中外法学,2007,(2).
[9]郝宏奎.论视频监控系统在侦查中的应用[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5).
责任编辑:贾永生
D918
A
1009-3192(2014)05-0020-07
2014-07-29
王彦学,男,辽宁本溪人,博士,辽宁警察学院侦查系教师。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卧底取证策略——以新《刑事诉讼法》‘秘密侦查’条款为研究起点”(项目编号:L12DFX03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