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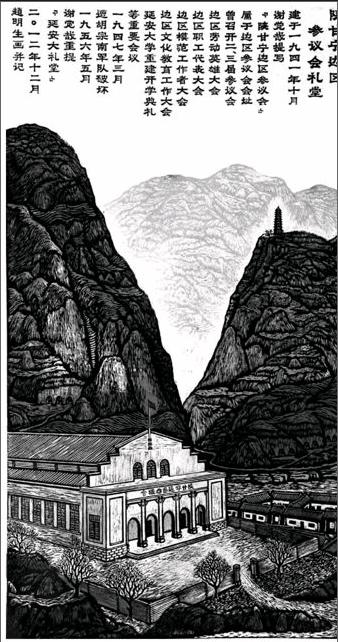
惠潮,男,1981年出生于陕西安塞,200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南庄的困惑》《土地与召唤》等。
很多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我随年轻貌美的小满姨上山采蘑菇,一阵小雨过后,一道彩虹挂在湛蓝的天幕。
那一年我七岁。我小满姨十五岁,胳膊上挎只大篮子,里面盛满了鲜嫩鲜嫩的黑蘑菇,两条大辫子在她浑圆的臀部活蹦乱跳。
“彩虹!……”
“彩虹!……”
我们站在高处驻足观看,夏日雨后爽人的微风吹到我们被淋得湿漉漉的身体上。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的彩虹。
采回来的鲜蘑菇抛进沸腾的热水锅,咕嘟咕嘟的声音美妙而亲切,小满姨将一把雪样晶莹的盐巴撒进去,雾气笼罩的灶台前溢出蘑菇的阵阵香气,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令人尴尬的咕噜声。
七岁的我和十五岁的小满姨相依为命已经两年多了,说我们相依为命一点儿也不过分,这个自称来自一个叫做舍科的大姑娘成了我的母亲和姐姐,照料我生活的全部。而且,从她嘴里唱出的歌总是让我感到那么别样那么温暖,听她唱歌真的是我那时候最为幸福的事情,“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呀么杨柳梢……”
婉转悠扬的歌声陪伴着我孤寂又神伤的童年时光,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和小满姨学唱歌,她肚子里的歌子委实太多了,如同山上采不完的鲜蘑菇,不仅如此,她自身又有很多让人难以捉摸的神奇手段,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家。还记得那是一个秋季的黄昏,我们村里一个好喝酒的后生吃了鲜嫩的野蘑菇又喝了半瓶烧酒中毒了,恰好村里的赤脚医生外出行医,大家个个束手无策。是小满姨应声而出,我们家长期在村里的屈辱地位因小满姨的这一次表现改变过来了。她要后生的父亲赶快去刨柳树根,把柳树根熬成汤给后生灌下,后生起死回生了,自此以后她就被这家人奉为娘娘。
我年轻貌美的小满姨是个特别内敛的姑娘,她在村里赢得声誉后并没有把这当成自己立足的资本。我相信在她看来,她就是一个十足的外来户,能被收留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她没有表现出一点矫情来,反倒一如既往地照顾我,照顾我抱病在床的父亲,义务给村里人唱歌听,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她帮助的每一个人。
生意赔得血本无归的父亲奄奄一息,他一架大老爷们的身体垮掉了,先前170斤的身体一下子跌到110斤,等于从他身上砍掉一袋子面粉的重量,他脸颊深陷,颧骨高耸,用我们村里老辈人的话说,就是我父亲的鬼脸子都下来了,我长大后才明白,那样的人是快要去见阎王了。父亲的起死回生眼看无望,但是,奇迹往往让人意想不到,他竟然渐渐恢复了人样。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父亲的身体状况大有改观,我能从隔壁听见他牙齿发出铮铮的金属般的声响,原本我以为他在吃东西,而当我爬在窗户上透过破破烂烂的麻纸看进去后才知道,他犹在梦周公,发出那样的声音或许是梦中胃里饿得慌的缘故吧。
父亲重新站起来以后脸上有了光泽,我记得那是一个艳阳天,他起来后,蹲在一棵大柳树下大口大口地吸着自制的卷烟,那副饥渴的模样让人胆战心惊,起初他自己一边卷一边吸,后来赶不上了,动员周围的人帮他卷,大家七手八脚地帮他卷了一大堆,后来他将吸到烧疼手指的烟头狠狠仍在地上,缓缓地说出一句话:“这烟香啊,都吃到我肚子里了。”
父亲像小草一样破土而出,迎来了自己生命的一个艳阳天,我父亲好起来后对村里人说:“小满这孩子伶俐,是她用洋柿子酱一调羹一调羹地把我从阎王那里抢回来的。”按理说我父亲和小满姨是平辈,小满姨十五岁,父亲三十三岁,村里有人开玩笑对父亲说:“你把这姑娘娶了吧,年龄是差点,但合适着了,你艳福不浅,就当找了个小老婆。”别人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在附近,我的心脏突然在一瞬间停止了跳动,我要看父亲的反应,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的态度,父亲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激动,也没有那样不屑,更没有表示否定,良久他对调侃他的人说:“日你娘的,我能把救活我的恩人压在身底下吗?”
为父亲这句话,我心里难过了好长时间,多年以后这句话总使我相信父亲对小满姨那份根植于内心的好感和情愫。虽然是平辈,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没有把她的恩人压在自己的身底下,反倒把小满姨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有加,而小满姨和我,渐成亦母亦姐的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我家的平静还是被打破了。
我壮汉形象的父亲身上有使不完的蛮力,这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领,他不爱种庄稼,那是出力不讨好的慢活。此前他生意赔光后大病不起,起来后他忘记了生意的事情,他怕了,但他就是不想和村里多数人一样靠种庄稼养家糊口,他还是要出去折腾的,他远离无法预测的生意后,自然就靠满身的蛮力了。有一天他丢下我和小满姨独自一人去西山林场当了一名伐木工人。林场的主人叫张百万,这不是他的别号,而是他的本名。年过半百的张百万戴一副石头镜子,据说很贵,他对壮汉形象的父亲很中意,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我们平静的日子过了两年之后又一次被打破了,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林场的柏木私下被大量贩卖,这罪落到了我父亲身上,但是连我,一个九岁的小屁孩都知道,我父亲是张百万的替罪羊,村里人都这么说。已经多日不见父亲的我和小满姨各自在自己的被窝里哭了大半夜,天不亮小满姨就起床了,小满姨摇醒了我,她眼睛红肿,嗓音沙哑地对我说:“来生,起来,和我找张百万算账去。”
说实话我害怕张百万,我只见过他一面,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皮笑肉不笑的活阎王,他能把壮汉形象的父亲算计到监狱里,自然不会把我和小满姨这样的小屁孩放在眼里,他会用怎样的手段算计我们呢?但我还是起来了,毕竟他是我的仇家,我是我父亲唯一的骨血,不为他报仇的话,我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九岁的我痛下决心,抱着视死如归的豪情随十七岁的小满姨踏上了复仇之路。
我第一次由看到了张百万,他身边几个父亲一样壮汉形象的伐木工人令我望而生畏,我来之前的豪情瞬间荡然无存。我退缩了,但是我年轻貌美的小满姨撇开我的手,大步流星地走向了戴着石头镜的张百万,我远远地站下了,我不知所措,在和张百万的对峙过程中,我最后听见小满姨说出这样一句委屈的话:“坐在监狱里吃牢饭的人应该是你!”endprint
小满姨平日里甜美婉转的声音充满无限委屈,她试图上前抓住张百万的领口,但是被那几个壮汉形象的伐木工人推开了,在伐木工人粗壮的身体面前,我年轻美貌的小满姨就像一只刚刚出窝的小鸡弱不禁风,被推倒在地的小满姨挣扎着起来,越挫越勇,最后力气全无的小满姨无声地坐在地上,但是始终都没有向我发出呼救信号,这让我感到面红耳赤,她无助地耸动着肩膀,并没有哭出声来,最终慢慢平静下来。
我们同张百万的正面交锋败下阵来,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助,我竟然对恃强凌弱的仇人妥协了,没有及时援助我年轻貌美的小满姨。我的内疚小满姨早就看出来了,她安慰我说:“来生,硬上不行,我们根本就不是那老东西的对手。”
小满姨沉默了,她像一只温顺的绵羊一人承担起了照顾我的职责,我开始以为她放弃了和张百万算账的决心,然而我还是错了,有一天她独自一人偷偷去了西山林场,回来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再次开门出来后,村里人再也不会对她怀有丝毫敬意了,连曾经被她救过的那个后生的家人也对她表现出了鄙夷之色。九岁的我略略明白了,独自去找张百万算账的小满姨被张百万那狗日的糟蹋了,我甚至瞬间想起了父亲此前的那句话,怎么能把自己的救命恩人压在自己身底呢?但是禽兽不如的张百万将小满姨压在了他的身底,因为小满姨不是他的什么恩人,他压得有些理直气壮,五十多岁的恶棍张百万毁灭了我的理想,我七岁时候父亲的那句话记忆犹新,我因此对父亲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因为他没有把小满姨压在自己的身底,而小满姨两年后被另外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理直气壮地压在了身底下。从西山林场传来这样的消息,使我一时间几乎要窒息,事件被村里人加工之后,更让我的心脏好久没有跳动的感觉。
村里人说张百万老牛吃嫩草,给小满姨肚子里下了种,小满姨的肚子会大起来,我不相信,压在身底下肚子就会大起来吗?但是一个无法欺骗自己的事实是,小满姨让恶棍张百万糟蹋了,欺负了,凌辱了……
我复仇的种子在渐渐消沉的小满姨面前生根发芽,气势汹汹地生长起来,有时候我甚至用恶毒的心去想小满姨,当张百万把你压在身底下欺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反抗?你说你力气没他大,那你为什么不咬他,为什么不喊叫,为什么趁他不注意时候偷偷用伐木的利斧把他劈成两半,为什么……
我年轻美貌的小满姨远比我有心计,她的肚子没见很快大起来,小满姨不再去林场找张百万算账,倒是张百万怡然自得地来到我们家登堂入室。我记得那天夜里小满姨殷勤地给张百万擀面条,臊子汤油花花的,张百万接过小满姨端上的满满一大洋瓷碗面条,先是尝了一口汤,然后一下将一筷子面条吸进自己的喉咙。
我再一次恶毒地仇恨起了小满姨,相反我已经无法再仇恨张百万,欺负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压在身底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得而知,也不愿再多想。委屈让我眼泪憋在眼眶里,但是我不想让它流出来,认贼作父,把欺负你的人竟然当客人招待。我是半夜被小满姨从村头的打谷场后的草料房背回来的,我饿得瑟瑟发抖,委屈的眼泪没有流出一滴,小满姨将我背回家放在炕上,我就开始发烧,不想吃饭。这时候我听见隔壁张百万轻唤小满姨的声音,他竟然还没走,听他的意思是既然找见我了,就赶紧过来睡,这话的意思无疑是要把小满姨压在身底下,我又一次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我对小满姨的仇恨顷刻间爆发出来,我使劲将自己的双脚蹬在小满姨隆起的胸脯上,我不知道我的力气到底有多大,只见小满姨神经质地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脯,发出长久压抑的闷哼。
恶棍张百万和我的仇恨渐渐消失,我也不太想起监狱里的替罪羊父亲,而是一天天仇恨起年轻貌美的小满姨,一个一夜之间变得让我认不清楚真面目的坏女人。是的,她不再是我亦母亦姐的小满姨,而是我最大的仇人,我复仇的矛头从张百万变换成了小满姨。村里的后生总会对我说一句,你小满姨的身子好活了张百万那头老叫驴。
我的仇恨很快又变成了无尽的委屈,夜里我常常一个人哭醒。小满姨无法走近我的生活,她开始害怕我,总是在我含着眼泪委屈地吃完饭后收拾碗筷,然后独自一人到隔壁去睡觉,而我的失眠症,从九岁开始一直伴随到现在。
我们关系和解是源于我父亲在劳改场的遭遇,太多的柏木流失,非法做成棺材以比木材更高的价格卖给有钱人死后享用,替罪羊父亲被判了刑,送到了我们村妇孺皆知的虎抱崖劳改场。我父亲像我一样满怀委屈却没有人愿意听他啰嗦,不管怎么说都是你亲手把碗口粗的柏木伐倒的,我壮汉形象的父亲百口莫辩,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精神又一次垮掉了,连卷烟也不让吸。我后来才知道,他被送进劳改场的时候,因为自身的壮汉形象,激怒了劳改场的红头老大,这个红头老大其实很瘦弱,他用自己的思想统治了大多数的壮汉,父亲被他惩罚的方式就是不让吃饭。我父亲饿着肚子干了三天活,胃疼得要死,但是他强撑着,据说每天早上他还要给红头老大倒尿盆,倒之前他倔强的脑袋还要被按在尿盆前照镜子,饿昏了头的父亲精神彻底崩溃了,他对红头老大说了句类似士可杀不可辱的名言。他的这句话引来整个劳改场基建连狱友们的哄堂大笑,红头老大更是捂住肚子喊疼,我壮汉形象的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将膝盖跪在红头老大的脖子上差点活活打死他,我父亲忘记了这是劳改场,他的不忍和任性彻底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我父亲是被红头老大用工地上偷偷带回来的水泥钉从左面的太阳穴钉进去的,被红头老大一起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性命的还有两个,他亲手一次性将三个宿敌送到了地狱。消息传来以后,我和小满姨不约而同地一路狂奔,我们漫无目的地奔出村子,奔向城里方向的川道,最后我们累得蹲下来干呕不止。
我们无功而返,只能是这样,小满姨变得更沉默了,此前她对我的委屈和仇恨很愧疚,很害怕。但是现在她对我不理不睬,我不明白她的态度为什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是说实话,我也恨不起她来了,我们的仇恨矛头再次一致直指恶棍张百万,是他将父亲变为他的替罪羊才使父亲身陷囹圄最终蒙冤而死。
原本村里人认为随着我父亲的死亡,所有的事情也会就此罢休。儿子要为老子报仇,起码得长大成人,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他们觉得这事不新鲜了,要把这事给忘记,因为还有更好的故事等待着他们。但是我没有忘,我感觉我的左太阳穴到右太阳穴绷紧了一根弦,发出嗡嗡的响声,也因为我父亲的死,包括张百万在内都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大梁倒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张百万又来我家了,小满姨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抓起菜刀奔向他,我相信以她的身体,足能对付骨瘦如柴的张百万,但是小满姨还是接纳了他,平心静气地接纳了。就在我住的房子的隔壁,我看见笑嘻嘻的张百万在小满姨浑圆的臀部捏了一把说:“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能熬得住?”endprint
我的心脏又一次停止了跳动,我看见小满姨一侧身躲开张百万的手,慌乱地朝门窗外看来,恨恨地说:“你死了这条心!”门外的我委屈地躲开了,但是我没有想流泪,我觉得小满姨是故意假惺惺装模作样给我看的。我走了,我要走得远远的,这不是我的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发烧到半夜,我命大,是被我们村外出行医的赤脚医生提回来的,他给我屁股上打了柴胡,我才退烧了。他对我说:“王来生,你大死了,他想让你好好活下去,你这么小就这样赌气任性,你将来能有什么出息?你记住我的话,要想不被人欺负,首先要自己强大。”
我是没出息,我也不想有什么出息,我甚至连学校也不想去了,我被医生提回来以后小满姨不见了。我们村里的人说小满姨没脸和张百万在我家干那见不得人的事情,毕竟这不是她的家,她没脸,也没理,他和张百万去深山老林逍遥快活去了。
我脑子里短时间觉得小满姨死了,即使她活着,我也永远不会再见她了,我再也不会想起她唱的歌了,那么好听的歌,“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呀么杨柳梢……”然而我想忘记也不能,越是想忘记歌声越是清晰可听,我对小满姨的仇恨、诅咒都平息下去了,我和她压根就没有任何关系,我何必自作多情呢?她这样不堪的人,终究是活该被欺负被恶棍压在身底下的女人。
就在我信誓旦旦与要小满姨恩断义绝的时候,从林场传来石破天惊的消息,我年轻貌美的小满姨为我父亲报仇了。传闻是这样的,她在张百万快活得忘乎所以的时候,用剪刀剪掉了他那该死的玩意儿。
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我被赤脚医生短时间收留在家,我想问赤脚医生一个问题,就是剪掉那玩意儿以后张百万会不会死,假如张百万死了我年轻貌美的小满姨能否逃脱干系?虽然世人皆知我父亲是他的替罪羊,但是杀人要偿命,我很小的时候老师就说过这样的话。老师还说,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杀人总要偿命,非偿命不可?我认为我们村最有文化的人就是赤脚医生,在很多人看来他远比我们的老师还要有文化,我就是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复仇杀人到底有没有罪。
就在我困惑不解的时候,一个令我更为吃惊的消息稍后传来,我年轻貌美的小满姨用剪刀捅进自己的小肚子,捅进她渐渐有型的小肚子。
赤脚医生对我说,小满姨是想自杀,她剪掉张百万的玩意儿后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主观上讲,她先是想把肚子里的小生命结果掉。听着他的话我惶惑不已,难道,难道小满姨连我也不要了吗,她亦母亦姐地照顾了我几年,真的忍心连我也丢下一个人去死吗?
赤脚医生和村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同情小满姨的遭遇,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调侃嘲弄的话。在我九岁的年龄状态下,很多事情是我后来渐渐想明白的,那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不治而亡,小满姨活下来了,但是她肚子里三月大的小生命夭折了。这是她的愿望,其实她将剪刀捅向自己小肚子的最初目的就是要结果这个小生命。
但是当我确切地知道小满姨想要果断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泣不成声,我的眼泪鼻涕一连串流在胸前,流在赤脚医生家长着青草的地板上。我在流泪的过程中渐渐释怀了,这时候我最想小满姨,我知道她不会死,更不会抛下我不管。
我揩掉眼泪,从赤脚医生家飞奔出来,一口气跑上了我们村通往林场的走马梁。雨过天晴,一道彩虹瞬间出现,光芒四射,它横跨眼前的峡谷,像一座桥,灼人眼目的色彩由远逼近,速度很均匀,我几乎能计算出它到达我面前的时间,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了,直抵内心深处的召唤蠢蠢欲动。
我看见了彩虹对我的召唤姿态,精神顿时轻松下来,无比的轻松和豁然,我又听到了那婉转悠扬的歌喉,“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那春风摆动,杨呀么杨柳梢……”
我大汗淋漓,泪水涟涟地奔跑在走马梁宽阔的脊背上,彩虹没有消失,反倒越来越清晰,我睁大眼睛,深恐它会因为我的懈怠稍纵即逝,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小满姨带我采蘑菇的情景,两条大辫子拍打在她浑圆的臀部,以及我们一起驻足观看雨后天上的彩虹,这美妙时刻将会伴随我今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魂牵梦萦。
是的,魂牵梦萦。
彩虹!
责任编辑:张天煜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