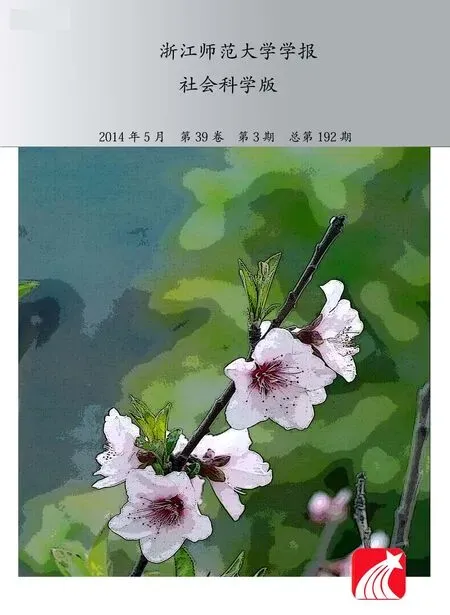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
宋高初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调解被誉为 “东方司法之花”,在化解民事纠纷、缓和当事人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简称附带民诉)是一种依附于刑事诉讼程序、解决民事赔偿纠纷的特殊民事诉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可适用调解方式处理附带民诉纠纷。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即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能否就附带民诉纠纷进行调解问题,未作出统一规定。
一、我国针对附带民诉调解前置问题的现行立法、执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后简称为《刑事诉讼解释》)第147条规定,刑事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后简称刑事被害方)自刑事立案后便可提起附带民诉,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在现实生活中,有部分犯罪嫌疑人愿意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积极赔偿以解刑事被害方的“燃眉之急”并获从宽处理,但基于与刑事被害方的对立状态及不信任心理,通常希望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主持调解活动以规避被刑事被害方“敲诈”风险。部分刑事被害方也希望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能居间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以便能尽快得到刑事加害方赔偿款救急。因此,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具有现实社会需求。
那么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是否会就刑事纠纷当事人提出的附带民诉纠纷进行调解呢?刑事法治要求任何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均须依法进行。我国司法实践中规范侦查活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27号)(后简称《刑事诉讼规定》)第281条仅规定侦查机关对被害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应记录在案并在起诉意见书末页注明;规范审查起诉工作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高检发释字[2012]2号)(后简称《刑事诉讼规则》)第393条第3款仅要求审查起诉机构在制作起诉书时应在起诉书中注明附带民事诉讼情况。《刑事诉讼规定》、《刑事诉讼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后简称《六部门联合规定》)均无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针对附带民诉纠纷进行调解的权利义务性规定。《刑事诉讼解释》第148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可对刑事被害方提出的附带民诉纠纷进行调解。 但《刑事诉讼解释》的制定机关为最高人民法院,仅可规范人民法院的刑事诉讼活动,无法规范、调整刑事侦查、审查起诉活动。附带民诉调解前置问题的立法不统一,直接导致刑事纠纷当事人提出的附带民诉调解前置意愿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难以实现。当前我国附带民诉调解工作主要、甚至完全由人民法院开展,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在办案实践中并不开展附带民诉调解活动,通常要求刑事纠纷双方自行达成赔偿协议。对难以达成赔偿协议的附带民诉纠纷,通常随卷移送。[1]原因主要有:1.《刑事诉讼规则》、《刑事诉讼规定》关于附带民诉调解问题的立法缺失使具备较强刑事法治观念的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因担忧调解违法而不敢主持调解活动。2.在现实生活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基于司法信任危机,根据我国关于积极作赔可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要求调解人保证或者承诺较确定的从轻幅度,并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以避免赔偿后从宽处罚优待落空。因此欲使调解成功,通常需要调解人或明或暗作出不同程度的许诺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然而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构对犯罪嫌疑人的积极赔偿行为仅有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无法保证积极作赔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得到从宽处罚优待。为避免引发司法信任危机,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不愿开展调解工作。3.组织调解工作需要调解人付出大量时间、精力来说服纠纷双方当事人。基于刑事案件侦破压力大、审查起诉工作案多人少现状,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也难以有效开展附带民诉调解工作。近些年有个别地方如上海市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已陆续开展轻伤害(包括轻伤害案件中的附带民诉纠纷)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受理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情节轻微。从多年试行情况看,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附带民诉纠纷案件数量较少,效果并不明显。[2]另外,近些年也有个别地方公安司法机关试行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工作,如山东青岛市两级法院试行公检法司“四位一体”的附带民事诉讼联动机制,把附带民诉调解作为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办案必须内容。此举效果显著,能有效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兑现难困境。[3]
二、附带民诉调解前置的理论可行性分析
针对附带民诉调解前置的理论可行性问题,众多学者依据民事调解理论持否定态度。主要理由:调解的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刑事纠纷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通常仍处于事实不清状态。事实尚未查清的案件不具备“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调解前提。同时因犯罪嫌疑人法律地位特殊且人身自由受限,无法直接参与调解过程,附带民诉调解前置极可能背离自愿原则。[4]笔者认为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并不悖于我国民事调解理论。理由如下:
(一)致某种损害后果发生的民事侵权行为,而非被刑事指控的犯罪行为,是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即使被刑事指控的某种行为最后经刑事审判认定不构成犯罪,只要民事侵权行为存在,行为人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附带民诉审前调解认定的事实仅限民事侵权事实,而非犯罪事实。只要附带民诉审前调解时某种民事侵权行为客观存在,刑事裁判对这种民事侵权行为是否属于犯罪、犯何罪的认定并不影响附带民诉调解前置的合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如某种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被追诉,在刑事部分“是非”仍属“不清”状态下民事部分“是非”通常已达“分清”程度。因此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在开展调解工作时,附带民诉纠纷已具备“分清是非”的调解基础。即使刑事审判认定的被指控行为属阻却违法行为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原加害人也可在刑事结案后根据《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诉讼。另外,达成调解协议通常要求各方互谅互让,这说明开展调解活动时并不要求调解方查清各方的民事责任大小,只要查明民事侵权行为情况即可。刑事案件侦破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条件,便说明某起刑事案件在案件侦破后便达附带民诉调解所要求的“(民事侵权)事实清楚”状态。
(二)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并不强制犯罪嫌疑人的调解意愿。当事人的调解意愿是否受强制主要取决于不愿调解的当事人是否会遭受打击报复。因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无定罪量刑权,对不愿参与附带民诉调解或不愿达成附带民诉调解协议的犯罪嫌疑人无法构成刑罚报复威胁,故犯罪嫌疑人虽被限制或被剥夺人身自由,但并不担忧因拒绝配合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开展附带民诉调解工作而遭受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的打击报复。我国现行较完备的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保护机制也可有效抑制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损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行为。附带民诉调解是否成功对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而言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通常也不愿冒被投诉风险对不配合附带民诉调解工作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报复。因此,犯罪嫌疑人在附带民诉审前调解时的负罪待审状态并不构成对其自由调解意愿的强制。另外,尽管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受限,但其自由表达附带民诉调解真实意愿的途径并未被堵塞。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讯问或律师会见时可清楚、自由地表达附带民诉调解意愿。故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并不损害附带民诉调解应遵循的自愿原则。
(三)附带民诉是附随于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仅处理民事损害赔偿纠纷。基于契约自由法律精神,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处分原则贯彻于整个民事权益纠纷处理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刑事诉讼任何阶段就民事损害赔偿问题相互协商达成一致。因此除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外,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已达成的附带民诉调解协议应受法律保护。协商并能达成一致的前提通常是协商各方相互信任并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基于对立情绪,刑事纠纷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常须第三方即调解人进行说服活动。尽管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积极赔偿行为只有从宽处理的建议权而无决定权,但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相对于其他调解人而言,其公职身分能赋予其较好的公信力。同时由于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可真实了解犯罪嫌疑人的附带民诉调解意愿,对正在处理的附带民诉纠纷事实有较清晰的认识,如能开展附带民诉调解,一方面可有效避免刑事被害方夸大损失、提出过高赔偿要求;另一方面也可利用其所拥有的从宽处理建议权督促犯罪嫌疑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基于其特殊身分,比较适合担任附带民诉调解工作。
(四)由于现行附带民诉调解立法对人民法院调解时段未进行明确限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6月7日颁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6号)第10条所规定的“积极探索和加强庭前调解工作”文件精神,当前大部分基层法院均采取庭前调解方式处理附带民诉纠纷。[5]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开展的附带民诉调解与法院于庭审前开展的附带民诉调解,只是调解主体不同而已,基本事实状态及被追诉者人身自由状态相同。人民法院庭前开展附带民诉工作的合法性充分体现出附带民诉调解前置的合理性。
另外,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如能就民事赔偿部分调解成功,对希望能尽快弥补所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及愿意赎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是双赢;同时也可减轻人民法院处理附带民诉纠纷的压力、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为充分发挥附带民诉调解前置的积极功效,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通过司法解释方式明确制定我国侦查机构、审查起诉机构在刑事案件侦破后便可就附带民诉部分进行调解的授权性规范。
三、附带民诉调解前置的现实可行性设计
(一)构建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开展附带民诉调解工作的激励机制。附带民诉调解前置必将增大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的工作压力。为提高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开展附带民诉调解工作积极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可出台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地方各级审查起诉机关、刑事侦查机关应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将附带民诉调解开展情况而非附带民诉调解结案情况作为对办案人员进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以避免部分调解者追求调解工作绩效而损害调解自愿原则。
(二)明确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可开展附带民诉调解工作的刑事案件范围。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为体现司法信用、增强刑事裁决的被告方认同度,人民法院通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立法规定,对达成附带民诉调解协议并积极赔偿的被告进行轻刑化处理。“赔钱减刑”渐成民众通识与社会现象。[6]由于“赔钱减刑”难以化解公权与私权、传统复仇观念与现代刑罚理念、被告人经济状况差异性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间冲突,[7]“赔钱减刑”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操作不当,极可能蜕变成“侵蚀法律公正的蚁穴”,故社会各界均认为应对判前“赔钱减刑”适用范围进行立法限制。[8]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立法限制可能会衍生“赔钱减刑”消极社会效果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便是例证。为避免附带民诉调解可能衍生出的消极社会效果,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有必要通过联合制定司法解释方式对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开展附带民诉调解工作的刑事案件范围作以下排除性限定:1.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对此类案件进行附带民诉调解,如调解成功后仍旧判处被告死刑立即执行,被告基于积极赔偿可从宽处罚的司法精神及相关法律规定,通常会误认为司法不公而积极上诉、申诉;如调解成功后依法对被告从宽处罚,则导致被告“以钱抵死”,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极易遭致广大社会民众的非议,难以取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办案效果。2.刑事加害方明确表示要以刑罚结果作为协议生效条件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部分当事人有时会达成如此协议:加害方同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给被害方作为赔偿,但必须以法院判处被告刑期低于某个数值作为协议生效条件,否则退款。[9]由于刑罚权属公权,附带民诉纠纷当事人无权以刑罚权的适用作为交易砝码进行协商。依法履行审判权既是我国人民法院应尽的法定职责,也是不受公民个人非法干涉的法定职权。刑事加害方通过履行法定赔偿责任方式侵蚀审判权的行为应被禁止。3.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诉的前提是遭受某种犯罪行为侵害致国家、集体财产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诉。人民检察院虽被列入附带民诉原告,但其提起附带民诉时未经合法授权取得对被损国家、集体财产的处分权,故无法参与调解并就国家、集体财产的处置问题与附带民诉被告进行协商。故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诉,人民法院只能判令附带民诉被告将赔偿款直接支付给受损单位、受损单位继受者或上缴国库。4.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的公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规定》第281条、《刑事诉讼规则》第393条第3款规定,主持附带民诉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的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仅可将赔偿情况进行注明并附卷移送,无权就案件中的刑事部分进行任何处理;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主持刑事和解的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除对已达成刑事和解的犯罪嫌疑人可向有关机关提出从宽处理建议外,在特定情形下审查起诉机关还可就案件刑事部分作出终结诉讼决定。①另外,由于附带民诉原告可自由决定受偿程度及方式,故在附带民诉调解实践中,如附带民诉被告不愿或不能当场全部赔偿、但愿提供担保保证分期履行调解协议并经附带民诉原告同意的情形下,附带民诉调解协议成立;但根据《刑事诉讼解释》第502条规定,刑事和解须以即时履行赔偿内容作为和解协议成立要件之一。鉴于刑事和解与附带民诉调解在成立条件及赔偿后刑事部分处理结果的差异,故对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的公诉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应主持刑事和解,不宜进行附带民诉调解。
(三)灵活把握附带民诉调解协议成立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附带民诉纠纷一方或双方为多人且调解意见不一情形普遍存在。在调解实践中,法院通常根据自愿原则,将全体当事人同意作为附带民诉调解协议成立要件以避免异议方在调解结束后申诉上访。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内部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时,通常以调解失败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使我国附带民诉调解立法目的落空,在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还可能激化意见分歧方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调解机关在坚持调解自愿原则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存在意见分歧的附带民诉纠纷进行调解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方式建议如下:1.如被告人涉嫌数罪如抢劫罪、伤害罪,附带民诉原告方为多人且意见不一,调解者可分别考虑附带民诉原告的调解意愿进行处理。如抢劫犯罪的被害人愿意接受调解协议并进行谅解,调解机关则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抢劫犯罪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或进行从宽处罚;伤害犯罪的被害人不愿意进行调解,则依法对伤害犯罪进行处理后再由人民法院根据数罪并罚原则确定被告刑期。如被告涉嫌一罪如故意伤害罪,附带民诉原告方为多人且意见不一,调解机关则可以遭受物质损失较重的一方或多方的调解意见为依据来决定是否调解及调解协议是否成立。如遭受物质损失较重方意见不一,则视为调解失败。以故意伤害犯罪为例,如致多名被害人重伤、多名被害人轻伤,则应以重伤被害人的一致意见作为调解依据,如重伤被害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则以调解失败处理。如遭受重伤结果的附带民诉原告方一致认可某种调解协议,调解机关可视为调解成立,给不同意调解的轻伤被害人留下相应的赔偿款份额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10]2.共同犯罪案件中,如附带民诉被告方调解意见不一,调解机关则可参照《刑事诉讼解释》第505条第2款规定,对愿意履行全部或部分赔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或进行从宽处罚,但应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履行全部赔偿责任的附带民诉被告依法享有追偿权。另外,在附带民诉调解实践中,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附带民诉被告赔偿意愿、能力不一情形时有发生。如被告仅愿承担其应负的赔偿份额或因赔偿力不足仅能履行部分赔偿时,部分法院基于共同加害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原则,通常要求愿意赔偿的附带民诉被告全部赔偿或要求附带民诉原告同意作为全部赔偿,否则视为调解失败。[11]笔者认为,调解机关应当允许部分附带民诉被告承担其赔偿责任份额,不宜要求愿意赔偿的被告进行全部赔偿或要求附带民诉原告同意作为全部赔偿。理由如下:1.附带民诉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被害方提出的赔偿诉求以保护被害方私益。私益自治属民事司法基本原则之一。人民法院在处理本质属私益诉讼的附带民诉纠纷过程中,应尊重附带民诉原告关于私益保护方式的意愿,应在附带民诉原告同意情形下,允许部分附带民诉被告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仅就其赔偿份额承担赔偿责任。这既体现调解自愿原则,也利于被害方物质损失及时得到一定程度弥补。2.《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大小通常决定着民事侵权责任大小,如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承担全部或主要赔偿责任。因此,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各附带民诉被告民事侵权责任程度是可以区分的。在附带民诉原告同意被告可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情形下,调解者允许附带民诉被告仅承担其赔偿份额,可有效促使加害方于判前积极履行赔偿责任。3.部分加害方的赔偿意愿及能力存在着动态变化,其在调解时不愿赔偿或无力赔偿,并不意味着其永无赔偿意愿及能力。调解者为更好保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在部分附带民诉被告仅赔偿其责任份额情形下不宜要求原告同意作为全案赔偿,可要求附带民诉原告就通过调解方式得到赔偿的附带民诉撤诉,或对未通过调解方式获得赔偿的附带民诉部分,与刑事部分一并作出赔偿判决。
(四)司法机构在附带民诉已达成调解的情形下,应对刑事纠纷处理结果进行详细的理由说明。充分、详细的理由说明是支持纠纷处理结果具备正当、合理性的基础。由于附带民诉调解衍生的“赔钱减刑”外象与我国封建社会“赎刑”现象具有高度相似性,在附带民诉已达成调解情形下,对被追诉者从轻处罚的刑事纠纷处理结果如缺乏充分的理由说明,则极易侵蚀部分民众所具有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传统法制观念。另外,刑事纠纷处理决定过程的不公开,也使部分怀有司法腐败潜意识、刑事法律知识稀少的附带民诉当事人,对缺乏充分理由支撑的刑事处理结果心生疑虑,误认为遭受司法欺骗而对附带民诉已达成调解的刑事处理结果进行上诉或申诉。[12]因此,审查起诉机关对附带民诉已达成调解的刑事纠纷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对附带民诉已达成调解的刑事纠纷作出刑事裁决时,应向附带民诉当事人及社会民众加强刑事纠纷处理结果的理由说明。具体包括:1.调解者在附带民诉调解活动记录或附带民诉调解协议中详细说明:(1)开展附带民诉调解活动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2)附带民诉调解过程及调解结果;(3)附带民诉各方所持调解意见;(4)附带民诉调解失败原因或已达成的附带民诉调解协议内容。2.司法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或刑事裁决书中详细说明:(1)附带民诉各方所持调解意见、调解结果、调解过程及调解协议内容合法性分析;(2)附带民诉调解结果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的合情理性分析。
注释:
①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主持刑事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对已达成刑事和解、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参考文献:
[1]柴建国,赵智慧.审判、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职能的整合[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3):101-112.
[2]杜经和,余定猛.公安机关委托人民调解若干问题探析[J].公安研究,2011(7):25-28.
[3]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主动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兑现难问题——构建附带民事诉讼公检法司联动机制情况的调查[N]. 法制日报,2013-06-05(12).
[4]旷凌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问题与对策[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53-58.
[5]薛剑祥. 刑事自诉和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适用[J].华东刑事法评论,2006,8:256-265.
[6]丁萧. “赔钱减刑”现象的法社会学分析[J].司法,2010,5:121-130.
[7]卫宏战,刘静.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对量刑的影响[N].人民法院报,2008-09-10(06).
[8]徐光木. “判前赔偿减刑”莫成侵蚀法律公正的蚁穴[N].法制日报,2007-09-26(03).
[9]郑允展,钟育周. 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若干法律难题与对策[J].法治论坛,2012(2):271-284.
[10]柴建国,王宇辉.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中的几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9-07-01(06).
[11]余剑.如何规范附带民事诉讼中部分被告人与原告人的调解[J].人民司法,2007(20):74-76.
[12]宋高初.论刑事和解的社会效应[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0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