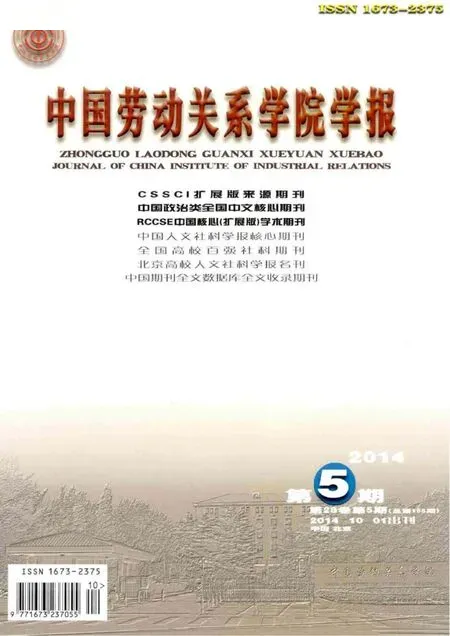并购视角下的企业劳动关系调整研究*
林 建,蒋俏玲
(1.广西科技大学 鹿山学院,广西 柳州 545616;2.柳州市金融办公室,广西 柳州 545001)
工业化社会以来,企业间的并购先后经历了以多元化为主的横向并购、产业链整合为主的纵向并购、多元化与产业链兼容的混合并购、金融杠杆并购和跨国公司并购五个阶段 (王化成,2012)。尽管不同阶段的并购手段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基于战略愿景约束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是诱发并购行为的直接动因。但是,企业的并购行为能否顺利实施,并购整合能否顺利推进,并购绩效是否符合预期,固然会受制于包括资本、业务、技术和管理等在内的诸多要素整合,但嵌入其中的劳动关系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而媒体近期报道的、包括微软并购诺基亚①2013年9月,微软宣布斥资71.7亿美元收购诺基亚的设备与服务业务 (即手机业务)和相关专利,同年11月,诺基亚股东批准这项收购行为。受此影响,诺基亚东莞工厂的员工在园区内的空地上打出了维权横幅,提出“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尊严和人权的!”(参见: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3_11/20/31403732_0.sht)。、联想收购IBM低端PC业务②IBM旗下深圳工厂超过1000名工人因不满向联想移交,近日开展了一场罢工活动。联想集团此前出资23亿美元收购IBM低端服务器业务,根据协议,IBM这家位于中国南部的工厂将被联想集团接管 (参见:http://tech.huanqiu.com/it/2014-03/4885880.html)。以及阿波罗轮胎收购美国固铂轮胎公司③2013年8月,固铂成 (山东)轮胎有限公司逾5,000名中国工人就该公司被卖给印度阿波罗轮胎公司一事举行罢工,这是阿波罗轮胎打算以25亿美元收购美国固铂轮胎橡胶公司交易的一部分。中国工人当时说,他们担心阿波罗的偿债能力以及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该交易后来告吹 (参见:http://money.163.com/14/0307/12/9MNVV4EO00253G87.html)。等个案④事实上,类似的个案资讯还有很多,如,2009年9月吉林通钢集团重组引发工人不满;2011年,百事公司旗下在华多个工厂发生罢工,起因是这家美国零食和软饮料公司宣布中国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将收购其在华饮料装瓶业务,后在两家公司向员工保证所签合同不会改变之后收购交易才得以继续;2012年,昌河铃木汽车工人罢工的起因也是因为其控股公司长安集团欲转移昌河铃木的汽车生产资质…所引发的劳资纷争事件则进一步表明,资本主导下的并购行为如果忽视甚至漠视嵌入其中的劳动关系因素,并购本身不仅会纷扰不断,更严重的是将会影响到并购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文章以企业的并购行为为分析视角,探究企业并购过程中的劳动关系特点,以此为基础,提出因应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以期为并购行为的顺利实施、产业关系重组的有序推进和劳资关系和谐稳定创造积极条件。
一、企业并购行为分析
广义地看,并购是企业基于战略愿景所需而进行的兼并 (Merger)和收购 (Acquisition)行为。因此,企业的并购行为一般会涉及到资本、产业、业务、人员、管理和技术等诸多要素的重组。
理论上,产生并购行为最基本的动机就是寻求企业的发展,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世界500强企业,99%都是通过并购予以实现的 (stigelize,2012)。具体到理论方面,并购最常见的动机有协同效应 (Synergy),具体包括经营协同效应 (Operating Synergy)和财务协同效应 (Financial Synergy)。显然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并购的成功实施以及并购整合的顺利推进为前提,协同效应将难以实现。因此,企业的并购行为必然会涉及到三个层面的整合。
(一)资本主导下的企业治理架构整合
企业是股东的企业。在现有的商法制度下,企业的最高治权均配置给股东,因此,没有股东的同意,所有并购行为将无法实施。因此,企业的并购行为首要的后果就是资本主导下的企业治理架构整合。
按照整合后事涉并购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变化,资本主导下的企业整合一般表现为吸收、控股以及新设等三种基本方式。吸收型并购中,被并购企业将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地位,其经营用的、包括雇员劳动力等在内的相关资源均纳入并购企业中,被吸收企业的原股东将通过股份置换或现金补偿等方式退出被并购企业;控股型并购是并购者以增资等方式取得被并购企业控制权的一种并购行为,其实现的路径包括被并购企业原股东的股份转让和并购者新增被并购企业股份并摊薄原股东股份,并购完成后,被并购企业的法人资格地位仍予保留;新设并购是并购行为发生后,事涉并购各方企业重新组合为一个全新的法人实体的一种并购行为,而包括并购者等在内的相关各方法人资格是否保留取决于新设主体的管理决定。
很显然,这一层面的并购行为是在资本主导下实施的,其治理架构将由资本所有者 (即股东)决定,基于治理架构的经营管理整合将在此框架下进行。
(二)管理层主导下的企业经营架构整合
两权分离下,管理层受企业股东之托并在股东所建构的治理架构下负责企业日常营运事务的推进。因此,管理层的核心任务是在授权范围内,对包括雇员劳动力要素等在内的资源进行整合,目的是实现并购绩效的预期目标。在内容上,管理层主导下的经营架构整合包括公司的营运架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业务范围、经营区域以及营运制度等,都将围绕并购绩效目标展开,对并购绩效有负向作用的要素将可能被采取包括出售、剥离或者关停等方式予以整合,嵌入其中的劳动力要素也将不可避免。
(三)以管理制度重新调整为手段的企业内部利益整合
制度治企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方式,并购整合中也不例外。就管理的逻辑来看,并购整合必然要回归到制度的重塑,其重塑压力源于资本主导下架构整合所冀望的业绩目标,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管理层基于受托责任背负的业绩压力必然要向其治下的要素所有者进行传递,采取的手段就是通过制度调整的方式重新分配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既得利益,并通过利益的调整来引导其行为围绕并购绩效展开,并将其作为并购绩效评估的最终依据。
二、并购行为中的劳动关系特点分析
微观层面分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以企业为载体的雇佣关系,因此,企业并购所涉的各类重组行为必然涉及到劳动关系的变化,其主要的特点有:
(一)基于并购行为所引发的劳方利益忧虑是普遍存在
利益是劳动关系的核心,也是诱发劳资纷争的关键因素。理论上,企业并购的决定权属于资方 (当然,劳动者也无意去挑战、质疑甚或剥夺制度所赋予资方的这一权利),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资方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对其所控制的资源从核心竞争力改进或提升的角度予以重组。在此过程中,劳动者对事涉并购行为可能导致的利益忧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理论上,劳动者在并购中的利益忧虑并非空穴来风,除了变革所带来不确定性因素外,已有的事证也表明,凡涉企业并购重组的行为,劳动者利益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波动,尤其是基于并购绩效所需的整合涉及到成本消减动机时,工人对预期利益的担忧就更为明显,其维护权益的行动也将更加有力,如果制度框架内的维权行为无法得到积极妥善回应,工人将不惜冒背负制度惩戒之成本来争取权益,而前文引注所涉的相关个案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二)资本主导下的企业架构整合必然会带来劳动关系合约的主体变更
前述分析表明,在资本的主导下,事涉并购的相关企业架构必然会被重组,参与并购各方的法律地位可能会出现变化,尤其是在吸收和新设合并,并购前的原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必然会被改变。
劳动关系合约作为企业与劳方 (某些时候是劳方的代言性组织—工会)缔结的事关劳动者权益的合约,也必然会伴随企业架构整合而出现变化,因此,只要基于并购行为的企业架构重组发生,与劳动者缔结雇佣主体必然改变,否则,劳动者的权益将无法维护。当然,从现有法律规定和实务操作的经验看,很多公司在并购所涉的架构重组中一般都会提及原有的、包括劳动关系合约等在内的有效性问题,但这种承诺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的合约安排,基于并购,尤其是并购后的劳动纠纷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基于并购行为的企业架构重组所引致的劳动关系合约变更则是确保并购整合顺利推进的重要环节。
(三)劳方利益诤诉的救济模式出现改变
劳资利益长远地看是一致的,但理性的劳资双方也清晰地知道,合作与冲突的动因更多地是源于短期的利益诤诉。在企业的并购行为中,这些利益诤诉既有因业务或结构调整所涉的就业方式 (如工厂迁址等)改变,也有因业务调整所需而主动或被动离职所涉的利益补偿以及与并购整合相关的工作习惯改变所带来的不适等。不可否认,这些改变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当企业层面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伸张时,工人或工会将可能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向政府劳动监察管理部门等申请权利救济。但是,由于并购行为所涉重组的复杂性 (既有架构调整,也有管理层调整,还有更重要的制度调整等),工人利益的权利救济不仅成本会增加,而且有相关救济权利的执行主体也可能出现变更,而这或许是在并购发生之时,工人更希望资方将并购所涉的、包括岗位、薪酬等经济事项讨论清楚的重要原因。
三、并购行为中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资本主导下的企业并购行为在商业的逻辑上无可厚非,但单纯的商业逻辑显然无法彻底解决嵌入其中的劳动关系问题,尤其是事涉劳动者利益预期的事项,如果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劳资纷争将可能出现,直接的后果不仅会让资方的并购意愿付之东流并导致并购失败,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并购行为中缺乏对劳动关系问题的应有关注并采取适当的调整机制,并购后的整合也将无法顺利推进,并购绩效也将缺乏稳定的经营环境。因此,资方主导的、基于企业战略愿景所虑的核心竞争力改进或提升的并购行为意欲达成并购绩效的初衷,就应在并购中建立和完善以劳动者利益可保障的集体谈判机制,因为:
(一)与并购相关的集体谈判机制有利于消解工人潜在的利益隐忧
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均表明,资本主导下的企业并购行为之所以引发工人的不满甚或抗争,根本的原因还是工人无法从已有的并购行为中筛选出有利于自身利益保障的信息。而集体谈判机制的好处就在于劳资双方能够在并购行为尚未正式实施前,就各自所需的目标、行为、路径以及措施等进行充分讨论并表达意见。对资方而言,其好处就在于并购过程中可以得到工人的支持并减少因并购可能导致的摩擦成本,即使并购行为无法取得工人的认同或者支持,资方也可在更广的路径下寻求更优的办法来解决。当然,对工人而言,通过并购前与资方的谈判,有助于理性分析并购行为对自身预期利益的影响并做出合理的决策。因此,开展与并购行为相关的集体谈判对劳资双方而言是共赢的,尤其是对于战略目标密切相关的并购行为,将有助于资方更加合理和科学地做出安排,为并购重组的顺利推进创造积极条件。
(二)与并购相关的集体谈判机制将有助于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劳动关系的经济社会属性表明,单纯的利益保障对换取劳动者的支持是必要的,短期看也是很重要的。但长远地看,劳动者的权益诉求除了以就业安全、薪酬合理的利益因素外,衍生于此的被尊重以及基于尊重所激发的劳动积极性也不能忽视,更不能被漠视。在已有的个案资讯中,工人在得知资方的并购行为时之所以喊出“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尊严和人权的”等口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劳动得到尊重,希望权利得到体现,希望尊严得到维护。而嵌入并购中的集体谈判机制,将有助于工人的体面感、尊严感的维护,进而寻求与资方的主动合作,为并购行为的实施、并购整合的顺利推进创造能动的要素潜力。
(三)与并购相关的集体谈判机制也是劳动关系调整法律所鼓励和要求的行为
不可否认,现有的商法制度将企业的主要治权分配给了资本所有者,但不能回避的事实就是,与商法对应的劳动关系法律制度也将劳动者的权利索取权赋予了工人。在我国现有的劳动关系法律制度中已经明确规定:事涉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应征求其意见,某些时候还需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类似机构予以审议通过。企业并购作为事关雇佣主体、业务结构、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制度的商业行为,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商业行动,实施的结果必然会对劳动者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落实制度规定显然也是并购行为中需要嵌入集体谈判机制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地说,这一谈判机制是工人的权利而非资方的赠予亦或施舍。
当然,要把嵌入并购行为的集体谈判机制落实,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操作性规定的同时,不断培育和完善工会组织,进一步加强其能力建设,尤其是与并购行为相关的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对提升谈判质量和达成谈判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在谈判中收获尊重,制度因素固然重要,但能力因素或许是根本。当然,对集体谈判另一重要主体的资方,也应从观念、行动和措施上,积极回应工人的谈判诉求,积极探寻有助于降低并购风险的最优方案,为劳资合作、产业关系稳定乃至社会和谐创造积极条件。
综上分析,尽管企业并购是资本主导下的商业行为,但这一行为如果嵌入了劳动关系因素,其仅有的商业逻辑并非局限于单纯的商业考虑,相反,嵌入其中的劳动者利益诉求应得到相应的尊重,因此,需要在并购行为中建立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将有助于并购行为的实施以及劳资关系的稳定,而要将嵌入并购行为中的集体谈判机制坐实,制度需要完善、工会要行动、资方要努力,唯如此,以核心竞争力改善或提升为目标的企业并购行为才可能顺利实施,基于并购绩效的重组行为才能顺利推进,基于劳资合作的利益共享也才有坚实的基础。
[1]任小平,许晓军.职工权益自救与工会维权策略研究 [J].学海,2008,(5).
[2]任小平.中国工会:转型期的诉求责难与制度救济[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2).
[3]王化成著.高级财务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孙立平著.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