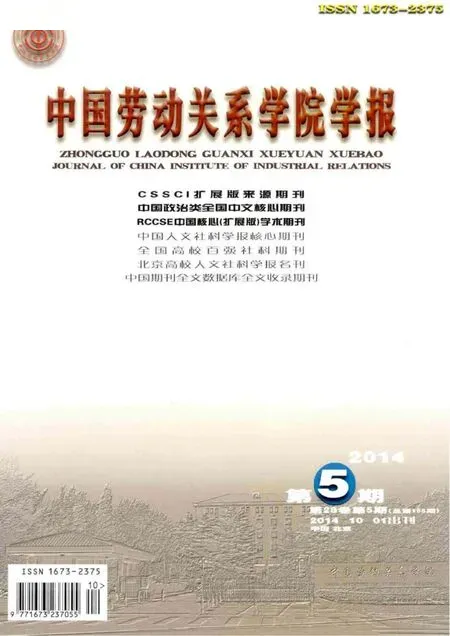影响养老金的主要人力资源因素*
蔡宁伟
影响养老金的主要人力资源因素*
蔡宁伟
(中国工商银行运行管理部,北京100140)
养老金也称为退休金,用以保留一部分职工年富力强时的劳动成果,并使之延期分段使用,以确保老有所养。养老金业务的实质离不开个人乃至社会的人力资源变迁,其主体是正在作为或曾经作为劳动者的人,与人力资源一脉相承。因此,养老金与人口学意义的人口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管理学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劳动关系等概念有着一定联系。研究尝试从理论上分析上述因素对养老金的影响,并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
养老金;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劳动关系
养老金也称为退休金、退休费,是目前国内一种最主要的养老保险待遇。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及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一定期限(一般是每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不难看出,养老金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效率、年限和水平等有密切联系。在此,按照相关概念的有关逻辑,我们设计了如下研究架构:

图一:养老金业务的主要人力资源影响因素研究架构
如图一所示,养老金前因即影响因素、本质即核心内涵以及作用等一脉相承,联系比较紧密。由于很多研究者对其本质、作用等已经有了丰富的探讨,不再赘述。本研究的重点在于从理论上探讨养老金的前因部分,特别是影响因素中的人力资源因素。由于养老金的本质与人休戚相关,养老金与人口学意义的人口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管理学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劳动关系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等常被视为宏观因素,而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关系等则被视为微观因素。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人力资本、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关系又与劳资双方有关,既有雇员(员工)的努力,也有雇主(管理者)的推动,一般视为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人力资本的重要积累途径是培训,这不仅需要雇员自身在工作中善于学习,也需要雇主提供有利的培训平台;又如,劳动生产率不仅在于雇员工作的熟练程度,也需要雇主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服务。
一、养老金的本质与作用
当前,养老金的积累本着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积累的原则,其实质是强制保留一部分职工年富力强时的劳动成果,并使之延期分段使用,以确保老有所养。不难看出,无论养老金的形式、分类、条件、方案和评价如何变化,其实质离不开个人乃至社会的人力资源变迁,其主体是正在作为或曾经作为劳动者的人,与人力资源一脉相承。这里的人力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结构,也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还包括管理学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劳动关系等概念。这些概念相对比较常见,有其特殊的理论内涵,但又与本文讨论的主题养老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专业核心知识和技能的来源就是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综合。20世纪初,人力资源管理的前身人事管理即以应用劳动经济学的身份诞生。因此,养老金无论其渊源还是发展都与人力资源的相关领域联系紧密,只有认清了人力资源相关领域的重要概念才能更好地了解养老金以及养老金业务的创立、开展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创新养老金业务的相关管理要求和制度流程,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变迁。根据笔者的分析,总体来看,养老金主要与该国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积累、劳动报酬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关系等因素休戚相关。
以往,在未建立养老金制度之前,中国人习惯“养儿防老”,实质是将人力资源的高峰与低谷“错峰匹配”,将年轻力壮子女的劳动报酬高峰期与耄耋年老父母的劳动报酬低谷期相匹配,从而形成家庭式、独立式、自发式的养老方案。相比之下,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是一种国家式、互助式、统筹式的养老方案。这一方案的影响较之前更广,从家庭上升到国家;较之前更有保障,吸纳了除个体之外的组织和国家;较之前更有计划,进行了更高层面的设计和调度。在目前“养儿防老”观念并未完全转变之前,对于老龄人士增添了一重保障,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各国由于国情国力、法律法规、观念思路等方面的差异,养老金方案与设计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并不辨析哪种养老金方案或业务的利弊好坏,主要就养老金业务本身探讨其主要的人力资源影响因素。毕竟,养老金和作为个体的职工及作为群体的世代(理论界一般以十年时间为一个世代,如60年代生人、“80后”、“90后”等)关系非常紧密,只有了解了养老金业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宏观和微观人力资源趋势的变迁,更加有效地发挥养老金的作用,更好地发展养老金管理和托管等相关业务。
二、人口结构对养老金的影响
人口结构是养老金机制成功与否的关键影响因素,养老金业务的发展与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联系最为紧密。具体而言,人口结构中青壮年与老年人口的比例至关重要。例如,四位年轻人供养两位老年人和两位年轻人供养四位老年人的支持度、安全感、承受的压力与稳定性完全不同。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养老结构一般呈现“四供二”、“三供一”、“二供一”等“金字塔模式”。这一模式的支持度和安全感相对较高,承受的压力较小,支撑的稳定性较高,当然这一模式是建立在这类发达国家人口基数较小、社会福利制度完善、政府鼓励生育的基础之上的。这类国家目前大多数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相对较低,人口呈现低自然增长甚至负自然增长的形态。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养老结构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恰恰相反,主要呈现“二供四”、“一供二”等“倒金字塔模式”。这一模式的支持度和安全感相对较低,承受的压力较大,支撑的稳定性较差。当然,这一模式的基础受到我国国情国力和法律法规的限制,如计划生育政策等,目前“二供四”的结构恰恰是城市中常见的“双独家庭”或“单独家庭”。这一政策的出台主要考虑了国家的发展和国情,否则资源和环境都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这两类家庭中,年轻的夫妻双方或单独一方都是独生子女,需要长期供养双方四位老人,且在目前医疗条件不断健全的情况下,支持的时间可能较此前更长。
事实上,人们熟悉的“人口红利”恰恰反映了一国青壮年人口即适龄劳动者的存量和增量所带来的潜在需求和经济效应。蔡昉等国内学者提出,1980年——2010年3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动因之一就来源于人口红利。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橄榄型”,青壮年劳动力占比相对较高,儿童和老年人占比相对较小,而这一阶段的青壮年劳动力主要受益于计划生育实施之前的政策激励,“多子多福”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倡导的。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1980年以后,成为适龄劳动者的数量和占比相对较小,而老龄人口不断增大,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往的“橄榄型”结构逐步向“倒金字塔型”结构转型,养老金的持续补充和支持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不足,使得劳动报酬等成本因素不断上涨,后续还将对此展开讨论。目前,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逐步放开了生育限制,解除“双独”和“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禁令。如果这一政策有效落实,未来中国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未来适龄劳动者供给的增加也将缓解养老金不足的压力。
三、人力资本对养老金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人力资本及其渊源的关注由来已久,其提出和高峰伴随两次产业革命产生并推动了两次产业革命,深刻影响了养老金的形态和形式。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视劳动力为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力,也是资本的重要组成之一;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进一步指出个人能力的分类及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并主张把教育投资上升到国家投资的高度以期获得高额回报。信息革命时期,学者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一个高峰。在美国经济学家明塞尔建立个人收入与职业培训投资模型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也是此后的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和贝克尔分别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对个人收入和分配的关系。其中,舒尔茨发现:从宏观视角来看,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3%。这一发现激起了发达国家对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和过程的重视,并逐步加大对这些领域的关注和投资。不难看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养老金的发展也有着密切联系:如果年轻时期人力资本积累较为丰富,回报率较高,投资相对持续,那么年老时期的回报额也相对较高、可支持的时间也较长、获取也相对稳定。即便一些高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士到龄退休,还可能享有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障、资金来源和工作支持,例如一些高级管理者就享有与公司盈利挂钩的“金降落伞计划”,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往往被相关领域的企业、政府机构返聘成为高级顾问或资深参议等。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具有长期性、高回报性和持续性,而且不少领域的人力资源投资还具有增值性和累加性,如果“少壮不努力”,往往“老大徒伤悲”。这种投资回报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跨越了国界和年龄的限制,比如一些名人的书籍可以多次再版,到下几辈都可以享受版税等收益;而一些专家的工作年限远远超过了法定的退休时间,美国90岁以上全职工作的劳动者甚至突破了5万。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中国等东亚国家具有先天优势,相比其他国家更加重视教育,更加关心下一代的培养。但是,人力资源的投资也会存在一些误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并非完全可靠。既然将人力资源视为一类资本,那么这一资本一定符合基本的经济学供给规律。因此,如果盲目投资、“随大流”投资也可能导致一些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增值前景堪忧。例如,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的专业先后流行了“数理化热”、“计算机热”、“会计金融热”,但每次热潮褪去,一定会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硕士研究生难以及时就业,或者难以寻找到适当的岗位。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不能按时或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金积累和领用。
四、劳动报酬对养老金的影响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价值体现,是衡量劳动者劳动成效的标尺之一(这里提到的劳动报酬主要指可衡量的,组织认可的、通过合法劳动所得到的物质报酬,不包括劳动者创造的精神财富或其他类型的财富,因为后者更难以衡量,有的精神财富甚至被视为无价之宝)。影响劳动报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看,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报酬,一般适龄劳动力越少报酬越高;行业周期影响劳动报酬,通常行业处于上升或成熟期可以获取较高的劳动报酬,GDP增长和CPI上涨都可能助推劳动报酬的提升;产业结构影响劳动报酬,往往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劳动者报酬水平较高。从微观上看,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劳动报酬,通常人力资本投资越多劳动报酬越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单位比较看重学历,而莘莘学子也为了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不断勇闯高考独木桥;个体的技能也影响劳动报酬,一般越是掌握了熟练技能越能提高自身的产出,越能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就越能得到更高的报酬,在一些计件工作中体现较为明显;劳动关系也可能影响劳动报酬,个体与组织的关系越密切、越具有话语权、越拥有不可替代性,越可能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只有在青壮年时期获得了较高的劳动报酬,才可能为今后的养老金积累创造更丰富的基础。当然,通过分析也可看到,劳动报酬的获得抑或养老金的积累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首先需要获取和积累的主体长期的努力和付出。
五、劳动生产率对养老金的影响
如果说上文提到的劳动报酬可能受到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那么劳动生产率又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和影响呢?劳动生产率与养老金又有哪些联系呢?一般而言,劳动生产率主要指单位时间内劳动的生产效果或生产能力,通常用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或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也可简称为生产率,可视为生产力也就是生产能力的组成之一。我们常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质是指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简而言之,生产力好比工具,生产关系好比工作,有什么样的工具就能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例如,以蒸汽机发明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大幅提高了生产力,从而颠覆了以往分散的生产关系,转而采用集中的、大规模生产的新型模式。因此,劳动产生率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在于生产力的水平,一般而言,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其他宏观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也有影响,如人口结构、劳动报酬水平等。不难理解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更容易获取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报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往往易于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微观层面,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与组织的劳动关系也影响劳动生产率。一般而言,个体受过良好的培训,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等,往往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利条件;如果个体与组织关系得当,组织承诺度、满意度和忠诚度较高的个体更愿意主动付出,甚至在完成自己份内工作的同时(职内绩效),通过组织公民行为帮助其他组织成员共同提高绩效(周边绩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个体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前提下,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可以完成更多数量甚至更高质量的劳动,创造更具价值的劳动。依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个体通常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所以,劳动生产率通过劳动报酬之一中介机制,建立了与养老金缴纳之间的因果关系。劳动生产率越高、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越大,获取的劳动报酬越多、享有缴纳养老金基础相对越高、未来所得的养老金累积越丰富,这是一系列的正向因果逻辑关系,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六、劳动关系对养老金的影响
这里的劳动关系是一种广义的劳动关系,不仅包括劳动者(被雇佣者)和代理人(雇佣者)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了劳动者(被雇佣者)和资方(出资人、股东)的关系,并且也包括了劳动者(被雇用者)和代理人(其他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这一关系的纽带在于劳动合同,这类合同往往以文本的形式明确劳动者(被雇佣者)和代理人(雇佣者)之间的义务和责任,明确代理人(雇佣者)和资方(出资人、股东)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在劳动者(被雇佣者)和资方(出资人、股东)之间也建立了某种委托代理关系。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劳动者(被雇用者)和代理人(其他被雇佣者)或者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不会由直接的合同明确,这类代理人指的是不具有法人定位的被雇用者,他们也和雇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管理、指导、指挥等角色,是劳动者(被雇用者)的上级。因此,这类代理人与劳动者(被雇用者)的关系是由各自与代理人(雇佣者)之间确立的关系所形成的,看似没有文本约束,却建立在对各自岗位职责分析和明确的基础之上,往往会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例如管理责任等。通常而言,组织内劳动关系的好坏,会影响组织内部的工作氛围,进而影响组织文化,最终影响组织绩效。当然,劳动关系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设想,愿意为劳动者提供较多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可以获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也容易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这些因素对于劳动者养老金的积累都比较有利。
劳动关系的研究和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备受重视,在经历了资本主义早期积累过程中产业工人和资方劳动关系的紧张、对峙和冲突之后,双方更加意识到通过劳动谈判和沟通维护良好劳动关系的价值和重要性。为了实现和资方同等对话的目的,也为了形成新型的劳动者组织同盟,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特别是自组织异常强大,在后资本主义时期往往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例如,1990年以来,英、法、德等国的航空业工会为争取所属团体工人和雇用者的权益,开展了多次大罢工,不断提升了工会会员的工作报酬,改善了工作环境,明确了可容忍的行业失业率上限。值得关注的是,失业率特别是城镇人口失业率对于员工的养老金影响很大,由于没有收入,失业者往往只能依靠社会保障和救济,即便在允许有失业养老金保障的体制下,养老金的积累由于基数的薄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累积更举步维艰。近年来,我国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越发关注,例如,对农民工讨薪、下岗工人再就业等都展开了积极帮助和再培训,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各方的义务和责任。可以展望,在未来的劳动关系实践中,随着人口的整体人力资本递增、劳动者效率和报酬的提升以及相关约束的明确与严格,更能够建立长期、和谐、双赢的劳动关系,更有条件保障未来公民的养老金。
七、养老保险待遇理论研究的探索
目前,中国正在加快步入老龄社会,与每一位公民密切相关的养老金机制体制建设备受关注、亟待完善。如前文所述,养老金业务的实质离不开个人乃至社会的人力资源变迁,其主体是正在作为或曾经作为劳动者的人,与人力资源一脉相承。因此,养老金与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管理学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劳动关系等概念有着一定联系。尝试从理论上分析上述因素对养老金的影响,从根本上认识养老金的形成与演进,有助于充分理解影响养老金业务的主要人力资源因素,进而从源头入手,未雨绸缪地优化顶层设计。毕竟,正如其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的人力资本一样,养老金也需要长期的积累。
本研究从理论上探讨了养老金的影响因素,从逻辑上分析了有关人力资源因素的作用过程,但也比较明显地感觉到研究的不足。首先是缺乏实证的研究设计,特别是数据的支撑。由于养老金和养老金业务在国内起步较晚,而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等数据获取也需要相当长的周期,因此我们未能采用规范的实证研究设计和数据模型检验,这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和遗憾。其次在影响养老金业务的主要人力资源因素中,人口结构、人力资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而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劳动关系之间的联系可能更加明显,例如,杨燕绥、刘懿就认为人力资本影响薪酬结构。但是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究竟有多大,有无细分之下的共变因素影响和交互作用,依然需要实际数据的支撑与检验。
[1]党俊武.老龄问题研究的转向:从老年学到老龄科学[J].老龄科学研究,2014,(2):3-9.
[2]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2013,(11):1-16.
[3]范硕,李俊江.亚洲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挑战以及应对策略[J].人口学刊,2013,(4):32-41.
[4]杨燕绥,刘懿.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节点与政策路径——以人力资本和老龄化为视角[J].探索与争鸣,2013,(1):66-71.
[5]胡湛,彭希哲.老龄社会与公共政策转变[J].社会科学研究,2012,(3):107-114.
[6]蔡泳.联合国预测:中国快速走向老龄化[J].国际经济评论,2012,(1):73-81.
[7]刘进才.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12):88-91.
[8][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The Main Human Resources Factors Affecting Pension
Cai Ningwei
(Industrial&Commercial Bank of China,Beijing 100140,China)
Pension is used to save some working pay in people’s juvenility and postponed to use in order to subsist her or his oldness.Thus,pension is related closely with human resources.The actors of pension are people or laborers.As a result,pension is related with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demology,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s,labor productivity,labor remuneration and labor relations in management science.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sis those factors above,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pension;demographic structure;human capital;labor productivity;labor remuneration;labor relationship
F840.67
A
1673-2375(2014)05-0068-05
[责任编辑:鲁微]
2014-07-07
蔡宁伟(1982—),男,辽宁大连人,博士,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运行管理部,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银行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