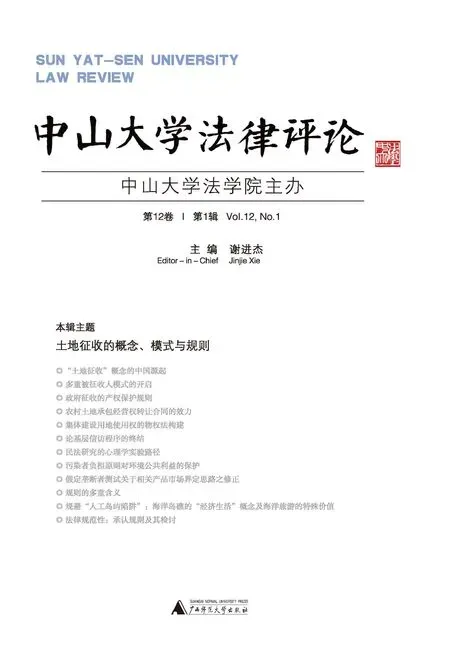污染者负担原则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
叶媛博
污染者负担原则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
叶媛博[1]
环境公共利益损害主要是指污染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害,表现为环境质量下降、物种数量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等。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公共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着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水平。污染者负担原则作为环境责任领域的基本原则,为公共环境保护设置了从损害预防到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体系,这种以义务为导向的法律保护体系比传统的以权利为导向的法律体系更加适合我国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目前,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适用困境,可以在参考国外应对对策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新的解读,并完善我国立法和相关制度,更加灵活地适用原则,使其在环境公共利益保护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污染者负担原则;环境公共利益;环境成本内在化;义务中心主义
一、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缘起及含义
(一)污染者负担原则之缘起
所谓“污染者负担”,是指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治理污染、赔偿损失、恢复生态环境的责任。尽管在今天看来,环境法中的“污染者负担”已经同民法中的“损害者赔偿”一样成为一项普遍的责任承担原则,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污染者”并不必然承担其对环境资源造成的不利后果。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使用环境资源,当然不必支付费用。工业社会的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自然作为生产的物质能量基础,一方面为生产提供必需的能源和物质;另一方面接受生产排放出来的废弃物,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逐步体现出来,生产者开始为生产所使用的能源和物质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对于生产造成的空气、水、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则主要由政府使用公共资金开展治理和控制活动。
政府自愿承担“清理者”的行为纵容了企业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环境排放废弃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社会的污染危机不断加剧,伦敦光化学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等重大污染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环境问题开始转化为民主问题,民间的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不断开展,一些污染企业遭到社会和媒体的一致批评与抗议。公众反对政府使用公共资源治理这些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要求企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它们能够解决污染问题。[1]参见田丰、李旭明等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9—170页。公共舆论的压力迫使政府在如何分配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责任方面寻求新的出路。
1972年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为了遏制政府环境补贴和环境关税影响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关系,首次提出了“污染者负担”原则,“该原则用于污染防止和控制措施的成本分配问题,鼓励合理使用稀缺环境资源,并避免因此产生的扭曲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行为。换言之,这些措施的成本应当反映在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中,而不应当是由政府提供补贴,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2]Guiding PrinciplesConcerning InternationalEconomic AspectsofEnvironmentalPolicies, annex,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Doc.C(72)128,May 26,1972.。作为一项国际经济管理原则出现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立刻得到了国际环境法学界的认可。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正式将污染者负担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认为“政府应当在考虑环境公共利益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础上,鼓励污染者承担环境污染防治责任,鼓励环境成本内在化及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环境保护”[1]《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随后,污染者负担原则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可,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确立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其他国家也纷纷将污染者负担原则作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进行专门立法。
(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含义
污染者负担原则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从经济管理原则到环境法原则的转变,其内涵也随之改变,从最初的遏制政府环境补贴、维持交易公平向污染者承担污染防治责任、保护公共环境的方向转变。通过比较和总结国际文件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表述,以及我国有关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立法,笔者认为,污染者负担原则是一项以义务为导向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包含了污染者在污染预防、治理、补偿、赔偿四个方面的环境保护义务,蕴含着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效率价值。
第一,污染者预防。1972年“经合组织”最初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时,将其含义表述为“将污染防止和控制措施的成本反映在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中”。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认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实现方式为“环境费用内在化和使用经济手段”。由此可见,污染者负担原则自产生之日起,其落脚点就在于“环境成本的内在化”,所谓“内在化”是相对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问题而言的。“外部性”是指“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2][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5页。。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即生产经营者没有在成本中反映出环境成本,而由公众被动接受环境污染的后果。污染者负担原则对环境成本内在化的要求矫正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促使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选择污染较小的原材料和生产技术,采用清洁环保的生产工艺,降低单位产品的污染物产生量,积极预防污染。当然,只有在环境法制健全、执法严格、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的社会中,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预防功能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污染者治理。污染者治理是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指污染者应当承担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恢复和治理责任。在我国环境立法和环境政策中,污染者负担原则就是通过“污染者治理”的立法内容体现出来的。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曾规定:“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规划,积极治理,或者报请主管部门批准转产、搬迁。”1981年《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强调:“工厂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必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切实负起治理污染的责任。”1989年《环境保护法》又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表述为“污染者治理”原则。如今,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行政强制法》有关环境污染案件中政府机构代执行制度的规定,使得污染者治理的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实现了分离。污染者可以将生产工艺等相关资料交由专业化的污染处理单位负责治理污染,或者由政府代为治理污染,而污染者需承担污染治理的费用。
第三,污染者补偿。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生产难以避免的产物,即使污染者采取了污染预防、污染治理的相应措施,仍难免会有部分污染物最终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影响区域以及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环境公共利益。考虑到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可替代性,应当在允许污染者依法排放污染物的同时,要求污染者承担相应的环境补偿责任。污染者补偿责任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生态补偿制度中。所谓生态补偿是指国家为了调解和平衡环境生态利益,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和市场经济手段,对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进行开发限制,对生态破坏严重的区域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对发展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企业进行鼓励等一系列措施的统称。目前在我国适用范围较为广泛的生态补偿方式是由污染者向代表环境公共利益的国家交纳排污费,由国家财政统一安排用于生态环境保护。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将在“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四个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推进生态补偿制度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污染者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方式和途径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第四,污染者赔偿。由于污染者负担原则最初是一项经济原则,因此该原则提出之初,其责任范围并未包括污染者赔偿责任,而仅仅强调污染者对污染造成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防治和补偿责任。事实上,根据环境史学的研究,早在1932年,法国就出现了多起炼铝厂排放的氟气污染大气环境事件,造成当地农民的果树、蚕虫死亡,从而由工厂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例。[1]参见田丰、李旭明等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8页。因此,在污染者负担原则出现之前,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造成的公民人身、财产损失的情况,已经根据侵权法的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1992年,“经合组织”发布的一份污染者负担原则分析研究报告指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成本不仅应当包括污染预防和治理,还应当包括政府采取的环境行政措施、大部分的事故污染和污染导致的民事损害赔偿,逐步达到污染成本完全内部化的目标。[2]See OECD,The Polluter-Pays Principle OECD Analyses and Recomm Endations,Doc OCDE/GD(92)81,1992.随后,1993年欧盟的《环境损害补救绿皮书》、2000年欧盟的《环境责任白皮书》以及2002年“经合组织”发布的《污染者负担原则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报告》都强调污染者就损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污染者负担原则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重要应用。对此,有学者将包含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称为“延伸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即由污染者完全负担因其污染行为造成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损失。[3]参见柯坚《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嬗变》,《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第87页。然而在实践中,污染者的损害赔偿责任通常只局限于对私益损害的赔偿责任,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却因损害鉴定困难、损害索赔主体缺失等原因,无法完全实现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二、污染者负担原则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理论革新
(一)以权利为主导的环境公共利益法律保护体系的内容与缺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严峻的环境危机催生了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运动。1969年,美国萨克斯教授在解答“公众要求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宪法依据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提出了“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信托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民环境权理论。该理论认为,生态环境属于公民共同所有,公民将生态环境托付于国家管理,因此享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包括享有各种环境要素、环境功能和环境资源的实体权利,以及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管理的程序性权利。环境权被认为是环境法的基本权利,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推崇,4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立法文件对环境权进行了专门立法。
我国并没有对公民环境权进行专门立法,但是肯定了“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信托论”,立法确立了国家对公共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以及政府对公共环境的管理权,以权利为导向从环境行政管理的角度设置了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措施。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理论依据包括两点,一是国家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宪法》规定,水、大气、土地、矿藏、河流、森林、草原等环境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借助其作为政权主体所具有的行政管理权利,为国家所有财产提供行政保护措施。二是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根据环境信托理论,生态环境属于公众共同所有,政府受公众之托管理公共环境,因此政府有保持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的责任。
国家和政府依据对公共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以及对公共生态环境的管理权,设置了一系列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如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度限制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行政收费、行政处罚制度防止国家财产浪费与破坏;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区域环境规划、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维持环境质量;等等。在以上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行政机关是环境管理的主体,而作为环境管理行政相对人的污染者则始终处于被动承受的状态,将环境保护视为阻碍生产和发展的绊脚石,使用各种方法逃避责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通过司法途径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立足于公民环境权。公众享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当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时,法律授权的公民、组织或机关有权代表公众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经验主要源自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1970年美国的《清洁空气法》首次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执行,保证联邦和各州的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其职责,并且补充其资源的不足。[1]参见汪劲、严厚福等编译《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1993—2002年间,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判决的环境案件中大约75%的案件是公民环境诉讼案,公民诉讼已经成为驱动环境法发展的动力。[2]参见别涛主编《环境公益诉讼》,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法院也都受理了一些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第五条,增加了公益诉讼条款,正式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确立了法律基础。然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却任重道远,首先是我国立法中没有公民环境权的专门规定,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也不完善,仅《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海洋行政机关有就海洋环境损害进行索赔的权利,对于其他类型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则缺乏诉讼主体;其次是我国环境保护团体规模有限,且与政府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具备国外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团体所具有的独立性,难以独当一面;最后,环境公益诉讼成本高,环境损害鉴定、因果关系证明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即使立法放开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面对高额的成本,环境公益诉讼仍然让人望而却步。2007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审理环境污染案件,保护公共环境利益,我国各地陆续建立了130多家环保法庭,如今却面临无案可审、门可罗雀的窘境。[3]《77个环保法庭的尴尬》,登载于法制网,网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zmbm/content/2012-06/12/content_3636649.htm?node=7567,访问时间:2013年12月30日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仍然是个未知数。
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环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地下水污染、湖泊富营养化、严重的雾霆天气等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正如环境法学者蔡守秋先生所说,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里面临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几年集中爆发了。面对严峻的现状,基于权利中心主义设置的环境公共利益保护机制却举步维艰,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环境公共利益保护过于依赖行政力量,未能调动污染者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于忽视了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索赔难的特点,以及公众在面对环境公共利益时“搭便车”的心理,谁都想分一杯羹,却不愿意多出一份力。
(二)污染者负担原则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从权利中心主义转向义务中心主义
以权利为中心建立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体系并非环境法发展中的偶然事件,而是环境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的习惯性选择。在法学理论中,权利一度被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属。权利本位思想认为,权利优于义务,义务来源于权利、从属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在法律领域中,一个人的义务总是以他人的权利为缘由”[1][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6页。,相应的,以义务为法的重心的义务中心主义则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是不以人为本的思想。梁慧星先生说:“没有个人,何来社会?故社会观念必自个人观念始,社会利益观念必自个人权利观念始,无个人权利观念之社会观念,不过是奴隶观念之别称。”[2]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页。
目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公共环境损害问题,其折射出的是以权利为主导的环境公共利益法律保护体系存在的天然缺陷,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有必要在环境公共利益领域建立以义务为主导的法律保护体系。从重视效率和结果的经济学领域孕育出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强调污染者在环境保护中的义务,蕴含着义务中心主义之思想,其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环境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迅速在环境法的土壤中成长发展,这种有悖于传统法学思想的现象,是否代表着义务中心主义才是有效解决公共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代表着环境法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从权利中心转向义务中心,从通过保护公民环境利益增进公共环境利益转向通过强调个人环境义务增进公共环境利益,义务中心主义的污染者负担原则之所以能够在环境法领域扎根生长,在理论上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其一,污染者负担原则提倡的义务中心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体现了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传统法律体系所遵循的权利中心以保护人权为最高宗旨,作为环境法的基本权利,公民环境权的具体内容包括通风权、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等有关健康和感观享受的权利。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公民环境权的前提,然而,实现公民环境权并不必然代表着生态系统将健康持续地运行,即保护当代人的环境权并不能保证后代人同样享有良好的健康的环境,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并不能保证整个生态系统能够健康持续地运行。污染者负担原则提倡的义务中心主义跳出了传统法学理论中保护人权的目标,要求所有从公共环境资源中获得利益,从而对公共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人承担相应的环境公共利益补偿或赔偿责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是通过规范当代人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其二,建立以义务为导向的法律体系是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要求。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公共利益”是一个内涵丰富、极难界定的法律概念,但其特点是极为明确的。公共利益具有消费上的不排他性和不可分性,消费主体具有不确定性,供给有一定的外部性特征。[1]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公共利益的特点决定了公共利益的维护难以通过个人或某个组织实现。环境利益是典型的公共利益,生态环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对这一体系产生影响,保护环境公共利益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其三,义务中心主义符合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特点。传统的以权利为导向的法律体系倾向以事后法律惩处产生的威慑效果来预防违法行为,而我国环境法制中一向存在着“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顽疾,环境污染惩罚的威慑效果非常有限,且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一旦遭到破坏,其后果通常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难以预计、难以挽回的,如果等到事后再处罚,往往为时已晚。污染者负担原则要求所有潜在的污染者承担预防污染、治理污染、生态损害补偿与赔偿的责任,既有助于防止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能够起到事后救济的作用,更符合生态环境以预防为主的保护特点,也更适合我国目前环境执法尚不完善的环境保护现状。
其四,义务中心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污染者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法律的效率价值。环境公共利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具有的利益多面性。对于不同公民或法人,环境利益的大小、形式各有不同。例如对企业而言,环境利益主要表现为经营性利益;对公民而言,环境利益主要表现为生存利益;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区域居住的公民而言,环境利益的大小又存在差异。环境公共利益的多面性需要一种灵活的利益分配机制来高效率地满足各主体的环境利益需求。以权利为导向的公共利益行政管理模式过于刻板,不适合分配环境公共利益,而污染者负担原则要求潜在的污染者将环境成本计算到生产成本、生活成本中,从而将环境成本带入市场运行机制中,由市场根据需求对环境利益进行灵活分配,国家行政机关则负责监管和引导环境市场的运行,这种环境市场的建立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高效分配,体现法律的效率价值。
最后,义务中心主义并非否定环境权在环境法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也并非否定政府的环境行政管理权。污染者负担原则所提倡的义务中心主义以环境保护义务为逻辑起点,通过要求污染者或潜在污染者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以实现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目的。权利和义务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公民环境权是污染者承担环境保护义务的前提,而政府的环境行政管理权则是适用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重要保障。
三、污染者负担原则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实践困境
污染者负担原则从义务中心主义角度为环境公共利益打造了从预防到赔偿的一系列保护措施,然而,生态环境损害特有的滞后性、累积性等特点,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新型环境污染问题,使得污染者负担原则在环境保护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污染预防方面,建设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市场机制困难重重。污染者负担原则要求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从而使环境成本进入市场流通。欧盟在2002年发布的《环境责任白皮书》中认为,建立环境成本的市场机制,既能够鼓励企业采取更多、更有效的环境预防措施,促进环保技术的发展,又能通过市场鼓励消费者减少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的消费力,从而减少污染。[1]Eric Thomas Larson,Why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Regim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European Community,and Japan Have Grown Synonymous With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38,2005,p.541.然而,我国企业的环境成本内在化从市场运行到政府监督都存在问题。1.企业不愿自觉地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中。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是建立环境资源市场的前提,然而,在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境执法宽松的背景下,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污染防治责任,偷排污染物的情况屡见不鲜。2.消费者有关绿色消费的观念淡薄。受社会文化、居民收入、教育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概念普遍比较淡薄。调查显示,超过54%的人们认为产品有无绿色标志对自己是否购买影响不大,而对如何辨别绿色产品,我国消费者同样缺乏相应的知识。[2]参见柳彦君《浅析我国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绿色消费的对策》,《商业研究》,2005年第2期,第161—162页。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企业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动力。3.政府监管不到位。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特征,无论是污染者的环境成本内在化过程,还是环境成本在市场中运行都需要严格的政府监管。我国环境保护机关从属于本级政府,在以地区生产总值为政府考量标准的大环境下,财政、人事都受制于当地政府的环境行政管理机构,很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樊笼,因此也就难以严格执法。
第二,在污染治理方面,常常出现公共环境污染无人治理,或者由政府代替污染者治理的情况。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政府使用公共资金用于污染防治,使公众既承担了环境污染的不利后果,又要承担环境修复和治理的财政负担。然而,实践中因为一些客观或主观因素,政府常常代替污染者承担公共环境治理责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无法确定污染者。生态环境污染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性,当环境污染后果出现时,往往距离污染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此公共环境污染经常出现找不到污染者的情况。二是污染者没有能力治理污染。公共环境污染通常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尤其是生态性损害,其昂贵的损害鉴定费用、环境修复费用对排污企业而言都可能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印染、造纸等高污染的小型企业而言,即使停产停业、变卖生产设备恐怕都难以支付一起环境污染事故的治理费用。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环境管理者,自然要承担环境修复和治理的责任,否则只能由公众承担环境质量恶化的后果。这种由于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的特殊性产生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适用困境,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加灵活地运用污染者负担原则。实践中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即污染者非常确定,但当地政府为了迅速平息事端,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在企业不积极守法时,自愿代替企业承担清除污染责任的情况,对这类问题,同样属于执法不严、守法不自觉的问题。
第三,在污染补偿方面,公众缺乏环境补偿的意识,有关补偿责任的具体规定也存在不足。由于我国立法中没有公民环境权的明确规定,公共环境资源长期无主的现状使得我国公民严重缺乏环境生态补偿的意识。环境污染者认为只要实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使用公共环境资源;公众和政府则认为只要没有侵犯个人身体健康权、财产权,污染者的合法排污行为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环境补偿意识的淡薄造成环境质量不断下降,而污染者却拒绝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同时,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目前尚不完善,对于污染者的环境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问题缺乏具体的立法规定,公共环境领域的污染者补偿责任机制始终无法建立。
第四,在污染损害赔偿方面,公共环境损害索赔主体缺失,损害赔偿额无法完全弥补实际造成的环境生态损害。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而对于造成公共环境污染危害的情况,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污染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赔偿对象。从外国环境保护立法来看,公共环境损害的索赔主体通常是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或者行政机关。由于我国诉讼法将诉讼主体资格局限于利益相关人,因此环境公共利益损害长期面临无人索赔的状况。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尝试性地开展环境公益诉讼,2012年民诉法修改也增加了公益诉讼条款,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亟须进一步明确。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主要采用行政机关与污染者协商的方式要求污染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1]例如,2011年康菲石油泄露事故造成我国大面积海域受到污染,渔业资源受到严重损害,2012年4月,农业部与中海油、康菲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对污染造成的环境生态损害与渔业资源损失赔偿10亿元人民币,该协议一经公布立刻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认为10亿元远不能补偿事故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实际损害。参见《康菲石油10亿“中国式赔偿”迷雾待解》,登载于国际能源网,网址: http://www.in-en.com/finance/html/energy_09190919181269230.html访问时间:2013年12月30日。。然而,这种协商索赔的方式缺乏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程序,损害赔偿额难以真正弥补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实际损害,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反映出我国在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赔偿领域的立法缺失。除此之外,由于环境污染的累积性、污染物在环境要素中的流动性,公共环境损害赔偿中还存在着因果关系证明难、损害鉴定难、损害赔偿周期长等问题,使得公共环境污染损害难以及时得到救济。
四、污染者负担原则实践困境之破解
公共环境污染的特殊性、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环境执法不力共同造成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在环境公共利益保护实践中的困境。为了充分发挥污染者负担原则在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中的作用,有必要参考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国际社会的新发展、新动态,对我国现行污染者负担原则进行更新完善,建立从原则到制度的环境公共利益法律保护体系。
(一)立法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
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目前采用间接立法的模式,由学者对环境立法中零散的原则性规定归纳总结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也是我国环境法学者归纳出的环境法基本原则之一。在我国环境立法中暂没有“污染者负担”的表述方式,仅对污染者的责任有一系列的原则性规定,如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1989年《环境保护法》将其更新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还规定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环境责任原则,其中“污染者付费”就是对国际社会“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直译。
无论是“污染者治理”还是“污染者付费”都无法涵盖“污染者负担”所包含的环境责任的内容。“污染者治理”仅限于污染的治理,排除了污染的预防、补偿和赔偿责任;“污染者付费”只强调对污染者的经济惩罚,似乎只要付费就可以污染,忽视了污染者的公共环境保护的义务。国际社会对“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解读也不仅限于“付费”,而是包括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所有行为和措施。鉴于此,我国环境法学者在总结我国环境法基本原则时通常使用“污染者负担”原则,较少使用“污染者付费”或“污染者治理”原则。[1]参见李挚萍、叶媛博《我国环境基本法中基本原则的立法探析》,《政法论丛》2013年第5期,第57—63页。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严峻的环境污染状况、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和执法的不足急需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环境责任法律体系。“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它指导和协调着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2]张文显:《规则·原则·概念——论法的模式》,《现代法学》1989年第3期,第28页。污染者负担原则具有我国现行立法中“污染者付费”“污染者治理”原则所不具有的全面性,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内环境法学者的一致认可,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目前,我国具有环境基本法地位的《环境保护法》正在修改之中,可利用这一契机,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污染者负担原则。
(二)立法明确公民环境权
权利和义务是相伴相生的概念,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公民环境权,立法明确公民环境权是污染者负担原则成立的前提,也是污染者负担原则突破实践困境的重要动力。
首先,公民环境权的内容是明确污染者负担内容的基础。公民环境权在实体法上的内容是污染者承担相应环境保护义务、建立环境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例如清洁空气权所要求的空气质量标准是污染者废气排放标准的计算基础,清洁水权所要求的水环境质量标准是污染者废水排放标准的计算基础,风景权对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是污染者维持当地环境质量标准需要提供多少补偿的计算基础。
其次,确立公民环境权能够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公民环境权在程序法上的内容是公民监督政府环境行政执法、监督企业环境守法的主要法律依据,例如公民环境权中的环境知情权要求政府和企业公开有关公共环境的信息;公民环境权中的公众参与权允许公众参与影响公共环境利益的决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实践中防止环境成本外部化,走出污染预防困境的重要监督措施。
最后,公民环境权能够培养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环境保护。一方面,公民环境权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只有立法明确了公民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公众既是环境保护的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立法明确公民环境权才能够使公民认识到自身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当公共环境安全受到威胁时,能够为维护自身权益主动承担相应的环境保护义务。培养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能够促进绿色消费、公益诉讼等一系列环境公共利益保护制度的完善和实施,有助于公共环境污染预防和污染损害赔偿。
(三)对“污染者”进行扩大解释
“经合组织”对“污染者”的最初定义为“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人”,然而,生态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危害结果滞后、鉴定周期长、损害赔偿额高等特点常常导致污染发生后污染者不可知、污染者已停产关闭或者污染者无法承担治理或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为了避免公共环境污染后果无人担责或由政府担责的状况出现,各国遵循扩大“污染者”范围的思路对污染者负担原则进行了新的解读。
美国1980年通过的《超级基金法》针对土地污染者建立了“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无论潜在的污染者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地污染,也无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污染者都必须为污染场地负责。德国、日本则直接将污染者负担原则改为“原因者负担原则”“受益者负担原则”,“原因者”的范围不仅包括污染行为人,还包括污染项目的决策者。“受益者”不仅包括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者,还包括产品的消费者。对污染者负担原则“更名”的做法也得到了我国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支持。[1]参见陈艳艳、周国模、田信桥《气候变化背景下污染者负担原则的适用》,《生态经济》2011年第11期,第69—71页。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补充性规定扩大“污染者”的主体范围。如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在污染者负担原则之外规定了“污染者法定继承人责任原则”、“污染者清算破产情形下的环境责任原则”及“政府辅助责任原则”,[2]塞尔维亚《环境保护法》(2004)第9条第5项、第8项。用以处理污染者不可知、污染者破产关闭等情形下公共环境的治理。
为了摆脱污染无人治理的困境,我国污染者负担原则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扩大“污染者”主体范围。由于“污染者负担”是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环境法原则,也是我国学者长期以来总结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考虑到原则的稳定性和连贯性,笔者认为不宜采用“更名”的方式扩大污染者负担原则主体,而是可以参考美国、塞尔维亚等国的做法,在具体立法中增设“原因者”以及污染实际“受益人”的公共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合理扩大污染治理者的主体范围。
(四)创新污染者的责任承担方式
长期以来,污染者责任承担方式都是建立在“环境不得被污染,否则就要承担相应责任”这一前提之下的,针对我国污染者负担原则适用过程中面临的污染者不积极承担相应污染预防责任、合法排污后不积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以及造成污染损害后赔偿额无法弥补实际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况,应当跳出“污染才要担责”的思维模式,根据实际问题灵活适用污染者负担原则,创新污染者责任承担方式。
首先,对污染环境者征税,对不污染环境者提供奖励,鼓励污染者主动采取污染防治措施。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污染者作为“经济人”的主要目标,激励污染者承担公共环境保护责任要遵循污染企业的本性,通过经济手段调节污染行为。征收环境税是各国常用的环境经济调节政策,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我国目前采用的排污收费政策是一种不规范的准税性质的收费,改“费”为“税”能够更充分发挥税收在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中的作用。除征收环境税外,对绿色企业或产品进行财政补贴也是促进污染者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激励措施之一,例如美国、加拿大在农业污染防治中的“交叉合规措施”(Cross-Compliance),交叉适用“污染者负担”和“提供者补给”,对那些遵守良好生产活动、提高了环境利益的人由政府提供补偿;而对那些采取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活动的人,则需要为造成某种特定的环境污染行为承担治理责任,同时禁止申请政府的农业补贴。[1]Margaret Rosso Grossman,Agriculture and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An Introduction,Oklahoma Law Review,Vol.59,2006,pp.48—50.
其次,要求污染者对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污染提前进行补偿。对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大型项目,可以在项目开始建设前启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要求项目方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环境影响、降低环境风险的同时,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支付一定金额的补偿金。这种事前补偿措施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所实践,例如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针对大型项目可能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2008年就惠州大亚湾华德石化有限公司航道码头工程和广州出海航道三期工程的生态补偿问题,分别协议补偿600万元和650万元;2009年先后就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工程东莞段海洋生态损失补偿、鉴江口上剑利沙海砂开采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湛江港调顺岛港区300号泊位技术改造等项目达成补偿协议,取得了良好的环境生态补偿效果。
最后,建立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救济机制。传统损害救济机制要求损害者赔偿,然而生态环境污染损害的特殊性使得仅仅依靠“损害者”难以负担环境生态损害后果。建立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救济机制是充分救济公共环境损害的有效措施。例如建立环境损害强制责任保险机制,将分散的污染者所缴纳的环境保险费集中起来,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将排污费、环境税或企业捐赠的环境保护资金汇集为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由独立机构对资金进行监管,当发生公共环境损害时及时救济公共环境利益。
五、结语
我国公共环境目前正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雾霆天气、土壤重金属污染、地下水污染等严峻的污染状况已经切实影响到了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水平。强调义务中心主义的污染者负担原则从公平、正义、效率的法律价值出发,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公共环境污染防治设置了预防、补偿、治理和赔偿的法律责任体系,对保护公共环境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我们也可以在参考国外先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新的解读,更加灵活地适用污染者负担原则。相信随着立法的完善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将在公共环境保护领域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初审:王欢欢)
[1] 作者叶媛博,女,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环境资源保护法学,E-mail:yeyuanbo87@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