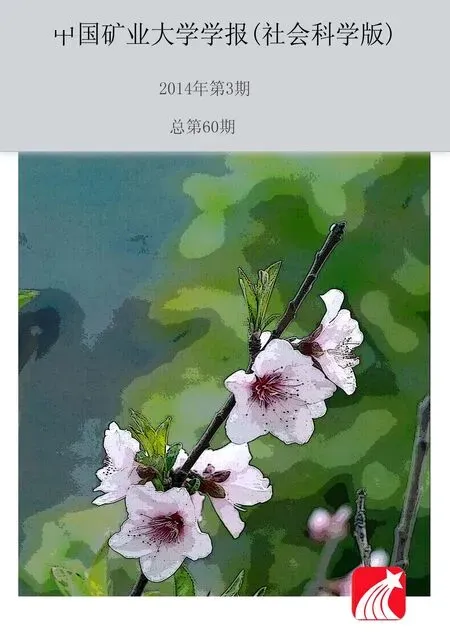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许屹山
(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伦理学家,是一位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海内名儒”。正如近代湖南著名学者李肖聃先生在《杨怀中先生遗事》一书中说的那样:“怀中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先儒之书,十余年中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则友朋皆莫及也。”[1]379-380另一湖南学者曹典球先生在《杨昌济先生传》中也指出:“先生经戊戌政变之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1]384毛泽东认为“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2]12-13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3]121-122
从目前公开刊行的《达化斋日记》和《杨昌济文集》二书来看,杨昌济对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佛学都进行过长期专门系统的研究,由于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下工夫研究得最深的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对此,杨昌济曾经指出:“思者作圣之功也,圣无不通,无不通由于通微……王船山通微……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应天下之万变而不穷于用。”[1]25可以看出,杨昌济认为王夫之是圣无不通的伟大哲学家,他不仅对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做了全盘系统的研究,而且运用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来诠释、通融西方哲学,并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1]16的宝贵思想,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本体论”、“认识论”、“造命论”、“动静观”等核心内容,他希望藉此创立一种新的“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来构筑起一个能够指导全民族的新的哲学体系。虽然这一工作只是刚刚开始,却为后人特别是为其高足青年毛泽东等人继续完成这一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借鉴和新的思想起点。
一、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
湖湘文化发源于宋明道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本体论上,杨昌济早年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认为世界的本源与支配者是无所不在的“天理”,即“无往而非天理,天理无外,何逾之有?”[4]14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观”,支配了杨昌济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后来他留学英国时,进一步受到了西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更加坚定了原来的“天理”本体论的思想。为此,他曾进一步指出:“中国之宋儒承佛教之思想以补救儒教哲学者也,其理气之说,亦实达于此阶段。彼等以太极为万有究竟之大元,谓气自太极之动静而成,而阴阳二气之所以一动一静相交错,则理也,理不能离气而存,气亦不能离理而存。气本自太极而生,故阴阳亦一太极,离太极更无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成万物,万物皆阴阳之所合而成也,有气则有理,理即寓乎万物之中,一一之万有固皆为一太极也。”[1]303在这里,可以看到杨昌济对王夫之哲学中“理在气中”(理即寓于万物之中)、“气先理后”(有气则有理)的唯物主义“理气观”的吸收,已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如果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杨昌济可以由此而进一步走向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他又引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对理作了唯心主义的规定和解释,他继续指出:“在泰西哲学之历史,黑智儿(即黑格尔)之思想亦能表显之,彼以理为万有之本体,此理发显,遂成诸种之现象。当吾人思维观察之之时,若自其最单纯者始,则可知理自‘有’经诸种之阶段,渐进于高尚复杂之域,终至‘绝对理’而止,彼所显之面虽多,然莫非理也,理于最初但为纯粹之有之时,其本质毫无所减,即至为最后之绝对理,其本质毫无所增。”[1]303可以看出,杨昌济把中国哲学“世界本体论”中的“理”解释为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绝对观念”(绝对理),将二者等同起来,从而背离了王夫之以“气”为“世界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原则,从而滑向了客观唯心主义泥潭。
二、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
杨昌济对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高度欣赏,并用它来丰富和发挥中国古典哲学,他曾指出:“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陆象山曰:‘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近世伦理学家,多主张自我实现说,所谓自我者,大我也,以宇宙为一体之大我也。”[1]49对什么是“自我实现”呢?杨昌济运用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作了崭新的诠释:“充实自我具有发达的可能性,谓之实现自我,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谓之自我实现主义。”[1]268杨昌济还认为,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亦皆有此见解”。[1]268同时,他在研究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对此有更加深刻地体会和发挥:“王夫之《诗广传》曰:‘或曰,圣人无我,吾不知其奚以云无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必狭其有我之区,超然上之而用天,夷然忘之而用物,则是有道而无德,有功效而无性情矣。苟无德,不必圣人而道固不丧于天下也,苟无性情循物以为功效,而其于物亦犹飘风雨之相加也。呜呼!言圣人而亡实,则且以圣人为天地之应迹,而人道废矣。’船山亦主张人本主义者也,其言道与德之区别,即客观与主观之别也,近世伦理学家言‘自我实现’说,与船山之论暗合。”[1]83-84可以看出,王夫之的这段话高度肯定了人为功于天地的主体作用,批判了所谓“圣人无我”论的实质是“狭其有我之区”,即限制人的主体作用的范围,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王夫之则指出了世界的客观规律——“道”与人的认识或思维规律——“德”的联系和区别,即“道”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而“德”既是人对客观之“道”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又体现了人为功于天地的巨大能动作用。杨昌济引进西方哲学中的“主观”与“客观”这对范畴,正确地指出了王夫之“言道与德之区别,即客观与主观之别也”,第一次把主观与客观的概念引进了王夫之哲学的研究中,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亦有重大的启发作用。
此外,杨昌济指出的“近世伦理学家言自我实现说,与船山之论暗合”, 这也说明他正确地看到了王夫之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高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夫之强调人能“造命”、“竭天”,既指出了客观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又指出了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具有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动作用,杨昌济把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与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指出:“以人言人,自当立人之道,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亦不与天地同不忧,故曰立命,曰造命,人为天地所生,而反以为功于天地,故尽人事者人之责任也。赫胥黎《天演论》谓人治常与天行抗,庭园修饰,人治之功也;草木荒芜,天行之状也,人治稍懈,则天行逞其势力,故人生者不断之竞争也。近人以达尔文倡进化论,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遂以主张自我争权攘利为人道之当然,此不知立人之道之义者也,生存竞争,本生物界大行之原则,然人类所造出之宗教、政治、道德,则以合群为教,欲以减杀人生剧烈竞争之苦痛,是亦人治与天行抗之一事也。”[1]83-84可以看出,杨昌济的这些论述充分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同时也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规律引进了人类社会,这并不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三、引进培根哲学中的“实验科学”,改造王夫之哲学中的“知行观”
在认识论方面,杨昌济对王夫之哲学中的知行观理解得最深刻,也阐发得最为精彩,他在其日记中大量地摘引了王夫之论述知行关系的语录:“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曰:‘知善知恶是知,而善恶有在物者……’又曰:天下之物无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复拘于量。颜子闻一知十,格—而致十也;子贡闻一知二,格—而致二也。必待格尽天下之物而后尽知万事之理,既必不可得之数……则格物、致知亦自为二,而不可偏废矣。”[4] 45这一大段精彩的关于认识论的论述,深刻说明了世界的无限性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个人直接经验的有限性与整个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此外,杨昌济还初步分析了人类认识过程中“格物”与“致知”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4] 45-46可以看出,杨昌济引用王夫之的论述既批判了朱熹只重学问而不重思辨的片面性,又批判了王阳明只重思辨而不重学问的片面性,并赞赏了王夫之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看成是认识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中的知行观,杨昌济对此全文抄录,足见他对这段话尤为重视。
杨昌济还进一步引进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实验科学,来重新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知行观,他指出:“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辨格物致知之义甚详……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4]26-27杨昌济认为,与欧美先进各国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治物之学”,即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中国应该下大气力培育培根所开创的独立科学研究的精神。对于此,连马克思也曾经指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5]503事实也是如此,培根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热心提倡自然科学,奋起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为了扫除发展科学的思想障碍,他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培根还着重考察了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这使他成为欧洲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和科学归纳法的奠基人。
杨昌济从思维方法上来探究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缺乏培根那种实验科学精神与科学归纳方法,杨昌济又指出:“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盖与我国科举时代专读经书相同,后培根等起,倡自由研究之学风,不置重于古代语之学习而且重于近世语之学习,不贵求知识于书籍而贵求知识于事物,不倚赖古人传说而倚赖自己之考察”。[1]54这些都促进了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杨昌济把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引进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学说,把王夫之哲学中的知行观发展为既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包括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物质文明的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活动,这是对以王夫之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知行观的重大发展。
杨昌济还把培根的实验科学引进中国古典哲学,并运用西方的逻辑方法,来阐发中国古典哲学,他指出:“穷理有二法:一为归纳法,一为演绎法,归纳法合散而知总,演绎法由总而知散。子贡之多学而识,其功夫近于归纳法,夫子‘一以贯之’,其所用者则演绎法也,欲理解宇宙之现象,不可不用科学的研究,欲体认宇宙之本体,不可不赖哲学的思考。”[1]86可以看出,“合散而知总”,即由个别到一般;“由总而知散”,即由一般到个别,杨昌济济认为只有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认识世界宇宙的各种现象和规律,这进一步克服了培根只重归纳而轻视演绎的思想局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知行观引进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
四、引进牛顿力学,阐释王夫之辩证法中的“动静观”
在王夫之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动静观占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例如,王夫之认为:“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6] 1044这指出了运动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根本属性,他还提出了“静者静动,非不动也”[7]411、“静即含动,动不舍静”[7]430-431的精辟命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此,近代弘扬湖湘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谭嗣同,同时也是杨昌济的挚友,也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发挥,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天行健,自动也”[8]36的命题。
对王夫之的动静观,杨昌济也给予了新的解释,他指出:“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物之静止者,非加以外力则永永静止而不能动;物之运动者,非摄以外力则永永运动而不能静。”[4]161可以看出,杨昌济运用牛顿机械力学的惯性定律,来解释王夫之哲学动静观中的个别结论,从而作出了事物有“永永运动”与“永永静止”两种状态的论断,并把这种绝对运动与绝对静止的原因归之于外力,这就把王夫之充满辩证法的动静观作了形而上学的解释,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而王夫之的阐释是:“太虚者,本动者也”,这种运动的源泉是事物内部阴阳对立统一的作用:“盖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7]23而静止只是运动的某种特殊形式:“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7]36可见,杨昌济并没有完全领会王夫之动静观的辩证法实质,但他把牛顿力学引进中国哲学中的动静观当中,毕竟这是一种宝贵的探索,表明他自觉地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并试图把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以提高哲学的精确度。
此外,杨昌济还吸收了牛顿力学第二定律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永远不会抵消的思想,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见解,也有积极意义。他曾经指出:“有原动力,有反动力,原动力生反动力,反动力又生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此天演自然之用也;有原动力,则必有反动力,原动力大,则反动力亦大。前知其必反,必动而无惧,是谓先天;当其势之再反也,必动而无惧,是谓后天,务为原动力者,可谓志士矣。”[1] 311杨昌济把原动力与反动力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矛盾统一,“反反相衔,动动不已”的过程,已经具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他进而号召人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更是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他在修身课中,不但向自己的学生(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讲述了这一思想,而且还提炼为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验学生:“有原动力则必有反动力,原动力大则反动力亦大,试举社会事例以证明之。”[4]120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充分吸收和发挥了杨昌济的这一思想:“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2]160
五、通过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
杨昌济不仅注意比较、分析中国古典哲学与欧洲哲学,而且也十分注意比较、分析中国古典哲学与印度哲学,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最终达到改造和发展中国古典哲学之目的,也备受称道。他在研究中印哲学之异同时曾经指出:“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有不同之处:印度思想于理论的探究穿微钩玄,中国思想则惟明其大体而已;印度思想考究之对象次第趋于经验以外,中国思想大率止于经验以内;印度思想明宗教的大纲,中国思想详伦理的细目;印度思想为出世间的、为超绝的、为伦理的、为哲学的、为宗教的、为空想的、为理论的;中国思想为世间的、为经验的、为常识的、为政治的、为伦理的、为观察的、实际的。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又有其相同之处:—、重标准而轻说明;二、重道德而轻科学,三、讲纯正哲学,亦为伦理的;四、论宇宙之第一要义,亦为伦理的。”[4]50-51正因为看到中印哲学各有长短,各有特点,所以杨昌济对于作为印度哲学之一的佛学思想,并不因为它是宗教而盲目加以排斥,而是十分注意吸取其中的思想精华,以丰富和发展中国古典哲学思想。
此外,杨昌济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了佛(释)学大乘与小乘两大流派之异同,例如,他对佛教两大派别通义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之通义有六:“一、唯心的倾向;二、厌世的倾向;三、断惑;四、涅槃;五、轮回;六、伦理的倾向。”[4]50-51同时,杨昌济对其挚友谭嗣同重视佛学,融合儒佛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在其日记中大段记录了谭嗣同融合儒佛的语录:“重读谭浏阳《仁学》,抄其精要者于此……又曰:天下治也,则一切众生,普遍成佛,不惟无教主,乃至无教;不惟无君主,乃至无民主;不惟浑一地球,乃至无地球;不惟统天,乃至无天;夫然后至矣尽矣,蔑以加矣。”[4]42
杨昌济在其日记中又指出:“吾闻某某之讲《大学》,《大学》盖《唯识》之宗也,《唯识》之前五识,无能独也,必先转第八识;第八识无能自转也,必先转第七识:第七识无能邃转也,必先转第六识;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谓知意识转然后执识可转,故曰:‘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借乎格物;格物致知者万事之母,孔曰:‘下学而上达也’,朱紫阳《补格致传》,实用《华严》之五教……且夫《大学》又与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诚意正心修身,理事无碍法界也;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事无碍法界也,夫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4] 42通过以上杨昌济引用谭嗣同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谭嗣同吸收佛教“一切众生普遍成佛”的思想,来论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的合理性;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八识”对人们认识过程的精细描述,来阐发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知行观。同时,谭嗣同也正确看到了自佛学传入中国之后,儒佛逐渐互相融合的一面,并为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4]45对此,杨昌济给予了高度评价:“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上述所钞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4]45这足以说明正是谭嗣同上述思想直接影响到杨昌济,使杨昌济改变了对佛学的看法,并认识到佛学在中国古典哲学上的重要价值。
此外,谭嗣同不仅吸收了佛教“灵魂不灭”的思想,而且吸收了王夫之哲学中物质不灭的思想,他指出:“第一当知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谓死者,躯壳变化耳;性灵无可死也,且躯壳之质料,亦分毫不失。西人以蜡烛譬之,既焚完后,若以化学法收其放焚之炭气、氧气与蜡泪蜡煤等,仍与原蜡烛等重,毫无损失,何况人为至灵乎?”[8] 321杨昌济既接受了王夫之哲学物质不灭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谭嗣同灵魂不灭的思想,并加以综合地发挥:“事物之生也非自无而有,事物之灭也非自有而无,皆有所以使之生灭者,惟姑变其形而已。现象虽时时变化,物质固不增不减,势力亦常住不灭……吾人于是乎知本体之决不可无,吾人感觉、知觉之所得知者不过此等本体发显之状况而已,是故吾人所感之状态无论如何变化,彼等之本体固始终不变者也。”[1] 311杨昌济当时无疑早已了解西方哲学中物质不灭思想,但从这段论述来看,其思想却更多地是来自王夫之哲学中的思想,王夫之以“车薪之火、一烈已尽”的实验事实,生动地论证了“气”只有“往来”、“屈伸”、“聚散”、“幽明”的变化,即不断地从一种物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物质形态,“其本体不为之损益”[7]17的物质不灭思想。而杨昌济所说的“物质固不增不减”、“本体固始终不变者也”,[1] 311不仅与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一致,连使用的术语也很雷同,但同时杨昌济又吸收了谭嗣同哲学中的“灵魂不灭”的思想,在此基础之上还提出了“势力亦常住不灭”的思想,“势力不灭”也就是“灵魂不灭”。他在《告学生》一文中进一步作出了发挥:“物质不灭,势力不灭,独患尤诚耳,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28这里把“势力”与“物质”并立,这个“势力”显然是指精神、意志、思想、灵魂等,这也就是谭嗣同在《广学》一文中所鼓吹的“心力”说:“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8]74这种“心力说”,也被杨昌济全部接受。
杨昌济对谭嗣同特别鼓吹佛教那种“灵魂不灭”、“三界惟心”的主观精神力量来鼓舞斗志,并通过“普度众生”的方法来救国救民的构想,也表示了高度赞叹与向往,他曾指出:“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其序言网罗重重,与虚空无极,人初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次须冲决天之罗网,终须冲决佛教之罗网。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万倍。开篇言以太能显出宇宙之全体,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阳,自太阳而昂星,自昂星以及无限之世界,皆互相维系,终古如斯,无非以太之力。”[4] 165
杨昌济不仅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中进行融合东西文化、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工作,而且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灌输东西结合的哲学思想方法,使学生树立新的哲学信仰,掌握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思想武器,也值得称道。例如,他在1914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有:“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尔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熹)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尔: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变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致知注意之事也。”[4]26这足以说明,杨昌济不仅在其学术著作中,而且在其课堂教学中,时时处处注意中西哲学的融汇贯通,充分吸收中西各家学说的思想精华,既看到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又看到他们之间的异中之同,广汇百家,取精用宏。
综上所述,杨昌济提出的“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与主张,并把指导思想信仰的哲学融合与重建工作摆在第一位的主张,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进步青年才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青年毛泽东为例,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就树立从大本大源入手改造中国哲学、伦理学的宏伟志愿,那时的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73在此基础之上,青年毛泽东形成了“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他还具体提出了东西方思想文化必须同时融合与改造的主张,也是直接渊源于其业师杨昌济的教诲和影响,如同他指出的那样:“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73这是对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的吸收与充分发挥。
毋庸讳言,杨昌济提出的“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并没有给予他像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陈独秀等人“思想界明星”的崇高声誉,但是却被他的高足毛泽东所继承和发展,在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转变之后,这些都成为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思想文化源泉之一,这些都是杨昌济生前所未曾预料到的,但思想的光芒就在于它的历史渗透性,在某一时代名不经传的思想,却能成为后世的金科玉律,这似乎是历史的悖论,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肖聃.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4]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7]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8] 谭嗣同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