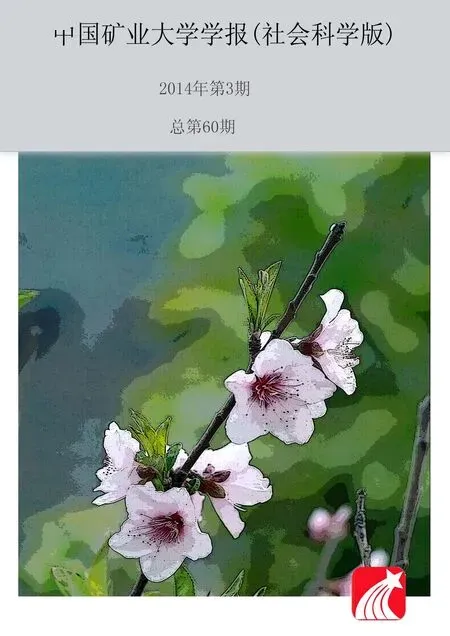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初次探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本解读的四重维度
唐 永,徐 军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中学时期的马克思怀抱理性进化论,成长在十九世纪初德意志这块“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当时的德国属于少数例外”[1] 28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2]63之中,从开始对黑格尔的痴迷追崇,继之不断清算批判,接着在辩证超越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坚定地站在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上,最终完成了革命思路和意识形态的两次飞跃。作为马克思早期探索的理论结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虽然“使用了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或依旧是黑格尔的表述”[2]42,虽然文中涉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尚显不成熟、不成体系,但已深深地打上了唯物主义的色彩,预示着一个必然撼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即将启程。
刚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马克思,因主编《莱茵报》的职业需要广泛地接触到资本主义现实,也不可避免地涉足“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然而,当时大行于世的英法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并不能对此给予合理的答案。加之德国现实与德国哲学的巨大反差激发了他强烈的问题意识,促使马克思将他“从社会退回书斋”的理论研究成果《克罗茨纳赫笔记》等与观察德法工人运动的实践成果整合,凝炼成《导言》。此文主要围绕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展开论述,在吸收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德国现实的滞后性,进而提出德国革命历史进程三重解放的科学论断。
一、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分析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4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赋予哲学的新历史使命,从青年黑格尔派将政治批判归结为宗教批判的批判路径中跳了出来,把搏斗式的批判矛头直指德国现实。他指出“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3]7并号召猛烈地向“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结合”[3]13成的怪胎普鲁士专制开火,把实实在在的革命引入德国滞后的现实,从而开辟了将宗教批判转为政治批判再到社会批判的批判路径,从而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开辟了现实路径。“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3]6
回溯《导言》写作的19世纪40年代,当英法美等国已乘着工业革命的羽翼飞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快速发展之门时,德国刚刚遭受由法国大革命继之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巨大动荡,被打上了不能实现民族统一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烙印,而德国软弱的资本家只能残喘于死灰复燃的普鲁士复辟王权的幽灵之下亦步亦趋。在这场时代错乱的滑稽剧中,德国人面对的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3]4,面对的是视农民捡枯枝为犯罪、否定新闻出版自由的普鲁士政府,面对的是德国四分五裂的疆土和民族意志。因此,“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3]8。它没有和现代各国在同一时间节点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而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态,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首先必须补习民主这一课。
与滞后的政治同卵双生的是滞后的经济,专制王权和分崩离析的封建割据严重捆绑了德国资本家急切想要伸展的手脚。“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3]8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让他们在面对强势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总是唯唯诺诺,他们虽然也想建立英法美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却又如此害怕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会砸掉自己的饭碗,因而根本不具备领导人类解放的能力。
与德国政治经济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民族过分发达的理性头脑。与接地气的法国人的政治头脑和英国人的经济头脑不同,德国那些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巨子却囿于思辨哲学的藩篱之中,即使是振聋发聩的费尔巴哈也只是抱着一本《基督教的本质》沉溺在抽象的博爱之中。而青年马克思却在《莱茵报》被查封等残酷事实的教育下,以英法两国为实践参照将批判视野开阔到德国现实,提出必须把宗教批判扩展到政治领域,将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人间。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批判德国现实的“副本”和“抽象继续”——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以继续清算保守主义,弥合德国“思维的抽象和自大”与“现实的片面和低下”[5]9之间巨大的裂隙,为唯物史观的形成进一步扫清思想障碍。
二、德国革命的解放主题
1843年,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单纯地划归为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拿起批判的武器,激愤地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在剖析鲍威尔思想理路的基础上,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直捣其错误思想的内核。在《导言》中,马克思把鲍威尔含糊的宗教解放一分为三,梳理出德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应然逻辑,即由宗教解放向政治解放进而向人类解放的递进跃迁。
当西方从漫长的中世纪的坚冰中解冻,基督教世界驶入“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3]3的大语境之下,昔日不可一世的宗教原来只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抽象实现,只是对现实苦难的表现和抗议。马克思继承了贯穿《基督教的本质》中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维度,认为革命的第一道工序不是依旧戴上宗教这条失去幻想和慰藉魔力的锁链,而是砸碎宗教之于人的异化,从而将德国革命的逻辑起点定格在对宗教的批判,而这一切都必须诉诸于人的现实理性。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宗教的胜利不是革命的完成,只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4天国的真理被打倒之后,革命进程自然过渡到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3]44,即筑基于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此外,对个人而言,一方面“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3]46可是,正如个人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一样,人类也并没有走入自由的幸福的国度,“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恰恰就在它对现实生活领域存在的差异和压迫的放任,并以之为前提”[4]38。政治解放之后的民主国家,实质上仍是私有制的维护者,恰恰剥夺了多数人的权力,且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滋生了两极分化、利己主义和金钱崇拜等社会痼疾,因而必须向人类解放深化。在这里,马克思没有停留于黑格尔对政治解放陶醉的鼓吹之中,而是将眼光深入到政治解放的深层矛盾,从而开辟出崭新的革命路径。如果说在《论犹太人的问题》里马克思是通过对宗教残余与世俗基础的头足倒立的方式,那么在《导言》里则是通过革命的新力量——无产阶级——的发现,完成了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深化。
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为依托,将他的离群索居、拥抱自然而疏离于政治、社会问题转为积极地介入现实,突破了黑格尔的“国家”范畴,将“社会”作为理论视野的着眼点,高喊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界定了德国的解放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3]11。这是消除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的实践,是人本质的完全复归。这也是对普遍的不公正的彻底革命,是摧毁一切奴役制度的理性探索。为了夺取人类解放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文尾开出一剂药方——“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18,从而在心脏与头脑的协同并用中,完结了德国革命进程三重解放的逻辑论述。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写作《导言》时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思想范式,虽然还时不时挪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术语,虽然涉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待理论与实践锻造,然而,马克思这一阶段一直秉承着为全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哲学人类学视野与批判立场,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源于启蒙理性和无神论思想的政治批判的局限性,借助德法工人运动的跳板敏感地发现了这群沉默的大多数的革命伟力,进而认识到了德国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对此,马克思做了“带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黑格尔思辨哲学”[5]16痕迹的回答: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3]16-17
这个阶级是“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公开的奴役者阶级”,遭受着普遍的苦难和不公正,因而它没有属于本阶级特殊的权利,因而能够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从而激起革命的狂潮。马克思致力于对现实的揭露使他们大吃一惊,“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3]6-7,进而使他们觉醒出巨大的革命勇气,翻身砸碎私有制等一切人性的锁链。这要求无产阶级超越个体、民族乃至国家,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人类历史主体意识,在赢得自身解放的同时也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18
德国无产阶级,只有以哲学武装头脑,联合起来形成革命洪流,彻底废除一切奴役制,在消灭血腥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消灭自身,实现无奴役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时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科学的,还是哲学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基础上”[6]81,打上了马克思理论成长时期的鲜明烙印。
四、三重理论逻辑视野的融合
如果说“德国现实的滞后性”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德国革命进程的三重解放”回答的是“怎么办”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那么马克思写作《导言》时渗透的研究视角则通过穿针引线,将文本主要论述的三个基本内容很好地贯穿了起来,把看似杂乱无章的批判式行文框定在思维理性的逻辑脉络之中。概括来说,《导言》主要贯穿三重视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成果,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已经开始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术语、范畴和研究视角。
首先,《导言》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深化。这种深化建立在马克思正在萌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坐标之上,主要体现在对四个基本问题的阐释之中:宗教异化根源于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经济异化在全部异化现象中的决定性意义、人类解放高于政治解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导言》作为马克思短暂停留于民主主义并迅速转为共产主义的理论表征,通过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之间分离的具体历史考察,探索出消除这种二元对立和根本改造社会的三重解放的革命道路。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虽然还受到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辩证法的影响,但已开始逐渐跳出黑格尔思想范式的魔爪,为以后对他的辩证扬弃和综合超越奠定了基础。
其次,马克思直接使用或者化用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范畴和思想,虽然无意识中已有所突破,但仍明显受制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架构之中。一方面,在“现实的人”、“人的高度”、“人的本质”、“人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完全回复”等范畴和思想背后,不难看出当时马克思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思想直接粘连。另一方面,马克思虽然在探讨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的问题时,科学预见了德国革命“三步走”的历史进程,并历史性地发现了无产阶级之中深藏的革命伟力。但是,“他仍然按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方式,把工商业活动看成是受利己主义需要支配的人的自我异化活动。因此,尽管他力图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把政治批判变为经济批判,但仍然停留在法权和财产权领域,仍然是借助于人的理想的类本质对这一领域异化现象进行外在的伦理批判”[7]55。此外,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批判的范式的影响,即主谓颠倒。如他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颠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小小的文字游戏,却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巨大的分野。马克思也承认,费尔巴哈“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可见,这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对马克思思维的压迫如此深重,尚有待之后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积淀,才能最终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萌芽。之所以称之为萌芽,主要是因为论文中只是政治经济学术语、范畴和研究视角的开始出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系统性架构,如他对德国现实的批判,更多地是从宗教法律政治等角度切入等。主编《莱茵报》时的马克思,迫于“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难题并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以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思想为跳板,开始涉足政治经济学这块丰腴的哲学处女地,而不是“扭过头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3]10。比如对“低于历史水平”的德国制度的睿智地嘲讽,号召将其送进坟墓;比如揭示了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摇身一变成了爱国志士的荒唐;比如挖掘林木盗窃法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本质;比如用工业运动解释无产阶级赤贫的原因;比如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论文各个角落,成为论文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虽然就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很多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而且当时马克思给出的答案也并不完善,但是此时的马克思毕竟已经稳稳地扎根在现实这块结实的土地之上。
可见,写作《导言》时的马克思,虽然慢慢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阴翳中逃离,虽然“已经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门户”[7]56,却还没有完成新世界观的系统确立。
“哲学家也有自己的青年时代”[2]49,《导言》作为马克思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产物,虽然尚显幼稚,并有一些缺憾与不足,但是,马克思的主张“使哲学成为意志,使哲学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2] 51就肇端于此,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哲学共产主义也将被科学共产主义所置换,人类的历史也将因此而改写。正如印度诗哲所言:“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虐待者的胜利”[8]38,马克思也一定在等待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会不会也仿照阿基米德说一句:“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撼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 刘增明.论马克思对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的批判和重构——从《论犹太人问题》的文本解读来看[J].哲学动态,2009(3).
[2]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4] 刘富胜.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理论解放[J].社会科学辑刊,2008(5).
[5] 赵家祥.《黑格尔学哲学批判导言》的历史地位[J].北京大学学报,2012(4).
[6] 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 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 (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诗集[M].王立,等,译.北京出版社,2004.